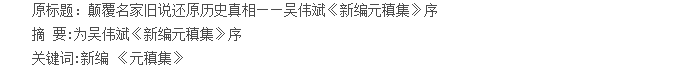
吴伟斌同志一生最重大的研究课题是元稹研究。在研究生毕业之前及以后,他是我家的常客,谈论得最多的自然是元稹研究。三十五年来,吴伟斌同志心无旁骛,专心致力于元稹研究,先后出版了《元稹评传》、《元稹考论》等专著,学术界反映甚好。我曾经说过:“《元稹考论》与《元稹评传》两书互相补充,互为印证:《元稹评传》全面展示了元稹生平的各个方面,是《元稹考论》论述元稹的坚实基础。而《元稹考论》解决了元稹的诸多重要问题,是《元稹评传》阐述元稹一生事迹的有力支撑。”
而即将出版的《新编元稹集》成果更是丰硕,这是迄今最全、最新、最可信、最权威的元稹诗文整理本。吴伟斌同志从每一篇元稹诗文着手,不放过诗文中的一词一句,针对千百年来诸多名家、大家否定元稹的不实之辞,提供更多、更实、更具体的证据,继续颠覆诸多名家的旧说,为饱受冤屈的元稹全面翻案。它既是《元稹考论》、《元稹评传》的出发点,也是《元稹考论》、《元稹评传》的继续与拓展,成为元稹研究更为坚实、更为广博、更为可信的基础。
根据《旧唐书·文苑传》、《新唐书·文艺传》以及《旧唐书·元稹白居易传》的描述,元稹是唐代文苑里的著名诗人与文章家,他与张说、苏颋、权德舆、李德裕等大家并名文苑,又与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李贺、杜牧、李商隐等名家齐名诗坛,史家有“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的结论。而近一百年来出版的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却对元稹评价甚低,批评远多于赞誉,这既不符唐代历史的实际,对元稹来说也极不公平。
而吴伟斌同志正是在研究生学习刚刚开始的时候,就紧紧抓住了这个非常重要的元稹评价问题,将它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内容。作为他的辅导老师之一,我曾亲眼目睹了他开始起步时的艰难:当时国内只要涉及元稹的,毫无例外都是批评元稹之为人,贬低元稹之诗文,其中也包括少数名家、大家;而吴伟斌同志对元稹的研究一开始即表明准备为元稹作实事求是的评价,稍有常识的人们都会明白,初出茅庐的学子这样做将面临怎样一种困难的境地,他能够如愿成功吗? 我在暗暗鼓励他帮助他的同时,也不禁为他捏着一把汗。三十五年的岁月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吴伟斌同志却以他近千万字的元稹研究成果告慰为他付出汗水的老师们、朋友们。综观吴伟斌同志的元稹研究,我有如下体会:学术研究贵在独立思考,不拾前人牙慧,不炒他人冷饭。现在学术界有一种不易为人理解的怪现象,就是没有经过自己艰苦卓绝的钻研与深入细致的研究,就将前贤今哲的某些研究成果随手拿来,拼拼揍揍就成了自己的“著作”。更有甚者,有些人采用了他人的研究成果之后,却不在自己的著作里面作任何说明,这就更不应该了。吴伟斌同志的元稹研究不是这样,他从元稹原有的每篇诗文着手,从每篇的字、词、句开始,从实际出发,根据查询所得的依据,经过独立思考,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其与他人结论不同之创新成果,也就水到而渠成。吴伟斌同志对元稹诗文的编年,首先要把每一篇诗文放在元稹三十九年诗文创作实际中加以考察,确定其应该所在的位置;其次是把它与同时代诗人如杨巨源、李德裕、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张籍等人的同一年份作品进行比较,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再次是将有关元稹诗文编年的同类学术著作,如《元稹年谱》、《元稹集编年笺注》、《元稹年谱新编》加以比对,发现异同,采录其合理的编年,摒弃其错误的意见,从而得出自成体系的二千五百六十六篇元稹诗文创作的“路线图”。如果以《新编元稹集》的编年为参照,《元稹年谱》、《元稹集编年笺注》、《元稹年谱新编》的编年相同率仅仅只有百分之五上下,书后附录的《< 新编元稹集 > 与 < 年谱 > 、< 编年笺注 > 、< 年谱新编 > 编年对比表》就清清楚楚将四书的异同呈现在读者面前,读者一目了然,自可作出判断。
学术研究贵在不唯多数是从,贵在不唯名家马首是瞻。吴伟斌同志的元稹研究是以详实的证据、周密的论证,全面考论元稹事迹,对不符元稹生平的诸多名家的权威结论进行大胆的商榷,因而订正了《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中的不少错误记载,提出了与传统说法大不相同的许多新观点,从而勾勒出元稹的历史本来面目,破解了中唐历史上的不少谜团,并解决了学术界关于元稹评价上一直无法自圆其说的诸多问题。这样的正误在《新编元稹集》中随处可见,近期已经发表的《后人对元稹诗文的误读误解》、《论刘本 < 元氏长庆集 > 之贡献与缺憾》、《关于元稹 < 郭钊等转勋制 > 的标点与编年》、《< 元稹集编年笺注 > 错误举隅》就是其中的一些例证。尤其如更正鲁迅先生对《莺莺传》“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的错误论断,改正陈寅恪先生关于《莺莺传》作于贞元二十年的错误编年,纠正岑仲勉先生对元稹家族世系的不当叙述以及对元稹诗中“李六”与“李十一”的错误判断,以及《新编元稹集》对诸多名家关于元稹“勾结宦官”、“以张生自寓”等等说法的订正,尤为用力而珍贵。
学术研究贵在证据,贵在严谨,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所谓的“结论”就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不仅经不起时间的检验,而且常常要闹出令人捧腹的笑话。吴伟斌同志的元稹研究,大到《莺莺传》作年的认定、长庆元年科试案真相的揭示、元稹与薛涛男女私情以及唱和关系的否定,小到一词一句的考实,无不举出令人信服的证据,然后作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如元稹《和乐天赠吴丹》有“传闻共甲子”之句,《元稹集编年笺注》以为“共甲子即同龄人”,将年龄前后相差三十五岁的元稹、白居易、吴丹三人视为“同龄人”;而吴伟斌同志根据有关文献如白居易《故饶州刺史吴府君神道碑铭并序》、《新岁赠梦得》、刘禹锡《乐天示过敦诗旧宅有感一篇吟之泫然追想昔事因成继和以寄苦怀》、《元日乐天见过因举酒为贺》作为证据,结合《旧唐书》之《白居易传》、《刘禹锡传》、《崔群传》的记载,对此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共甲子:即共有同一个甲子周期。”亦即“他们三人都出生在同一甲子周期之中”;“共甲子”不等于“同甲子”,“同甲子”才是“同龄人”,“白居易、刘禹锡、崔群均出生于在大历七年(772),因此刘禹锡、白居易、崔群他们才可以在诗篇中说‘同甲子’”。类如的例子还有很多,如举出元稹《赠田弘正等母制》“幽魏并扬”之“并”、《送崔侍御之岭南二十韵》之“崔侍御”以及《见人咏韩舍人新律诗因有戏赠》之“延之”等,都是纠前人或时人的误读,就是其中的一些例子。
学术研究贵在思路严密,吴伟斌同志的诗文编年就是这样:《新编元稹集》采录诗文二千五百六十六篇,从元稹最先面世的第一组文章《答时务策三道》,到元稹谢世前最后一篇存留的《遭风二十韵》,不问是文章,还是诗歌,也不问是“刘本”《元氏长庆集》内之诗文还是散佚散失在诸多文献中的诗文,一律都是按元稹写作时间之先后排序,不仅落实到某年,甚至还精确到季、月、日,虽然不能保证所有排序的诗文全都合理,但由此形成的则是元稹一生诗文创作清清楚楚的“路线图”,既方便研究者查阅,也方便读者使用。而随手翻阅近年出版的几部元稹研究的同类著作,编年就比较随意。如元和四年,元稹《除夜》诗之后,《元稹年谱新编》编年诗歌《竹箪》等诗九首,《元稹集编年笺注》编年《灯影》、《行宫》等诗十四篇,《元稹年谱》编年《刘颇诗》等四首,而这显然是有悖常理的编年。
学术研究贵在追求真相。吴伟斌同志在元稹诗文辑佚的过程中,也曾遇到前贤时哲将一些本来不属于元稹的诗文归属于元稹名下,如《论裴延龄表》、《又论裴延龄表》、《咏莺》、《桃源行》、《送裴侍御》、《漫酬贾沔州》、《西郊游瞩》、《咏徐正字画青蝇》、《长安道》、《咏瑠璃》、《椶榈蝇拂歌》、《始闻夏蝉》、《精舍纳凉》、《咏露珠》、《南园》、《看花招李兵曹不至》、《红藤杖》等等诗文 66 篇,均有古代文献记载,有些研究元稹的著作即将它们都归属在元稹名下。但吴伟斌同志根据有关文献加以严肃的甄别,将它们剔除在元稹诗文之外,并附录在全书最后,列出根据,考出这些诗文的真正作者,辨明真伪,告知读者。
学术研究贵在还原历史的真相,探求事物的本来面貌,吴伟斌同志的元稹研究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北宋末年刘麟父子整理编集的《元氏长庆集》原有 978. 5 篇,前人估计“十存其六”,散佚之篇不在少数,散失之篇更多。前人辑佚 304. 5 篇,吴伟斌同志独家辑佚 1283 篇,共辑佚元稹诗文 1587. 5 篇。
这样,《新编元稹集》共收录元稹诗文2566 篇,是今存刘麟父子编集的《元氏长庆集》诗文的2.6 倍,这在我国古代文学的整理中并不多见。虽然还不能说元稹的全部诗文已经毫无遗漏地毕集于《新编元稹集》之中,但与前人相比,与时贤相较,吴伟斌同志可以说是做得最努力的一个。由于他的辛勤劳动与深入研究,元稹诗文创作的篇目得以基本呈现,元稹诗文创作的原貌得以基本还原。根据辑佚元稹诗文1587.5 篇的事实,与刘麟父子编集的《元氏长庆集》原有978.5 篇相比较,前人估计的“十存其六”,应该是“十存其四”。而且更为难得的是,他还对元稹全部诗文逐一编年,落实到年、季、月、日,极少例外,还原一千多年之前元稹逐年逐月走过的创作道路,为读者认识元稹、了解元稹提供了可贵而又可信的资料。
学术研究贵在坚持。从《元稹评传》、《元稹考论》、《新编元稹集》可以看出,吴伟斌同志研究元稹既有相当的广度,更有相当的深度。而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三十五年来始终如一的坚持。开始研究元稹的时候,吴伟斌同志的研究困难重重,但他不轻言放弃,默默地坚持,甘坐“冷板凳”,一直坚持到《元稹评传》、《元稹考论》出版的 2008 年,人们才开始认识他研究元稹的价值所在。取得一定成绩后,他仍然不言放弃,继续孜孜不倦地埋身在古代文献之中。天道酬勤,篇幅巨大的《新编元稹集》果然接着面世,为元稹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
总而言之,吴伟斌同志的新著《新编元稹集》从最基础的字词句做起,注释并非照搬工具书,而是结合元稹的生平实际,精详独到,发他人之未发,令人信服。笺证时见警语,融进其三十五年的研究心得,更见功力。而其编年,纠他人诸多之误编,更是难得。诗文混合编年,打破传统习俗,有利后人研读,实属不易。甄别采录,别具新貌,值得关注,应该重视。
元稹研究的道路仍然任重而道远,希望吴伟斌同志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研究,希望他有更多更好的元稹研究著作问世,使元稹研究开辟新天地,再上一层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