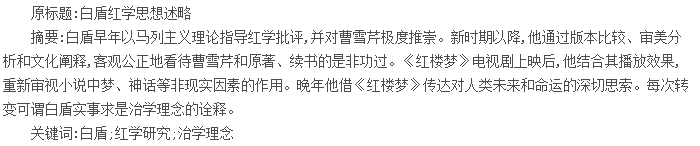
引言
白盾的人生和学术经历无疑具有传奇色彩。
20世纪50年代初期,因与当时红学权威俞平伯观点不同,白盾撰述《〈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吗?———评俞平伯的〈红楼梦底风格〉》一文投稿《文艺报》,却遭退稿。
1954年,评红批俞运动兴起,他再将此文转投《人民日报》,得到该报高度赞许并全文刊载(按:段启明、汪龙麟主编的《清代文学研究》曾说:“率先对《红楼梦研究》发难的其实是白盾,其《〈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吗?———评俞平伯的〈红楼梦底风格〉》一文写成于1952年11月,距《红楼梦研究》出版刚刚两个月。但该文投寄《文艺报》被拒,直到学界批判胡适、俞平伯的运动已全面展开时,白氏又将该文投寄《人民日报》始得发表。”
此刻,白盾被奉为了“红学家”,稿约、访谈纷至沓来,工作也由巢县中学调至安徽省文联。尽管谈不上所谓“一夜成名天下知”,即无法与此后同样以批判俞平伯而声名鹊起的“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的影响相比,但毕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3年后,他以“右派”罪名入狱,出狱后遣返农村,达20年之久。新时期伊始,已是花甲之年的白盾克服自身疾病、地域偏僻、资料匮乏等客观因素,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光明日报》、《学术月刊》、《文史哲》、《红楼梦学刊》等重要报刊发表红学论文二百余篇,就《红楼梦》文本魅力、版本得失、曹雪芹思想及创作心态等热点、难点问题提出一系列新见解,不少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等刊物全文转载,或作摘要介绍,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和讨论。出版了《红楼梦新评》、《红楼梦研究史论》、《悟红论稿》等专著3部(按:另有《悟红二论》、《曹雪芹论稿》2部待出版)。大起大落的人生境遇对白盾红学思想的形成、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冯其庸和李希凡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有“吴文慧”词条:“笔名白盾,安徽泾县人,1922年生。
现任教于徽州师范专科学校。五十年代在《人民日报》发表《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吗?》并在《人民日报》、《延河》发表《贾宝玉典型意义》、《史湘云论》等论文。八十年代在全国各报刊上发表过《研究红楼梦也应实事求是》、《论红楼梦的悲剧美》等红学论文三十多篇,已选编出版论文集《红楼梦新评》。”
可见,这部1990年出版的大辞典已将白盾列入“红学家”名录。
一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绝大多数人而言,长期战乱导致的巨大灾难,渴求国强民富的强烈愿望使得人们对新政权充满期许,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灵魂的洗礼,在学习和改造中告别过去,获得新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白盾开始了他早年的《红楼梦》研究。今天看来,那篇使他名闻遐迩的文章并无多少学术价值,它既未综合吸收、借鉴以往红学研究的成果,也未对小说作者、文本系统展开分析,却猛烈炮轰俞平伯的士大夫情趣,文末表示同所谓封建审美情趣彻底决裂的宣言更是火药味十足,完全违背了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当然,这样的批判文章仅仅是白盾的初步尝试,此后,《贾宝玉的典型意义》、《从“太虚幻境”看曹雪芹的创作思想》、《史湘云论》、《“二美合一”辩》等文章,试图系统地运用马列主义理论,详尽地论述小说的人物和情节。
首先,社会历史批评中融入阶级意识。社会历史批评古已有之,从柏拉图到狄德罗,从丹纳到别、车、杜(即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他们均强调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注重从环境、时代等外部因素研究文学,但将两者结合,则是马列主义理论的要旨。所以,在白盾的人物分析中,共性取代个性,言行举止皆是其阶级特性使然。
史湘云的天真烂漫、敢说敢笑深受以“童心说”为代表的明末进步思潮影响,是对封建淑女性格的叛逆,而与宝钗交好则体现“封建贵族女子的内心空虚”和“精神苦闷”。贾宝玉“天下无能”、“古今不肖”,敢于反抗政治和封建礼教的双重压迫,是“封建贵族的没有回头的浪子”,他的出家是对“宗法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彻底否定”。
其次,批评曹雪芹的宿命论思想。宿命观念源于人类面对自然与自身时的迷茫和无助,古希腊的命运悲剧、哈姆雷特“活还是不活”的两难、理性与自由的抗衡、科学和道德的冲突……时至今日,这些困扰人类的难题也未能得到很好解决。但在当时主流思潮和传统乐天精神的双重影响下,白盾将宿命观等同于思想软弱。在他看来,既然曹雪芹以反封建为己任,小说中“留意孔孟”、“委身经济”等说教就不是他的局限,他忌惮当时的文化专制,不得不借此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脂砚斋所说的“骂死宝玉,却是自悔”乃其自身庸俗,不能代表曹雪芹。曹氏的不足在于认识不到他所处的社会可以改变,不懂得无产阶级必定登上历史舞台,却用“通灵宝玉”、“神瑛侍者”、“绛珠仙草”等神话宣扬因果报应。
再次,高举现实主义理论大旗,否定自然主义创作手法。现实主义虽非马列主义理论专利,但它揭露和谴责意识强烈,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批判旧制度,歌颂新社会的时代要求,故被文艺界奉为圭臬。
白盾高度赞扬《红楼梦》的杰出成就,立足点正在于其敢于正视现实、揭露黑暗。甚至连被他否定的“神瑛侍者”、“绛珠仙草”等神话,因彰显了曹氏“探索现实底蕴,寻求生活奥秘”的思想力量,也有了积极意义。“太虚幻境”更是曹氏努力解释生活,评价社会的明证。相比较,自然主义文学虽然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对人的本能、欲望、生理、遗传等自然因素进行全方位的审美观照”,深化、拓展人类自我认知,为现代主义文学产生奠定基础,但它过分强调客观,忽视人的社会属性,这既是其弊端,也不合主流节拍。所以,凡论及曹氏伟大处,白盾均表明其与自然主义的不同,并将后者斥为“庸俗”。
总之,本阶段白盾的《红楼梦》研究从属于批俞运动,沾染了浓烈的时代色彩。其实,白盾能够一夜成名,被奉为上宾,并与《红楼梦》结下一世情缘,也是时代使然。据白盾自述,《〈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吗?》遭《文艺报》退稿并不在于后者反对其观点,相反《文艺报》认为“批评的道理是对的”。只不过当时建政未久的实际情境要求争取一切积极因素,所以该报回复白盾“俞氏这样的老专家应团结”。其实,白盾只是批评俞平伯传统文人情趣,并未对俞平伯的红学思想做任何政治定性。当然,在时代大环境的影响下,白盾也不可避免地依附、接受某些既定观念。他将贾宝玉判定为“封建贵族的没有回头的浪子”,契合当时流行的“新人说”;分析曹氏“太虚幻境”的构思、探讨贾宝玉的性格也都和大观园女子的悲惨遭遇紧密相联,意在证明《红楼梦》并非“怨而不怒”,而是要抨击封建专制。然而白盾并非毫无主见,亦步亦趋。譬如,同为批俞,李希凡、蓝翎另外两个“小人物”的发难文章更具理论水准,但有意味的是,他们的后续之作情绪高涨,学理成分减弱。相反,白盾则深知自己仅是《红楼梦》的爱好者,不但未见到脂本《石头记》及各种有关材料,即便胡适、俞平伯论“红”文章也看得不多,根本谈不上自己的看法。这种自知之明使白盾更加努力阅读中外名著,学习相关理论,试图从作者创作动机、文本客观意义等不同视角研究《红楼梦》。他采用由此及彼的研究方法,先研究曹雪芹所处时代的中国社会,研读清史、清代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由此涉及到程朱理学、庄老思想乃至佛学思想。
在此基础上,试图探讨《红楼梦》与《金瓶梅》、《三言二拍》、《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等著名的明清小说之间的关系,比较其异同、优劣与得失,以衡量《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为了把作品放到世界文学的广阔领域去考察,白盾既尝试了解文学理论家评论和分析文学作品的观点方法,又考察了马、恩、列、斯等有关文学的评论,力求做到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视角评论《红楼梦》。除去时代因素,即便在文学研究方法早已多元化的今天,这种由点及面的治学理念自有其诸多合理性。
更为重要的是,白盾的这一研究方案是在躁动、狂热的大背景下确定的,彰显了清醒、冷静和不盲从的精神个性。经过系统地钻研,白盾对《红楼梦》逐渐产生和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人千篇一律地抨击俞平伯所谓“资产阶级唯心论”,白盾却着眼其“缠绵悱恻”、“温柔敦厚”的传统审美理念。针对“自传说”的批判,白盾结合中外作品,摆事实,讲道理,指出曹雪芹和贾宝玉在生活环境、性格特征等方面的相似。而就“二美合一说”,白盾虽予以否定,但他认为该现象在小说中大量存在,是曹雪芹自己的观点,俞平伯是代人受过。以上观点虽分散、零碎,未成体系,但这种坚持真理、敢于怀疑的治学精神却为白盾日后从事红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这一切也都拜政治所赐,如若没有批俞运动,《〈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吗?》一文不可能受到关注,白盾也不会骑虎难下,被误认为是“红学家”而“不得不研究《红楼梦》”,他一生的红学成果和影响也就无从谈起。
二
面对红学的热闹景象,白盾是清醒的,他认为,《红楼梦》虽热,观点还是旧的。比如,此前有关《红楼梦》主旨、版本优劣、人物评价等议题皆有定论,不容置疑,红学研究也被认为取得重大进展。现在,笼罩学界的政治烟雾逐渐散去,学术活动步入正轨,这些问题不仅悬而未决,反因政治的过度介入平添了诸多混乱。《红楼梦》究竟写了什么?曹雪芹的真实面目又是怎样?历来红坛纠纷的根源何在?如何就分歧作出令人信服的阐释?很显然,白盾对红学的现状并不满意,他在《红楼争鸣二百年》中说:“遭遇‘十年动乱’,《红楼梦》领域主要是‘乱’了思想……幸运留下主持‘红坛’的红学家,也面临着双重的挑战:一是着意于‘卫冕’,维护既成事实的主流地位;一是致力于‘发展’,应付新局面、适应新形势。但因思想过时,考证生疏,便借助于‘索隐有理’之说,坚持其‘掩盖’、‘政治’之论……在《红楼梦》研究领域中,自从索隐猜谜派热衷于寻找有关‘雍正夺嫡’的‘微言大义’以来,又经‘评红闹剧’中出现‘爱情掩盖’说重拾旧题,以为《红楼梦》的爱情描写‘掩盖’着‘雍正夺嫡’的‘政治秘密’,牵涉到所谓的‘儒、法斗争’,于是旧说又逢新机,沸沸扬扬,甚嚣尘上。本来,即使曹家果真因为卷入所谓‘雍正夺嫡’而深受其害,我们对曹雪芹的《红楼梦》也只能从它的形象体系所显示的意义与价值作出评判,而不是以是否与那场政治事件有关为臧否,这应该是很明白的事情。但是由于以政治为核心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人们神经上的‘政治’这根弦总是绷得太紧,学者们总是念念不忘地热衷于探寻伟大作品所隐藏的‘政治秘密’。”
对于白盾的这番评论,高淮生在《红学学案》中这样认为:白盾是“翻了跟头”的过来人,他的这一番分析自然透着更深刻的体验。他对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之初的红学家的评估是八个字———“思想过时,考证生疏”,于是便“重拾旧题”。其实,就其“旧说又逢新机”的自觉实践而言,也并不是“‘乱’了思想”,倒是“‘政治’这根弦总是绷得太紧”差可拟似。这一番评论是很中肯的,白盾因在政治上“翻了跟头”,所以能够在红学研究上保持清醒的认识。
在白盾看来,当时的《红楼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庸人自扰,因为研究者不关注作品本身,却对资料难考的曹雪芹大做文章,忽而否认他《红楼梦》的著作权,忽而就其生卒年、出生地争论不休。这并非说作者问题无关紧要,而是说与其舍近求远,还不如脚踏实地,通过对文本的详细梳理,呈现作者的思想性格、精神风貌。此时,戴不凡发表了长篇论文,宣称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作者。
1981年6月,白盾的代表作《〈红楼梦〉研究也要实事求是》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文章呼吁求实精神,不仅猛烈抨击捕风捉影的错误方法,强调“在没有更新的资料和更有说服力的论断提出以前,《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的论断,还是推不倒的”,更建设性地提出区别对待不同版本的主张。他仔细对比“今本”和“脂本”,认为在宝黛爱情结局、钗黛矛盾冲突、宝玉出家和贾府败落等情节的处理上,两者差异显著,它们使各自版本中的宝玉、宝钗、袭人、贾母、王夫人等人物体现出不同的性格特征。
表面上看,白盾在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基本工作———文献学研究,但他不是机械地为考证而考证,而是要“就脂论脂,就今论今”,即在版本比较的基础上,考察它们的得失:脂本好在何处,今本妙在何方?它们又有什么不足?进而客观、公正地评价曹雪芹和续作者。很显然,这是对他先前全面肯定曹雪芹的反动,白盾不再将脂砚斋和曹雪芹割裂看待,认为两者关系密切。“留意孔孟”、“委身经济”、“骂死宝玉,却是自悔”等观念都是他们的真实想法,他们都无法超越其所处的时代。白盾结合秦钟遗言、三姐托梦等情节,指出曹雪芹受家庭环境影响,较高鹗保守,难以写出续书的结局。
白盾的结论撕开了长期覆盖在曹雪芹身上的光环,也引起了新的争议。白盾以“脂本”、“脂评”为依托,全方位,多角度地阐述己见,回应置疑。不少学者坚信原著与续书系一人所为,艺术构思也会随着创作而改变。白盾则借《“大悲剧”与“小骗局”必须分清》、《论〈红楼梦〉八十回后的续书》二文申明,前八十回荣府二房衰败根源是赵姨娘、邢夫人的夺权和夺嫡,续书忽略该线索,将彻底毁灭的大悲剧变为“家道复初”的小悲剧。前者否定社会、人生,后者依旧迷恋现世。续书写“争婚”,与原著“还泪”宣言相左。以上差异是对立的,是不同的世界观使然,“一时难以发生根本变化”。《“严父”、“慈母”及其他———从贾政、王夫人的形象塑造看曹雪芹的创作危机》一文分析贾政和王夫人客观意义上的凶残,曹雪芹有意为其褒奖,正反映出他“世家子”的局限。
《试论高鹗续作之功》一文则专谈续书贡献,指出它尽管有不少缺陷,但“焚诗绝粒”、“黛死钗嫁”等情节是全书高潮,具有“惊心动魄、迷人心魂的力量”。
《〈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成就和不足》一文则认为“二美合一”、宝玉与贾政和好等构思是“子孙不孝、后继无人”消极观念的流露,但曹雪芹尊重女子,创造出大量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应该说,白盾建立在版本辨析之上的诸多观点,具有相对的合理性,其中对困扰红坛的混乱与纠纷也有独立思考和阐述。他将原著与续书分而论之,各自的成败得失也就泾渭分明,一目了然。文章结尾提出打破“凡是曹雪芹原意就好,凡是脂本定胜于今本”的束缚,呼应了先前“曹氏较高鹗保守”的论断。
或许有人认为白盾的这些观点极为平常,既然原著与续书出自不同作者,它们的思想倾向、情节内容、艺术水准自然不尽相同。然而,程本广为流传,脂本发现较晚,加之对曹雪芹的崇拜,人们在很长时间内对小说版本和作者并未有清醒认知。白盾的这些观点的确发别人所未发,它对长期被人们忽视的诸多问题予以正视并做出解答,对困扰红坛的种种乱象追根溯源,颇多思考的亮点。
作为文学的重要属性,美学观照长期受红坛轻视,索隐红论也好,阶级斗争说也罢,它们都与美学绝缘。因此,立足审美,探讨小说的魅力所在,这本身就是对主观臆想、随意附会等学风的反拨。白盾的《红楼梦》美学观照并不受制于叔本华的悲观理论,也没有意识形态的干涉,即摆脱一切既有观念的纠缠,完全以读者的感受为惟一旨归。这些感受不是少数观众偶然的心血来潮,而是历来绝大多数读者的共同心声。白盾着力于发掘小说中蕴含的人文气息和人文精神,他认为,宝玉关怀、体贴所有青年女子,体现了具有“近代色彩的人性觉醒”,这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泛爱”思想使无数读者为之倾倒,“红迷”现象由此而生。宝玉将少女喻为水和珍珠,传达出对美的耽爱,但她们的悲惨命运则使读者为之同情不已。因此,《红楼梦》的主题是“耽美、泛爱、悼红———悼念在封建制度压迫、摧残下所有美丽、有才能的女子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美和美的毁灭。”
这一结论无疑更符合作品的真实面貌。而在对小说悲剧美的分析中,白盾的人文精神表现得更为显著。白盾认为“在和灾难、不幸搏斗的过程中”,人的智慧、节操和艺术才会诞生,思想美、性格美和心灵美才能彰显。只有“以宝、黛为代表的一代有叛逆气质的年轻人才是最有价值的”,“他们的灾难和不幸———他们的毁灭才是美的和最有价值的毁灭”,才能“引起读者的同情和眼泪,显出悲剧的意义”。基于此,白盾以审美取代道德,努力探讨大观园女子的生命火焰与人性光辉。
如前文所述,在白盾的红学研究中,作品分析和作家研究融为一体,他不孤立地探讨曹雪芹的祖籍、身世,经营所谓的“曹学”,而是通过解读作品来把握曹氏的思想。同时,他又将研究作家所得到的认识应用于作品分析,以期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小说的美学特征。在他看来,既然《红楼梦》以耽美、泛爱、悼红为主题,那么曹雪芹必然是该理念的坚定奉行者,故一旦述诸笔端,他内心的绵绵情意喷涌而出,小说也就诗情洋溢、画意葱茏。平心而论,以往论者也注意到小说的诗情画意,但他们仅将其归咎于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等具体手法,白盾却进入曹雪芹的内心,探寻他手法背后的深层动机。正由于不囿于传统思想,曹氏才敢于摆脱好人全好,坏人全坏的偏见,塑造“真的人物”;才敢于打破大团圆的骗局,创造了“悲剧中之悲剧”;才敢于抛弃三角纠纷的俗套,酝酿出“二美合一”(不是二美争斗)的构想。值得注意的是,在版本比较中,白盾认识到描写宝黛爱情并非曹雪芹的主要目的。他通过审美分析,从思想层面论述曹氏“美的毁灭”、“二美合一”等构思的成因,从而给予先前论断强有力的证明。
此外,白盾还将曹雪芹和《红楼梦》置于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审视,从中挖掘小说创作构思、人物性格的深层意蕴,探讨其背后隐含的文化心理。从某种程度上看,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众所周知,文化影响和支配着作家对现实的感悟和认知,而文本就是实现该功能的媒介。因此,探寻小说的文化意蕴既是人们自我发现、自我认知的寻根之旅,也是更高层次的文学批评。不过,自身学养、阅历有别,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也不尽相同。白盾并不否认血缘基础、实用理性、乐感精神、天人合一等理念在客观意义上的积极作用,但他进一步指出“所谓血缘基础者,即伦理政治化与政治伦理化之谓也”;所谓实用理性者,乃“中国的王权摒弃了宗教文化的彼岸世界,立足于实用目的的体现”;所谓天人合一者,乃“皇帝是天子———天的儿子”,“皇帝和人民的关系乃天和人的关系,久而久之,就协调、合一起来了”。也就是说,在主观上,它们都是中华民族特殊帝制的衍生物,故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帝制文化。帝制(王权)压倒教权,俘获宗教(儒、释、道三教和平共处,共同服务于王权),成为评判世间万物的惟一标准。用它来解读诞生于该文化系统中的《红楼梦》,不少问题便有了更加清晰、透彻的阐释。
20世纪70年代末,白盾就已跳出“拥薛派”和“拥林派”的纠缠,指出薛宝钗具有儒、释、道三教的多重性格。她严守“主子姑娘”身份,是儒家思想使然;她对大观园内种种机密视而不见,“可介入又不介入”,深得黄老思想精髓;而其居所“奇草仙藤”,服用“冷香丸”,则体现“以‘冷’为特色的佛家情趣”。“拥薛派”和“拥林派”各取所需,前者赞赏她典雅大方的风度,后者厌恶其城府深严的冷漠性格。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再次立足传统资源,先后对小说里诸多存在争议、令人困惑的现象追根溯源。最为精彩的当属白盾对曹雪芹“拟帝王”思想的分析,譬如林黛玉严守“主子姑娘”身份,却默认“潇湘妃子”称号的矛盾,贾宝玉是大观园众女子的核心,拥有“绛洞花王”、“混世魔王”、“宝天王”、“宝皇帝”等绰号,刘姥姥也称大观园为“天皇宝殿”等,以上均暗示曹雪芹欲将贾宝玉塑造为王。只不过该“王”不是“后宫三千、伏地求欢宠”和“一怒而伏尸百万”的“王”,而是以关心、体贴一切女子,欲补“情天之缺”的“花王”。
“潇湘妃子”的称号同样是为了突出贾宝玉的王者地位,尽管它不符林黛玉的性格。如果缺少对中华帝制至高无上、压制一切现象的深刻洞察,缺少对民众称帝做王隐秘心理的了然于胸,就不可能知晓曹雪芹心灵深处的集体无意识,也无法对他这种奇特构思作出令人信服的解答。
可以说,白盾通过版本比较、审美分析、文化阐释,建构起较为系统的《红楼梦》研究体系。在该体系中,上述三大要素各司其职,逐步深入。版本比较是基础,具有正本清源,廓清红坛纠纷、混乱的重要意义;审美分析是关键,只有把握文学的审美属性这一要义,才能探寻《红楼梦》的魅力和价值;文化阐释是升华,能透过现象,深入本质,提升思想性与敏锐度。它们并非互不关联,各自为政,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前面提到,在对《红楼梦》的审美分析中,白盾既从封建专制与读者期待视野的落差中分析小说美感成因,又在掌握《红楼梦》美学风格的基础上区分版本间的差异。“曹雪芹较高鹗保守”的推断来源于人类普世价值与自身传统观念的比较;“拟帝王”思想则以曹雪芹耽美、泛爱、悼红情结为立论根基,而这正是基于审美分析得出的。薛宝钗、花袭人遭受排斥固然反映古今价值观的变迁,但续书写她们参与“瞒机关”密谋,也误导了读者的情感取向。由此三重解读,白盾对曹雪芹的真实面貌有了重新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研究方法、理论视角与先前迥然有别,但白盾依旧对现实主义理论情有独钟。
他延续社会历史批评,从家庭、时代等外部因素阐述曹雪芹与高鹗的性格差异,从传统中寻觅文本背后的文化内涵,这些工作均着眼现实。这固然与文艺界长期独尊现实主义,排斥其他思潮有关,他的自身境遇也为其选择现实主义推波助澜。曹雪芹“生于繁华,终于沦落”,相似的经历跨越时空的隧道,拉近了他们的距离。白盾将《红楼梦》的主题归纳为“耽美、泛爱、悼红”,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借大观园女子的不幸咀嚼自己的多舛命运,哀悼早已随风而逝的青春年华。只不过他不仅仅满足于此,他还要对自身境遇深入反思,从中探索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真谛。所以,他高举人文主义大旗,充分肯定林黛玉、史湘云、妙玉等少女的智慧与才情,并对塑造一系列“真的人物”的曹雪芹高度赞许。
三
1987年,《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登上荧屏,引起众多专家、学者的广泛争论,也吸引了白盾的目光。
总体而言,白盾对电视剧持否定态度,但他不是简单地用既有研究成果批判电视剧增删取舍的失当,而是结合它播放的实际效果,对先前自己的红学主张进行总结与反思,并用最新结论评论电视剧和小说文本,这在他对小说中梦、神话等非现实成分的态度转变上体现得尤为显著。如前所述,新时期白盾的红学研究依旧注重现实主义理论,针对作品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厌世、解脱、生活如梦等情绪,他仍视为消极,予以谴责。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别是在掌握“石头/宝玉”构想的深层意蕴后,白盾认识到,表面上看,“悟破”虽然颓废,但实乃执着的另一种表现,是曹氏“对自己所经历人生的一种反思”,他要“以具体的人生世相为媒介,寄托自己对生命价值与人生理想的沉思”。在这里,白盾仍旧将作家和作品视为整体进行全面考察。他认为,曹雪芹要对社会、人生做更高层次的哲理性概括,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便难以胜任。白盾以庄周梦蝶、汤显祖“临川四梦”、叔本华对梦的解读为参照,指出梦是曹氏“生活巨变的写照”,是“千红、万艳香消玉殒的象征”,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的人生感悟”。太虚幻境是小说里“最大的梦中之梦”,“在艺术构思上是《红楼梦》的枢纽、心脏和高层建筑”。电视剧改编者删除太虚幻境,只能导致“艺术构思的背离与艺术风格的破坏”。他将批评文章冠名为“‘梦’魂失落何处寻”,更是直接宣告对“梦”等非现实因素的高度重视和对改编者忽视其价值的强烈不满。
抬高神秘荒诞成分的地位并不意味贬低现实主义,从“执迷现世,以人生世相寄托生命沉思”等表述中,我们仍能窥探出白盾对现实主义理论的看重。在随后写就的《人生感悟与艺术境界———曹雪芹的创作心态》、《红楼交响多重奏》、《〈红楼梦〉的荒诞、随机性》等文中,他再次重申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品格,并将其归纳为“如实叙写”、“高度典型化”、“文风新颖独创”、“情感真挚”等四大特征。只是在洞察曹雪芹托兴寄寓的创作意图后,白盾意识到仅立足现实已难以把握《红楼梦》的全貌,他还要进一步探讨曹氏“对现实人生所作的哲理性概括”的表现方法。所以,他虽从人们的普遍感受中发现梦、神话的美学价值,但也看到小说作者自身的独特,多次强调《红楼梦》中的象征与西方象征主义的区别。他指出《红楼梦》有两种读法,顺着现实主义的路,读出“女性美”和古代社会“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沿着象征主义的路,则看到“还泪神话”对儿女真情“最美、最有诗意的象征”和《好了歌》“变的哲学及其引起的人海浮沉的沧桑之感”。但他同时申明该象征必须附丽于现实生活,否则就“变成了抽象的、虚空的说教”,小说仅在“现实主义的基调中弹出了象征主义的变音”。
正由于对曹雪芹的思想性格、创作动机洞察之深透,白盾认为“画黛之石”、“绿蜡之典”、龄官画蔷等情节并无高深玄理,它们都是曹雪芹“信笔而去”,大胆虚构的成果,是荒诞不经、“随意所至”的“梦”的特性的外化。可以说,白盾的这类看法和分析是对猜谜、索隐等不正之风的有力回应。
在批判编者篡改小说主题中,该回应也得以贯彻。在白盾看来,改编者正是受“小说是社会悲剧”、“写爱情渺小,写社会伟大”等观念影响,才特写“葫芦案”,补上“天香楼”,让史湘云沦落风尘,王熙凤死后拖尸,才淡化青年女子红颜薄命和宝黛爱情悲剧现象。为此,他再次立足审美,不断从新的角度深入阐述《红楼梦》的主题。《“梦”魂失落何处寻》一文辩证看待爱情悲剧和社会悲剧,认为呼唤爱情自由是当时社会悲剧中的核心问题,而将两者割裂,“是出于浅层次的庸俗社会学的理解”。《论〈红楼梦〉的审美序列与主题的界定》一文则将改编者看重的社会悲剧———贾府衰亡与宝黛爱情悲剧、大观园女儿悲剧按审美强度排列,通过对比,白盾指出后两者写出了“人性之深与人情之美”,前者仅是“恶有恶报的分所应得”,这就无法引起后人关注,进而从反面点明电视剧指导思想的失当。《红楼梦创作过程初探》一文则另辟蹊径,认为小说的不同异名是曹雪芹数易其稿的“痕迹”,反映其思想情感的变化。在《风月宝鉴》、《石头记》、《情僧录》、《金陵十二钗》和《红楼梦》五稿中,“情”的成分依次增强,色的描写逐步减弱,末稿《红楼梦》聚焦“千红一哭”的悲剧故事,“悼红”之情彻底取代风月劝诫之旨。《论“红迷”》一文则以上文结论为依托,在对女性智慧美、心灵美以及儿女真情进行审美解读后,又将小说美感与读者生理本能巧妙联结。文章指出曹雪芹不明写其所钟爱人物的性意识、性生活,却用宝玉吃胭脂,梦中唤秦可卿乳名、黛玉脸红、宝钗含羞、“金莺微露意”、“醉眠芍药裀”等情节暗示,引而不发,含而不露,“产生了微妙的、不到高潮的审美效应”,从另一层面证明宝黛爱情、大观园女儿悲剧的不可或缺。《可悲的历史倒转———评红学索隐派的“复活”》、《曹雪芹的“原意”之“谜”》则以上述诸文研究成果为基础,驳斥电视剧“忠于原著”、“后六集是探佚成果”等观点,从源头上剖析指导思想的产生流变、思维模式和理论来源,强调它与索隐红学一脉相承,都是帝制心理使然。《也谈“雍正夺嫡”对〈红楼梦〉的影响》一文结合小说中流露的虚无情绪,指出雍正夺嫡对曹雪芹的最大影响不是憎恨雍正皇帝,而在于使他看到权力争斗的可怕,进而“痛绝了那个黑暗的时代”。以上种种论点在有力地抨击电视剧指导思想荒谬的同时,也使白盾愈加坚信“悼红”就是曹雪芹的毕生使命。在《论“悼红情结”》一文中,他紧扣曹氏这一心灵深处的“生命律动”,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它在作者著书目的、情感取向、思想悟破等诸多方面的主导作用。这些问题都是洞察曹雪芹心路历程的关键,显然,白盾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体悟和理解进一步深化了。
白盾还就电视剧播放的实际效果对版本得失深入思考。尽管电视剧严重违背曹雪芹原意,但在改编者眼中,贾宝玉沦为乞丐隐含重大政治内容,故予以保留。然而,电视剧播映后却饱受质疑。白盾以此为基点,结合先前分析得出的版本差异,运用小说结构美学知识,从客观意义上揭示在特定范围内续书优于原著的奥秘。《〈红楼梦〉讨论的重大分歧》、《曹雪芹的“原意”都是“好”的吗?》、《程、高续成〈红楼梦〉的不世功勋》等文章认为,宝黛爱情、钗黛冲突、宝政对立等矛盾的缓解使小说的中心线索“急剧转折、跌落、下垂,而终至松散、瓦解与消失”。思想上则模糊了与封建礼法的界限,削弱了小说的批判力量(宝黛爱情悲剧、大观园女儿悲剧与家庭、社会无涉,一切皆由命定,贾宝玉沦于“击柝之役”后出家是“啖饭之道”,实属无奈)。续书强化冲突,打破“二美合一”和“怨而不怒”的束缚,客观上批判了封建文化和传统美学,也有利于维护贾宝玉的“新人”形象。尽管较之于先前的版本比较,批评重心不再聚焦社会、时代等外因,但它们以审美为经,以人文思潮等普世价值为纬,继承了先前的研究范式和主要观点。
1999年,《脂、程得失各千秋》一文详细分析钗黛斗争/和好、宝政对立/和解、宝玉中举/贫穷后出家的是非功过,进一步指出脂本两项优点,即钗黛和好体现出“宽容、宽厚”的民主精神,宝政和解填补中国文学“父爱描写之阙如”。毫无疑问,该文是白盾版本研究的总结之作。
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白盾的第二部红学专著《红楼梦研究史论》付梓。该书梳理、分析自《红楼梦》诞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研红论著,探讨诸多纠纷根源,展望红学发展途径。白盾提出“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不同性质”、“认清脂本与程本的根本差异”、“正视曹雪芹的消极面”、“摆脱题材决定论”等四大主张。它们既是该书的立论之本,也是白盾二十年来红学研究成果的集中回顾和展示。白盾曾经说过:“情怀《红楼梦》,直面红学史”,这是他红学研究的感情基础和学术视野的自我表白。
结语步入21世纪,白盾对自身红学思想的回顾与总结仍在延续。
2001年2月,《皇帝新衣与红学———红楼大战的世纪回眸》一文发表;2002年8月,《评红批俞的世纪回眸》一文问世;2003年,《江淮论坛》刊载《论红魇———解读红楼梦》一文;《黄山学院学报》分别于2004年第2期、第5期和2005年第5期推出《误读红楼二百年》、《旷世奇才与落魄公子》、《红楼怎样成为“魇”的?》等三篇文章;2005年11月,《胡适评红的百年反思》一文也由《红楼梦学刊》刊出。在这些文章中,白盾放眼全局,力求从宏观的视角剖析困扰百年红坛的奥秘。
《红楼梦学刊》2009年第6辑曾刊发一篇追念白盾的文章,文章称“著名红学家白盾先生”“上世纪50年代初在《人民日报》发表《〈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吗?》,在《人民文学》发表《贾宝玉的典型意义》,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白盾先生在《红楼梦》文本批评、主旨研究、版本研究、作者研究、史论研究等方面,均有建树。
2005年,由白盾先生领衔黄山学院师生会校、以程甲本为底本,参照近10种版本并做出会校注释的‘黄山版红楼梦’出版,是《红楼梦》研究与红学文化普及相结合的一次重要尝试。”
该文对白盾红学建树的评价是中肯的,这一评价将有助于认识白盾红学研究的红学史价值。
参考文献:
[1]段启明,汪龙麟.清代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2]冯其庸,李希凡.红楼梦大辞典[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3]白盾.红楼梦新评[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4]张冠华.西方自然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5]白盾,汪大白.红楼争鸣二百年[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6]高淮生.红学学案[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7]白盾.“大悲剧”与“小骗局”必须分清[J].阜阳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3).
[8]白盾.试论高鹗续书之功[N].光明日报,1983-02-15.
[9]白盾.红楼梦研究史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