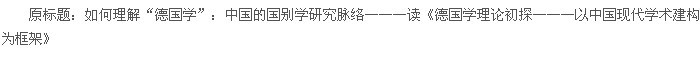
中国的“西方”概念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 按时序有关“西方”的学说大概被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上古时期内外关系‘基本之形式’之形成。 第二,秦汉帝国时期神圣方位的东移。 第三,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天观点之诞生及神圣方位复归于西的进程。 第四,隋唐帝国时期到‘晚期帝制中国’(宋元明清)时期与海洋世界密切相关的‘南海’与‘西洋’观念的产生与异域方位观念的转变。 第五,以古代西方学各阶段之积淀为历史基础的近代‘中西文化接触史’。”
〔1〕狭义的中国西方学应该属于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接触史”,在学术研究角度,近代中国的西方学关注重点非常有限,不外乎“术”而已,“西洋物质文明输入中国,始于明末清初,而西洋思想文明传入中国,却迟至甲午战争之后”。 在救亡图存的强烈意图下兴起的“西方学”的内容肯定远不及欧洲东方学包罗万象,继以两次鸦片战争为代表事件的西方强势入侵之后,“军事”、“资本” 成为“西方学”内容的两大关键词。 此后,中国的“西方学”从未摆脱致用层次的含义,西方发达的军事、科技、经济是中国的西方学首要关注的重点,西学几乎成为舶来科技的同义词。 虽然当今中国对西方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制度、思想层面,但是在“西方学”这一地域框架下的研究方法、内容则没有得到及时更新。 而《德国学理论初探-以中国现代学术建构为框架》 一书(以下简称《德国学理论初探》)所提出的“德国学”概念恰好提供了一种新的中国的国别学研究脉络。
“德国学 ”理论的定位显然从西方的国别学研究中得到了启发和参照, 但是又有其独特之处。 “德国学”与“东方学”、“西方学”相对模糊的地域定位不同,也与“梵学”、“闪学”等精确的民族、 语言定位不同, 它的定位注重“德国 ”这一国别 、“德意志 ” 这一民族的精神文化资源,它“特别强调解构原有‘西学东渐’概念,凸显‘国别资源’的重要性”;“它不是一个有着统一尺度的客观研究对象范围, 而是以民族—国家为高度坐标轴的学术概念”,明显“德国学”理论除意在学理角度的开创外,也考虑了在社会、学术、国家层面上的互动和发力的可能。
作为本书的内容主体部分,《德国学理论初探》的第二—四章“分别从涉德跨学科学术史、大学体制内德语专业教育、德语文学学科三个层面来讨论德国学建立的基础性问题”,即在“德国学”立场上对德语、德国研究进行学科史的归类和梳理,期待在社会现实层面特别是大学教育层面实现“德国学”同德语、德国相关学科的衔接。 作者特别提及大学教育中德文学科同“德国学”之间的关系,“现时代背景下德文学科的出路和意义,或许都在于‘德国学’的建设”。 德文学科和“德国学”互动背后隐含的是对学科、教育体制改变的新尝试。 第五—七章则进一步阐发了“德国学”在学术、国家层面的定位和作用,“分别从 ‘现代民族国家’研究与跨专业学科群定位、德意志道路及德意志精神史探求作为核心命题、理论资源与中国视域整合等方面在理论上进一步阐发和提高德国学命题”。 在民族国家高度的学术层面,“德国学”体现的是“以文明为背景的综合研究”,如果在学科、教育体制层面得到落实,则说明“民族-国家 …… 将这一对外国的理性探索与研究规制化,体现其理性精神与文化层次”;在超越致用层次的国家现代化角度,“德国学”理论迎合了“现代中国”乃至“中国现代化历程”对世界视角的需求并提供了一套如何完整审视异质文化的方法,“‘世界胸怀’ 的有无,‘外国对象’的意识,都影响到对现代中国的认知程度与层次”。
从学科角度看,“德国学”作为一种“以现代德国(十九———二十世纪)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种跨学科意识为主题的‘学科群’建构”,可谓把学界熟知且大量实践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提升到了理论高度。 针对现有的德语德国相关学科,“德国学” 研究方法有两点, 一是“分”,二是“并”:“分”是将德语 、德国相关研究从文学 、哲学等学科中分出,自成一统,作为涉外学科,这种“分”背后体现的是观察一个异质文明的完整的视角。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将德国文学等按国别置系的改革就显现了其思想高屋建瓴之处,但是后继者蒋梦麟并没有按照这个路子走下来,今日大学里的德语文学一科也多归置在外国语系或者西方语系下,“文学、 历史、哲学、教育、政治、经济等,都被置于不同的学科之中,有的更未能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如就没有专门的德国史专业(放在世界史之中),没有专门的德国哲学(放在现代外国哲学之中),更没有德国教育(放在比较教育之中)”。 这种体制上的延续暗示了中国的“外国学”视角的缺憾,“至今为止,……东方人几乎还没有能够在完整的意义上建构起一套‘西方学’”,其中缘由可见一斑;“并”是将德语、德国相关研究学科统一到以“德国学”为前提的学科群下,到目前为止,以“跨学科”研究为主要的“并”的方法依旧体现在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 以“并”为主的“德国学”研究自觉还没有得到普遍重视,学界内的学科界限和分科意识仍深深烙印在学者身上。 以德语学科为例,虽然德语学科建设保持了速度和规模,但是范式没有发生新的转变(从德国文学系到德语系),其学科设置体现了部分德语学科建设者的一种理念,即向“外语学科”而不是“外文(文学)学科”发展。 这种理念本应该作为学生登堂入室的基础,却异变成学生经世致用的手段,与重视德语文学发展的初衷背道而驰。 作者认为,“我们也应当深刻认知学科分割知识造成的严重后果,而努力探寻一种可能的出路”。
特别在德语、德国研究相关学科中,由于德国精神文化的特殊性,比如经典文学作品常常是带有哲学意味的, 从古典启蒙到浪漫主义, 德国的文学史中总能瞥见哲学的踪影,歌德可算此中大家。 所以,想要理解德国文学作品真谛,不对德国哲学的发展脉络有基本了解是不能想见的;而学哲学者(与德国哲学有关联者)必以德语哲学原着为尊,为求不曲解、不缺解,则学德国哲学者以有德语语言学习基础者最佳, 与此类似的还有德国历史等学科,德语在资料搜集整理工作中不可或缺。 除了在语言应用层次的联合以外,在学科史层面的联合比如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的碰撞同样重要,比如探究歌德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或者从文学的角度对爱因斯坦的解读等等。 当然,“并”不是唯一也不应是唯一的思路,否则就会陷入类似“研究生学习要专还是要博? ”这个并不理智的选择中,当然,理想答案是“既要专也要博”,同样在“德国学”这一命题下,要求学者既要“超越学科”,又能“坚守学科”,但是高层次的“学科互涉”无疑对学者的学养要求很高。 理想的“德国学”研究貌似普及的可能性很低,即便是相近学科的叠加组合式的研究,对于习惯了学科内研究的学者来说也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对此,作者“主张应从具体的基础性学科本身开始,先求内部之‘联通’”。 不仅仅是文、史、哲等大学科的交流互动,更体现在实在的语言学、翻译学在思想史维度的联合。
“歌德学 ”即被作者作为 “德国学 ”建构的一个最佳例子引证说明,歌德作为德国的一个象征,其学术研究意义自不必说,从“歌德学”在日耳曼语文学领域的发端直到今日 “歌德学”成为德国研究领域的“显学”,乃至成立了实体研究组织“歌德学会”,仅在学科史范畴下就已足够我们汲取在其他具体的对象上开展“德国学”研究的方法。 这也可证明“德国学”的理论意义所在。
不过,相关领域目前还没有鲜明打起“德国学”的大旗进行学术实践的,这种状况除了对理论本身的生命力和价值持有疑问以外, 难说学术故垒和学科门户不是其中要因。 “德国学”理论不是一般的国别学研究的方法论, 对 “德国学” 理论的利用和实践并不会被打上什么门户标签,这更像是一场“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晚会,有添柴者,才会有“薪不尽,火继传”的学统绵延;有兴高喝彩者,才会有源源不断的节目和创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德国学的理论探讨应该放在学理创新上,“事实是客观存在的, 但其意义则是由研究者所赋予的”〔3〕。 而在作者选择的立足点上继续发散,形成国别学研究的坐标系,不但应成为德国、德文相关学科学者的任务,也应成为构建现代中国学术的题中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