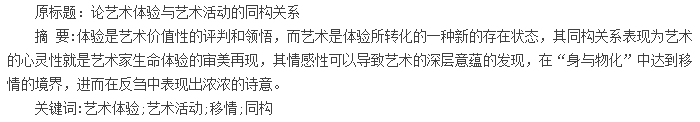
艺术家对作品中人物心理进行系统描写或对自我心理世界的系统阐释,首先是从体验开始的。体验是艺术活动的核心概念,因为体验触及到了艺术的本质属性。可以说没有艺术家的自我体验,艺术活动就不可能具有意蕴性的心理展现和忘我中的诗意表象。那么艺术体验有哪些特性? 它与艺术活动有哪些同构关系? 本文对此就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艺术是体验所转化的新的存在状态
人的一生要经历许多重要阶段,大多数人会经历许多困难挫折,会有自己的见闻和自己参与过的事情。有些人不但有过这种经验,而且在这经验中感悟出了生命的意义、深刻的思想和动人的诗意,那么这种经验就成为一种体验了。体验就是“作为人的生物的与社会阅历的个人的见闻和经历及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
体验是一种价值性的评判和领悟。艺术家看到的东西和画面都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但是他们看到这些情景或者物品时,往往会产生创作冲动,并创作出震撼人心的作品。而普通人则只是停留在一般的经验上面。经验是体验的基础,但体验是对经验的意义和诗意的发现与升华。艺术与人的体验有更密切的联系,因为艺术是对人的生命、生活及其意义的叩问。米勒的《拾穗者》描绘了三个农妇在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田野上,弯着身子拾麦穗的情景,扎红色头巾的农妇袋子里小有收获;扎兰头巾的妇女将左手撑在腰后疲惫不堪;右边的妇女,侧脸半弯着腰,手里捏着一束麦子,正仔细巡视那已经拾过一遍的麦地。整个画面安静而又庄重,牧歌式地传达了米勒对农民艰难生活的深刻同情,以及对农村生活的特别挚爱。这幅画面每个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曾经见过,甚至还亲自做过,但是他们没有将这种经验转化成新的存在状态的冲动,所以他们是只有经验而没有艺术体验,对于这些情景只是一种习惯而熟视无睹。
再比如,罗立中的油画《父亲》用精微而细腻的笔触,绘出了父亲脸上的毛孔中渗出的淋漓汗水,把纯朴憨厚的父亲展现在我们面前,以颂歌般的画面表达了对生活中劳动者的崇敬和赞誉。正因为他有极强的代表性,才让人如此潸然泪下,如此感人心怀。我们每个人都有父亲,我们的父亲都有对孩子对生活大山般的爱,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去刻画他们,有的人甚至对这种场景产生麻木,只有当艺术家将这种外在质朴的美和内在的高尚美结合在一起并展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才会突然发现,原来这种场景我们是有经验的。
法国作家莫泊桑说:“无论在一个国王、一个凶手、一个小偷或者一个正直的人的身上,在一个娼妓、一个女修士、一个少女或者一个菜市女商人的身上,我们所表现的,终究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不得不向自己这样提问题:‘如果我是国王、凶手、小偷、娼妓、女修士、少女或菜市女商人,我会干些什么,我会想些什么? 我会怎样行动?’”同样,对于“晚钟”“睡莲”“竹子”“虾”等事物,我们作为普通人也是没有能力也没有意识将之描绘刻画出来,使之产生激动人心的魅力。
因此,可以说,人们的生活经验与艺术家的体验,其结果有较大的差异。
二、体验的生命性与艺术的心灵性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具有社会性,人的生命是与社会关系以及文化、历史紧密相关的。个体的人的感觉、情感等内心活动,一定与社会存在、社会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人的体验首先面对的是社会存在、社会关系和文化历史。但是当个体的人去体验社会的时候,他不是被动消极的去反映,而是主体生命的全部投入,是人的生命的全部展开。正如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讲的,人类的特性就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人通过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使一切对象物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展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体验是生命的体验,属于生命内部的情感活动。体验具有生命性。
艺术是艺术家个体化生命体验的转换状态。艺术家体验(或者说审美体验)的生命性与艺术活动的心灵性是同构对应的。可以说,艺术的心灵性就是艺术家生命体验的审美再现。艺术从表面上看所表现的常常是外在的人、事、景、物,但实质上所表现的其实就是艺术家自己的生命迸发出来的火花,属于他的心灵世界。
梵高的《向日葵》能使简单地插在花瓶里的向日葵,呈现出令人心弦震荡的灿烂辉煌。梵高的宇宙,可以在《星夜》中永存。画家莫奈 1890 -1891 年间,对同一个干草垛,分别在不同季节的早上、中午、傍晚的阳光下所呈现出的不同色彩,进行多达 15 次的描绘,充分说明经验到体验的转化需要艺术的积累和充分酝酿。余光中的代表作《听听那冷雨》,勇敢地涉足让庸人却步的政治湍流,有意让作品的社会意义、美感价值经历洗礼和考验。文章开篇写道:“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连在梦里,也似乎有把伞撑着。
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从安东尼奥尼那里来的。不过那一块土地是久违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二十五年,一切都断了,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裾边扫一扫吧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这段话准确简洁地让艺术把真情实感反馈给现实———它的母体,表现出作者能清醒认识到:如果用艺术伪装现实,艺术只能沦落这一真理。
三、体验的情感性与艺术活动的意蕴性
由于体验直接指向人的生命,以生命为根基,所以体验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可以说,情感是体验的核心。我国六朝时期的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情者文之经”,正道出了艺术体验的一个重要特征。体验的出发点是情感,主体总是从自己的命运、遭遇以及全部文化与情感的积累出发去体验和揭示意蕴;而体验的归结点也是情感,体验的终结常常是一种新的更深刻的情感的生成。比如一个养殖孔雀的人在养孔雀的过程中也许会有情感上的收获。但是当一个文学家或者艺术家在面对孔雀时,就会给孔雀赋予一定的意蕴,从而将它画到纸上,摄入镜头中,或者描绘在文学作品中,而舞蹈家杨丽萍就会把它通过优美的舞姿加上动人和谐的音乐和色彩搬到舞台上,给人们展示生命的美好和魅力,从而激发人们对孔雀的欣赏,对美好事物的鉴赏和追求。列夫托尔斯泰看到牛蒡花时说:“这朵小花捍卫自己的生命直到最后一息。”
托尔斯泰发现了花与生命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对花的兴趣不是生物学的,而是美学的、哲学的。他对花倾注了自己的情感,发现了花的顽强不屈,这样一来,他的体验也就超越了花本身。托尔斯泰从情感出发,并以新的意义生成作为结束。如果这次体验没有深义,那么这次体验也不能称为真正体验。
莫言能写出《红高粱》之类的乡土小说作品,主要是因为他有乡土生活的体验和经验,他能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的生活。莫言把对故乡的惦念渗透在文字中,树立了“高密东北乡”这一文学地理概念。莫言对故土粘稠而纠结的情感,爱恨莫辨,无法解脱,这是他乡土小说独特之处的来源,从而也构成他作品的独特魅力[5]。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里,我们也能清晰看到路遥本人生活的影子。同样,所有的作家、诗人都是在自身生活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提炼,才能有震撼人心的作品。
优秀的艺术作品,大都有着一些更为内在和深远的深层意蕴,就是艺术作品内在的含义、意义和意味,包括一种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等等。比如说,只有感受和领悟美术作品的深层意蕴,才能更好地了解美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有自身的表现形式,像音乐用声音一样,美术的表现语言有线条、形状和色彩等,美术作品就是运用这些方式与他人进行信息交流的。
总之,艺术体验的情感性可以导致艺术的深层意蕴的发现。艺术家在体验过程中,情感灌注对象的结果,就是让对象的意蕴显露出来。如果以理智与情感相比,存在及其意义更向情感敞开。
四、体验的“忘我”与艺术的“移情”
经验作为一种认知活动具有明显的主客之分。主体认识客体,主体不会忘记自己的身份与存在,客体也不会“丧失”自己的存在。就是说,在经验中主体与客体是分离的甚至是对立的。但在体验中,“物”与“我”的距离缩短乃至最后消失,进入“物我同一的境界”。庄子的蝴蝶之梦就是“身与物化”。庄周和蝴蝶一定是不同的,但在这种情景下能互相转化。
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移情说”讲求情景交融,不可分离。《诗经·小雅·采薇》记载:“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菲菲。”金圣叹在散曲《凭栏人》中说,“人看花,花看人。人看花,人到花里去,花看人,花到人里来”,十分清楚地阐述了移情的基本思想,“人到花里去”“花到人里来”,将人与花相互融合,仿佛呈现一幅画面,人在花之蕊,花在人之心。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写道:“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我”化身为银蛇、蜡象施展于天地之间,创天公所不能的奇迹。在《送瘟神》之二中,“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景物完全化为了情思,自然景物变得通人心、随人意,人与美丽的景色交融一体。暮春的落花飘入水中,随人的心意翻着锦浪,一座座青山相互连通,就像专为人们搭起的凌波之桥,整个中国呈现出一派兴盛的气象。温庭筠的《梦江南》这首闺怨词中,“斜晖脉脉水悠悠”一句是思妇的痛苦心境移情于自然物而产生的一种联想。“落日”“流水”本是没有生命的无情物,但在此时此地的思妇眼里,成了多愁善感的有情者。“斜阳”欲落未落,对失望女子含情脉脉,不忍离去,悄悄收着余晖;不尽江水似乎也懂得她的心情,悠悠无语东去。物我交融,创造出很强的审美效果。
在移情作用下,我们会给无生命的静止客体灌注以生命。在移情作用中我们会觉得:高山似仁者,无言而长寿;流水如智者,欢快而温和;风在细语,树在低吟。类似的还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李逐水流”“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品读后,我们就知道,花、鸟、柳絮、桃李、蜡烛等这些本无感情色彩的“物”在诗人的笔下,宛若与人的喜怒哀乐之情息息相通,别有一番审美情趣。这种“移情”在诗歌创作活动中起到了重要的表达效果。正如柳宗元在《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中所说:“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
在移情作用中,我们会心情外射,把自己心中的情感,认为是客体具有的情感,一曲音响的流动,我们感受到它是悲哀的或是欢快的。“泪眼问花花不语”“一花一世界”“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都是因我把自己的意蕴、情趣移于物,物才呈现出我所见到的形象。同一个世界,观察的眼睛不一样就会有不同的世界。所以我们看世界实际是在看自己,读作品也是在读自己。
正是由于移情作用,我们才会“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情与物同,心物交感,情境交融,意境自然天成。与中国相比,西方的“移情说”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德国美学家里普斯(Theodor Lipps,1851 ~1914)说:“这种向我们周围的现实灌注生命的一切活动之所以发生,而且能以独特的方式发生,都因为我们把亲身经历的东西,我们的力量感觉,我们的努力或意志,主动或被动的感觉,移置到外在于我们的事物里面去,移置到在这种事物身上发生的或和它一起发生的事件里去。
这种向内移置的活动使事物更接近我们,更亲切,因而显得更易于理解。”里普斯的“移情说”侧重于对主体心理功能的体验,把主体的感觉、情感等提到了审美对象的地位,揭示了美感中包含审美主体的心理错觉等美感心理规律。概略地说,里普斯的移情作用指的是,在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一方面把自己的价值情感在对象中加以客观化,在这里完成客观的审美价值内容;另一方面观照给定的对象,使之在自己心灵中主观化,然后在自己的现实情感中加以体验。其理论核心是把对象主观情感化过程同时作为自我情感的客观化加以考虑,据此深刻地把握审美意识中主客观融合的关系。在 19 世纪以后,浪漫主义兴起,强调感情和想象,强调自我的解放和自由的人格,因此,移情说具有很多优势。里普斯的移情说过分强调感情,只看到感情的外射,而没看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把人与现实在实践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动态关系,简化为静态的审美关系,忽略了产生美的客观因素。只强调主观的移情而没看到离开客观对象的性质与形式是不可能产生移情现象的。其实人的审美活动决不仅仅限于情感,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部展现。
五、体验的反刍与艺术的诗意
体验的忘我性是将情感移置于对象,作家的体验不但要能“入”,而且还要能“出”。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入乎其内”就是前面所说的“移情”式体验,“出乎其外”就是体验主体对体验的反刍。体验者似乎把自己一分为二,一方面他是感觉者,他在感觉世界,并在感觉中受到刺激,不能不产生反应,这个过程他是受动的;另一方面,他是被感觉者,他自己在受动中感觉到的一切,让另一个“自我”来重新感觉和感受,这一过程他是主动的,因为此时他是在体味和领悟。从这个意义上说,“出乎其外”就是跳出去,与自己原有的带有功利性质的经验保持距离,再次感受自己的感觉,或者说把先前自己的感觉、感受拿出来“反刍”“再度体验”。例如,法国作家雨果写《巴黎圣母院》之前,雨果首先对圣母院的构造进行了解,熟悉圣母院的知识,突出了哥特式建筑的特点,这个过程是受动的。但当雨果把圣母院淋漓尽致地掌握后,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较量不断冲击着他的心扉,他把圣母院的结果及其发生在其中的事件拿出来“反刍”,重新体味,从中领悟到了中世纪的建筑及其宗教对人性的压抑。克洛德副主教因性欲受压抑无处发泄而表现出极端的残酷性,把无辜少女爱斯梅拉达送上了绞刑架。雨果把自己感受到的爱与恨写进了小说。这是一个主动的过程。
西方美学上的“距离”论认为审美体验是一种拉开功利距离的体会。“距离”论的提出者英国心理学家爱德华·布洛(Edward Bullough,1880 ~ 1934)认为,心理距离并不是指空间或时间上的距离,而是观赏者对于艺术作品所显示的事物在感情上或心理上所保持的距离。这种距离由于消除了观赏者对作品的实用态度,而使得美感有利于快感,因此使观赏者对眼前的事物产生崭新的体验;然而,若是主客体在心理距离上失去了,例如差距或者超距,则不会获得美感。
布洛曾说,对大多数旅客来说,在大海航行中突然遇到大雾,都是极不愉快的。但是只要我们把眼前可能发生的危险等抛在一边,换一种客观的眼光来看这景象,周围的大雾迷迷蒙蒙,变成了半透明的乳状的帷幕,这不是很美吗? 这里实际上是对已有的经验换了一个角度重新审视,即所谓在观照中“插入了距离”。
布洛解释说:“意识到的方面,距离的作用不是简单的而是相当复杂的。它有否定的抑制的一面,割断事物的实用方面以及我们对待事物的实践态度。它还有积极的一面———精心制作在距离的抑制作用所创造的新的基础上的经验。……通常,经验总是把同一方面向着我们,即具有最强的时间的感染力的方面。一般情况下我们意识不到事物不直接不实际地触及到我们的那些方面,我们一般也意识不到同我们的自己的接纳印象的自我相分离的印象。把事物颠倒过来,意外地观看通常未注意到的方面,这使我们等到一种启示,这就是艺术的启示。”即换了一个视角之后,重新审视自己的经验,以便看到通常未注意到的方面,即诗意的方面。我们也可以想见,当武松打虎时看到的是老虎的凶恶残忍。但是在画家的眼中,老虎却有着雄壮的虎威,有着力量之美。所以,只有当艺术家与对象具有一定的距离时,才能跳出局外对老虎进行观照。正如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所说:“陌生人比当地人更能对所居住的街取审美态度,前者比后者更容易现出一定的‘距离’。”
艺术体验一般说也是反刍式的,而对体验的反刍往往是产生美感的必要条件。对此,明末清初的陆世仪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人性中皆有悟,必工夫不断,悟头始出,如石中皆有火,必敲击不已,火光始现。然得火不难,得火之后,须承之以艾,继之以油,然后火可以不灭。得悟亦不难,得悟之后须继之以躬行,深之以学问,然后悟可以常继。”[8](卷三)尽管当时并没有显示出诗情画意来。隔了若干年后,重新回忆这段经历,在回忆中体味和领悟,由于经历时的“功利”考虑都变淡了或消失了,那么经历的另一方面———美感价值也显示出来了。例如屈原被逐、司马迁受辱、曹雪芹家道中落后,有了对政治对人生对人性的深刻认识,才能具有深刻的体验,有了这种体验才能写出不朽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才有感人肺腑、摄人魂魄的艺术力量。
总之,个体体验与艺术活动的心灵性、意蕴性、“忘我”和“诗意”等特性,是同构对应的。或者说,在艺术活动中凝结了个体体验的种种特性。没有这些特性,艺术活动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艺术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正是作家的个体体验的凝结与表现。
参考文献:
[1]童庆炳,程正民. 文艺心理学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杜夫海纳. 美学与哲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4][俄]列夫·托尔斯泰. 1896 日记:列夫·托尔斯泰论创作[M]. 桂林:漓江出版社,1982.
[5]魏诗娟,仝欣. 莫言乡土小说的魅力所在[J].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5).
[6][德]里普斯. 论移情作用[A]. 西方美学史资料选编:下卷[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7][英]布洛. 艺术距离———艺术与审美原理中的一个因素[A]. 西方美学史资料选编:下卷[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8]陆世仪. 思辨录辑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