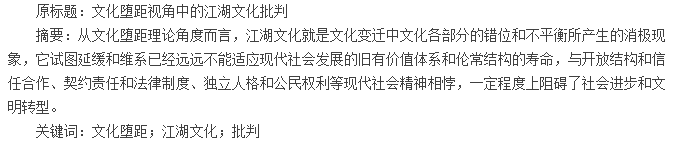
1923年,美国社会学家W.F.奥格本在其《社会变迁》一书中首次使用了“文化堕距”(culturelag)这一概念。所谓“文化堕距”,是指在社会发生变迁时,相互依赖的各部分所组成的文化的变迁速度不一致,有的部分变化快,有的部分变化慢,导致各部分之间的错位和不平衡,并由此造成社会问题。“文化堕距”概念一经提出,就吸引了不少学者用以解释社会变迁中的诸多现象和问题,成为社会学领域影响较大的概念之一。而江湖文化是深刻影响近现代代中国社会发展和变迁乃至主流价值观的特殊文化现象。
一、江湖和江湖文化
江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概念。和许多重要的名词概念一样,在中国人的语境中,江湖一词经常被提及,但其含义常常是语焉不详。江湖的本意是指长江和洞庭湖,后泛指三江五湖,即自然界所有的江河湖海;但春秋后,江湖一词逐渐抽象化,从一个地理名词演变成为中国文化中重要的文化概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文人士大夫官场失意或逃避名利的隐居之所,也成为一部分失意文人政客的理想之所在;一种则是游民觅食求生的场所,脱离了宗法网络的游民们为其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奔走打拼,不经意间又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宗法网络,这也是我们现在经常活跃在口头上的江湖,也是本文着意关注的江湖。
一般认为,江湖是指与“庙堂”相对应的民间社会或底层社会乃至秘密社会。但这显然不是江湖的本质。底层社会或民间社会中外皆有,尽管江湖的范围很大程度上与此重叠,但那不完全是中国人所说的江湖。因为江湖绝不仅仅是底层社会或民间社会。
研究中国游民问题的学者王学泰在其《游民和中国文化》一书中提出了“隐性社会”的概念,我觉得是十分恰切。甚至有学者认为,“显性与隐性的二元社会架构,是王学泰先生贡献给学界的最大理论成果,也是他观察历史的基本方法论”。中国社会是由显性社会和隐性社会所组成的特殊社会,而在某些情形下,隐性社会更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更能反映社会的本质。这是中国社会的特点,也是中国文化的两面性决定的。显性社会反映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观,凸显道统和正宗;而隐性社会自有一套不为人熟知的运行规则和运行机制,覆盖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往往从各个层面,对显性社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个隐性社会其实正是中国人的江湖。所以,观察中国社会,不仅要观察表面显示出来的一切,更要观察潜藏着的隐秘的一切,而且有时候隐性社会更能反映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因此,严格来说,中国人的江湖,横跨政商学各界,不仅仅存在于底层社会或民间社会,也广泛存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正所谓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但江湖的主体仍然是底层社会。江湖产生的前提是大量游民的出现。游民乃是农业生产赶不上人口生产的产物。游民从严密的宗法社会中“脱序”而出,其“人员构成,除破产农民、市民、手工业者、小商贩等失去生活依靠的劳动者外,还有散兵游勇、流氓光棍等游手好闲之辈以及倡优隶卒等操‘贱业’之人,他们都是游离于正常经济生活和经济秩序之外的下层人物”。游民们游走在社会边缘,采取种种正当或不正当手段谋生,将陌生人纳入自己熟悉的符号系统,彼此建立了一种“类血缘”的亲近关系。江湖本质上仍然是儒家文化的变异,是一种泛家族主义的宗法制度的扩展和延续。江湖社会内部,帮主或江湖老大类似于族长,异姓兄弟通过结拜成为手足,江湖规矩彷佛家规家法,在此体现的仍然是宗法制度的伦常结构。
那么,什么是江湖文化呢?刘平认为,“江湖文化就是指存在于江湖人、江湖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总和”。但我认为江湖文化的含义显然要更深一步。江湖文化至少有两层含义:一个就是刘平所谓各种江湖现象的总和,诸如“五花八门”的“三教九流”之类;但更有意义的其实是第二层含义,即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价值观,尤其当这些价值观已经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并且与主流价值形成深刻互动,这就更值得关注。我的理解,“江湖文化是在(儒家文化)泛家族主义基础上,以利益交换或者利益共享为目标,以人情、面子、关系或程式化的文化符号等建立并维系起来的小团体或小圈子文化,在这个小团体或小圈子中,没有信仰及远大目标,只有私欲私利;没有原则,只有哥们义气;没有独立人格,只有蝇营狗苟充满机会主义的人身依附和交换关系”。其中江湖义气是理解江湖价值观的一把钥匙,也是江湖文化的核心所在。
二、江湖文化是社会变迁的产物
江湖文化和社会变迁联系在一起。社会变迁是社会学的重要概念之一,它是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是社会的发展、进步、停滞、倒退等现象和过程的总和。社会变迁既包含社会的进步和退步,又包括社会的整合和解体。江湖文化无疑产生于社会变迁。从历史上看,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以及连年灾荒,是江湖产生的主要原因。斯时大量农民丧失家园流落异乡,成为流民或者游民。流民们经过辗转磨难最终仍然会回到原先的生活轨迹,而游民则永远地离开了故土,进入了陌生人社会,他们按照宗法网络建立了江湖并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不断冲击既有秩序,加剧社会变革,某些情况下即成为社会变迁的潜在推动力量。
贵族势力的过早衰落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按照王学泰的观点,先秦社会仍然是贵族社会,贵族社会是身份社会,贵族和平民之间泾渭分明;而宋以后游民文化泛滥,至此中国就成为平民社会或世俗社会了。过早进入世俗社会,贵族势力不断被削弱,作为一个整体的贵族文化不断衰落解体,原本属于底层文化的江湖文化则活跃异常并向全社会广泛扩散;江湖文化随着底层游民多次入主中原而逐渐被主流价值观接受甚或成为其一部分,这种社会的不断崩解、停滞乃至倒退,朝代更迭。“城头变幻大王旗”,长时期的分裂割据,江湖和庙堂角色的经常性转移,正统和非正统地位的周期性置换,底层文化和上层文化之间没有明显的区隔,恰恰是中国社会变迁的特点之一,也是理解江湖文化长期横行于华夏大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代以来的江湖文化则又有其特殊的一面。“我们现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社会变迁。———我们最感兴趣的不是特定规划,而是社会变迁中那些最一般、最基本的东西”。和历史上内源性的社会变迁不同,近代以来的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国家陷入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之中,其社会变迁模式是“挑战—反应型”。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再也不能自外于世界,而被迫卷入世界文明大潮,中国文化被迫按照和以往完全不同的西方文明模式进行改造甚或重构,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和民族优越感跌落谷底。相应地,每每和大变动时代联系在一起的江湖文化此时也活跃异常,江湖义气、江湖做派风行一时,江湖气弥漫社会,江湖规则横行于世,形形色色江湖人物层出不穷。革命党、保皇党,立宪派、守旧派,概莫能外。历史上看,江湖文化从来没有像近代中国这样接近主流文化,甚至一定程度上主导了我们的社会生活,成为主流价值观的一部分。
那么,近代江湖文化的特点是什么呢?
陶连生提出近代江湖文化具有五大特征:是一种反文化;是宗法制度文化的缩影;活动的秘密性;道德上的缺失;价值观的腐朽。杜向阳认为江湖文化具有五个基本特征:聚群、趋利、恃强、尊上、寄生。他进而作了解释详细:聚群是说江湖文化强调拉帮结伙,形成帮会或建立人情网络;趋利是指江湖组织成员聚集在一起,其目的是为了获取个体或组织利益,这种利益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利益;恃强是指江湖组织获取利益的过程不是通过在体制内的正常经营获得的,而是把他人的存在当作满足自己的资源,通过恃强凌弱,钻营取巧得到的;尊上是指江湖组织的结构是“唯上”的。在帮会等江湖组织中,尊上主要体现在组织成员听命于帮会“老大”和上一级会众,在人情关系网络中,尊上主要体现在人们喜欢结交社会地位或经济地位高并控制一定社会资源的人。社会生活中,面子有时具有信用功能和货币功能,也是人们尊上的体现;寄生则是江湖文化价值观的体现。他指出:“江湖组织通常不从事社会生产,追求的是社会资源的再分配而不是创造,而这种分配都是以个人主义和特权思想为基础的。他们奉行弱肉强食的价值观念,通过坑蒙拐骗、强取豪夺的手段来获取社会资源,寄生于社会”。
我曾经把江湖文化特性归结为四点,即:挥之不去的江湖情结、无所不在的江湖规则、包打天下的江湖义气、高于一切的江湖圈子。我认为近代江湖文化是古老中国糟粕文化的集合体,是国民性中不适应现代性的消极成分,反映了农民阶级对现代化的本能的恐惧和抗拒,它以一种不为人察觉的方式,阻滞着社会变迁,使所有现代化的努力最终都化为泡影。
如果说早期的江湖文化还存有一点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意味(所谓侠客文化);那么,近代以来的江湖文化,则彻底堕落成为一种落后的反现代化力量,与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民主观念、人本主义、独立人格等格格不入乃至背道而驰。从文化堕距理论角度而言,江湖文化就是文化变迁中文化各部分的错位和不平衡所产生的消极现象,它用漂亮的伪装,用各种花哨手段,改头换面、借尸还魂,试图延缓和维系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旧有价值体系和伦常结构的寿命,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进步和文明转型。
三、江湖文化何以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阻碍
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沉淀物。文化本身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奥格本曾多次谈到文化本身的保守性。的确,文化具有稳定和保守的性质,消极的文化无疑也会抵制社会变迁,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之所以说江湖文化是一种文化堕距现象,是因为江湖文化终究反映了一种文化不适和文化变异。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自被迫踏上了社会转型之路开始,其变化之大,社会震动之剧烈,反复迂回之曲折,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让人眼花缭乱。尤其是,以个人主义和契约责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西方文明,不仅彻底颠覆了传统价值体系和文明根基,而且这种强势文明最终将彻底终结江湖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然而吊诡的是,近代中国,皇权的衰落,主流价值体系的崩解,却给了江湖文化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使之如过江之鲫,得以全面侵入社会的各个层面。一方面各种变革力量纷纷试图利用江湖势力达到自己的目的;另一方面,江湖文化又与现代文明及其制度体系存在深刻价值冲突;一方面物质文明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变迁,人们尽情享受着现代文明的物质成果;另一方面现代文明体系又受到选择性排斥,人们依然习惯因袭传统,物质文明的光鲜外表掩盖不了腐朽不堪的价值真空,新的价值体系始终无法得到广泛认同乃至最终确立。这种目的和手段的分离,物质和精神的分离,现实和价值的分离,凸显了东方古老文明社会变迁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成为奥格本文化堕距理论的极好注脚。
开放结构和信任合作是现代社会的基础。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开放式社会结构中陌生人之间的普遍信任与合作,是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法律现代化的前提。依靠契约和法律制度,陌生人社会的诚信体系得以构建,各种现代社会所必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联系得以维系和保护。
近代英国正是依托开放式社会结构,以维护和保障这种普遍信任为目的,形成了法律职业阶层,明确了私人财产权利,确立了司法公正,发展和建立了议会制度,催生了工业革命的发生,从而确保英国成为第一个资本主义强国,进而过渡到现代社会。
契约责任和法律制度是现代社会的基石。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说过:“迄今为止,所有社会进步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身处变化中的陌生人社会,其利益的获取、调整和维护,应当也只能依靠契约和法律来规范。比之于道德和宗教,法律是人类社会发明的最好的调剂手段,以法律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也已经是文明社会的普遍的成功经验。契约精神源于商品交易的发达,与陌生人进行商品交换才需要契约,有契约才会守约。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里,商品交易极度匮乏,是产生不了契约精神的。创造辉煌政治或商业文明的国家,无一不是契约精神的楷模,西方文明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契约的发展史。到了现代社会,契约内涵已被广义化:在经济层面,它是社会公认的让渡产权的方式,是创设权利义务关系的途径;在政治层面,它是联结政府与民众的纽带,是公共权力合法性的根源;在伦理层面,它是个人或团体信守承诺的道德体现。契约精神不但蕴含了现代商业法则和风险管理原则,而且也体现了平等、尚法、守信、公平和合理、承诺和执行等“底线伦理”。从传统身份社会到现代契约社会的范式转换,实质是人的解放,是用自由流动取代身份约束、用机会平等取代社会不公、用后天奋斗取代先赋特权、用法治取代人治、用民主取代专制的历程,是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变革。
独立人格和公民权利更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是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一起产生并成长起来的。它与民族国家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民族国家需要公民的支持,而公民的权益也需要国家的保护。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发展,决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和GDP的增长,而首先应是公民人格的发展,是使公民独立人格得以充分发挥的那一套规范的制度体系的进步和完善。公民独立人格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交流沟通中,也体现在个体面对强大的国家威权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平等意识上。
儒家文化主导下的中国社会,宗法制度是其核心,家族组织成为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家族式的特殊信任(也称熟人信任)与合作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基础,也是江湖文化得以延续和蔓延的基础。虽然经过近代以来历次政治风雨的冲刷洗礼,但几千年形成的文化积淀不可能一日消除,遇到合适机会依然会沉渣泛起。江湖文化通过血缘或“类血缘”的关系,织成复杂而广泛的人情关系网,使人际关系世俗化,并形成新的人身依附关系。它赤裸裸地以小团体利益为纽带,混淆公共价值观,一切从小圈子私利出发,漠视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削弱社会凝聚力,使社会失去远大目标,破坏社会公德,破坏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使所有的法律制度和责任体系形同虚设,社会永远在封建宗法制度的封闭结构中空转,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开放式社会结构和普遍信任的社会价值观无从建立,独立人格和公民权利更无从谈起。
作为一种文化堕距现象,江湖文化在社会剧烈动荡和变迁中的当下中国其实不可避免,它反映了一个古老文明负重前行及转型之艰难。它的兴衰起伏、流布消亡,与社会氛围及历史际遇密切相关,与国民素质及人的现代化密切相关。探寻其特点和规律,用现代观点进行严格审视和批判,对其危害性和破坏性自觉保持高度警惕,就成为所有关注中国未来发展人们的共同历史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