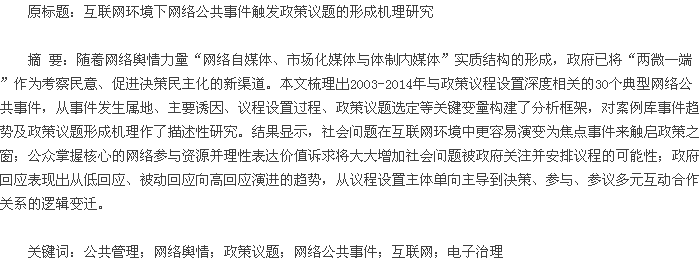
一、现象与问题
网络之于社会,即如手机之于个人,已然成为解决实际状态与社会期望落差的刚需,政民关系、公共服务、社会安全、公众人物等都会在网络舆情中得到直接且真切的沉淀、聚焦、扩散、趋同或激化。公民通过网络舆情获知真相或增进政策接受性等并非现实公域分化后的偶然之举,其实质包含了公民对政府决策权力制约以实现个体价值的理念.在系统反思十多年来网络公共事件的规律后,政府已有意促成互联网舆论力量“网络自媒体、市场化媒体与体制内媒体”三足鼎立的实质结构,以“两微一端”(政务微博、微信、客户端)为核心的网络自媒体更是成为了政府考察民意、促进决策民主化的有效平台。殊不知,大多数社会公众除了运用“选举”参与影响政策过程,似乎再也找不到其他正式途径,但社会问题得以解决恰恰是在政府决策者被“选举”之后。
如果公民不能从起初就作为议程设置主体参与筛选议题清单,也就谈不上政府会在该问题上“选择作为或不作为”,更谈不上“实际状态与社会期望间落差”的解决。
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我们身边广泛存在:①有些问题在其萌芽之初就能被高层主动关注并提上议事日程;②有些问题在出现恶化但未被社会广泛关注时就为高层所察觉而提上议事日程;③有些问题最初仅仅源于公民个人,却为政府所关注,而更多的个人问题却难以安排议程;④有些社会问题需要“直接-间接利益群落”的出现,才能为政府所关注而被提上议事日程;⑤甚至有些社会问题即使波及范围广、性质深,政府却始终不安排议程;⑥而许多原本可能为公民带来巨大利益的决策却又面临着全国范围的抗议冲突风险,以致于政府必须将原决策作为社会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总之,只有少数触发了“政策之窗”,被决策者接受并最终列入“议题清单”的社会问题才能输入政策制定过程,政策议题被界定之后的政策制定也可能是在“针对错误的问题寻找权威的解决方案”.所谓议程设置,即“对政府官员以及其密切相关的政府外人员在任何给定时间认真关注的社会问题进行编目”.
实际上,社会公众认为政府应该关注某个社会问题,往往是通过媒介形成广泛的公共舆论引起政府关注的,而政府决策者是对各种社会问题依重要性进行排序以及选择的最后裁定方。在多数情况下,网络关注与传媒曝光几乎同时介入某一社会问题,从“问题范围、强度及触发时机”等方面共同推动话语在事件当事人群体中的扩散,继而波及到间接利益群体,在公众、媒体、专家学者或社会组织等之间形成足以引起政府关注并提上议事日程的网络舆情力量。如果公民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在常态情况下难以成为政策议题,利益冲突被长期搁置所内聚的政策风险就可能突破网络舆情阈限,最终以焦点事件的爆发来触发政策之窗的开启。这种议程设置反向于传统的政治权威主导,本文将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这种非常态的由网络公共事件触发政策议题的模式上。
因此,我们需要知道,近十多年的网络公共事件是否具有某种趋势?如果有,在这种趋势中是否蕴含了社会问题最终被提上议事日程的一般机理?如果确实蕴含了某种机理,这种机理是什么,即政策议题的形成机理是什么。
二、研究综述及方法
经梳理考证,目前鲜有通过梳理十多年来网络公共事件趋势,分析中国政策议题形成机理的研究文献。在网络公共事件趋势研究方面,通过梳理历年网络公共事件,从趋势中总结其诱因、表现和结局的文献极少,多以网络舆情为分析对象,或从舆情生态研究多元协同治理机制、应急处理机制,或强调舆情管控的行为倾向,或认为舆情事件经历了“引发、展开、变化到消退”的演变,而仅有的涉及趋势的文献也只从新闻传播的角度作了描述性分析,甚少偏向议程构建的特征、途径及效果等。在中国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的研究方面,王绍光借助孙志刚(2003年)等个别早期案例重点讨论过网络时代的外压模式;刘伟等借用“厦门PX项目”(2007年)等少数案例来佐证过多元主体互动议程创建模式的存在,不过都是为了认识当前中国政治制1丰,或讨论网络舆论形成的几个阶段,或运用扩散议题战略模型就呈散点分布的部分案例限于建构阶段分析,或以经典个案进行实证分析,或通过归纳部分案例探索决策回应过程、机制或模式,极少以政策议程设置及其“产出”政策议题为直接对象深度剖析。鉴于上述情况,下文将梳理归纳2003-2014年与政策议题深度关联的网络公共事件趋势规律,分析政策议程设置的阶段过程,并从途径、特征及影响等方面来讨论在网络环境中社会问题何以最终被筛选为政策议题。
所谓网络公共事件,即“由焦点事件触发,众多公民围绕特定议题目标在以互联网为主的话语平台上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对事件当事人、间接利益群体甚至其他社会公众产生重大影响的公共事件”.
本文通过梳理既有文献的网络事件数据库、人民网舆情案例库及诸多文献常用经典案例等,最终编制出2003-2014年影响政策议题形成的30个典型网络公共事件案例库(参见表1),再针对数据库的每一案例事件使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获得收集相关资料。

网络公共事件最终被筛选并进入典型网络公共事件案例库需符合三个标准:
第一,案例必须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即参与网络讨论的公众、专家学者、媒体等的规模及强度大,社会问题的政策影响性(范围与效果等)显着。如“陈易卖身救母”(2005年)、“虐猫事件”(2006年)、“铜须门”(2006年)、“强制安装‘绿坝’软件”(2009年)等,这些案例或者仅仅只是网络个人事件,或仅仅为市场行为等,所以不列入案例库。
第二,案例必须涉及政策议程设置与成文的议题清单,即参与能够触发政府关注该社会问题,且从实质上促使了政府将该社会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如“重庆最牛钉子户”(2007年)、“免费午餐”(2011年)、“广西玉林狗肉节”(2014年)、“兰州自来水苯含量超标事件”(2014年)等,虽然均属于网络热点舆情事件,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但并未直接触及到具体的政策议程设置,所以不列入案例库。
第三,案例必须过程完整、影响可验证及结果无争议。如“湖北石首骚乱”(2009年)、“富士康员工跳楼”(2010)等,此外还如“邓玉娇案”(2009年)、“我爸是李刚”(2010年)、“药家鑫案”(2011)等,事件过程完整性不足,多有网络泄愤情绪出现,且存在诸多争议,所以不列入案例库。
当然,社会问题最终被界定为政策议题本质上是非线性的互动博弈过程,上述三个标准显然不能完全涵盖政策议程设置的特征与范围,文中的30个案例也并非都绝对地符合以上三个相互关联的标准。个别案例是为了对比分析的需要,如“番禺区太石村民罢免村官”(2005年)、“江苏滨海封杀论坛事件”(2010年)、“汕尾乌坎事件”(2011年)。此外,在坚持以上三个标准的同时,案例还需考虑到网络反腐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所以诸如“表哥事件”(2012年)、“周永康案”(2014年)以及2013年以来的典型司法舆情事件均不列入案例库。针对相关资料,我们抽取了案例库事件的发生属地、主要诱因、核心过程(触发范围与类型、政府外参与主体及手段、政府回应的特征及方式)、政策议题的选定(源问题的性质和过程、途径、效果)等关键变量构建了分析框架,下文将对这些趋势及政策议题选定的规律作描述性分析。
三、影响政策议程设置的典型网络公共事件趋势分析
据人民网的舆情分析显示,“2014年网络舆情总体热度呈下降趋势”,这似乎与网络舆情发展的乐观愿景背道而驰。难道是公民的网络参与热情出现了实质性下降,还是政府通过粗暴封锁来为自己释放舆论压力?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网络舆情总态势的下降恰恰验证了两种趋势:第一,网络参与经历了从非理性到理性的行为嬗变,现实落差将被有序表达;第二,微信、新闻客户端在“两微一端”架构中将最终超越微博,成为影响社会价值权威性分配的最大网络舆论自媒体。这两种趋势裹挟了一种参与现象,即现实问题在网络中更有可能被政府所关注并给予合理的解决,而掌握网络参与的核心资源并理性表达将大大增加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可能性。
在30个案例中,只有PM2.5事件(2010年)、郭美美微博炫富(2011年)、微博打拐(2011年)、光盘行动(2013年)的事件属地不是来自地方,而是全国,且属地呈现模糊性。这确实说明纯粹发生发展在网络空间的公共事件极少,公众更倾向于深切关注甚至是仅仅关注发生在身边、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在属地为地方的26个案例事件中,占到61.5%(16件)的案例来自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主要是广东(4件)、浙江(4件)、江苏(2件)、上海(2件),福建、河北、北京及辽宁(各1件);其余38.5%(10件)均来自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且零散分布于山西、河南、安徽、贵州、云南等地。由此而知,虽然发生在北京的网络事件最多,但真正因为政府处置不当造成广大社会影响而成为网络公共事件的案例则极少;次之于北京的广东、浙江分别占到网络事件的8.2%与6%,然其造成广泛社会影响的网络公共事件案例却明显较多。这说明在经济发达地区,公民具有比较高的文化素质与媒介素养,且面临利益纠葛时会比较有意识地通过网络获取公众、媒体与政府的广泛关注,促使政府必须针对问题快速作出议程调整。换言之,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越会有一系列机制促使当地政府主动回应舆情民意,公民有更多的话语力量促使政府关注,并将其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作为重要议题列入清单。
发生属地具有全国性的案例的发生诱因主要是倡导公共行动或涉及公众舆论人物,地方案例事件发生的诱因则可以归纳为权力腐败(滥用公权、渎职、恶性执法等)、道德隐私、环境冲突等社会问题的不决策或决策失误等。从案例可以粗略看出,类似“PM2.5”(2010年)等全国性事件往往具有显着的公共性与服务性特征,且利益诉求中更多地包含了一种以个人理性制约决策权力的价值倾向。地方案例事件的发生诱因则相互交织,涉及的利益相关者结构也十分复杂。根据考证,地方案例事件的具体诱因呈现出地区差异,东部发达地区的诱因主要是市政环保、权益纠纷、劳资关系,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诱因则主要是官民对立、贫富分化、医疗卫生、暴力执法等。北上广浙苏等地的网络公共事件较多,但多涉及公共服务领域,事件引发的危机基本可控;河南、山西、安徽等地区的网络公共事件较少,却往往引发激烈的社会震荡与舆论谴责,多数情况下可能对地方政府合法性基础形成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