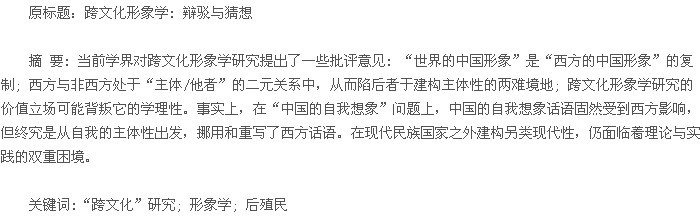
跨文化形象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文化自觉,据此展开为“西方的中国形象”“世界的中国形象”和“中国的自我想象”三组课题。2006 年笔者《天朝遥远: 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出版,五年后《跨文化研究: 以中国形象为方法》问世,涉及了第一、二组课题,但研究的势头已经减弱,这是学术思考本身的困境使然,还是存在其他原因? 2012 年底,论者以一篇《跨文化形象学: 问题与方法的困境》全面反思批判自己的研究,同时也指出了中国文化自觉的僵局。论者自己的思路也表现出了当下中国学界的思考境况。近年来,学界同仁从各种角度对跨文化形象学展开研讨和批判,其中多有创见,并显示出趋同的关注点与思路。在已有跨文化形象学研究的基础上,梳理相关的质疑与批判,可以看出我们这个时代关注的焦点问题与思想方法,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跨文化形象学的三组课题: 重复还是推演
跨文化形象学为自身设置了三组研究课题: “西方的中国形象”“世界的中国形象”和“中国的自我想象”。从《天朝遥远》到《跨文化研究》,相关研究基本完成了前的两组课题,随之学术界的质疑也出现了: “世界的中国形象”似乎不过是在复制“西方的中国形象”; 在第一组研究中那个黑格尔绝对理念般的西方中心话语,在世界语境的传播中,只是被反复证明更加牢不可破。得出这一结论是令人绝望的———“要批驳黑格尔很容易,然而他是对的”: 一方面,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永远陷于“做西方/做自己”的两难( 建构本土特色的主体性仍然处于西方现代性话语逻辑下,成为被西方凝视的一个可疑的他者) ; 另一方面,西方内部的差异、矛盾,甚至像后殖民主义这样的叛逆,终归成为西方的自我否定、自我反思的表现,最终被扬弃进入一个更强大更完满的西方主体,正所谓“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
这一哲学上的难题可以概括为“无法摆脱的二元结构与何以可能的中国( 东方) 主体”。周云龙在《西方的中国形象: 源点还是盲点———对周宁“跨文化形象学”相关问题的质疑》一文中指出: 相关研究预设了一个绝对强势的、整体化的西方,它以金字塔的方式自上而下向非西方国家分配自己的观看方式和中国形象; 这些国家也被笼罩在这种话语的逻辑下,重复西方关于中国或褒或贬的论述,只是根据自己要“做西方”还是“做自己”的不同情势,来调整自己有关中国的话语,亦即自己同西方/中国的关系; 而这又意味着,非西方国家成了另一个同质化的整体,它们的中国形象不过是西方之中国形象的复制,其褒贬的变化不过取决于这个整体想要倾向于西方/本土哪一极。
这是问题的关键。从第一组课题转入第二组课题,论者被质疑并没有真正进入各个国家复杂具体的本土语境,而是仍然在简单推演“黑格尔式的历史因果链”。周云龙指出,要走出这一困境,关键在于不从整体化的“源点”———西方和整体化的接受者———非西方出发,而是从东西方的互动和共谋、从西方话语在旅行中被重塑和改写的角度来思考,亦即,将重点放在理论在不同语境中的“跨文化翻译”以及异质混杂的主体。李勇也指出: 中国近代以来的自我想象固然离不开西方影响,无法摆脱自我东方化的因素,但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是立足中国本土状况对西方话语进行重塑和改写,而非毫无反思地被动接受。
王晓平认为,第二组课题仍然是对第一组课题的拓展或重复,这一方法论难题也使得第三组课题后继乏力。
总的来说,批评者们的修正意见可以归纳为: 西方中国形象的传播并不是完全单向度、无阻力、不走形的,它若要真正进入非西方国家,往往需要接受者的合作与共谋,而依据本土情势的挪用和改写已然发生了。
关键的问题是,重复是研究内容的重复,还是研究前提与方法的重复。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方法是统一的,重复是必然的,而且,从第一组课题到第二组课题,研究的问题已经转移了。第二组课题的问题核心在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中异体同构的核心力量,即自我认同和异己分化。自我认同,不单单是指西方自己和自己认同,也是指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向心性吸引力,使它们与自己认同; 而硬币的另一面,就是非西方国家在现代性的向心力结构下彼此之间的异己分化。前现代传统社会已有的文化结构出现难以弥合的断裂冲突,譬如共属儒教文化的中国和日本,共享佛教文化的中国和印度,在进入现代世界秩序后彼此的东方化、彼此的否定和排斥,就是最好的例证。研究的前提与方法始终如一,但问题与研究内容却变化了。论者更关注现代世界秩序中西方的文化霸权,强调西方文化在现代性世界秩序中表现并实现的那种强暴的、自恋式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塑造了现代世界的观念秩序,也塑造着现实秩序。观念史的研究已延伸入地缘政治与现代世界体系问题。
当然,非西方国家的本土语境是不可忽略的。的确,它们都处于自我认同和异己分化的总逻辑之下,但每个国家对自己历史道路的选择、对自己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对待西方和中国的态度,都是因其具体历史文化背景而各不相同的。譬如“俄罗斯思想”起源于俄罗斯民族天选独特性的意识;日本这种“脱亚入欧”的想象中国的方式,与日本民族性格以及地缘政治格局相关; 而印度的现代性自我认同,根植于骄傲的印度文明的历史和近现代屈辱的殖民地经验。所以,第二组论题是第一组论题的继续,是跨文化研究领域中问题的自然与必然延伸,其基本思路的逻辑是一致的,研究的前提与方法是统一的,但研究领域与观点有所拓展,而真正的问题可能在两组课题共有的、潜在而不宜察觉的西方中心论假设。二、跨文化思辨: 解构还是共谋那么,批评者们所建议的“跨文化翻译”的“共谋论”,或霍米·巴巴式的对“异质性”或“混杂性”的研究,是不是拯救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途径呢? 在这个问题上,论者参考了多方观点,有着自己的警惕,也有一些不确定的、有待商榷的构想。
一方面,在学理上,共谋论可以说是对二元论的某种重心转移。
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虽然在方法论资源上借鉴萨义德、福柯、曼海姆和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但对于主体/他者之关系这一核心问题的理解,似乎仍陷于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从德里达解构二元论的思想方式来看,解构哲学并不是颠覆、拆解,而是重新理解诸如“中心/边缘”“主体/他者”之类的二元结构。这样的结构必然总是存在,但奥秘在于,它们并不以自己所宣称的那种方式存在。即是说,中心总是被边缘的潜在存在所界定的,而又反过来显得是在先的、主导的、决定性的一方。这样一来,我们虽然无法在二元结构之外思考,但起码发现了这两项并非自然而然、永恒不变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具体的实证考察和理论分析,来调整两项的意义分配和比重关系———这不能取消二元论,而是承认它又搁置它,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去拯救边缘他者,也撕开貌似整体的中心者的异质裂缝。
实际上我们无法建构一个实质上异于西方、逻辑上又与之齐平的其他主体,正如我们不可能在二元结构之外思考。黑格尔的确是对的,西方总是主体,反西方最终还是成就了西方———然而这样的研究范式已经耗尽,不想重复,怎么办? 那就是考察双方的共谋、各自的异质性和混杂性。
霍米·巴巴的这种策略并不是二元论的解药,不是平行于二元论的另一条康庄大道。它不想挣脱、也不应被“辩证地”纳入西方中心论。它只是一种研究重心的转换,即: 我们承认二元论; 但若想建构非西方主体,我们就不能在二元结构中总把力量都归于中心,而是要以这个主体自身为重心; 那么经过具体考察,主体是不是真的十分自主、统一、完整,可能已经不重要了。
其实,跨文化形象学也不是只会钻二元对立的牛角尖: 东方主义除了具有殖民压迫性,也是“东方主义通过‘自我东方化’的民族或国家对东方主义的积极回应,为东方的觉醒与复兴提供了想象的资源与思想的力量。东方……从东方主义话语中获得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自信与权威,同时也可能获得了对于西方文化的某种文化权力。这是东方主义的复杂性之一”。
这段表述显然证明,论者并非完全关闭了“共谋论”“混杂性”的思路。但问题是,论者固然注意到了混杂性中所包含的积极因素,却没有在这条路径上走得太远,转而还是回到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中。这是因为,“跨文化翻译”的策略可能会推进跨文化形象学第三组可图的研究以及后殖民主义理论自身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在价值立场和实践、操作的层面,论者担心共谋论“不能回避西方文化的主导话语势力”,也无法“拯救非西方世界的现代性文化主体”。
“跨文化翻译”会不会是一种自我解嘲的共谋? 承认非西方国家在其现代主体性建构中有限的能动性,并不能回避西方话语的主导性霸权。在经过两组课题的研究和自我反思之后,论者对后殖民理论怀有的警惕似乎加强了。理论总是在具体文化语境中显示其意义,在西方世界,后殖民理论本欲撼动西方中心主义,结果却成为无伤大雅的挑衅,或虽无动机却有实效的“合谋”; 在非西方世界,这种理论经过移植,意义和功能全变了,它正为各种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国家主义所利用,造成偏狭地自我肯定、排斥他者、反西方甚至反现代文明的文化陷阱。
近来,论者参考解构主义对二元论的澄清,初步构想: 跨文化形象学倾向于将“西方”视作结构性的大他者,而将一切主体( 无论西方主体还是边缘他者的主体) 视作不自足、不完满的虚无。从结构上讲,那个姑且名为“西方”的大他者实际上是一个无法准确界定、无法穷尽表述的缺席中心,所有主体意识所趋向、所参照的极限。这样一来,说“一切都是西方的”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也可能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西方”不再是实在的西欧北美现代文化,而是统摄着一切文化、没有界限、最大的丰富性———连实在的西方本身也要纳入这个“西方”中去。那么,拆解了西方中心和对主体的偏执,是不是就打开了一个实用的研究空间呢? 这其中隐含着的理论漏洞,可能最终动摇跨文化形象学的理论合理性与可行性。
三、跨文化实践: 超越权力还是倚重权力
既然说到了价值立场,论者感到也有必要总结一下跨文化研究的学术使命、后殖民研究的“同路人”以及第三组问题的前景。
吴励生是学界同仁中较早对跨文化研究有所回应的一位,他高度评价了《天朝遥远: 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的学术价值。
但在他热情的赞美之中,却隐隐透露出一种我们难以评价的导向: 纯学理的跨文化形象学研究,是否应该、是否可能回答中国文化自觉这一现实问题? 跨文化形象学是否可以担当文化自觉的重任? 许多疑问就出现在这一所谓“以学术的方式回答时代重大问题”的学者的使命上。
跨文化形象学无法回避价值立场,中国文化自觉也不单是学理上、同时是实践中的问题。复旦大学林曦博士写出系列论文,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考辨跨文化形象学这项研究与权力的关系①,其观点可商榷但也值得重视,有待我们进一步讨论。林曦认为跨文化研究有可能是一个暗示着要借助国家权力来达成的战略———他称之为“跨文化形象学的第一张面孔: 与权力联姻”。
这项研究固然隐含着价值立场和实践导向,但中国文化主体性是什么、如何建构,在这些问题尚未清晰的时候,后殖民学术与权力联姻往往导致反现代性、偏狭的文化保守主义和狂热的民族主义,弊大于利。
于是设想出第二张面孔: 超脱于权力。这个“超脱”不是妄求权力的飞地、实际上回避权力,而是指超越单一的政治权力,“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全球主义’或‘世界主义’”,“强调世界历史发展中不同文明互动的关系,强调不同种族、文明之间的所谓‘跨文化空间’或‘跨文化公共空间’的发展动力,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分界不仅仅是相互对立与排斥的过程,同时也是超越界限、互通有无、互渗融会的过程,强调‘文化间性’的思维模式”。
然而,论者彼时谈及全球主义和世界主义,只是借鉴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和协商伦理,初步提出一种展望,至于这两种“主义”的实质内涵和可行性究竟是什么,尚需要我们继续探索: “超越民族-国家框架”是对民族国家的激进简单的解构吗? 抑或能由哲学的主体间性构想发展出一种文化间性? 上文提到的混杂性和共谋论也可以纳入这个范围吗? 全球主义和世界主义具备可操作性吗? 抑或仅仅是空想?
近两年论者暂停推进跨文化形象学的三组课题的研究,开始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试图从解构跨文化形象学的理论前提入手,探索研究的突破口。在跨文化形象学之外,亦有其他学者———有些人虽然没有顶着“后殖民主义”的头衔———以自己的方式在处理“中国文化自觉”的大问题,例如陈小眉的《西方主义》( 霍米·巴巴式的混杂性和异质性的研究) ,还有葛兆光、汪晖等人的研究,都在此方向上做出了可贵的努力。或许在解构哲学澄清二元结构之后,我们便可以承认和搁置这一颠扑不破的逻辑,转向实用主义的研究。后殖民主义始于拯救非西方主体,却终结于证成西方中心论。“只有经由将认同对象的多元转移,以及建立其不同于殖民主义的另类参考架构,我们才有可能摆脱对于西方极其顽固的妒恨。”
也就是葛兆光所说的: “从晚明到五四乃至 20 世纪 80 年代新启蒙都是以西方为参照的‘一面镜子’的时代,那么,现在我们应该“菱花前后照”,不仅照见正面,也看看后身———进入‘多面镜子’的时代。”
并且这种多元参考不能像“世界的中国形象”那样被抽象纳入二元结构。
以我为主,多元参照,这就是目前渐为“显学”的东亚区域研究的方法。葛兆光从细部入手,通过大量扎实丰富史料来考察东亚-中国的思想史,并且对文化整体论始终抱持谨慎的批判态度。
叶隽在《问题之繁和方法之难》一文中,也指出东方和西方内部都有更复杂的多元异质性,他直率地批评了“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丛书”乏善可陈,建议不如“以良好的问题意识为着眼点,选择可操作的研究范围,进行打点式的个案研究”,这也与葛兆光的路数不谋而合。当然,没有任何一种研究方式是完美的,这种历史研究或许在理论性和体系性上稍显薄弱,史料史论史观总是需要艰难的平衡。区域研究或具体的历史研究,或许有益于回答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但除非你不追究理论前提,否则观念与方法的困境同样会出现。王晓平在《“以中国形象为方法”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分析或许是阐释中国现代性文化主体的新方法。这种思路是否可行,目前还没有实证的研究可供检验。
问题已经渐渐明朗,但解决问题的出路与方法依旧朦胧。如今,跨文化形象学的最后一组课题———中国的自我想象———仍未展开,这似乎已成为一个哈姆雷特式的延宕。显然,问题出在方法上。如果西方中心论是错的,另一条道路在哪里? 如果西方中心论是对的,我们还能否在这一框架下继续建构非西方的文化主体? 李勇在《现代中国的自我想象———跨文化形象学的终极问题》中初步触及了中国自我想象的一些问题。他认为,中国的自我想象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话语的影响,但本质上这不能被视为一种简单的自我东方化。首先,西方的中国形象和中国的自我想象在时间上有差距: 西方对中国哲人王式的清平盛世或者田园牧歌的想象,都聚焦于古代中国,而处于现代转型焦虑中的中国人对这一类话语并无兴趣。其次,两类话语在性质上也有所不同: 西方的中国形象归根结蒂是“为西方的”,而中国同样也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乃至像论者所批评的那种“有主体而无思想”的民族情绪,中国的自我想象是扎根在中国的现实和历史传统之中的,是在此基础上对西方话语有选择的接受、重塑和改写。
难题也正出在这里。中国寻求现代性一直以民族振兴为核心,其主体意识过于强烈,中国文化本位意识和现代性之间始终存在矛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幽灵始终飘荡在各种现代性设计方案中。那么,我们可以更加大胆一些,去解构民族国家,或至少承认一个边缘模糊、内部多元的“中国”吗? 众所周知,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成果,也是现代进程的基本单位。与非洲、印度这些并无国家意识、接受从天而降的政治边界的国家不同,中国历来的大一统意识和天下观,使得我们轻易地将其转换为现代民族国家,甚至掩盖了内部的复杂异质性。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现代性之路也要先确立一个同质、完整的民族国家,再沿着西方的步履前进? 后发现代性国家是否可以践行复数的现代性? 譬如,我们能否以后现代的方式实践现代性? 即,以解构民族国家的方式实现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发展? 葛兆光的研究已经在暗示“中国”边缘的模糊和内部的复杂性。
这意味着更深入也更敏感的问题。思想起于疑问,终于更深的疑问。什么才是学术的使命? 最基本的一点是保持心灵的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