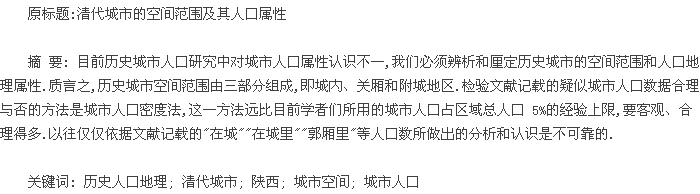
一、问题的提出
历史城市人口问题研究,是中国人口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亦是我们了解和认识中国历史时期城市化率和判断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可或缺的依据.然而,由于历史时期的人口调查、登记、统计缺乏城市与乡村人口的划分标准和统计口径,这就使得我们对历史时期城市人口问题的认识一直是"雾里看花".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 1953 年中国实行城乡人口分类调查、统计之前,中国城市人口数量、规模简直就是一笔糊涂账.
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历史时期城市人口规模问题的研究,都是一种复原、估计、推测所得出的认识,期间的看法也难得一致.以近代中国的城市化率来看,学者估计高者可达 34%,而低者为 28. 1%[1]267.对同一研究客体,研究者所得出的认识差距如此之大,恐怕不仅仅是历史资料匮乏、研究方法与手段"滞后"所能解释得通的,对研究客体认识的差异,可能是根本原因.在清代城市人口研究中,美籍学者施坚雅的研究成果最为着名,在他 1977 年发表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中,施坚雅以四川盆地的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晚清帝国的城市等级体系和人口规模序列,并以此估算出两个标准时点 1843 年和 1893 年的城市人口基本规模.然而,他的研究成果却受到广泛质疑,对近代中国人口史颇有研究的姜涛就认为,施氏的研究太过于"理论化"而有违中国城市人口发展的基本史实[2]141.在明清城市人口研究中进行过系统且卓有成效研究的着名学者曹树基教授,更是从资料来源、研究方法等方面怀疑施坚雅研究的"合理性"①.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一些学者开始另起炉灶,从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实际出发,采用区域分析方法,通过个案研究对中国古代城市进行细致刻划.如许檀对明清山东城市人口的研究、曹树基对明清时期中国城市人口问题的研究以及姜涛对近代中国城市人口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成就斐然.然而,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迄今为止,中国历史时期城市人口问题研究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甚至可以说我们还没有超越施坚雅的研究水平.仔细梳理和审视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会发现,学术界在对历史时期城市人口研究中,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如同我们对古代城市的认识一样是如此的"熟悉"而又"陌生",比如古代城市的空间范围,古代城市的人口构成、性质等问题的认识就存在很大的不同,甚至是"质"的差异.因此,辨析和厘清历史城市人口的基本属性,就成为中国古代城市人口问题研究能否进一步深化或取得突破的基础和关键.需要说明的是,按照学术界通常的看法,中国古代县及其以上的行政中心城镇均可视作为城市.其中又可分为普通县治城市和省、府附郭县城两种层次.由于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受到行政等级的强烈影响,因此对后一类县治城市人口属性的探讨,在行文中将会视具体情况予以特别说明.而对一些在人口数量、占地规模、商业活动都堪比县城或府城的市镇,本文暂不涉及.基于中国古代城市"质"的同一性,本文主要以清代陕西县治城市为分析样本,对古代城市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作一探讨.不当之处,尚祈当世方家予以指正.
二、文献表述的城市空间形式
城市空间范围问题,是一个长期被人们忽视的问题.中国在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人口普查中,由于没有考虑城市空间范围属性,导致随着人口统计口径、人口分类标准的不同而造成了统计意义上的城镇人口忽高忽低的变动[3]288 -290.客观上来说,无论是按照人口规模抑或是人口的经济特征来进行城市人口的统计,都必须考虑人口的地理属性,因为任何统计口径的人口规模,都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口规模.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1990 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才正式将城市范围作为城镇人口统计的基础和标准,因而这一次的城市人口普查,被学术界称之为"具有较强的科学性"[4]107.古今同理.但对于古代城市而言,由于缺乏独立的城市行政建制①和城乡人口分类标准,使得城市人口统计范围极为模糊,因而也更富有弹性,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城墙内的城市"和"城墙外的城市"的讨论和争论即是明证.学者们对历史时期中国城镇人口数量、规模乃至城市化率的研究、估测之所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原因固然不一,但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城市人口统计地理口径的不同所致.如一些学者在研究古代城市人口时,只是将城内人口和关厢人口作为城市人口,而将附城人口排斥在外,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城市人口不仅仅包括城内和关厢人口,还应该包括附城人口.在城乡区分中,一些学者之所以不认同或不同意另一些学者以"街、坊、巷"作为区分城市人口与乡村人口的依据,推测其原因可能是"街、巷、坊"并不是古代城市的专有地理属性.地理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城市有兴废而地名却具有继承性和稳定性,因此以"街、坊、巷"为通名的聚落也就很难单纯从字面来确定其性质.事实上,地方志中记载的以"街、坊、巷"为通名的聚落很多并不是城镇而是乡村.如民国《乾县新志》记载乾县各乡村堡名称中,就有桲落坊、薛梅坊、罍支坊、永生坊、四里坊、后街、前街、东街、西街等村落.这些以"坊""街"为通名的村落,其距离县城近者有 15 里,远者在 50 里[5]卷2《疆土志》.很显然这些聚落都属于乡村区域.类似乾县这种情形的很多,如户县、蓝田、澄城等均是如此.另一方面,一些看似为乡村的聚落其地理属性却属于城市范畴,如光绪《渭南县志》记载县城内有仓后堡、南家堡[6]卷2《舆地志》,《礼泉县志》亦记载城内有南堡子、北堡子等[7]卷4《建置志》.因此,对古代城市范围、内涵认识的模糊与不确定,必然导致城市人口统计中地理尺度的不一致,由此所得出的认识自然缺乏可比性,也就难免形成各说各话,甚至相互怀疑、否定的混乱局面.从逻辑角度来说,对城市空间范围的捉摸不定,必然会出现两种偏差,一种是将城市范围划的过大,使过多的乡村人口被纳入到城市人口统计范畴之中,形成"虚假城市化"现象;二是城市范围划的过小,又不可避免的将本属于城市范畴的人口被排除在城市人口考察范围之外,形成研究结果的"失真"或"失实",而于历史事实不符.因此,古代城市空间范围的确定不但是理论认识问题,也是现实观察问题.
城市空间范围问题,实质上就是城乡界线划分的问题.而城乡界线,今人如同古人一样对此概念是显得如此的清晰而又模糊,以致于人人都知道什么是城市,什么是乡村,但要说具体的城乡界线在哪里,恐怕没人能说得清楚,除非人们出于特殊的任务或需求如行政管辖权的归属、地图测绘等,可以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按照设定的标准人为的划定城市与乡村的分界线.而对于古代城市与乡村的划分,我们显然不具备这方面必要的资源与条件.尤其是古代城市"城内田"与"城外市"并存,使得古代城市与乡村既存在天然联系又存在人为"鸿沟",因此要从具体的地理单元中划分出此地属于城彼地属于乡,则是如此的困难.然而城乡边界或是城市地理区域的确定又是如此重要,以致于我们无论是个案研究还是分时期、分类型、分区域探讨城市人口发展的基本规律,都必须明了城市人口的空间范围,舍此我们无法复原城市人口存在的"真实"状态,也无从探讨其发展、演变的规律.事实上,在目前学术界关于古代城市人口研究中,都在遵循一个极为模糊的城市概念---历史文献记载或表述的城市概念.然而,历史文献记载的城市概念及其内涵是极其复杂而多样的,我们究竟遵从哪一种城市概念? 须知古人对此也是表述不一或大相径庭,因此轻信文本或不加分析地利用文献资料记载的人口数据,本身就存在问题,关于这一点后文将有详细阐述,此不赘.
一般而言,作为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其在地域上表现有多重空间形式:既有形式空间,又有功能区域;既有行政管辖范围,又有文化展布区域和感觉区域,等等,不一而足.而随着关注要素的不同,城市空间范围因而也有大有小,有重叠有交叉.但不管是哪一种城市空间范围的界定与划分,客观上都存在核心区与边缘区之分,并且城市特征由核心区向边缘区呈现逐渐弱化趋势,直至某一个区域或边界,城市景观则转化为以乡村景观为主,这个转折线或面即可视为城乡边界线(面).因此,对古代城市不同的空间形式予以辨别、区分,就成为我们进行科学、客观划分古代城市与乡村范畴的基本前提.下面依据清代陕西 79 个县治城市(含附郭县)的文献记载①,对古代城市的几种空间形式给予大致勾勒.
(一) 形式空间.所谓形式空间,是指以某一组或某一类地理事物为界标,界标以内属于城市范畴,界标以外属于乡村区域.中国古代城市与乡村最明显的分野就是城墙,尽管城墙不是城市与乡村唯一的标志,但却是最初和最清晰的分界线.从城市诞生之初,城墙就成为城市与乡村的天然"人为"鸿沟.虽然城墙之内未必都是城市景观,城墙之外也未必就一定是乡村,但从古到今,城墙以内是城市的核心部分却从未发生过改变.地方志对此记载也相当详细和清楚.按地方志的编排格式,一般在卷首或第一部分大都是县域形势图和城池衙署图,而在建置或地理卷目下则往往将城池修筑的时间、周长、形状乃至城墙的长、宽、高、建筑材质逐一描述."城内""城外"或"城内街巷""城外关厢"是方志关于城市平面布局描述的一般顺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城墙还成为城乡的区域分界线.如佛坪厅,光绪《佛坪厅乡土志》就记载厅境四里与厅城的关系是:"兴隆里,西连城垣";"升兴里,东接城垣";"永兴里,北达城垣";"高升里,南通城墙"[8]《地理》.很显然,城墙成为佛坪厅厅城与乡村的自然分界线.而类似如佛坪厅这样以城墙作为城市与乡村分界标志的,在陕西各地亦复不少,如府谷、扶风、乾州、麟游、旬阳等即是.而今天我们对古代城市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延续了传统的城市概念,如学术界所使用的"城市形态"概念②,其内涵是指由城墙所界定的城市轮廓形态,亦即城市的外部形态.只是以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是讨论中国古代城市外部形态的"规范"与"不规范"③,并没有考虑其与古代城市地域范围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 礼制空间.中国古代城市基本上都是王朝控制地方的据点,城市不但承载着物质力量的控制功能,而且还承载着超越性的精神力量控制功能.普遍建置于城墙内外的各种封建礼制性建筑,如先农坛、历坛、社稷坛、风云雷神山川坛、城隍庙等,就是封建王朝以"文治教化"控制地域社会的外在表征.而这些礼制性建筑不但从物质方面丰富了古代城市的内涵,也从精神层面上界定了古代城市的文化区域.从清代陕西 79 县的近乎 200 种方志记载的这些坛庙的相对位置来看,除个别县礼制建筑集中分布于城内或距离县治大于 3 里(清里)外,绝大部分县城的礼制性建筑都在距离县治 3 里范围之内.如果将这种礼制建筑所代表的王权空间视作一个均质的平面,那么我们就可以以县治为中心,以 3 里为半径划一个圆形区域,这个区域即可被视作为县治城市的礼制空间范围.应该指出的是,这一城市范围的划定仅是依据处于内陆的陕西县城而得出的,其他地区尤其是东部沿海城市是否符合此格局,尚需更多不同区域的数据支持.
(三) 机能空间.或称之为功能空间,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功能空间,是指城市在物质和精神方面所控制和辐射的地域范围;而狭义的功能空间,则是指设置于城市的行政、经济、文化等管理机构及其物质要素所展布的空间范围.本文所论述的县治城市的功能空间仅是指狭义的功能空间.相对于形式空间而言,功能空间既可以是封闭的、连续的地理单元组合体,亦可以是间断的、跳跃式的不相连属的地理单元混合体.从原则上来说,县城是县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控制、辐射乡村是县城的基本功能,亦是其主要的功能.但由于特殊行业、特定区位或重要的交通节点控制的需要,使得原本设置于县城的行政、经济等管理机构不得不逸出县城,从而在县治城市之外形成了次县级行政区域,如巡检司、河泊所、厘金局、县丞所在地等功能区域.这种行政机构的外设,无疑扩大了县城的功能空间范围.但很显然,这些区域与县城在空间上大多是分离的,尽管其行政机构乃至公役人员是属于王朝行政系统的组成部分,但由于空间上的不连续性,已不符合城市人口的基本特性---地理聚集性,其人口自然不能当作城居人口来处理.事实上地方志的编纂者往往将这类区域单列,或予以特别强调,以表明该区域既与县城有别亦与乡村不同.如位于大荔县城西 25 里的羌白镇,由于商品经济发达,"皮货作坊荟萃于斯,繁富亚于县城",因而"县丞公署在焉".作为对比,该志作者还特别补充和强调说县域内其他各镇,是既无官府又无巨商[9]卷4《土地志》,表明羌白镇仅次于县城的政治经济地位.在大荔县保甲编制中,羌白镇也因此被编为第二保,"其编次城内为第一保,羌白镇有县丞分驻为第二保,余则自东北乡刘官营起第三保,由是而南而西而北终于小坡底第四十二保,秩然皆有次序,于是纲举目张焉"[10]卷4《土地志》.很显然,这种行政安排是有意为之.
(四) 行政管辖区域.从原则上说,中国历史上的行政建置仅止于县制级的,县以下的地域行政单元或行政管理机构则并未纳入到正式的行政管理等级序列中,因而其地域单元、机构设置、人员构成等便因地而异,不能一概而论.清代陕西县以下的行政单元,或称之为准行政单位为乡、里、甲,但亦有变异如操、所、铺、堡、镇、屯、村、寨、坝、地方等等,名称不一,但都是将县域进行政治地理分解,以达到或实施从县衙到农户门对门的行政管理.县治城镇虽然处于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但其本质上仍然是县域内行政单元的组成部分,与县域内的其他乡里区划单位等同,或直接就是县以下乡里行政区划的一部分.从清代陕西地方志记载的县城所属地域行政单元来看,常常是以"在城乡""在城里""在城镇""郭下里""郭厢里"等字样与其他区域相区别.虽然有如西乡县丰富里---其所管辖区域正好为县城内及四关[11]《地理》、宁羌州本城南北二牌所辖区域与城内及四关吻合[12]《地理》以及佛坪厅厅城为单列的行政区划单元外[13]《地理》,其他各地大部分情况下县城与县城所属的行政区域并不等同,文献中所谓的"在城里""在城乡""郭下里""郭厢里"等县级以下行政单元,不但包含县城,而且包括有与县城毗连的广大乡村区域.如兴平县,"附城者为在郭里",所属村堡有33 个[14]卷1《地理》;岐山县,"附郭曰在城乡",统村20[15]卷2《建置志》.尽管县治城镇所在的行政区域包含县城以外的乡村区域,但从行政属性的统一、同一角度看,我们完全可将之视作县城的行政空间范围.
(五) 感觉区域.或称之为习惯区域,这是一种存在于社会大众意识里边的一种约定俗成城乡概念.它是如此的清晰与模糊,说其清晰,是因为在人们的心里,"城里"和"乡下"的概念是截然分明,以至于人们不需要经过任何分析、辨别即可判明"此"为城,"彼"为乡.说其模糊,是指这种存在于人们心里的城乡地图,相互之间的界线是如此的不明确,以至于从文本角度很难对其进行地理属性的划分.文献中常见的表述格式是"县城或本城"以及东、西、南、北四乡,如道光《安定县志》卷 4《户口》和嘉庆《扶风县志》卷 4《赋役》在着录县域人口时均是以"县城""东、南、西、北"四乡分别记载.很显然,在县志作者心目中,"县城"及"东、西、南、北"四乡概念及其地理内涵是如此的确定与确切,以至于没必要指明县城范围及乡域四至.直到清末民初的《砖坪县志》仍然遵循这种约定俗成的城乡概念,该志记载的"县城"与东、南、西、北四乡的交界均为"城关"[16]卷1《地理》.虽然约定俗成的城乡界线是如此的模糊,但各自的内涵却是相当清楚的,如乾隆《同官县志》记载该县的地理情况是:"印台山,在县治正西,与虎头、济阳二山南北相接.按三山皆旧城所附,自截筑新城(指康熙时城池内缩),山乃在城外矣.城民大半居三山之上,其城下居者特十之二三耳"[17]卷1《舆地志》.
而乾隆《合阳县志》先说"四郭俱无门大小不可志也",接着又相当清楚地指出了四郭的内涵:"东郭有奕应侯庙,在旧迎春场,距城约一里……南郭有文昌祠距城里……西郭有真武庙,邑范明经堤记,北郭有东岳庙……"[18]卷1《建置第二》.而类似如同官、合阳的城乡认识及区域划分,在清代陕西大部分县都存在,如户县、朝邑、淳化、麟游、陇州、甘泉、清涧等县即是.尽管这种城乡概念及区域分野是如此的模糊而难于界定,但从认识论角度来看,这种存在于民俗社会中的城乡分野仍然为我们认识古代的城市与乡村提供了参照系.
除以上空间形式外,县治城市还存在诸如文化空间、宗教空间、经济区域等等,不一而足.对于城市人口问题而言,上文所述的形式空间、礼制空间、机能空间、行政管辖范围以及习惯区域等,应该说,都在某种程度上囊括了我们所要研究的地理对象的大部或全部,不同点在于其对城市范围的界定有大有小,城乡边界的划分有清晰有模糊而已.
从理论上来说,以城墙为界标的形式空间是如此的清晰、实用,以至于从古到今人们会有意无意的用这一标志来区分城市与乡村.但其缺陷也是极为明显的: (1) "城内田与城外市"并存的格局,使得单纯的以城墙为标志来划分城市与乡村,并不能反映中国古代城市的真实形态,尤其是县城的经济功能难于得到体现.(2) 古代城市所承载的政治、经济控制功能,使得城市景观体现为以诸色官署、公廨、营房及官员、士绅、衙吏住宅与园圃为主,尤其是当城市的政治功能或军事功能予以强化时,城池内的建置设施主要就成为官署和军事设施,普通商民不得不居住于城外.如此以来计算城墙之内的人口显然不能代表城市人口的全部.
如,处于陕南秦巴山腹地的留坝厅,在道光时期其城池的平面布局及功能分区是"太平山居其半,文武官廨居其半,兵房又居其半",以致于"卒鲜隙地以处民,故商旅皆居南城外焉"[19]卷1《厅城图》.关中平原的白水县,县志记载明清时期县城居民主要分布在县城的东北郭[20]卷4《艺文记》.而处于陕北黄土高原腹地的葭县,清代调查本城 142 户,男女大小 621 人,南关 271 户,男女大小 1 121 人[21]《户口》,县城近乎 2/3 的人口居住在城外关厢地区.而类似如白水、葭县县城人口的地域分布格局,在陕西其他县情况都大致相似,如安定、保安、澄城、洵阳等县即是.(3) 城池一经设定、建筑,除非遇到特殊情况需要增、扩、展筑外,一般情况下,城墙的形态、走向、周长基本不变.而城居人口则是一个活跃的群体,视经济发展与城市行政等级的变动而变动.而在一个相对固定不变的城池范围内,人口容量有一个极限值,当人口增加到超过城池范围容纳极限时,多出的人口便自然而然逸出城外,历史上泾阳、三原、富平等县城城池的增、扩建以及关城的修筑即为明证.
(4) 唐宋以来,随着"坊市制"被打破,城墙愈来愈不成为城乡"固有"的分界标志,无论从行政区划还是经济、文化、人口等特征来看,均是如此.因此,仅仅局限于城墙所围护的空间范围,显然已不足于涵盖县治城镇的基本特征.而礼制空间虽然从形式到内涵都可以作为古代城市的标准区域,其空间界线也相对是清晰的、确定的.然而,由于按照礼制建筑为标志所划定的城乡分界线,并没有考虑地形、地貌、河流水文乃至交通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其与实际的城乡范围存在一定的出入.不仅如此,我们目前所能利用的资料或依据是方志所记载的人口数据,而方志对乡村聚落的记载往往是仅关注其相对于城池的方位以及彼此之间的远近,缺乏具体的里程数据,即使有里程但乡村聚落的人口数据又极为缺乏.因此,依据礼制建筑所划定的城乡范围,看似完美且合理,但却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资料提取的困难.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办法仅仅依据方位来区分此村属于乡,彼地属于城.习惯区域虽然从文本角度上给出了明确的感觉地图---城乡界线、城乡内涵是如此的泾渭分明,但富于思辨传统的文学描述,使我们很难将城市与乡村界定在具体的地理区域范围内,这遇到了如同礼制空间一样的问题---资料的对应与提取问题.而机能空间虽然并不存在上述二者所遇到的障碍或缺陷,但由于其在空间上的不连续性,违背了城市人口的地理聚集特性,因而不予以考虑.相比较而言,行政管辖范围由于行政区划层次清楚、行政边界相对明确,幅员大体稳定,且有行政中心.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调查、统计,大部分是以地域行政单元为统计单位的,资料对应的一致性以及资料来源的易获得性,使得行政管辖区域成为历史城市人口研究中普遍采用的城市空间形式,然而这也是目前历史城市人口研究中问题最多的方面.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学者不加区分的将城市所属的行政区域的人口数字作为城市人口数字,得出一个看似完美其实很不合理的城市人口等级序列.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县城所属的行政区域在大部分情况下所覆盖的范围不限于县城,还包括县城周边一定地理范围内的乡村区域,如道光《紫阳县志》卷 1 记载:"本城东至旧县梓潼阁抵中北界,西至西门河抵大北界,南抵汉江,北至娘娘殿抵中北界,计东西五里,南北五里".紫阳地处秦巴山腹地,史书称其为"蕞尔小邑",山城城周仅 2 里,且无关城.仅从城池围长来看,是清代陕西最小的县之一.然而县志记载的本城范围却远远超过县城城池面积,即使将附城村落计入,其城市范围也不可能达到"东西五里,南北五里".同样是山城的镇安县,县城所在的中一区面积更大,光绪三十四年刊印的《镇安县乡土志》卷下《地理》记载,当时全县分为 9区,其中中一区为"本境治城及附城村庄向归城堡者为中一区",而同卷记载中一区包括"本境治城,东关、西关,海棠山、王家坪、槐树坪、青山沟、次沟、旧司里、菜园子"等,其"东界东一区草庙寨堡鲍家沟口,南界南一区表德铺,西界西一区铁洞沟,北界北一区枣园子",全区周约 105 里.如此一来,一些学者将该乡土志卷 5《户口》记载的县中区人口 547 户 2 459 人作为县城人口加以利用、分析,显然是不适当的.再如定远厅,光绪《定远厅志》记载"其在附城者曰固县坝三保九甲 138 牌,见共男妇 7 596 丁口"[22]卷4《地理志》,尽管学者对本文献中的"丁口"持保留意见,但将固县坝人口作为定远厅城人口则是明显错误的.定远为"荒远僻邑",厅城所在的固县坝,按地方行政区划为定远厅 24 地之一,"嘉庆七年析西乡县 24 地为定远厅,属汉中府,建固县坝平溪山之麓"[22]卷1《地理志》.查光绪《定远厅志》卷 4《地理志·保甲》寨堡条下记载"附城寨有七,曰七星寨、青龙寨、风青寨、保全寨、双龙寨、红岩寨、黄龙寨"等,从寨堡距城里数来看,其甚至有距城120-150 里之遥.因此,此处的固县坝很显然是包括厅城在内的"地方"概念,类似于乡里的行政单元.如果我们将此人口作为定远厅城人口数据,如何从理论上解释 70 年后的 1949 年镇巴县(清定远厅)调查的县城内南关、牌坊、新城三乡共 633 户 2 397 人.即使是 1954 年的调查,镇巴县城关镇也仅 724 户 3 668 人,尚不及清光绪时期固县坝人口数的一半.与此类似,陕北的靖边县城镇靖城,光绪二十五年调查"计烟户 776,男女大小丁口4 564,外庙宇 14 所,僧人 3 名"[23]卷1《户口志第三》.如果不加分析的将此镇靖城人口数据作为县城人口数,不但在理论上解释不通,而且与历史事实不符.按清代靖边县的行政区划是"查县属向无里甲,旧分五堡一镇,曰镇靖,曰龙州,曰镇罗,曰新城,曰宁塞,曰宁条梁镇"[23]卷1《户口志第三》.其中镇靖堡,其范围是"东界龙州,北跨五胜鄂套两蒙地,正西正南界镇罗,惟西南错互龙罗两堡,东南又掺入安塞界……计东西广 70 里,南北袤120 里"[23]卷1《图》.因此,此处的镇靖堡是靖边县五堡一镇行政区划单位之一,其人口自然也就是镇靖堡行政区域人口.类似上述看似为城镇人口实为区域人口的记载在文献中最为常见.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我们引用数据相对清晰的民国资料来说明.民国《乾县新志》记载,时全县分为 1 镇 9 乡,各乡镇所辖面积大小不等,其中"在城镇"面积为 626. 7 方里,其面积仅仅小于薛王乡(760. 5 方里)、阳庄乡(691. 3 方里)居于10 乡镇第 3 位,而远远大于关头乡(343. 2 方里) 、注泔乡(346. 5 方里) 和临平乡(345. 7 方里) .其他如洛川、户县、中部(今黄陵)等县均与此类似①.
三、判别"疑似"城市人口数的基本方法---人口密度法
上文的分析表明,目前学者所应用的历史城市人口资料,多是城市所在行政区域的人口资料,其显然已含有过多的乡村人口.而如果我们不加分析的利用这种看似城市人口资料,实为城镇行政区的人口资料,必然会导致难于解释的观点.此处仅以陕南石泉县为例,这也是学者认定文献记载的人口为县城人口的典型案例.石泉县设县很早,早在魏晋南北朝时石泉即已置县,此后虽有废、析、并、省的变迁,但到明清时期石泉县制基本趋于稳定.明末清初乃至清康熙雍正年间,石泉县如同陕南其他州县一样人口还是很少的,随着乾隆至道光时期陕南大规模的移民开发,石泉县域经济也获得到了快速发展,到道光后期已出现人满为患的地步,其区域人口也达到了清代的高峰值.纂修于道光八年的《石泉县志》记载:"在城户 1 155 户,男 3 872名,女 1 943 口."这即是学者所认定的石泉县城人口数据.由于道光年间陕南县治城镇人口只找到此一例,无法进行横向比较.但我们可以通过石泉县本身来加以考察.学术界已有的研究表明,嘉庆至道光时期是陕南地域社会极为动荡的时期[24]57 -70,陕南民变、兵变多发,无以为生的流民被迫铤而走险,"山贼窃发","厢匪""芋贼""蝈匪"成为地方志作者关注的重要内容.处于如此动荡环境的陕南地方社会必然会采取各种办法以寻求自保,最常见的做法有两种,一是县城周边的人口迁入城内,以借助城墙保护安全,这即是所谓的"小乱进城,大乱下乡";二是修辑城池,包括加固、补修、增建包括关城在内的城墙,以围护商民安全.从已有文献记载来看,嘉庆、道光时期在陕南修建城池、堡寨等活动频繁见于白河、洵阳、安康等很多县.处于秦巴山地中部的石泉县虽然在乾隆、嘉庆、道光时期亦有修城活动,但基本上是在原城墙的基础上补修或重修,由城墙所围护的城池范围并未见变动.这使得我们有理由认为,文献所记载的"在城户"全部居于城墙以内---即由城墙所围护的空间范围内.石泉县城筑于明成化至正德年间,城池"依山阻水",初始"城周三里",到清道光年间已不足 3 里,"城围二里二百五十步"[25]卷1《建置志第二》,约为 2. 7 里.据此,我们按方周面积计算办法 S = c2L2/64 来计算石泉县城面积,其中 S 为面积,单位为 km2,L 为周长,c 为转换系数.计算结果为清道光时期石泉县城面积约为 0. 151 km2,其相应的人口密度为 38 510 人/ km2,这一人口密度几乎与清宣统年间京师北京城外城前三门外人口密度相当[26]335,远超过清末陕西省府---西安城约 10 000 人/ km2的人口密度[27]412.按古代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城市等级愈高,人口愈多,人口密度相应也大.反之,则相反.因此,作为一个山区县城,人口密度如此之高,显然不符合逻辑.即使我们考虑到城池面积因形状、具体走向的不规则而产生的误差,但其密度之高仍然令人难于置信.唯一的解释是,我们用以计算的城居人口数据有问题.其实,只要我们仔细阅读文献,而不被古人的文字游戏所迷惑,便不会出现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此,我们仍然回到道光《石泉县志》卷 2《户口志第五》,其完整的记述是:"在城户 1 155 户,男 3 872 名,女1 943口,保长二名,乡约四名,保正三名,编为 7 甲,甲各有长,为石泉里,绘溪附焉."就在同卷同条下又云:
"绘溪户453 户,男1 808 名,女1 351 口,保长二名,乡约二名,保正一名,编为4 甲,甲各有长,在县城之西."这里,在城人口与绘溪人口一起共同构成道光石泉县八里之一的石泉里,成为清代石泉县承担赋役的基本单位.而按清代陕南地方习惯,这种绘溪是"地方"概念,因此,在城,亦应是"在城地方".换句话说,所谓"在城"是一个包括县城在内的一个行政区划单元,即"在城里"或"在城镇",这类似于后世"城关区""城关镇"等行政区划单位.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在经过 120 余年的发展,到 1949 年石泉县才仅有 4000余人[28]339.
石泉县的事例也启发我们,应用城市人口平均密度---在此姑且称之为人口密度法,就很容易判别文献记载的"疑似"城市人口数据的合理与否,这远比学者们用经验设定的城市人口占区域总人口 5% 的上限要客观、合理的多.以学者们所认定的陕西扶风、定远、靖边县城人口数为例,用人口密度法对之进行检验.扶风县,光绪《扶风县乡土志》卷 2 记载在城里户 977,口共计 4 302,有学者将此人口数据与嘉庆《扶风县志》卷 4记载的县城人口为 487 户 2 055 口相比较,认为"户数与口数均增加了 1 倍左右",确实,在 88 年间人口增长率虽然有点高,但仍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如果从县城人口密度来看,情况就大为不同,嘉庆时扶风县城人口密度与清代陕西县城的一般人口密度相当,而光绪三十二年扶风县城的人口密度高达 11 174 人/km2,超过省城的人口密度.如果认为光绪时扶风县城的人口密度是合理的,那么就意味着扶风县城的经济是超过省城西安,最低也应该与西安相埒.然而史实是,从嘉庆到光绪年间,扶风县由于地理位置偏离干道,其县域经济乃至商业经济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正如乡土志作者所言:"扶风虽秦蜀之冲,而非四达之要.
故商务不集,前时惟本土牲畜,县人自相贸易."[29]卷2《商务篇第十三》况且在此期间,扶风县也经历了战乱与自然灾害,其县域总人口光绪年间比嘉庆年间大幅减少,嘉庆二十三年全县 21 160 户,153 499 口,到光绪三十二年时全县 20 870 户,103 816 口,人口减少了约 1/3.按一般规律,县城人口亦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减少.已有的研究也表明,在缺乏商业和工业因素推动的条件下,传统城市的人口规模清末不会超过清中期的水平,更不会大幅度超过清中期的人口规模.合理的解释是,光绪年间的人口数是包括县城在内的准行政区"在城里"的人口数,而不完全是县城人口数.事实上,乡土志对"在城里"有详细的描述,光绪三十二年《扶风县乡土志》卷1 是这样解释和界定"在城里":"城在在城里,周回四里";"在城里,县城居之.东界信义里,南界大通里,西北界黄甫里,凡 42 村."与嘉庆志对照,扶风县从嘉庆到光绪年间其县域行政区划没有变化.如此看来,问题就出在嘉庆志记载的是县城人口,而光绪乡土志记载的是县城所属的行政区域人口数,二者不是一回事.而且嘉庆志对县城人口的统计表述是"嘉庆二十二年奉文编查保甲,查明县城一保五甲四十九牌共土着四百五户,男妇大小一千七百四十七口,客八十二户,男妇大小三百八口",其余依次记载了全县 29 里的人口数,而光绪志只记载了 29 里人口数.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文献,就不会产生这样的误判.而对于光绪《定远厅志》卷 4 记载的"其在附城者曰固县坝三保九甲一百三十八牌见共男妇七千五百九十六丁口",学者对此数据采取了远比其他资料更为谨慎的态度,只是怀疑它是"县城附近"的人口还是城市人口? 事实上,略一检验,便可明确否定其不是城市人口.定远为荒远僻邑,厅城周长仅为 472 丈,面积约为 0. 143 km2,每平方公里分布人口高达 5. 3 万人,如此离谱的人口密度,谁敢相信数据的真实性? 再如陕北的靖边县,光绪《靖边县志稿》卷 1 记载的镇靖城人口为"776 户,男女大小丁 4 546 口",而镇靖城的规模只有 4 里 3 分,换算成面积为0. 385 km2,其人口密度接近每平方公里1. 2 万人.如果真如此,我们很难解释该志作者、光绪二十年靖边县知县丁锡奎因镇靖居民仅有三四十家,城阔难守,请"截去一半"[23]卷1《建置志》.因此,此处的镇靖人口实为镇靖堡人口,而镇靖堡是光绪靖边县五堡一镇行政区划单位之一,上文对此有分析,此从略.从这个角度我们亦能理解何炳棣所说的,文献中有关城市人口数据大多是一个区域性的人口数字的含义.因此,对于文献记载的疑似城市人口如"在城""在城镇""在城里"等人口数据,应格外小心,谨慎分析.断不可不加分析的将之当作"真实"的城市人口数字加以应用.
四、清代城市空间范围的厘定
历史城市人口数据与城镇行政区域人口数据的混淆与偏差,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历史城市空间范围的模糊与不一.因此,如果我们仍然按照文献记载的城市概念来进行城市人口研究,必然原地踏步,不可能出现实质性突破.为此,我们借助现代地理学的城市概念,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对古代城市的地域空间范围作如下界定:古代城市的地理空间构成大致上可分为三个部分,即城内、关厢和附城地区.城内,是指由城墙所围护的区域;关厢,是指城门外的附近地区.所谓附近地区,是指与城墙紧相毗连的地区,与城内仅一墙之隔,实是城内区域向城外的延伸部分,其以民居和商铺为其显着的景观特征.而附城地区,则更是在关厢以外的环城区域.这一区域虽然因城市的等级高低、规模大小、人口多寡而幅员不等,但其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 (1) 在地域上与城或关厢紧相毗连并有一定的外缘界限; (2) 在行政上与城市隶属于同一个行政单元; (3) 兼有城市与乡村的景观特征,是城乡的过渡地带.
对古代城市空间范围作如此判断与界定,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1) 城墙及其关城从其出现以来就是县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区域,无论从地理景观、机构设置乃至人口构成,它都与乡村聚落具有明显的差别,如以城墙、城壕为外缘标志的城池范围,以衙署、坛庙、书院、仓库、监狱为主的政治功能区域,以旅店、商铺、茶馆酒楼为主的商业活动区域等.(2) 由城内、关城及附城地区组成的城市区域,业已涵盖或包含有上文所述的古代城市的形式空间、礼制空间、习惯空间和功能空间,在这一区域几乎集中了传统意义上的城居人口.宣统至民国年间的人口调查,被认为是具有现代人口普查意义,其城市人口调查的范围即与上述界定的城市三部分区域一致.现存甘肃省图书馆的宣统年间甘肃人口《地理调查表》,在其涉及的45 个府、州、县、厅治城的人口统计范围即包括治城内、关厢和附城村落.在陕西,民国十五年刊行的《澄城县附志》卷 2《建置志·城镇》中关于县城地理事物记载的顺序是:"治城内外,包括治城内、东关、南关、西关、北关、土城角".《朝邑县乡土志·地理》谓"境内分 14 巡警局",其中"中局在治城内,辖四街两关 21村".民国《户县志》记载的县城人口,按区域可分为城内四街、城外四关以及关外近城地区的人户[30]卷2《乡村第九》,等等.(3) 由城内、关厢和附城地区组成的城市区域,其界线相对清楚,便于利用文献展开相关研究.如关于城墙的长宽高、走向、周长以及关城形态乃至附城村落,地方志记载的信息都相对较为清楚.(4) 由城内、关城、附城组成的城市区域,与现代地理学的城市地理概念较为一致.古代城市的城内地区,可视作现代城市地理中的"建成区";关城地区,与现代城市地理学中的城市过渡地带相当;而附城地区虽然其景观已与乡村地区无二致,但由于其受到来自城市核心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强烈影响,因此,将之视为城市的边缘区域,亦无不可.
应该说明的是,虽然在理论上城市从其产生之时就存在城内、关城与附城地区①,但基于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实际考察,由于受到行政等级、地域经济、军事建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区域城市便因时因地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因此,城市空间结构也难得如我们界定的整齐划一,有的有关城,有的无关城,有的有附城地区,有的无附城地区.更应该引起注意的是,由于地方志作者的认识以及行政区划的影响,一些本应属于城市的区域被排除在城市范围之外,而有些明显不属于城市范围的地方,却被当作城市的一部分.如府谷县,乾隆年间编纂的《府谷县志》就将附城村落划入乡区[31]卷1《里甲》,而乾隆四十二年编修的《户县新志》不但将一些附城村落归入四乡范畴,甚至将本属于县城的礼制性建筑如社稷坛、历坛也一并划入乡区[32]卷1《地理第一》.县志作者的这种习惯性认识,在民国时一些地方志的编纂者仍然存在,如民国《澄城县附志》就将距城里数为零的刘家庄、党家庄、蔡家庄、庐漥、郭家庄、卓子、程庄等村落归属乡里[33]卷1《乡区村镇一览表》.
其它如富平、蓝田、大荔、旬阳、宝鸡、麟游等有类似情况,恕不一一列述.与此相反的是,一些地方无论从城市空间的不可分割性还是城市人口的地理聚集特性来看,都不应该属于城市范畴,然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些地方或地域却成为州、县、厅城的地域组成部分,如朝邑的柳村、孝义厅的石嘴子街、中部县的石山村等即是.康熙五十一年纂修的《朝邑县后志》记载:"朝邑城东南五里许曰柳村,柳村邑附郭,人饶于财而尚礼."[34]卷8《艺文》.与此类似,光绪九年编修的《孝义厅志》将与县城有 5 里之遥的石嘴子街作为厅城的一部分①,中部县的石山村亦是距县有 5 里地,但民国《中部县志》却将其作为"县城及关"来对待[35]卷5《户口志》.如果说,朝邑县的柳村,仅就县志本身的陈述我们无法对其属性作出明确的判断,但孝义厅的石嘴子街和中部县的石山村,则明显不属于县治城市范畴.此二县是山区县,自然空间的分割使石嘴子街和石山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地域上与各自的县城相连.只是我们不知道县志作者出于什么原则或处于什么样的观察角度而做出如此归类.用现代地理学的城市"飞地"理论来看,倒是可以解释得通.但即使如此,这些城市"飞地"的人口亦不能作为治城城市人口,这在今天的城市人口统计中依然如此.因此,基于文献记载、表述的种种歧异,本文所界定的城市区域组成仅是理论上的、原则性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充分重视行政区划、习惯认识、功能区位等影响因素,从文本形成的历史情景中去把握或区分古代城市的内涵,任何囫囵吞枣或不加分析的利用文献记载的城市人口资料,都可能导致不可避免的认识性错误.
四、结 语
在历史城市人口研究中,研究者碰到的最大障碍或问题是历史城市人口资料的匮乏,正如曹树基教授在评论施坚雅的研究成果时所说:"历史学家如严格地按照历史学的规范从事研究,断不敢轻易地构造涉及全国城市人口的模型.他们知道,在缺乏实证研究的背景下,奢谈中国城市人口是不明智的."[36]724而我们在怀疑、诘责甚至否定施坚雅研究成果之时,研究者面临的是与施坚雅同样的问题---可供分析的城市人口样本极为有限,用以支撑所谓的"山东城市等级模式"和"陕甘城市等级模式"的样本数量分别为 9(2)②、10,样本数量均不足 10%.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说,我们用于诘责别人的短处,也恰恰是自己的软肋.因此,如何从"区域"人口数据中提取城市人口数,就成为中国历史城市人口研究能否取得突破的基础和关键.而对历史城市空间范围和人口属性问题的廓清和认识,无疑是基本的前提和关键的关键.本文研究表明,历史城市地域空间可由三部分组成,即城内、关厢和附城地区,对于文献记载的疑似城市人口数的检验与判断,用城市人口平均密度法要远比目前学者们所用的城市人口占区域总人口 5% 的经验上限,客观、合理得多.应当指出,本文对历史城市空间范围及人口属性的有关认识和判断,仅是依据处于内陆的陕西县治城市而得出的,其是否符合传统社会条件下城市的一般情况,尚需不同区域尤其是沿边沿江沿海城市的检验和数据支持.
[参 考 文 献]
[1] 胡焕庸,张善余. 中国人口地理:上册[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2] 姜涛. 人口与历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张善余. 中国人口地理[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4] 顾朝林,等. 中国城市地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续俭,田屏轩,范凝续. 民国乾县新志[M]. 民国三十年刊印本.
[6]严书麟,等. 光绪渭南县志[M]. 光绪十八年刊本.
[7]张道藏,等. 民国续修礼泉县志[M]. 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8] 佚名. 光绪佛坪厅乡土志[M]. 光绪三十四年抄本.
[9] 聂雨润,张树木云,李泰. 民国大荔县旧志稿[M]. 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