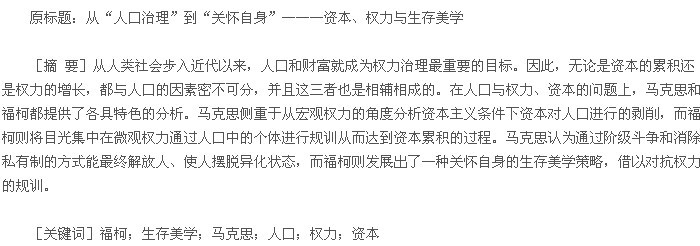
马克思将西方经济的起飞归结为资本积累的过程,福柯则将重点转向人口增长的管理方式。这里的“起飞”(take-off),是福柯引用的马克思关于 18 世纪西方社会的发展描述,首先是资本积累导致了现代西方经济的起飞,然后是新的权力形式的出现导致了现代西方政治的起飞。在阐述“全景敞视主义”问题时,福柯认为,“如果没有一种能够维持和使用大规模人力的生产机构的发展,就不可能解决人员积聚的问题。反之,使日渐增大的人群变得有用的技术也促进了资本积累”。因此,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必须依靠“人口”的支持才能使“起飞”成为可能。正是由于人口的增长引起经济的增长,于是这种增长才可能进一步促进资本转化为权力。因此,经济、人口、权力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三角形的循环促进过程。
一、人口的问题
福柯认为,在 18 世纪以前的“人口”一词主要是针对“人口减少”(depopulation)的现象而被使用。因此,当人们谈及人口(population)一词的时候,通常所指的是为了抗衡人口减少所采取的行动,即“经过严重的灾难,不管是流行病、战争还是食物短缺,经过人口大规模惨绝人寰地迅速死亡的戏剧性时刻之后,在变得荒芜的领土上繁殖人口的运动”。
“Population”一词在法语中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指居住在某一地区的所有人,第二层则是指统计中的同一种类的生物。因此,人口既是统计学的对象,同时也是在统计学的知识范畴内的一个政治实体,即全体人民。人口的概念一经出现,就迅速地成为了君主力量的重要象征之一(领地、人口与财富)。
人口是一种自然现象,但还是作为一种可被影响调控的自然现象。从整体上看,人口可以被视为一种被“欲望”(desir)牵引着的总体。欲望的人由此进入了权力和统治技术的管辖范围内。“人口作为权力技术的关联物建构起来,正是从这里出发,一系列可能的知识的对象领域开始形成。反过来,这些知识又不断勾画出新的对象,使得人口可以自我构建、自我延续、自我维持,作为权力的现代机制的特殊关联物”。
既然出现了人口的概念,紧接而来的就是人口的治理问题,这里就需要谈到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概念。“治理术”通常被认为是由福柯首先在法兰西学院的授课期间提出的概念,这一概念随后又从“英美新福柯主义”(Anglo-Neo Foucauldian)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通常来说,“治理术”可以被理解为“统治者试图生产出最适合统治者政策的公民的方式”,或者是“使主体被统治的有组织的措施(心态、理性和技术)”。
首先,“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对于人口而言,就如同隔离技术对于精神病学、规训技术对于刑罚体系、生命政治对于医学制度而言。福柯通过对 16 世纪法语 gouverner 的字源学研究发现,与古希腊及罗马时期的君主治理城邦所列举的船的隐喻有所不同,人们最初的和最根本的治理(gouverner)目标是人,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然后,“治理术”的概念对于人们如何理解权力也造成了影响。福柯鼓励我们,不要仅仅局限在(自上而下的)等级性特征上来理解权力。权力也体现在规训机构的社会控制形式(比如学校、医院、精神病院等),以及知识的形式当中。权力可以通过生产一定的知识和话语,不仅在微观层面上使得自身积极地内化于社会化的身体之中,而且在宏观层面上引导人口的行为和表现。权力产生出的知识使社会中的个体开始自发自动地管理并规范自身,最终使其对社会的控制变得更加有效。
在福柯那里,治理的科学和人口问题就这样相互联系了起来。“正是通过治理科学的发展,经济的概念被重置于一种不同的、我们今天称为‘经济’(économie)①的现实层面的中心,也正是通过治理科学,人们才有可能界定那些人口所特有的问题。但是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正是由于对人口特有问题的认识,以及我们称为经济的那个现实领域被分离出来,治理的问题才最终得以在统治权的那个现实领域被分离出来,治理的问题才最终得以在统治权的法律框架之外被思考、反思和计划”。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治理所朝向的对象,不是别的,而是组成人口的每个个体的人。治理的目标是有关人口的利益———改进人口状况并促进财富的累积,延长人口生命,以及提高健康水平。但是,人口是需要的主体、欲望(aspiration)的主体,但同时也是政府(gouvernement)手中的对象。因此,治理人口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人口,不如说是为了扩充统治者的力量。一方面,权力对人口进行治理,使生产力持续增长并促进资产的累积;反过来,资本作用于人口的劳动力,通过对人口的治理产生出剩余人口,使统治者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巩固加强。
在福柯将研究重点转向“治理”以及道德领域的相关问题之前,他曾经大量借鉴马克思的概念和论点。福柯认为,18 世纪晚期和 19 世纪早期的资本主义受到社会化影响的标志之一正是身体开始被视为生产力和劳动力。个体不再仅仅是由意识形态进行操控,而是通过身体受到全方面的控制。“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福柯写道,“生物政治是第一重要的,它是生物的、躯体的和身体的。身体,首先是一种生物政治的现实;医学是一种生物政治性的战略”。对马克思和福柯来说,资本主义社会与身体,尤其是作为社会学的身体紧密相连的人口概念,一方面受到权力的管制,另一方面受到资本的操控。
二、从资本到权力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通过购买活劳动进行生产,那么资本本身就转化为对劳动过程、劳动者个人的身体生命过程进行操纵的一种“支配权力”。然而,资本在生产关系中所掌握的是一种总体操控性的权力,这种权力作用于活劳动的人口,并分散渗入到每一个社会性的身体之中。问题是,资本和权力从整体人口到个体身体和生命的支配和调控是如何达到的呢?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引出马克思关于剩余人口的概念。马克思认为,相对过剩人口规律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要人口规律。马克思在继承李嘉图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之上,还从社会学角度对人口过剩理论进行了进一步发掘。他提出,在资本主义模式下,人口的增加从本质上来说完全取决于资本增值的需要,这与先前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受自然规律支配的人口增长理论有所不同。他认为,“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
资本增值的要求会不断地吸入人口加入生产劳动过程,而增加的劳动人口会不断进入和离开生产过程,直到产生出大量的剩余人口,并使得支付劳动力的费用维持在最低限度。“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从属于资本。……过剩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值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在《强迫移民》中,福柯指出,不论过去或是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人口的迁移流动(国际的和本国内地的)通常受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影响和调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导致的结果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人口在这里是财富的基本源泉”,同时人口也是被压迫和剥削的对象。
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来看,相对过剩人口理论认为,过剩人口是资本家进行进一步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同时又按照与社会积累的增进相适应的规模加速了产业后备军的生产”。
然而,资本不仅是一种支配整体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总体性权力”,它还在微观层面上控制着人口中的每一个活劳动力的身体。微观权力不仅能够从外至内对个体进行强制性的管理,还会穿透身体并在个体的身体内部“自动运作”。资本可以衍生出种种微观权力并间接地作用在社会性的身体之上,通过控制和规训参加生产的劳动力达到资本的累积。不论是宏观权力或是微观权力,控制整体性人口和社会性身体的目的都是为了达到资本的不断累积。为此,马克思指出,“资本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oekonom ische Macht)”。
三、从权力到资本
福柯认为,人口的概念可以被视为从中央集权的统治规则转换至一种充满着自由主义气息的“政府治理”的关键枢纽。在 70 年代,福柯更是将人口作为一种政治主体进行了思考和分析,并在 1977 年至1978 年的讲课内容里集中形成了“治理”(governmentality)的内容。他指出,人口正是政府在现代形式下的根本管理对象。通过政治经济学,人口的概念得到开发,再通过安全机器进行组织管理,最终导致了社会由统治者过渡到“政府”状态。在这一点上,福柯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所作的分析有所区分。
《真理与权力》收录了一次福柯接受 Alessandro Fontana 和 Pasquale Pasquino 的采访。在这次谈话里,人口的问题作为连接规训的微观权力(micro-powers of discipline)和各种社会关系的一般管理(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的核心被凸显了出来。谈话者们提出,规训技术并不是依靠自身而存在的,而是必须与人口最为普遍的现象挂靠在一起,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出现在 18 世纪的人口科学普查。实际上,规训权力与两个对象紧密相连:作为由大量的个体组装而成的人口以及它的组成部分,即驯顺的身体(docile bodies)。
从宏观角度看,国家政府通过资本和权力开发规训技术,巩固施加在人口上的主导权力,并为权力所有者用以累积财富。但是权力不仅仅作用于宏观层面,它还主宰着人口之中每个个体的日常行为活动,并通过训练个人进行自觉自发的自我规训以达到更为长久的管制效果。所有一切对于人口生产的规训机制无疑能够为统治阶层带来丰厚的利润,促进资本的进一步累积。
通过对资本积累与微观权力之间的关系的分析,福柯还注意到,“实际上,这两个进程———人员积聚和资本积聚———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一种能够维持和使用大规模人力的生产机构的发展,就不可能解决人员积聚的问题。反之,将日渐增大的人群变得有用的技术也促进了资本积累。在一个不太普遍的层次上,在生产机构、劳动分工和规训技术制定方面的技术性变化维持了一组十分紧密的关系”。现代社会条件下人口的生产和累积过程,也从整体层面体现出资本与权力(尤其是微观权力)在个体身体以及生命层面的持续作用力。而这种资本与权力深入到人口中每一个身体的持续互动,也同样反映出资本生产与人口生产的深层次关联。
因此,资本、人口和权力就内在地作为一个整体相互联系,福柯正是在这样一个整体视角中思考人口治理问题的。从这个角度延伸出去,福柯进而认为,治理、人口和政治经济其实都是一体的运动。福柯认为,“治理、人口、政治经济这三个运动,自从 18 世纪开始构成一个坚实的系列,这个系列直到今天仍然连为一体”。治理的实际施力者并不是统治者,而是无所不在的权力。人口是无数个个体组合而成的总体。政治经济运动与资本密切关联在一起。在社会活动中,这三者并行串联,构成一种相互推动的三角关系。“治理国家实质上作用于人口,治理国家参照和利用经济知识这一工具,它所对应的是由安全配置加以控制的社会”。
谈及人口,其关键意义并不在于人口的绝对数量,而是人口与权力的集合所组成的关系:领土的大小、天然资源、财富以及商业活动等等。福柯在《人口》中分析指出,人口与权力的集合内容越强大,那么国家和统治者则会越有力量。权力对人口做出不懈的管制和调整(福柯在分析中特别介绍了“警察”概念的发展史),使得整个统治者的领土全境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劳作之地(a large industrious town)。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首要特征之一就是为资本所有者不断累积财富,因此,由人口创造出来的巨大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在权力的监督和规训下转为统治者们的新加资本。
应当说,重商主义在欧洲甚至全世界的权力平衡游戏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第一,它要求每个国家都应该尝试拥有尽可能大的人口;第二,整个人口都应当是有生产力的,并且都应该被投入到工作之中;第三,通过权力和资本的游戏,将人口之中的每个劳动力的工资尽可能地压低,以求利益最大化;第四,商品的成本价被压至最低。因此,权力、人口和资本所形成的三角链开始持续运作起来,资本得到进一步累积,政治权力不断被巩固强化,人口愈发成为被严密监控的工具化对象。
四、人的解放与关怀自身
马克思指出了一条能够使得被剥削的、异化的人得到解放的途径,即推翻统治阶级使用权力和资本对个体的压制,使劳动力重归自身,由此消除异化,达到人的解放。福柯则提出了另一种角度的途径,即个体通过关怀自身,消除权力者施加在自身之上的种种禁锢,以求达到自由的超越状态,以一种塑造艺术品的心境建立属于自身的美的生活。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是异化的。劳动作为人的规定描述了人的自由本性,这不仅表现在人(自由的)与动物(不自由的)的区分之中,而且也显现在共产主义者(自由的)和雇佣劳动者(不自由的)的区分之中,因此人是按美的规律来创造他的生活的。自由的、人性的劳动活动是目的自身,但是异化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当中是一种手段。作为活劳动的个体在生产过程中受雇并属于他人,这是一种被雇佣关系,被雇佣即意味着被剥夺、被压迫。总之,人的本性在异化劳动中被改变、遮蔽,这不仅使得人的精神和意识活动异化,还使人的身体异化于人自身。从这个角度出发,消除异化就是到达人之解放的必要阶段。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就是个体对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
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和权力对人的控制不仅是微观和宏观双层面的,也是内外双向的。“统治的权力结构所进行操纵、管理和控制的程度不仅包括个人的意识方面,而且也延伸到了潜意识甚至无意识的领域”。阿尔都塞在《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中谈到,“对人类剥削的结束意味着对劳动阶级剥削的结束。人类的解放意味着劳工阶级的解放以及最重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解放”。因此,马克思主义所谈的人之解放,其首要目标是消除权力和资本压在个体身上的剥削。解放了的、自由的个体应当进行的是自由劳动。在马克思那里,异化劳动所对应的是私有财产和私有制,这必定导致权力和资本对人口以及每个劳动个体的压制和剥削,而共产主义则意味着新生和解放,即自由之人的联合体。
马克思主义美学所追求的首要目标是改造世界,而改造的主体正是人口之中每个个体自身。应当说,每个自由的、解放了的人就是美的实现者,而劳动个体的解放意味着整个社会人口的解放———马克思认为劳动就是人的本性。其后出现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们则将这一思想推的更远,例如马尔库塞就认为,除去物质生产的部分,人还具有文化和心理的部分。人的解放不仅是物质生产性的劳动解放,还应当考虑到个体心灵的解放,这意味着审美的解放、感性的解放。从美学角度来说,一个自由的人就是能够使自身的自然属性充分地人化的人,是能够充分感受并且创造自身的美和美的世界的人。从总体来说,马克思呼吁推翻资本主义的阶级制度,通过否定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肯定人对于自身存在的真正占有。这意味着人必须克服异化,寻求感性的全面解放,从整体层面上消除权力与资本对人的控制和压迫。
福柯选择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他试图将目光回归到古希腊的智慧之中,探索出一条关怀个体自身的自由之路。福柯之所以坚持研究写作《性史》,一个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希望通过梳理各个时代对性的理解———这对人类来说最本能也是最根源的问题,从而为受难于无所不在的知识和权力的禁锢之下的现代人找寻到一条可能得到回归和自由的道路,最终让人们可以“把生存建造成美好的生存”。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福柯的目的正是希望能够帮助人们摆脱无所不在的权力网络对个体的压制和束缚,并且鼓励个体追求生活之中的生存美学。
在福柯的哲学生涯后期,他将自己的研究方向锁定在“致力于研究人把他自身转变成主体的方式”。
将自身转变为主体,意味着使个体摆脱资本和权力的控制,个体因此成为关怀自身的主体。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福柯的美学思想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正是生存美学,而生存美学的中心词则是“关怀自身”(lesouci de soi)。关怀自身意味着个体将自身作为生活的目的,摆脱权力或资本施加在个体之上的种种规训与控制。一个自由的人,应当将自身作为艺术品进行创造,并不断地逾越自身的边界,以体验一个充满美学意味的人生。
“关怀自身”是一种完全自足的目的,而不是某种可以转向他者的事情。所以,自身最终成为了关心自己的唯一的并且确定的目标,它不应当受到外来权力的束缚和禁锢,更不应该成为权力阶级用以累积财富的工具。与此同时,这种关心自己的实践活动也不再应该被认为单纯为关心他人而为。总而言之,关怀自身是一种只以自身为中心并且只在自身之中的活动,即“关怀自身”是将把自身抽象化为关心的对象,且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它以通过修炼自身从而达到自身的圆满为最终结果。
从大体上来看,福柯探索这些问题的实际意图就是为了使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自身真正地恢复成为原本的“自身”。他反对一切来自人自身以外的权力施加在个体之上的规训和控制。福柯认为,人应当凭借自身的审美愉悦欲望,积极实现属于自身的思想、行为及生活。另外,他还极力推崇个体通过自由选择,将自身放入一个不断改造和完善的生命过程之中,从而实现个体风格化的存在方式。总而言之,福柯的生存美学强调,对于人来说,只有在审美超越中,才能达到人所追求的最高自由,也只有在审美自由中,才同时地实现创造、逾越、满足个人审美愉悦以及更新自身生命的过程。
受到福柯思想的影响,愈来愈多的思想家开始鼓励和号召人们不断地创造自身,将个体的生活变成艺术的和美学化的。应当说,美的生活是艺术。生活作为艺术,这不仅意味着人的生活之中可以追求和创造出艺术和艺术品,它指的更是生活本身,生活就是艺术———游戏的艺术、艺术的游戏。因此,艺术也就成为了生活的原本,就是生活的典范,也是生活的真正理想场域。这样一来,后现代的生活方式,就是游戏生活,或者说,就是在游戏中生活,在游戏中寻求新的自由,并在游戏中不断创新。正是因为这种敢于与权力和资本的压迫进行斗争的叛逆、怀疑和不断追求自由的精神,才有可能为改造整个人类社会文化带来真正的希望。
[参 考 文 献]
[1] 福柯.规训与惩罚[M].上海:三联书店,2003.
[2] 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 Susan Mayhew.A Dictionary of Geograph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4] Micheal Hardt,Antonio Negri.Empire[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6]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