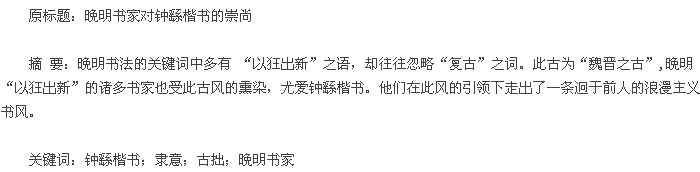
文化以经济为基础,又受政治的影响。明初期,朱元璋吸取历朝统治制度的利弊得失,在经济上移民垦荒,减轻农民的赋税,并为之兴修水利,还百姓家园;同时又扶持工商,从而使农业、工商业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政治上,极力巩固皇权统治,军政大权集于一身,永乐宣德年间又建立内阁制度,进一步发展了中央集权的统治。经济、政治上的决策必然会影响君主对文化政策的实施,他们对文人采取笼络和高压手段,这种政策加强了思想和文化的专制统治,同时在文学艺术上也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文人学士向来都有追求自由、散漫的情怀,当他们遇到某种高压政策时,必会有人掀起反抗的思潮。历史与艺术也总是在矛盾冲突中发展,晚明时期的社会更加动乱,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异常的尖锐,同时各种思想、各种文艺思潮也涌然而至。儒学与程朱理学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泰州学派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袁宏道的“性灵说”等都揭竿起义,反对长期以来的正统思想。他们认为文学艺术应任性而为,抒其性情,道出文人雅士的心声。
书法家也顺应时代潮流,开始寻找新的寄托点,寻找契合自己追求的书风。长期压抑的心灵需要得到解脱与释放,而魏晋那种洒脱、超逸、质朴之风恰好迎合了书家的追求。魏晋时期的书法正处于变革时期,隶书在一系列的变化中孕育出新兴的字体--楷书。钟繇学书正处在书体的变革之际,他的书法难免会受到旧式字体的影响,还会受到自己创新思想的左右,所以他的书法融合了两种书体的韵味。钟繇是将汉隶变革为早期楷书的关键人物。
从他遗存在世的《荐季直表》《宣示表》等书迹可看出,运笔的轻重缓急,结构疏朗旷达,或正或偏,并未完全脱离隶书横画夸张、捺画肥厚、总体呈宽扁之势的模式,点画关系处在由隶向楷的过渡之中,处处彰显出高古与淳朴的气息。与后期成熟的楷书相比,钟繇的书法不免带有多种书体杂糅的退化未尽的原始趣味。正是因为这种超神入妙、稚拙古朴的书法意趣,钟繇才会受到历代书家的青睐和赞扬。明晚期的这些书家在复古之风的倡导下选择了钟繇的书法,这种隶意犹存,高古淡然的书风必会影响书家的审美风尚进而影响到整个晚明书坛的书风及走向。
徐渭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朵奇葩。他疯狂又天真,可恨又可敬。他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寄情于书,挥洒天成。他喜宋代书法又爱当朝倪瓒之书。他的作品多以行草书见着,但不乏真书小楷。他真书取法曾主张“真贵方而通之以圆……楷书须平正恬淡,分间布白行笔停匀,亦要有潇洒纵横处。或云真要持重中有飘逸,谨严中有萧散。”徐渭在小楷上也遵循这一书学理念。他取法钟繇,追求钟繇书风中的散逸但又不失朴茂的意趣。徐渭曾这样评价倪瓒的书法:“书从隶入,辄在钟元常《荐季直表》中夺舍投胎古而媚,密而散,未可以近而忽之也。”[1]钟繇楷书以隶为古,点画之间自然流露出的古拙气息恰好迎合了徐渭的审美,由此他感叹钟繇书法的高妙,更热烈赞叹倪瓒之书。
与徐渭同时期的张瑞图,虽人品不足论道,但书法却被后人津津乐道。他是晚明革新派书家群中较早的一位。张瑞图的书法迥于前人又异于当朝人,以至后人认为他的书法无传统的底蕴,找不到前人的法则,但事实并非如此。从其传世的楷书作品《桃花源记》《王绩答冯子华处士书册》(右图)《书评》等可看出,其取法钟繇,注重横式,结体扁平后加尖利于其中,彰显另外一番韵味,古拙与散淡的气息亦遗留在其笔端。他的行草书也受到此体此气息的影响,结体与用笔突出横向的动态,转笔处又以方折见长,于钟王之外另辟新径。他的这种新径也是在传统中突破的,只是他的取法途径与常人不同。文艺思想的改变、钟书的古拙、个人的审美等各种因素都促使他在书法上要有所变异,正如近人张宗祥评其书所言:“解散北碑以为行、草,结体非六朝,用笔之法则师六朝。”[2]
他将目光投向北碑,取碑之字势与结体以及点画转折的方挺,创造出富有个性的书法作品。张瑞图的出现为那个时代的人展示了另类的书法美。他的书法、他的取法无疑是晚明书法史中最具有特色的一笔。
黄道周可以说是在晚明书史中既矛盾又统一的一个书家。他认为“学问为一、二乘事,而作书是学问中的第七、八乘事,切勿以此关心。”[3]
他虽是一个心口不一且言行不一的人,但从他的书论及作品中则可看出其书法当是下过一番苦功夫的。清王文治曾评价其字“楷法遒媚,直逼钟王。”黄道周在《书品论》中说:“楷法初带八分,以章草《急就者》中端的者为准。《曹孝女碑》有一二者似《急就》,只等通于古今,馀或远于同文耳。真楷只有右军《宣示》《季直》《墓田》诸具不可法。但要得其大意,足汰诸纤靡也。”[4]
他认为楷法中寓有八分为佳。虽然文字中褒扬王羲之的作品,但从他所列举的作品也不难看出他更崇尚王氏之前的钟繇。《宣示》《季直》等都为钟繇所写。王氏临钟繇之书,为宗古学古,虽然有“楚音习夏”的腔调,但却以表现钟书意趣为上。黄道周早期的临摹作品,大体上还是忠于原帖的风格。另外从其传世的小楷作品也不难看出,取法钟繇古法为多。以黄道周手写《孝经》为例,作品结体扁方朴拙,尤犹八分之势,笔笔体现遒媚之风,字字追求自然之态,与钟之风格相近,只不过是字里行间多了几分刚健,在横画、点画及钩角处时存隶意,凸显古韵之风。据史料记载他也是擅长写隶书,[5]只是后人很少提到这一点,但是并不阻碍后人对其书法的评价。
如果说黄道周的小楷取法钟繇是学古泥古,跟随复古之风,那么他临习隶书,并将钟之法、隶之意运用到行草书中,那就是一种创新。他超越常人之处就是能从魏晋、章草、隶书中寻求古意,这古意将其书艺推向高峰,从而影响后人。
动荡的社会,碰撞的思想,注定造就多彩的艺术生活,明清之际的傅山则是这生活中的一抹亮色。他出生在一个传统的文人家庭,其书法也亦步亦趋地走着传统的学书之路--从晋唐入手。
他在《作字示而儿孙》的附记中记载“贫道二十年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法,无所不临”[6].其《家训》中记道:“吾八九岁即临元常,不似。”[7]
傅山这样一个天资聪明又善于思考的人,怎会临不似呢?他的不似是有原因的。他是一个性情中人,追求神韵远远大于形似。不管似与不似,他的楷书还是从晋唐入手取法,特别是从钟繇和颜真卿两人汲取的养分为多--尤其是他的小楷作品。他曾这样总结写楷书的经验:“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钟王之不可测处,全得自阿堵。老夫实实看破,地功夫不能纯至耳,故不能得心应手。若其偶合,亦有不减古人之分厘处。及其篆隶得意,真足吁咳,觉古籀、真行草隶本无差别”[8].他从中阐释了学钟、王书不得心应手的原因,是未懂得从篆隶中寻求笔法,最终还发出古籀真行草隶无差别的感慨。这段话一语中的,道出了写魏晋小楷的根本是从篆隶中找套路,也印证了他书论“四宁四勿”中“宁拙勿巧”的理念。
从他传世的楷书来看,他的风格兼顾钟王与颜真卿,但小楷作品中造型、神韵取钟繇的质拙为多,又兼有鲁公的饱满,用笔沉着又不失灵动,古意犹存。每个人思想都会受到少年时期所学所经历所在环境的影响。傅山早年学书钟繇不似,乃未看清钟书的奥秘,但是经过学习颜真卿楷书,从中得到篆籀之气,进而上溯追源,从中悟得少时学钟书为何不似,是因为未领悟到正确的笔法。如今懂得钟王之书深不可测处就是其书中有隶书笔意。他的这些学书取法的经历必会对其书学思想产生影响。他的书论不同于前人,自有创新,着名的莫过于“四宁四勿”. 他与金石结缘,研究金鼎文,收集《张迁》《史晨》等汉碑。他将书学思想运用到实践中,进而临习这些碑帖。他提出的“四宁四勿”、崇尚篆隶的思想为晚明清初的书坛开启了一股新风。书家开始追求稚拙高古,开始有了取法篆隶汉碑的意识。
其实在晚明的这段书法史中取法钟繇楷书、崇尚篆隶的书家不止这几位书家,他们只是共性中个性的代表罢了。随着社会矛盾的增强,金石学的复兴,西方思想的东渐,书家这种“复古”与“出奇”也随历史的改朝换代进入到清初。他们对钟繇楷书质拙高古的青睐、对篆隶书的崇尚,为清代碑学的出现埋下了伏笔,也可谓是具有了碑学的先前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