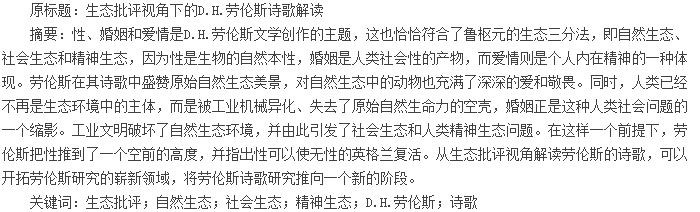
D.H.劳伦斯(1885-1930)是二十世纪最伟大、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他在44年短暂的一生中,为人类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他的创作几乎涉猎了所有的文学体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评论、游记等。长期以来,国内外读者和学者大多关注劳伦斯蕴意丰富的长篇小说,对其诗歌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则逊色许多。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劳伦斯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还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假若劳伦斯只写诗歌,他一定会被看成是最重要的英语诗人之一".[1]139
但是,从目前学术界对劳伦斯诗歌的生态主义批评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在这方面刚刚起步,国外现有的零星研究相对于劳伦斯诗歌的数量及其广博深远的蕴含而言,也只能是星星之火。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将以生态批评理论为依托,以诗歌文本细读为基础,参照现有的劳伦斯小说的生态视角研究,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个方面对劳伦斯的诗歌进行全面探讨,发掘其蕴含的深刻的生态哲学意蕴,开拓劳氏诗歌研究生态批评阐释的广度和深度。
一 生态批评理论与劳伦斯诗歌
生态批评(ecocriticism)早在20世纪70年代被提出,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到真正的确立。生态批评"研究文学与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2]18而文学生态批评包括以下内容:首先,文学生态批评关注自然生态,即关注自然生态环境在文本中的表述,从而揭示文学文本中的自然生态哲学寓意,颠覆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构建一种"生态整体思想"(ecological holism)。其次,文学生态批评关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态。工业文明的进步势必伴随着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而导致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简单淳朴的人际关系的异化,社会生态不平衡发展。最后,文学生态批评关注人类自身内在的精神生态。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与人类生态三者相互影响和制约。自然生态的破坏和社会生态的失衡必然导致人类精神生态的异化。这是一种被工业文明异化的病症。文学生态批评的根本任务就是找出文学文本中这三个方面是如何相符相成地被"表达、描写和安排的",进而找出"生态失衡的文学文化根源",[3]28这是文学生态批评的根本任务。
性、婚姻和爱情是D.H.劳伦斯文学创作的主题,虽然备受争议,但是却具有深刻的生态寓意。鲁枢元认为生态应该包括三种,即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而劳伦斯所关注的性、婚姻和爱情在很大程度上恰恰符合了鲁枢元的生态三分法,因为"性欲,是生物自然性的;婚姻,是人类社会性的;爱情,则属于个人的内在精神性的".[4]
三者在一定程度上相符相成。虽然在劳伦斯的前期诗歌创作中,爱情是一个重要主题,但是,劳氏的诗歌创作更多的关注还是机械工业对自然的破坏以及对人类的异化。劳伦斯在其诗歌中盛赞原始自然生态美景,对自然生态中的动物也充满了深深的爱和敬畏。同时,人类已经不再是生态环境中的主体,而是被工业机械异化、失去了原始自然生命力的空壳,婚姻正是这种人类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在劳伦斯的眼里,真正的婚姻是性爱与精神之爱的和谐统一体。然而,工业文明破坏了自然生态,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甚至性的缺失,进而引发人类精神生态的危机。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劳伦斯把性推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并指出性可以使无性的英格兰复活。从生态批评视角解读劳伦斯的诗歌,可以开拓劳伦斯研究的崭新领域,将劳伦斯诗歌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二 劳伦斯诗歌的自然生态解读
自然生态是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存在状态,有着自在自为的发展规律,是整个生态系统发展的基础。虽然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的因子,但是我们暂且先把他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谈的自然是指除了人类以外的包括花草、森林、动物等的自然生态以及任何一种自然形态。劳伦斯诗歌中的自然生态思想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第一、劳伦斯对待自然(植物和动物)的赞美和崇拜。第二、劳伦斯对于非人类的性的关注---植物的性和动物性。
劳伦斯素来对植物有特殊情感,仅在《鸟·兽·花》中就涵盖了多种植物,包括杏树、松柏、仙客来、山梨、枇杷,等等,有人甚至称他为"植物王国的桂冠诗人".[5]146诗人对植物的这种钟情不仅是他成长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经历的真实再现,而且与他在诺丁汉大学学习的植物学专业知识紧密相关。他不仅学到了有关植物的形态、属性和再生力等方面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他还从植物细胞质的旋转流动和细胞裂变中探寻到了生命的本源"[5]146,"并由此将他对植物的天然情愫内化为一种深切的共鸣(empathy),贯穿到他一生的各类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之中".[6]47因此,劳伦斯在诗歌中盛赞自然生态中的植物,被赋予它们某种灵魂或意识。
在《浪花》中,诗人通过5行诗句,颂扬了浪花"失败"的"美丽".在《杏花》中,诗人将杏树光秃秃的枝干比作生锈的钢铁和扭曲的兵器,然而,待到初春,这钢铁却能绽放花朵。哦,多么圣洁、优美的心,铁的绽放,杏树的生锈的剑。树木像人类一样,在长久的世纪中遭难。
它们流浪、放逐,长期生活在流亡之中像拔出的永远无法入鞘的剑,砍劈,变黑,……可是你看它冲出小小的砍伤的树桩,尽情地、生气勃然地冲向外部世界。[7]150-151这是一首优美的生命的赞歌。"杏花是复活的象征".[7]13它被赋予了细腻的情感和顽强的生命力。它具有人类一样"圣洁、优美"的心。它们被外界迫害,经过"流浪、放逐"后依然"尽情地、生气勃然地"冲向外部世界,发芽、开花,继续自己多彩的生命旅程。
除了植物,劳伦斯在诗歌中还关注了大量的形形色色的动物。需要指出的是,劳伦斯在其诗歌中对动物的关注颠覆了传统的动物文学,更多的描写了那些低等的、被世人鄙视甚至厌憎的动物们。老鼠、蝙蝠、蛇、蚊子等成了劳伦斯诗歌创作中的主角,而且被肯定、接受甚至褒扬。在西方传统中,蛇是一种被打入地狱的动物,但是,在《蛇》中,劳伦斯却本能地对蛇产生了一种敬畏和爱意。当诗人"所受的教育"告诉他必须处死这只蛇的时候,诗人犹豫了,因为他"非常喜欢他","格外高兴地看到他安静地来到这儿做客","感到如此光荣".而蛇在诗人的眼里就像一个皇帝,"像一个流放中的皇帝,废黜到了地狱".[7]157整首诗基本上以肯定的、带有褒义色彩的词语来描写蛇的,表达了对蛇的敬畏和喜爱。在《蚊子知道》中,蚊子深深地知道,自己虽然渺小,却是嗜血的野兽。
然而毕竟他只会填饱肚皮,不会把我的血存入银行。[7]190在短短的五行诗句中,诗人对世人讨厌的蚊子表示理解并赞扬。它们深知自己"渺小",只是自然生态中一个小小的物种,它们的生存方式就是吸食他者的鲜血。但是,它们虽然"嗜血",却并不贪婪,只要填饱肚皮就可以。诗人以"他"来称呼蛇和蚊子,一方面表达了诗人对它们的褒扬和喜爱,另一方面也对人类进行了深入的讽刺。
三 劳伦斯诗歌的社会生态解读
社会生态是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生活状态。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说明"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8]167早在18世纪的中国,曹雪芹先生在《红楼梦》一书中,"渴望一个合乎人性发展的社会环境",所以,他在书中创造了一个"大观园".[9]2然而,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密不可分,是无法摆脱自然生态发展的,自然生态的破坏必然导致社会生态的失衡。劳伦斯认为,工业文明极大地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也就是鲁枢元先生提到的"性欲"),进而异化了人与人之间简单而淳朴的人际关系。人们为了生存不择手段恶性竞争,导致社会生态失衡发展,而这种失衡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现代人失败的婚姻。
善良的丈夫造就不幸的妻子,邪恶的丈夫也时常这样;然而,与坏丈夫之妻的不幸相比,好丈夫之妻的不幸更加痛苦悲惨。[7]189在这首《善良的丈夫造就不幸的妻子》中,短短的5行诗道出了社会化婚姻的悲剧:无论丈夫"善良"还是"邪恶",他们的妻子都是不幸的,因为工业革命在给人们带来社会文明的同时,还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人类性活力的丧失,尤其是男性性活力(也就是鲁枢元先生提到的自然生态)。诗中所描述的不幸婚姻只是社会生态问题的一个缩影。劳伦斯曾说,"人类社会的不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男人与女人婚姻的不幸",[3]146而不幸的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是机械工业重压的直接后果。
新房屋,新家具,新街道,新衣服,新被褥---机器制造的一切新的物品从我们的身上吮吸我们的生命,我们拥有得越多反而越没有活力,变得冷酷。[7]181在《新房屋,新衣服》这首诗中,诗人通过简短的话语痛斥了工业机械的罪行。虽然"工业机器"为人类制造了新的物品,但是这是以"吸吮我们的生命"为代价的。没有了生命,人也就变成了一个空壳。
物质文明使人类没有了活力,人与人之间变得冷酷无情,成为了生态异化的精神病人。
四 劳伦斯诗歌的精神生态解读
精神生态是指"精神性存在主体(主要是人)与其生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和存在。"它一方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关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10]3精神生态虽然指的是人与自己的关系,但是确与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密不可分,互相制约。
劳伦斯在其作品中创造了一系列的"自然人".
他们身强体壮,生机勃勃,最重要的是拥有原始的性能力。《春天的影子》"胸膛有力地挺出,体魄健壮"的护林人;《你摸过我》中"充满了活力"的哈德良;《太阳》中强壮有力的农夫,"年轻而又有激情";《公主》中"身材颀长而又结实"的墨西哥导游,等等。这些都是劳伦斯笔下的"自然人".然而,伴随着英国工业化进程,美丽的自然生态遭到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异化,导致社会生态失衡,现代人的精神生态也陷入了空前的危机。工业机械下的现代人身上自然、淳朴的原始活力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生态文明异化的精神,一种文明的病症".[3]147干干净净的小白脸,像个蘑菇站在那里,光洁、笔挺、悦目---……触摸他,你就会发现,他内部已经蛀空恰似一个老蘑菇,里面被虫蛀得空空荡荡,只剩下光洁的皮肤和笔挺的外表。[7]183在这首《资产阶级多么讨厌》中,诗人指出了被工业异化的现代人的虚伪与空虚。物质丰富了外表,却挖空了现代人的内心。同时,男人和女人之间没有了真正的爱情,人的精神生态彻底崩溃。
自从我们把爱情想得完美,我们就已经把爱情弄糟。……当心灵与爱情发生冲突,或意志选定了爱情,或人格把它当品质来重现,或自我把它当财物来占有,它就不再是爱情,只是大杂烩。
我们已经制作了爱情大杂烩,扭曲心灵的、扭曲一致的、扭曲自我的爱情。爱情是属于个人的内在精神性的,受到外界自然生态环境,尤其是社会生态环境的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社会生态的失衡(在劳伦斯的诗歌中指的是工业机械对大自然的破坏和对现代人的异化)会"把爱情弄糟",爱情将成为"扭曲心灵的、扭曲一致的、扭曲自我的爱情"."男人们该做的事情就是打倒金钱,建造起清新生命之屋。然后他们才能恋爱。"[7]292诗人通过简短诗句向世人提出了获得真正爱情的建议,即推翻工业机械(打倒金钱),重返原始生态(生命之屋),人们才可以获得真正意义的爱情。
五 性与生态拯救
构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和谐生态格局,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意义。劳伦斯在其诗歌中大胆地对动物和植物的性进行描写正是实践了生态批评的这一要义,这也是对传统的人类为中心的物种歧视的一种有力反拨。
劳伦斯在诗歌中大量地描写了动物的性。在《乌龟的呼喊》、《白鲸不会哭泣》、《驴》等诗歌中,诗人都写到了动物的性。在《乌龟的呼喊》中,劳伦斯形象地刻画了雄乌龟追求到了性满足之后的情景:雄的乌龟,在严密的雌性乌龟的陋屋后面穿过,架好,拉近,像展翅的鹰,以乌龟的赤裸从壳中伸出,常常的脖颈、长长的脆弱的四肢伸了出来,深深的,秘密的,穿透一切的尾巴弯曲在她的墙壁之下,延伸,握紧,以最大的张力延伸更多的痛苦,直至突然地、在交配的激动中,痉挛地撞击,并且,噢!
从伸出来的颈上,打开捏紧的脸,发出微弱的呼喊,发出尖叫。[7]168乌龟为了追求性满足,受尽各种煎熬,甚至被钉上了十字架,但是为了圆满再生,乌龟成功地完成了"相交"并发出了"最后的一声/奇异、微弱的相交的叫喊".[7]95性让乌龟实现了整体的完善和生命的完整。在这首诗中,诗人还提到了青蛙、牛蛙、野鹅、夜莺、兔子、小母牛、猫和马儿在得到性满足之后的呼喊尖叫,并且把它们等同于产妇临产时的尖叫。在诗人看来,这些呼喊是"神圣的自然为促进生命的不断繁衍和完善而发出的呼喊","是生命过程中谁也控制不了的自然规律",[6]10这是为生命的完整而"呼喊".透过这首诗,读者可以看到兽性和人性的相通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劳伦斯在生命的最深处"开辟了一条人兽之间平等对话的渠道",从而"真正从本性上对非人类生命产生一种认同感".[7]154劳伦斯在其诗歌中还关注了植物的性,确切地说,劳伦斯在诗歌中描写了植物的果实与人的性器官之间的相像,"并在性之'中心之火'这一点上打通了植物与人之间的壁垒,正如他藉此打通动物与人之间的壁垒一样".[6]47在《石榴》中,其"粉色的、温柔的、闪亮"的开裂之处直通女性身上最隐秘之处;[11]278在《桃子》中,肉肉的、圆圆的桃子与桃尖上粉色的圆尖一起构成女性的乳房;《无花果》中,无花果则直接被相像成"女性的秘密之果","成熟的子宫".[7]194诗人通过这种"形神兼备的'植物人'"向读者展示了"植物与人同根同源、同理连枝"[6]10的意象。
在劳伦斯看来,动物的性爱与世人所抨击、鄙视的现代人头脑中的性爱是截然不同的。动物的性爱具有本能的、无意识的、纯粹的特点。劳伦斯对植物的性和动物性的描写不仅解构了传统的"人类为中心"的观点,而且具有重要的生态启示意义,即让读者可以对人类以外的生物产生一种理解和同情。从劳伦斯的生态思想出发,诗人的性就具有了生态拯救的意义。劳伦斯深信:"只有重新调节男女之间的关系,让性自由地、健康地发展,英国才能摆脱她目前的衰败状况。"[12]81劳伦斯崇尚性的自由健康发展就是倡导自然的原生态发展,从而挽救颓废的英国被异化了的人性关系,尤其是两性关系。
六 结语
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等方面全面探讨劳伦斯诗歌中的性、婚姻和爱情,可以发现其中深刻的生态哲学意蕴。诚如鲁枢元先生所说,性属于自然生态学层面,也是最基础的层面。如果自然生态遭到了破坏,人类的栖息地受到威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被异化,婚姻因其隶属于社会关系进而演变为悲剧。爱情属于精神生态学层面。如果说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可以理解为经济基础的话,那么精神生态就是上层建筑。三者是紧密联系,相互制约。劳伦斯在诗歌中所关注的非人类生物、性、婚姻和现代人的精神问题正是鲁枢元先生生态三分法的文学体现。从这三个层面来剖析劳伦斯的诗歌,读者可以领略诗人前卫的生态理念,进一步理解其具有生态意义的性爱观。
参考文献:
[1] 铂金斯.现代诗歌史[M].波士顿: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
[2]Glotfelty,C.&Fromm,H.ed.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M].Athens:The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
[3] 苗福光.生态批评视角下的劳伦斯[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
[4]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5]Manhood,M.M.The Poet as Botanist[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6] 闫建华.绿到深处的黑色:劳伦斯诗歌中的生态视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