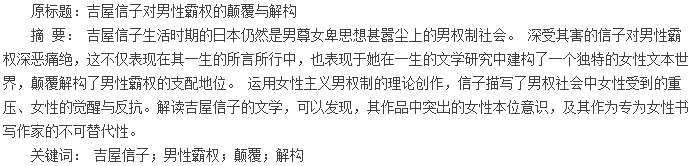
吉屋信子是日本少女文学的鼻祖,是日本大众小说的代表作家,和菊池宽一起被称为日本现代小说界的双璧。她一生笔耕不辍,在小说、俳句、评论上成绩斐然,创作出多部经典作品,表现出极高的文学功力和深刻的生活感受。尤其其独到的女性视角、女性心理、女性笔触以及其作品中形态各异的女性形象,都使得其作品成为研究日本女性文学不可不读的绝好文本。她的作品,展现的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女性世界,一个男性去势的话语空间。
一、日本社会男性霸权的建构
日本社会自古以来便是典型的男尊女卑、男性优位的社会,以男性的习惯文明而构成。男性是社会和家庭的中心,主导女性,女性迎合男性。
尤其在进入武家社会之后,男尊女卑、贱视妇女的思想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这些思想集中表现在江户时代的武家女训书《女大学》中,书中强调女人要以夫为天,"女人别无主君,以夫为主君,敬慎事之,不可轻侮,妇人之道,一切贵在从夫".其中亦不乏对女性的人身攻击,"大凡女性在心性上的毛病是不柔顺、怒怨、长舌、贪心和智浅。她们十之七八有这五种毛病,这是女人不及男人的地方","女人属阴性,和夜晚一样黑暗,所以女人比男人愚笨".其实这都不过是为男性霸权寻找依托而已。更有甚者,书中云"对夫之词色应殷勤而恭顺,不可怠慢与不从,不可奢侈而无理,此女子之第一要务。夫有教训,不可违背。
疑难之事问诸夫,听其指示。夫有所问,宜正答之,返答有疏者,无礼也。夫若发怒,畏而顺之,不可争吵,以逆其心。女子以夫为天,若逆夫而行,将受天罚".[1]203-204即是说,女子一朝嫁为人妻,丈夫就成了她的天、她的主宰,她处于家庭中的最底层,地位甚至尚不如家中的仆人。仆人想要请辞随时可以,而妻子要想离开丈夫家,则有着各种苛刻的条件,必须付出惨痛的代价。女人一生只有"服从",未嫁从父,已嫁从夫,夫死从子。而且女人一生无家,结婚之前,由父母抚养,家属父母;结婚之后,由丈夫供养,家属丈夫;丈夫死后,家属儿子。
到了近代,明治维新后,通过文明开化和与西方接触,日本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男性中心的社会思想却依然根深蒂固,女性的社会地位虽然也有所改变,但是仍处于被奴役、受压迫的地位。当时盛行的"贤妻良母主义",抹杀了女人的自我,使女人陷于只能为家庭为后代服务的泥沼,女人仍然无法像男人一样走出家门、走上街头,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奋斗。因此,所谓的贤妻良母主义不过是男尊女卑思想的升级而已。即便到了今天,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在全世界来说,仍然属于比较低的,大多数女性仍然结婚后就成为专职家庭主妇,生命里只有丈夫和孩子。显然,日本社会逐渐建构起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结构,男性霸权主导一切,女性则处于从属地位。
文学领域的建构亦是如此。翻阅整部日本文学史,可以发现女性作家不仅为数甚少,且文学史上对于女性作家的记述也比男性作家简略许多。虽然平安时代女性文学曾一度开花,但女性作家之所以得到培养,也只不过是因为男人想要利用她们实现其政治野心而已。甚至女人都不能使用男人所用的文字,所以女人只有去创造自己可以使用的文字,这才有了今天日语中的假名文字。而且多数文学作品的世界也是以男性习惯的卓越为中心来描述的,文学作品的话语亦是以男性话语而建构的。
为什么男尊女卑的思想如此根深蒂固?男性霸权的表象之下隐含的是什么?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男性优位是社会权力的一种表现,是社会文化形成的一种性别歧视,其后隐藏着社会制度、经济文化要素。因此,要真正实现女性的解放、两性的平等,最根本的是要改变经济文化结构、甚至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四种结构---生产、生殖、性和儿童教化---在家庭中结合在一起,相互依存,是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将男权制的心理加以转变,才能使女性得到真正解放。[2]53一般来说,文学是社会世象的一种反映,社会变化必然会对文学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随着要求变革男权中心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对男性霸权的批判亦成为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视点。古今中外,许多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都曾对这一压制女性的男权社会进行抨击,日本近代文学中,也不乏这样的作家。如清水紫琴、樋口一叶、田村俊子、宫本百合子、吉屋信子等人便是。
二、吉屋信子对男性霸权的终极反抗
女性文学评论家田边圣子曾指出:"仅仅外表具备了近代教养的男人们,行为十分粗鲁,看上去像是从知识分子模型里铸出来的速成绅士,在明治时期的日本不断被大批量地生产出来。若去向他们内部,则可见家父长意识、男权至上思想顽固地占据着他们的心灵。内里与维新前的发髻时代并无二致,外表则系着领带蓄着八字胡,在近代绅士的这种奇妙的二重构造中,日本的近代化在进步。富有观察力和感受性的信子早就发现了这种矛盾。听够了父亲和兄弟不断强调男性的优越性,她心中已经建立起了排斥和反抗的精神堡垒。即便某天,(信子)产生了'不要男人'的思想也不足为怪吧。"[3]22正如田边圣子所言,从小在男性霸权包围中成长起来的吉屋信子,是一位男性霸权的终极反抗者。
信子是家中唯一的女孩,但却并不受宠,反而常受兄弟们的欺负和指使。好吃的东西被他们吃掉,玩具被他们弄坏,学习被他们打断,还常受恐吓甚至挨打。诉诸父母,听到的却是诸如"女孩要顺从"、"要遵守妇德"之类的男尊女卑的说辞。即便在游戏中,作为女孩的信子对男性的强权也有着深刻的体会:信子总是自然而然地被置于最底层的角色扮演,甚至常被当作递物打杂的小兵。
那时,在信子幼小的心灵中,便萌生出了强烈的对男性霸权的反叛意识。再如,男子只要学习玩耍,而女子不仅要帮忙做家务,还处处受限制,被迫学习裁缝、插花等"女人的技艺".虽然信子对此种种男性优越的事实深感不满,但从小面对这些的她也只能感到无奈。后来哥哥们都如己所愿上了大学,虽然信子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却因为是女孩,上大学的请求便遭到了父母的反对。这也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例如,东京帝国大学一直不招女生,直到 1947 年才改变此规定。
对此,信子心中极为不甘,但又无计可施,甚至一度想到舍弃女性身份。在散文《如果是男人》中,信子就曾设想自己若是一名男性,便可就读东京帝国大学,研究考古学或者古建筑学。在《改造》杂志上发表的另一篇短文中,信子亦表露了想成为男人的欲望。在当时,拥有自由、时间,进行各种冒险活动,都是男人的特权。而女人的人生就只有嫁人这一条路。
虽然信子从小便深感男性霸权的重压,但却无力改变一切。当她渐渐长大,对男性霸权的反抗意识便变得非常明确。她不听从父母的教诲,不安心嫁人,对于母亲安排的新娘课程也敷衍了事,开始了对男性霸权的反抗。虽然反抗是温和的,但决心却是无比坚定。这种反抗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获得了去东京发展的机会。信子曾以为开放的东京全是自由的空气,但亲临其境,她感到的只有绝望。例如,在车站,信子看到的是强壮的男人包括西装革履、抱着洋书卖弄学问的绅士和年轻的学生们冲过妇女老幼拼命挤车的情形。这些体格强健的男人们夸耀着自己体力上的优势,简直就像无知的野兽,连接受新教育、担负新文明的年轻人也卖弄着从父辈遗传来的野蛮之力而泰然自若,这光景尤其令信子痛心。信子憎恶这些道貌岸然的青年绅士和学生,瞧不起他们。[4]203-204同时,信子由此进一步认识到整个日本都是男人的天下。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信子在其评论及感想文中,对当时日本的男性霸权社会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批判,甚至对当时文坛的男性作家也是如此。
信子就曾批判菊池宽对女性的描写并没有超出一般男性那种低俗的概念,而且还痛斥《羽衣》这部作品低级趣味。信子还曾将《改造》四月刊上男性作家的作品贬得一文不值,她认为全都是些以女性为参照的充溢着淫秽的色情文字的名作。她写道:"世上的男人们,诸位,从酒、女人、玩乐的概念中解放出来吧。如果男人一天不将女人这个概念从只能将之当作色情对象来接受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男人的人生阶段就将一直停留在低级阶段,就将常常阻碍你迈向人类理想的前进道路。"[4] 5101937 年,日本四谷税务署在评定信子的年收入时出了差错,大肆宣扬吉屋信子的收入水平当属文坛第一,连许多国务大臣、陆海军大将及实业家都难望其项背云云。信子对此非常不满,认为国家不给女人权利,却向女人要求许多,正是男性的强权政治的表现,但是她不畏强权,敢于抗争。她提出抗议,并向税务署提交了重新审查的请求书。
不仅如此,就是在文学界,也是男性霸权占主流地位,女作家往往遭受歧视,无法获得和男作家同等的地位。有不少男性作家都曾批判信子的文学创作,多有轻视之意。例如,小林秀雄就曾对《女人的友情》这部作品大加批判,他说:"这本书我只读了一点就放弃了。也有别的原因,但实在是太没意思,终于读不下去了。当然,我也并不是因为有趣才开始读的。引起我兴趣的是它的畅销,我想如此畅销肯定有它的可取之处吧。……简直就是抓住孩子们的弱点招摇撞骗的文体。如果我说因为孩子们上当受骗这书才会畅销,也许作者会发怒,但是我的说法比作者的文体要高尚多了。……有一点是肯定的,爱读《女人的友情》的孩子们心里有着远比'女人的友情'更加美丽健康的东西。"[3]76诸如此类来自男性带着偏见的评论,并不少见。因为信子的创作都是以女性为中心,而将男性放在了边缘的位置,所以男性作家和男性读者无法认同,只能将其视为异端。而面对反面的评论,吉屋信子也并没有保持沉默,反而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继续进行女性本位的创作,在文学世界中,不断贬低男性,彰显女性。
三、反抗男性霸权的话语言说
法国女性主义思想家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有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女人不是生而为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正是男权中心的菲勒斯中心主义,使女性变成女人。要想冲破男性霸权规定的"女人"这一社会属性,只能与之进行彻底的斗争。女人进行斗争的形式各异,而女作家们往往借助手中之笔对其进行控诉。吉屋信子亦对男性霸权深恶痛绝,这不仅表现在其一生的所言所行中,也表现在她的文学创作中。《花物语》虽然是一部描写女性间故事的短篇小说集,但是其中也有不少揭露日本男性霸权现实的篇章。
如 《风信子》一篇,就讲述了麻子遭受男性霸权欺压的故事。麻子是某公司的打字员,和其他女同事同在一间办公室。男员工闲暇时总来此和女打字员搭话消磨时间,且越来越过分,给她们带来了困扰。麻子见状就去和经理交涉,请求禁止男职员出入打字员办公室。但是经理作为男性,对麻子作为女性竟如此大胆深感不满,于是他决定维护男员工的特权,不仅将麻子开除,还以辞退为名恐吓其他女员工。在整个事件中,做错的都是男性,受到损害的是女性,可是最后受到处罚的却是女性。这说明在男权中心的社会中,是非标准都是以男性话语建构的,女性只是他者的身份。而在《蝴蝶花》一篇中,信子不仅通过与女性对比,来凸显日本男性的优位,即便是对男性蛮横行为本身的刻画亦是入木三分。
书中写道:"开来的一辆辆电车,都挂着令人讨厌的满员的红牌,一副佯装不知的样子疾驰而过。片刻之间,就聚集了许多没带伞的人们,等着电车。偶尔有电车停下,具有大和魂的健壮的日本男人便挤过老人孩子和柔弱的女子,争先恐后地上了电车。不仅仅是乘上了车,而且是一只脚勉强踏上售票台,一只脚悬空……悬挂着那耷拉脚的乘客的电车,打破外面低声私语的和谐,在小雨中,向前方驶去。留下的弱者们淋着雨,一副幽怨的神情,注视着电车的背影。"[5]92-93她在《阁楼里的两处女》中也有多处对男性中心的男权社会进行了强烈的控诉。例如,主人公章子放学后等电车时看到的情形。上下班高峰时,每天都有很多人在等电车,而从拥挤的人群中首先冲出去的一定是体格强健的男人。
其中,既有外表斯文的绅士,也有年轻学生们,还有盛年的强壮男子和动作娴熟的军人,他们推开女人、孩子和老人,争先恐后地挤上电车,毫无风度,甚至还冲着车外留下来的人们得意地吹着口哨和贱笑。这一切都使章子感到失望和痛心,也更加深了她对日本男人的厌恶。章子感到不可思议,难道他们的母亲妻子都不是女人吗?再如,章子她们在饭店吃饭时遇到的事情:几男一女热闹地吃饭,竟是在庆祝能够卖掉自己家的女儿,很快可以拿到钱。男人可以随意买卖女人,却没有任何法律或政策约束,生在这种家庭的女人只能自叹命贱。在《那条道路这条道路》中,妻子阿静勤劳善良,贤良淑德,却听凭好吃懒做的丈夫龙作胡作非为,还要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因为她从小被灌输的思想便是:男人是一家之主,在家里拥有绝对的霸权,女人只能服从男人。甚至在她刚生产不久,龙作仍然每天一早就出去喝酒,完全不劳动,越发懒惰,她也听之任之,自己拖着尚没完全恢复的身体照顾两个孩子。
如果说在以上两部作品里,女性只是男权中心社会现实的牺牲者,那么在《勿忘草》《直到地尽头》和《鬼火》中,女主人公则不再看着男人们充满优越感地胡作非为,而是奋起反抗。《勿忘草》中,牧子和一枝的父亲都是有着强烈男尊女卑思想的固执男人。一枝的父亲临死前留下遗书,把全家的重担加到一枝一个人身上,而且特别嘱咐她一定要照顾好弟弟,因为他是家里的男孩,要继承家业,代表全家。牧子的父亲亦是同样,将所有的关心都倾注在弟弟身上,而对牧子不管不问。牧子对于这样的父亲,也是决心对抗到底。书中写道:"在博士父亲眼里只有将来可以继承他学问的男孩,而对于长女牧子,因为是女孩,则抱着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好像她是别人家的孩子。
牧子非常了解父亲的想法,所以她从不向父亲撒娇,反而经常以冷眼相向,是一位反抗心非常强的女孩。她就是一位得不到父亲的爱,自己也不爱父亲的不幸女孩。当她取得好成绩时,只有母亲为她高兴。对于男尊女卑主义的父亲来说,女孩的学习根本无关痛痒。"[6]27牧子就是这样一位反抗心强烈的女孩,而她的反抗最后取得了胜利,改变了父亲顽固的思想,与父亲取得和解。在《直到地尽头》中,春藤绿是一位有理想、有个性、敢作敢为的女性。当相亲的男子列出将她作为结婚候选人的条件时,她愤怒到了极点。
那男人举出的理由有:头脑聪明、秉性良好、身体健康,和自己有着同样的信仰,年龄二十岁的处女。得知这些后,春藤绿看到的是男人在女人面前的优越感,是男人的高傲、冷酷和自私自利。于是,春藤绿断然拒绝了这门亲事,将高高在上的男性霸权狠狠地摔在地上。
在《鬼火》这个短篇中,信子借收煤气费的忠七展示了男性在社会上无比的优越感,和作为强者的男性对作为弱者的女性的征服欲。有一次,忠七到一个贫穷者的家里去收煤气费,那家的女人穿得破破烂烂,连和服带子都没有系。她说她的丈夫生着重病,所以哀求忠七不要停煤气。"忠七学着拉行话,语气带有几分'宽大'和'同情',其实是流露着某种优越感。"[7]400忠七看着这可怜的少妇,"他感到似乎已经成了'一派大人物',一种自我陶醉感涌上心头。"[7]400事实上,忠七不但没有同情这位妇女,反而动起了邪念。他提出不停气的条件是女子去献身于他。结果女人没有去,等到忠七再去她家的时候,看到的是病死的丈夫和吊死的妻子。猥琐的男人,竟然试图让女人用自己的身体来替补拖欠的煤气费,其实质是男性霸权对女性的轻视。而纤弱的女人,却用死来进行抗争,这可以说是对男性霸权最强有力的控诉和最高姿态的蔑视。
男权制在西方学术话语中被称为父权制,原因大约在于从词根上讲男权制与父系的男性家长同源,相对于母系的女性家长,表示一种男性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性不平等的制度。
但是这种制度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的作用,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是社会性别文化结构的产物之一。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权优位的男权制才是是女性受压迫、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女性要想解放必须彻底消除男权制。吉屋信子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她在作品中通过描写男性霸权下女性受到的重压、女性的觉醒、女性的反抗,创造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女性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男性不仅常常缺失,即便存在,也多是负面形象,由此男性的传统价值和地位或已消失殆尽,或变得无足轻重,男性角色已沦为女性的附属物,是女性角色存在的衬托。吉屋信子虽然不是日本文学史上占主流地位的作家,但是作为一位专为女性书写的作家,吉屋信子是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无论是其少女小说、大众小说,还是历史小说,都是女性本位的书写。
这里的"女性"不仅是她文本中的女性角色,还包括她自身,包括整个社会中广大的女性群体,甚至还包括她文本中每一个被去势了的男性角色。通过这些女性书写,信子一步步解构颠覆着男性霸权的统治,建构着女性话语的崭新天地。
参考文献:
[1] 日本思想大系 34(贝原益轩·室鸠巣)[M].东京:岩波书店,1970 .
[2] 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3] 田辺圣子。ゆめはるか吉屋信子(下)[M].东京:朝日新闻社,1999.
[4] 田辺圣子。ゆめはるか吉屋信子(上)[M].东京:朝日新闻社,1999.
[5] 吉屋信子。花物语(上)[Z]. 东京:国书刊行会,1985.
[6] 吉屋信子。わすれなぐさ[Z].东京:国书刊行会,2003.
[7] (日)吉屋信子。 日本当代短篇小说选[Z].文学朴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
[8] 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