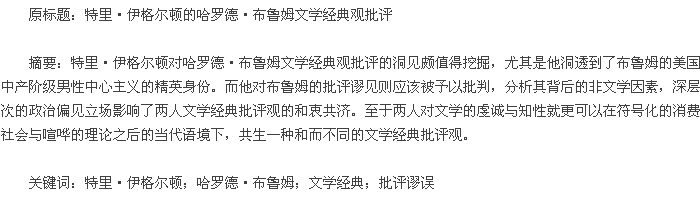
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干将特里·伊格尔顿对美国文学批评家“耶鲁四人帮”之一的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经典观向来持有很大的意见。早在1983年,伊格尔顿在其以论为立、轰动一时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就对诸多20世纪西方批评理论家作了史论结合而且针锋相对的批评(多为批判)[1].而布鲁姆作为与耶鲁结构学派关系暧昧的文坛大家,在伊格尔顿看来自然难辞其咎。而在21世纪初,布鲁姆出版了其着作《如何读,为什么读》 [2]之后,伊格尔顿[3]便于同年撰写了专文来批判布鲁姆,措辞剑拔弩张、异常激烈。伊格尔顿对布鲁姆的批评的洞视与锐度是显而易见的,如对其精英主义身份的挖掘就非常到位。但是,在伊格尔顿对布鲁姆批评的洞见中也隐含了他的盲视,这其中充斥着有意无意的谬误。
而这又体现了伊格尔顿自身立场的偏激与局限。论述伊格尔顿对布鲁姆批评的洞见与谬误,并进而在此二者中探求一种和而不同的文学经典批评观,这绝对是饶富意义的。
1伊格尔顿对布鲁姆批评的洞见:布鲁姆的精英主义身份
作为一个老辣的英式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对带有解构意味的美式批评家布鲁姆的批判是有其精准之处的。
首先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的第四章“后结构主义”里,伊格尔顿在批判耶鲁解构学派的“虚构性和任意性”之时,并未将布鲁姆与德·曼、米勒、哈特曼三人完全并驾齐驱,而用“某些方面”来牵连布鲁姆[1]169.
其后在第五章“精神分析”中,伊格尔顿又单辟出不少段落,来专论布鲁姆在弗洛伊德的影响下是如何创立了20世纪70年代最大胆而富有创见的文学理论之一,并且以浪漫主义回归的文学精神抵抗了他的解构主义同事的怀疑主义、反人道主义、xuwuzhuyi时代精神[1]202.与此同时,伊格尔顿也点出了布鲁姆所采用的晦涩而尼采式的修辞力量,其用意在于掩盖自己对真理、价值及人道主义的天真与绝望。最后,他甚至声称布鲁姆之所以陷入这种人道主义的绝境,乃是因为“它的基础仅仅是它自己的武断的信念,它已搁浅在不可信任的理性主义与无法忍受的怀疑主义之间”[1]203.
而在《伊格尔顿评布鲁姆的新着〈如何读,为什么读〉》一文中,伊格尔顿的言辞则变得更是极为针锋相对、不留余地。伊格尔顿先扬后抑地说布鲁姆曾经也有趣过,并再次褒大于贬地提到了其“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理论。但是,随后,伊格尔顿就指出了布鲁姆的批评实践未能够摆脱社会和文化条件的制约,并说他是以“带着浓重的纽约口音大声疾呼普遍人性,他对不屈不挠的意志的信念就如同樱桃馅饼一样完全是美国式的,只不过他把这一点误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3].作为一个乐天派抱有美国梦的中产阶级白人男性,布鲁姆似乎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自己西方中心白人男性资本主义的态度了。
不妨来细细审读一下布鲁姆名动天下的《西方正典》。在“序言与开篇”里,布鲁姆直截了当地将那些正在传播的他认为并非最好的女性、非裔、西裔和亚裔作家的作品总结为以怨恨为共同特征,并称之为“憎恨学派”.他甚至为“憎恨学派”将“影响的焦虑”这一观点放在“已死的欧洲白人男性”那里而感到高兴[4]5-6.
再审视一下布鲁姆的“哀伤的结语”和附带书单的话就可将问题看得更清楚了。在表达了自己并不欣赏边缘地域和族群的文学之后,布鲁姆在“哀伤的结语”中非常偏激地说“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科学还不如说是痛苦的呐喊”[4]430.怎么?难道除了文学经典之外,布洛赫希望哲学的展望、马尔库塞美学维度的拓展、萨特对人道主义的坚持、鲍德里亚对符号社会的剖析都毫无意义?其实这些思想恰恰为布鲁姆坚持他自身的文学经典研究提供了理论的基础、审美的要义、认知的思维。此处布鲁姆所展现出来的精英主义是很值得商榷的,而伊格尔顿对他的批判也确实不无肯綮之处。
在尖锐而集中地抨击了布鲁姆的美式中产阶级白人男性精英主义身份以后,伊格尔顿又心满意足地一一提出了布鲁姆的其他陋习,诸如评论的凡俗外行、话语的散漫芜杂、书写的公共大众化、姿态的英雄主义化、阅读的生活化、语言的廉价乏味、自我与孤独的过度放大等[3].这些批判大体或可以概括为两点,亦即话语的平民生活化和文学立场的精英化(看似恍如矛盾的共同体)。
黄灿然在《如何读,为什么读》一书中写的译序“大作家式的批评家”里评价得很是中肯:“伊格尔顿可归入专业批评家类别,他聪明机智风趣,对各种新潮流保持关注,论断都显得公正持平,可就是缺乏某种更个人、更接近读者的孤独,更提升或扩大读者的自我的深度与视域。如果他批评某位也是处于某个类别的偏见者,那确实会令人觉得公正持平且义正词严,例如他驳斥理查德·道金斯对宗教信仰的攻击。
但在批评布鲁姆这个复杂的综合体时,他只能用近于逻辑紊乱的语言!这也就是为什么伊格尔顿的文章我常看,但只是作为一种知识性的吸取,而不是作为一种启迪”[2]7-8.那么,正相反,布鲁姆给人带来的也许正是对于孤独和自我的认知与启迪吧。
其实伊格尔顿和布鲁姆各有各的洞见,可惜的是在这种洞见之下也很容易逐渐滋生出一些偏见甚至盲视。伊格尔顿对布鲁姆的批评有其不公甚至不讲道理的谬误之处,对这种谬误的挖掘在某种程度上更有助于对两人思想内涵的把握与认识。
2伊格尔顿对布鲁姆的批评谬误:伊格尔顿的文化-政治立场
“如果你是西方世界的白人,那么做谁也比做自己强。”[5]22伊格尔顿的这句后殖民语境下反讽的话,倒正适用于布鲁姆的窘境。会不会是一开始伊格尔顿就先入为主地以“感受谬误”(affective fallacy)来解读布鲁姆并进而产生“诠释谬误”,然后又“意图谬误”(intentional fallacy)地自以为是,造成了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批评谬误”呢?此中关节,不可不察。
上节已论述过伊格尔顿鄙夷布鲁姆的地方。大体归纳来说即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语言和话语的时而太晦涩与简陋问题,另一个乃是其文学经典的精英主义西方男性中产阶级中心主义立场。
先来探讨第一个修辞、用语的问题。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伊格尔顿责怪布鲁姆书写得晦涩,而在对《如何读,为什么读》的评论中,伊格尔顿又责怪布鲁姆书写得浅显。其实布鲁姆与本雅明非常像的一点是,他也是“大作家式的批评家”.黄灿然在译序中说过:“哈罗德·布鲁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批评家,但一般意义上的批评家的资格他又都具备。他是专业批评家……但他没有任何学院味,事实上对学院各种潮流非常不屑,总要在这里那里批评它们几句;他是高深而博学的批评家……他又是一位可以大众化的作家……在这一切之上,他还是一位大作家式的批评家,写起批评来可以看似不着边际、权威武断、省略跳跃、大肆铺排甚至戏剧性地夸张。总之他讲他的,他不理会你---但实际上有眼界的读者都能看出,他才是一位大修养的读者,他的自说自话正是对读者的真正尊重”[2]1.本雅明写的所谓批评的东西也大多晦涩难解,几乎令人怀疑是不是自动写作而不知自己在写什么,但深究起来,才能发现其中有珠玉在焉,瑕不掩瑜而有微言大义。这种文学性强烈、可称之为诗性哲学的论述,委实不能够去苛责其措辞的本体论结构。用语的或简或繁都为了通达具体而完整的人的审美与认知,理性无能为力之时当借助具体而完整的人性去把握这种文学和哲学。伊格尔顿对本雅明赞叹有加而对布鲁姆左右为难,实在不太应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