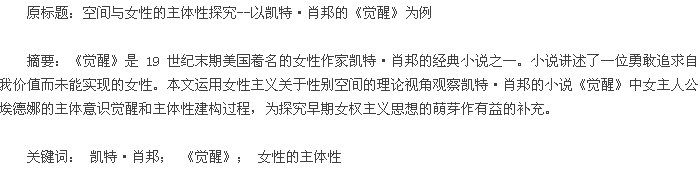
凯特·肖邦是 19 世纪下半叶女性意识最突出、文学成就最大的美国女权主义作家,其代表作《觉醒》成功刻画了一个具有自我意识和性意识、勇于追求自我的新时代女性形象。肖·沃尔特曾说,肖邦在情感主义和地域上继承并超越了美国 19 世纪两代传统女性作家,小说《觉醒》无疑是一本具有“革命性的书”,并声称“小说《觉醒》发出了对美国传统女性文学改革的新声”,开创了“新的主题和风格”.随着上世纪 60 年代女权运动的兴起,该小说的女主人公埃德娜夫人被赞誉为“新女性”,她具有女性的主体性意识。当代女权主义者从神话、原型批评、意象、历史、文化、隐喻的同性恋等不同的角度对作品进行评析,这些观点忽略了对埃德娜个人空间的权利的解读。
一、空间与性别
文学作品可通过空间的转换来展示小说的人物及作品的思想内涵。迈克尔·赛尔托说“每一部小说都是在空间中不断穿梭的故事”.空间并不局限于提供事件发生地,更与社会文化有紧密的联系。
特别是人物之间的性别权力关系。在男性作家作品中的女性角色总是被动地局限于家庭空间,而这些女性作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往往最终变成家庭营地的“逃避者”,她们在父权制度下,承受着难以逃脱的男性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压迫。
从女性的角度看,空间不仅是性别关系的产物,更为重塑两性关系提供了重要条件。在性别与空间的关系中,空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换言之,父权制则起了框架性的作用。正是这一原因,性别空间关系成为许多女权主义学者的理论切入主题。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一个人的房间》中,呼吁关注妇女的私人空间和实现的开创性的工作所必要的经济独立性。西蒙娜·德·波伏瓦在《第二性》观察到父权文化将女性定义为“他者”,从而剥夺了她们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当代女性哲学家艾丽斯·马里恩·杨在《扔得像个小女孩》中进一步发展了波伏瓦的观点,探讨了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与空间之间的关系。梅洛 - 庞蒂将身体概念化为构成空间的原始主体,她把女性空间归纳为三种特征: 第一,女性生存于封闭的空间; 第二,女性空间是由“此空间”和“彼空间”构成的“二元结构”; 第三,女性习惯于将自己禁锢在“定位空间”.杨认为所谓“贤妻良母”就是忙碌于封闭的空间( 如: 卧室、厨房、客厅、阁楼) 的形象。除了这里封闭的“此空间”,“彼空间”则是男性自由的空间领域。在父权制度下,女性空间被定位,她们的活动范围受限,导致活跃地构成空间的身体只能被动地存在于被构建的空间里。
随着空间和主题的转变,小说是按大岛、尚奈尔岛、庞德里耶的豪宅( 坐落于新奥尔良着名的漫步大道) 、鸽子楼、大岛这样的空间格局展开的。第一部分的位置,是大岛和尚奈尔岛附近,而第二部分,是新奥尔良市。埃德娜意识觉醒的过程中展现在第一部分,主体性意识的形成是在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是指小说中艾德娜在大海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旅程。埃德娜的私人空间,包括大岛的庞德烈小屋,新奥尔良的庞德烈小屋,以及“鸽子笼”.小屋和庞德烈家属于家庭空间,埃德娜自己购置房子的客厅和“鸽子笼”则是艾德娜的个人空间。埃德娜的意识主体性表现为遵循“营地逃离”模式。空间的转变包括从家庭到个人,从内在到超越,从“此空间”到“彼空间”.
二、空间与觉醒
埃德娜主体意识的觉醒是一个渐进的、充满矛盾的过程,包括埃德娜和庞德烈之间的两次主要冲突。觉醒的过程在小说叙述过程中分为三个阶段:当她的主体意识处于两种相互矛盾思想的冲突中时“庞德烈太太开始意识到她个人作为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 而后“埃德娜开始觉得像是一个逐渐觉醒的一个梦,一个美味的,怪诞的,不可能的梦想”.
艾德娜的觉醒近乎完善,在此整个过程中她入睡和醒来时文中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述。从沉睡中醒来,她的思想完全发生了改变: “她清醒地张开了明亮的大眼睛,满脸通红”意味着女主人公的主体意识的成熟---“用不同的眼睛审视不同环境下的自己”.
三、空间和人的主体性建构
小说第二部分首先对空间进行了描述。“庞德烈夫妇拥有一套漂亮的房子……”埃德娜回到新奥尔良后通过一系列的空间转换开始实现她的主体性。比如,她尝试着在空间上“把自己作为活动的主体”: 占有、限定、控制、转换空间。用杨的话来说,埃德娜主体性的实践是通过从内在的“此空间”向外在、自由的“彼空间”的转换中进行的。
首先埃德娜取消了每周二的接待日,理由简单、唐突,“没什么事。我想出去走走,就出去了”.与丈夫不愉快的晚餐后,“她的脸发红,两只眼睛闪射着怒火”“从手指上撸下戒指,丢在地上。然后用脚使劲地揉踩这枚滚落在地上的戒指,想把它碾碎”“抓起花瓶,向壁炉的砖墙掷”.这是对她的婚姻和性别角色的强烈反抗。
主体性的建构必然要求人重新作为原始主体构成空间,也就是,人作为空间的主宰理应能占据、定义、控制和超越空间,艾德娜所需要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己的空间”.“鸽子屋”使她真正走出丈夫的“牢笼”,走向属于她自己的自由空间,它是埃德娜用自己画画挣的钱加上父亲留给她的钱买下的。在这个小空间里,在与艾洛宾和罗伯特的交往过程中,她找回了自我,释放了被禁锢已久的对爱的渴望,对女性权利的追求。埃德娜最终成为“鸽子屋”---“彼空间”的真正主体。
事实上,“鸽子屋”无法置于父权制之外。它离庞德烈的住所仅“两步远”,就如同大岛别墅前面的吊床,只能作为埃德娜暂时的逃避空间。在小说中,庞德烈曾经暗示过“亲爱的,你不会离我太远,我无时无刻地不在注视着你”.因此,“鸽子屋”的存在是暂时的,迟早会被父权制吞噬。
从具有空间意象的“鸽子屋”这点可以看出,早期女权主义者所提倡的“自我空间”存在局限性。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埃德娜的超越封闭性的空间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她的主体性并未真正实现。在极度失望和疲惫中,她终于走向大海---一个永恒的、无限的想象空间,走向死亡的国度。
四、结语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埃德娜所探寻的女性个人空间时刻处于父权制的性别监视中。埃德娜所处的是受父权制度所制约的性别空间,随着主体意识的觉醒,她与空间的关系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构造,通过构造个人空间来维护独立的主体性。但是,父权制度的渗透和早期女权主义个人主义的局限性使其主体性建构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上述研究表明,性别空间的女性主义理论视角为女性身份认同的研究和父权制下女性个人主义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尝试。
[参考文献]
[1]赫荣菊。 从女性刻画看凯特·肖邦对女性存在的思考[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 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4) .
[2]刘卓,王楠。 女性意识的顿悟: 凯特·肖邦《一小时的故事》探析[J]. 东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4,( 6) .
[3]陈素媛。 凯特·肖邦笔下的爱与死[J]. 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7,( 4) .
[4]刘翌。 女性主义文本的典范: 再读凯特·肖邦的《一小时的故事》[J]. 考试周刊,2008,( 27) .
[5]李伟,范晓琳。 不过是一场自由之梦: 评析凯特·肖邦的《一小时的故事》[J]. 考试周刊,2011,(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