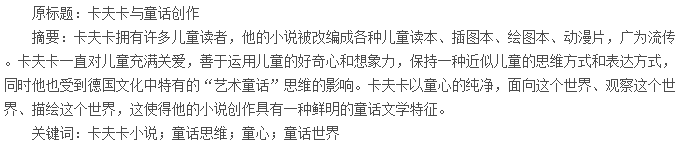
卡夫卡拥有许多儿童读者,他的小说被改编成各种儿童读本、插图本、绘图本、动漫片,广为流传。
卡夫卡笔下的文学世界具有浓郁的童话文学、奇幻文学、动物寓言特征,这一点已经被西方个别童话研究专家注意到了。美国当代著名童话研究专家杰克·齐普斯说:“童话故事的坦诚公正和它对民间文化的富有想象力的运用,使它证明了自己是一种典型的民族的艺术形式,它表达了在反对专横社会和政治压制的斗争中对更公正和更理性的替换性选择的需求。因此,几乎所有在19世纪和20世纪享有盛誉、受到敬重的作家……都转向童话故事创作绝不是偶然的。他们不仅从童话创作中寻求庇护,以逃离德国的残酷现实,而且用童话故事来评判这个现实,并暗示苦难的现实并非必然如此,现实中发生变化是可能的。”
在这些“享有盛誉、受到敬重的作家”当中就有卡夫卡。其实,德国思想家本雅明早就发现了卡夫卡创作的童话特征。他说:“童话是关于战胜神话威力的传说。而卡夫卡打算写传说时,写下的是给辩证法者看的童话。他在童话里插入了小花招;然后他认为这些花招已证明,‘即便手段不够有效、很幼稚,也能有助于拯救'.”法国当代思想家、小说家乔治·巴塔耶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卡夫卡的作品大体上表现出一种非常孩子气的态度。”
卡夫卡短暂的一生,他以童心的纯净,面向这个世界、观察这个世界、描绘这个世界,这使得他的小说创作具有一种鲜明的童话文学特征。因此,探讨卡夫卡小说创作与童话的关系是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
一、永远的童心
怀有童心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也许并非是必需的,但是,对于一个写作童话的作家,或者一个在创作中具有浓郁童话特色的作家而言,就应该是必需的了,卡夫卡恰巧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卡夫卡有一张似乎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脸。他外貌英俊,永远富有孩子气的魅力。“他35岁左右,在海滩上还被人们看作是一个腼腆的少年。”
在卡夫卡同学的印象中,“卡夫卡瘦瘦高高,像个孩子。他的样子显得肃静、善良、和蔼,打从内心里关心别人,但是经常离开人群,好像十分畏缩”.1917年,他与未婚妻菲利斯有一张合影。菲利斯出生于1887年11月18日,比卡夫卡几乎小4岁,但她看上去就像是卡夫卡的母亲。
1988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瓦根巴赫撰写的《卡夫卡传》,书中将这张照片误题为:卡夫卡和他的母亲。卡夫卡在保险公司的同事后来回忆说,卡夫卡是“我们办公室里的孩子(our office baby)”.在卡夫卡的一生中,“童话故事令他着迷。他贪婪地阅读冒险故事、极地探险的真实记录、遥远地区的旅行日志、歇洛克·福尔摩斯的神秘故事”.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遇上了最后一位女友朵拉。朵拉爱上了卡夫卡梦幻般的、奇特的想象,他们的共同生活充满童趣。卡夫卡的朋友布罗德后来回忆道:“他们经常像孩子般的互相逗乐。我记得,他们有一次把手伸进一只脸盆 里,并 将 这 只 脸 盘 称 之 为 我 们 的 ’家 庭 浴池‘.”1922年9月21日,卡夫卡在给奥斯卡·鲍姆的信中写道:“我的教育,从结果来看,不是太热,就是太冷,是在孤独的少年床上完成的。”
卡夫卡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对他的性格的形成,对他日后的生活方式和文学创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卡夫卡的一生就像是一个孩童行走在成年人的世界里。
1921年,卡夫卡在给马克斯·布罗德的信中写道:“我在壮年的森林中,像小孩子一样地徘徊行走。”
的确,卡夫卡不仅长相上像孩童,他的内心深处还有一颗不可泯灭的童心。卡夫卡曾经这样描绘自己:“有时候我在河堤上散步时,会故意拉扯脸部的肌肉,或把手放在后脑上。可能有人会以为这是很无聊的游戏,是很孩子气的。但是,对我而言,却是很完善的游戏。如果与里尔克年轻时奔放的行为比 较,我 的 行 为 实 在 太 天 真、太 像 小 孩 子了。”
1919年11月卡夫卡给父亲写了那封著名的长信。他在信中回忆了青年时代去犹太教堂的情形:“在那漫长的好多个小时中我不停地打呵欠和打瞌睡(我想,后来我只有在上跳舞课时才感到这么枯燥过),并不断尽可能在那里的一些小小的变化中寻找欢乐,比如人们打开约柜,这总使我想起游艺射击棚,在那里若有人击中黑心,一扇小门就会打开;所不同的是,那里出来的总是有趣的东西,这里出现的却永远是一些无头的木偶。”
这时卡夫卡已经36岁了,但是,在这里我们仍然能够发现卡夫卡那颗单纯的、充满强烈好奇的童心。1924年,在卡夫卡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卡夫卡经常和朵拉一起在墙上做影子戏,以此为乐。“当他们即兴创作童话和传说中的故事和场景时,这光线与黑影的戏剧,不靠实体上的俗艳之物,在墙间舞蹈、跳跃。”
对于卡夫卡来说,迫近死亡“好像使他更亲近他的童年”,而他自己则明确表示:“任何能保持发现美这一能力的人都绝不会衰老。”卡夫卡的朋友布罗德认为,卡夫卡像克莱斯特一样具有一颗“童稚之心”,而“童稚并非弱点,这只是对存在的不幸的 基 本情 况的一种比较诚实、比较认真 的理解”.总之,“卡夫卡性格的奇特之处,在于他主要是希望他的父亲理解他,体谅他看书时和后来从事文学写作时的孩子气,在于他没有把他从童年开始就和本质的东西、和他内心的特点结合在一起的东西抛在唯一不可毁灭的成人社会之外”.法国当代著名理论家德勒兹曾经提醒我们,“伟大诗人所写的也许与他曾是小孩或他喜欢的小孩有直接相关。”
德勒兹的论断尤其适合卡夫卡这类作家。
大约是在1923年11月,有一天,卡夫卡在柏林的一座公园里散步,他碰见一个小女孩在哭泣,说是把玩具娃娃弄丢了。为了安慰这个小女孩,卡夫卡硬是说那玩具娃娃动身旅行去了。卡夫卡说知道这件事,是因为娃娃给他写了信。第二天,卡夫卡写了一封信,拿给小女孩看。在信里,玩具娃娃说明了自己想到别处走走的想法,并保证会继续报告自己的消息。借助卡夫卡的编造,丢失的玩具娃娃确实不断“发”来消息:它长大了,上学了,过起了小女孩的生活。这个故事持续了好几个星期,到该结束的时候了。卡夫卡犹豫了好久,最后痛下决心,在一封像尾声的来信里,他让玩具娃娃嫁了人。
他描写了玩具娃娃与意中人相遇的情形,描写了订婚议事,为婚礼做的准备,新婚夫妇的房子,就像描绘自己的那些经历。玩具娃娃切断了线索,再也见不到小女孩了。不过,小女孩被这个略显残酷的长篇小说迷住了,早已忘记了失去玩具娃娃的忧伤。
卡夫卡非常喜欢童话,知道优美的谎言可以使人忘记痛苦。
大约半年后,1924年6月3日卡夫卡在维也纳近郊的基尔林疗养院去世。没有人知道那个丢失了洋娃娃的小女孩,没有人知道她的真实姓名,没有人读过在那三个星期里卡夫卡给小女孩写的信。在卡夫卡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朵拉隐约地向人们说起过这件事。这个故事1952年首先以法语发表,1984年该故事被翻译成英文出版。此后,卡夫卡学者们开始在公园附近寻找那个小女孩,他们在柏林的几家报纸上刊登了广告《谁在公园里遇见了卡夫卡?》。著名的卡夫卡研究者瓦根巴赫则一直在试着寻找那个小女孩。“他围着公园附近的居民区挨家挨户地敲门,询问周围的邻居,甚至在报刊上刊登寻人启事。很遗憾,他所做的一切都没有结果。但是他没有放弃希望,多年来他一直经常去那个公园,直到有一天,他终于找到了那个小女孩。他问她是否还保存着那些信件,而这些信件最终成为20世纪最伟大作家之一---卡夫卡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2004年西班牙作家霍尔迪·塞拉·依·法布拉(Jordi Sierra I Fabra,1947-)据此创作了童话《卡夫卡和旅行娃娃》。该童话曾多次获奖,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至今再版翻印了21次,还被改编成话剧,获得了极佳的评价和反响。作者在书后的《后记》中写道:“就我而言,我被允许改写这个故事,虚构了这些信件,给了它一个想象的结局。不管事实究竟怎样,我觉得都已经无所谓了。这段故事本身是那样的美丽,至于其他的,都不再重要了。最毋庸置疑的是,那些信是如此的精彩纷呈,给我的心灵带来了许多欢乐。”
卡夫卡面对伤痛的儿童时情不自禁地编织了一系列美丽童话,抚平了儿童受伤的心灵,儿童则伴随着这些童话也渐渐长大成人,并成为卡夫卡文学世界里的成年主人公。卡夫卡的童心和童话故事又直接影响或激发了当代童话作家的创作,使他们创作出当代杰出的童话故事,因此法布拉说,他要特别感谢那个匿名的小女孩和《变形记》的作者卡夫卡的杰出贡献。
二、童话思维
“童话(M?rchen)这个术语源自古高地德语'm?ri’、中世纪哥特语‘mers’以及中古高地德语'm?re',它最初的意思是新闻消息或者闲话杂谈……在英语中,fairy tale(童话故事)这一词语并非源自德语的‘Volksmarchen',而是源自法语的'conte de fees',比较而言,属于现代用法……根据《牛津英语词典》,英语中首次出现fairy tale一词是在1750年……很显然,童话故事指的是由16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的中产阶级或贵族阶级作家改编的文学故事类型。”
?卡夫卡的童话思维应该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童话思维,相当于儿童思维;第二层意思是德国文化中所特有的“艺术童话”思维,这种思维对于德国文学传统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这里先说第一层意思,卡夫卡不仅怀有一颗永恒的童心,他还一直对儿童充满关爱,善于运用儿童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保持一种近似于儿童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关于儿童的好奇心和想象力,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
卡夫卡的想象世界似乎就包括了这样一个世界。卡夫卡总是用新的眼光去发现和揭示生活的神奇,用卡夫卡自己的话说,就是“永恒的童年时代。生活的又一次召唤!完全可以设想,壮丽的生活就在每个人的周围,它永远那么丰富,但是被掩盖着,无法看见,极其遥远”.儿童眼光或童话思维使卡夫卡看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这个世界普通成年人总是视而不见。卡夫卡“掌握了某种特殊的童话发明和编织故事的能力,这与他迷恋早年的生活有关,童年时代,孩子们总是将所见所闻看作是着了魔的、梦一样变幻的世界”.卡夫卡的一生,他这种童话思维似乎永远具有魅力。
1913年9月,卡夫卡在意大利北部里瓦的一家疗养院遇到了来自贝鲁克的19岁姑娘格尔蒂·瓦斯纳,卡夫卡经常以奇特的方式与她约会,譬如以敲击房顶为暗号,因为瓦斯纳恰好住在他楼上的斜对角。1913年10月20日,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我很喜欢写童话(我为什么要痛恨那个词呢?)来取悦W(格尔蒂·瓦斯纳),她有时会在吃饭时把它们放在桌子下面,在上菜的间隙读它们,当发现疗养院的医生已经站在她身后盯了她许久之后,她会害羞地脸红起来。她有时会激动---实际上她听故事时始终都是激动的。”
这场短暂的艳遇对卡夫卡影响很大,他甚至承认:“在里瓦的停留对我来说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我第一次理解了一位基督徒女孩,几乎完全在她的影响下生活。”
看来,卡夫卡总是乐意为年轻姑娘讲童话或编写童话,而这些童话反过来又影响了卡夫卡的生活方式乃至创作方式。1916年9月,菲利斯听从卡夫卡的建议,到柏林犹太人民之家从事志愿工作。犹太人民之家主要负责对生活拮据的犹太家庭中的青少年进行民族和宗教教育。菲利斯在那里负责孩子的教学和儿童图书馆的工作,卡夫卡经常给她寄去一些儿童读物。
1916年10月31日,卡夫卡在致菲利斯的信中写道:“这些书各个年龄组的人都能看,没有必要把它们小心翼翼地和其他书分开。绿色的夏夫斯坦的书,也是我最喜欢的书,给那些男孩子们看最好,不过,我不想一下子全寄去,这些下回再寄。比如,其中有一本我读起来觉得特别亲切,讲的就好像是我的故事,或者说是我的生活准则,而我正在摆脱或已经摆脱这种准则(我常有这种感觉),这本书的书名是《糖果男爵》,书的最后一章是最主要部分。另外,很难判定哪些书算儿童书。”
《糖果男爵》是奥斯卡·韦伯的插图本作品,讲述一个前德国军官在南非的经历,卡夫卡特别喜欢读这类儿童读物。在卡夫卡看来,童话不仅是欢快的、愉悦的,而且也是“流血的”.“每个童话都来自血液和恐惧的深处。这是所有童话共同的地方。表面是不同的。北方童话不像非洲黑人童话那样有许多想象中的动物,但是核心、渴念的深度是相同的。”
为了证实这一点,卡夫卡还向雅诺施推荐弗罗贝尼乌斯编选的非洲民间故事和童话集。
这就涉及童话的第二层意思,即德国文学中的“艺术童话”概念。在这种艺术童话中充溢着一种童话精神。“童话作为精神,自发、天真、未加雕饰的产物,除却反映精神本来面目外,不能很好地反映任何东西。”
早在19世纪的德国,“人们总倾向于把童话故事认定是一种特定作家世界观的理想主义的表达,或者作为逃避现实的表达”,“所有的浪漫派作家都致力于在童话故事中或者通过童话故事来表现、理解和评论变化中的时代的本质因素,并且这一共同目标造就了直到当今的童话故事的总体特征”,“事实上,童话故事已如此根深蒂固地沉淀在德国的文学传统之中,以至于从19世纪初一直到现在,几乎没有一个重要的德国作家不以某种方式应用或者创作过童话故事”,用诺瓦利斯的话来说,就是“所有的事物都必须像一个童话故事”. 诺瓦利斯说:“不妨说童话是诗歌 法规。……一切诗意作品都须像神话一般。”一篇童话,实际上犹如毫不连贯的一幅梦中图画,是种种令人惊叹的事物和事件的汇集,好比一部音乐幻想曲,一台伊奥里安竖琴的谐和组曲,或者说大自然本身。总之,万物都是童话。
小说(Roman)只是童话(M?rchen)的一个变种。诺瓦利斯继而说道:“真正的童话故事作家是未来的预言者。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一定会成为一个童话故事---它将重演自己在初始阶段的历史。”
德国浪漫派童话是对德国古典民间文学传统的一次反叛和颠覆,它提倡一种“无形无拘、神秘莫测、偶然性人物和情节、开放性结局”的写作观念和创作方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国浪漫派童话思维就是卡夫卡的创作思维,而童话阅读则并不专指儿童的阅读。“每个童话都来自血液和恐惧的深处”,这似乎正好是卡夫卡小说的最重要特征。
三、童话世界
当代西方童话研究者在论述刘易斯·卡罗尔和他的两部“爱丽丝”小说时指出,“人们能够从两部’爱丽丝‘小说中发现许多后来体现在不少20世纪的文学大师笔下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因素”.“卡夫卡笔下的审判相似于《爱丽丝奇境漫游记》中由国王和王后把持的对红桃杰克的审判,发生在《城堡》里的事情相似于’爱丽丝‘故事的国际象棋游戏,那些能说会走的棋子对于棋赛本身的计划一无所知,完全不知道它们是出于自己的愿望而行动呢,还是被看不见的手指摆弄着行走。”
至于《变形记》,人们在《爱丽丝镜中世界奇遇记》第三章“镜中世界的昆虫”中已经见识了这种人与昆虫之间的互换体验,尤其是那只声音微弱,只能在爱丽丝耳边说话的小蚊子。由此可见卡夫卡的小说与童话的密切关联。
看来,对卡夫卡的任何阅读和阐释也许都是片面的,这种片面之一也许就是缺乏儿童的视角和经验,忽略了他笔下那个近似于童话的世界。所谓童话就是以少年儿童为主要对象,富有幻想性与趣味性的故事。童话大致可以分为三类:1.采用拟人手法,以各种自然物体,主要是动物作主人公的动物童话;2.借助于仙人、精灵和魔法、宝物等来展开童话叙述,具有神奇特征的神奇童话;3.具有传说色彩的传奇童话。
“童话故事实际上就像是一个梦境,没有连贯性,是奇异之事和奇异遭遇的汇聚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卡夫卡创作的文学世界就像一个童话世界。“他选择的是他作品的主人公那抑制不住的任性、他们的孩子气、他们那令人担心的漫不经心的作风、他们那引起纷纷议论的行动和有关他们态度的明显谎言。”
有趣的是,卡夫卡对自己的作品也曾一度持这种看法。卡夫卡在认识菲利斯后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不相信,在哪一则童话故事里曾有人为了追求一个女子,而比我在心中为了追求你作过更大、更不顾一切的奋斗,从一开始即是如此,而且不断反复重来,甚至直到永远。”
“把格奥格·本德曼当作屠龙的英雄格奥格?这若称不上是不顾一切的许婚承诺,那又是什么呢?还是这也不过是个童话?”格奥格·本德曼是卡夫卡的著名的短篇小说《判决》中的主人公。该小说写成于1912年9月23日,卡夫卡一气呵成,在极度的兴奋中完成了这篇小说。此时卡夫卡29岁,这是他自己满意的第一篇作品。小说中的主人公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卡夫卡自己,小说是题献给卡夫卡的女友菲利斯的。这是否就意味着该小说是卡夫卡写给女友菲利斯的一则童话?
不但《判决》如此,卡夫卡的许多小说都可以当作童话来阅读和理解。卡夫卡创作的第一篇小说《一次战斗纪实》就“显然有童话色彩”.卡夫卡的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中,《美国》可以看作是一则有关“美国”的童话,一则有关崭新的国度的童话;《诉讼》是一则有关“法”的童话,一则有关“罪与罚”的神话;而《城堡》就是一则有关“城堡”的童话,一则有关主人公K“追求和寻找”的童话。甚至有学者说,“没有比《城堡》中的K和《审判》中的约瑟夫·K更孩子气,内心更没礼貌的了”.
当然,卡夫卡心目中的童话与德国文学传统中的“童话”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
1795年,歌德在中篇小说《德国逃难 者 的 闲 聊》中 安 插 了 一 则 《童 话》(DasM?rchen)。这篇《童话》的内容无非是讲述某美女遭受种种痛苦和磨难,最后在好心人和神奇动物的帮助下,终于同亲王结婚,并当上了王后。这是一则象征-寓意作品,但其中的具体人物和动物象征什么,却并不那么明确,读者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因此这部作品意味深长,难以解释。小说中讲故事的老神父甚至明确表示:“请不要对我讲的故事做任何解释。”
歌德的这篇《童话》是德国文学中的“艺术童话”(Kunstm?rchen)的先导,对日后德国文学,尤其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深远。准确地说,歌德的童话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童话,而是以童话的形式写的中篇小说。如此看来,卡夫卡的那些中长篇小说也可以看作是以童话形式写的小说。歌德这则童话的特点其实也预示了日后卡夫卡小说创作的诸多特点。
卡夫卡写过一系列与动物有关的小说,如《变形记》《一份致某科学院的报告》《地洞》《新来的律师》《鸢》《一条狗的研究》《家父的忧虑》《一只杂交动物》等。卡夫卡的作品里有一系列动物形象:大甲虫、猴子、狗、鸢、耗子、像猫又像羊羔的杂种、地洞里不知名的小动物、亚历山大的战马、亚洲胡狼、巨型鼹鼠等,不胜枚举。这些小说大体上都可以看作是动物童话。卡夫卡还创作了一系列涉及魔法、奇幻的小说,如《家长的忧虑》《老光棍布鲁菲尔德》《猎人格拉胡斯》《铁桶骑士》等,这些小说则可以看作是神奇童话。卡夫卡一系列以古希腊神话人物为标题的小说,如《塞壬们的沉默》《普罗米修斯》《海神波塞冬》等,还有一系列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如《万里长城建造时》《往事一页》《一道圣旨》等,都可以看作是传奇童话。另外,像《乡村医生》这类小说颇有童话动漫特征,因此日本艺术家很自然地将其改变成动漫片。
《变形记》可以看作是一篇典型的童话。“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主人公为什么要变形?为什么变成了甲虫?变成甲虫后的格里高尔将怎样生活?他身边的人如何对待甲虫?他还会变成人吗?读者对此充满了好奇和想象,小说的魅力和意义也由此渐渐展开。在童话故事中,有一种叫作“变形记”的叙事模式,即“主人公经历了一种转变,从而获得了超越自身生活的能力”.“如果一个人醒来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如果这些事情能够发生的话,那么,后来的一切便肯定能发生了……我们必须首先接受这个最初的想象,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以爱丽丝在奇境中走近’吃掉我‘蛋糕时的心情来探讨这两位作家(卡夫卡与果戈理)。”
?在童话中,爱丽丝渴望变形:“通常吃一块蛋糕是很正常的事儿,可是爱丽丝总想有奇迹发生,否则事事照常、生活就太单调无味了。”格里高尔则在不知不觉中变形,他的变形完全是被动的,或者是“被变形”.因此,卡夫卡的《变形记》应当是一种反向的“变形记”,或者叫作现代“变形记”,即“格里高尔经历了一种转变,从而失去了他原本具有的生活能力”.
由于小说的这种鲜明童话特征,它已被改编成各种童话读物和动画片。比如1999年大卫·劳伦斯撰文、图兰德·戴尔菲绘图编写了《卡夫卡变虫记》,该书2000年在台湾被译成中文。至2009年,该书已经是第25次印刷了。这是一篇典型的童话,童话描写小男孩卡夫卡早上起床,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可是他身边的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只有他最好的朋友麦克例外。当然,童话最后小男孩卡夫卡又变成了人。这则童话让我们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习以为常”使我们往往忽略了身边最亲近的人。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要多久的时间,你才会发现自己的小孩变成一只虫?”
小说也被台北明日工作室股份有限公司拍成动画片《卡夫卡变形记》,长度45分钟。在这里,卡夫卡被誉为“开启想象力的魔法师”.
除此之外,更有甚者,像《在流放地》这样复杂难解的小说也常常被人们当作童话来阅读和理解。
从儿童阅读的视角看,该小说可以被看作是一部探讨儿童成年化、社会化问题的小说。卡夫卡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藉着其独特性来发展自我、产生影响,但他必须喜欢自己的独特性。然而在我的经验中,不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大家都努力抹去这种独特性。藉此世人让教育工作变得容易了,也让儿童的生活变得容易了,只不过小孩得先饱尝强迫所带来的痛苦。”
卡夫卡的解释又一次印证了该小说的童话特征。
卡夫卡无疑是个孤独的艺术家,但他“在极度的孤独中孕育着对社会和人类的爱”.基于这份爱,儿童阅读卡夫卡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由于卡夫卡的世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没有年龄鸿沟的世界,儿童可以从这里顺利地进入青年世界、成人世界,因此,儿童阅读卡夫卡还应该是必需的,也是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