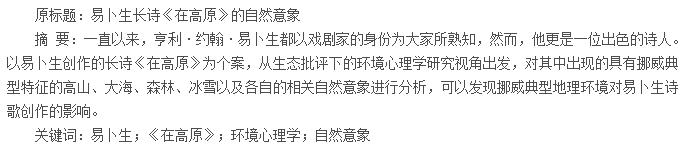
一直以来,亨利·约翰·易卜生(Henrik JohanIbsen, 1828-1906) 都以戏剧家的身份为大家所熟知,学界关于他的研究也大都集中在戏剧方面。然而,易卜生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戏剧大师,也是一位别有洞天的诗人。但是,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易卜生诗歌的研究,相较于易卜生戏剧的研究,只能算是九牛一毛。
从国内来看,最早涉及易卜生诗歌研究的是高中甫先生,他曾在《诗人易卜生》一文中对易卜生的诗歌做了整体评析。1995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易卜生文集》中收录了中译易卜生诗歌共 61 首(第八卷),成为大多数易卜生诗歌研究的样本。
基于中国知网平台的搜索数据,目前国内对易卜生诗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诗歌意象研究,如张廉《论易卜生诗歌中女性形象》、谭永《易卜生诗歌中的四类动物意象》等,着重对意象进行分类并依据分类进行分析;二、文学地理学观照下的相关研究,如邹建军《三种向度与易卜生的诗学观念---对易卜生诗歌的整体观察与辩证评价》、袁艺林《易卜生诗歌中的三重地理空间建构》等,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评析了易卜生的诗作;三、以易卜生具体诗歌为例所做的个案研究,如邹建军、杜雪琴的《易卜生长诗<在高原>的哲学之思与生态之维》、谭永的《<老水手行>与<泰尔耶·维根>之比较》等,力图通过个案分析解密易卜生诗歌密码。其他还有白英丽的《论易卜生诗歌的戏剧性》、王远年的《易卜生诗歌的民间歌谣特征》等文章,分别从不同视角对易卜生诗歌进行阐述。
从国外来看,易卜生诗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易卜生相关网站 中,内容多集中在易卜生的两首长诗《在高原》以及《泰耶·维根》的分析上。
由此可见,易卜生诗歌研究可以说是目前易卜生研究上“亟待补上的空白点”.[1](P124)因此,本文拟以易卜生创作的长诗《在高原》为个案,对其中出现的具有挪威典型特征的高山、大海、森林、冰雪以及各自的相关自然意象进行分析,力图从生态批评下的环境心理学研究视角出发,揭示挪威典型地理环境对易卜生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环境心理学概述
环境心理学作为生态批评的研究方法之一,由生态批评家司各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1960-)提出。斯洛维克以美国自然文学相关文本为研究对象,关注自然在作者心里所引起的共鸣等心理体验。在他看来,自然会在人的内心深处留下烙印。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交融中,人会对自身重新定位并调整与自然的关系。斯洛维克曾提出“荒野经验的内核”[2](P353)这一概念。其中“荒野经验”即人与自然接触过程中收获的经历,“内核”即为人类在与自然交互过程中产生的心理感受。换言之,生态批评中的环境心理学视角的研究对象,是在受到自然刺激下的人内心的应激反应。通过对这种应激反映的研究,可以发现作者的生态观与生态行为方式,从而帮助他人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
斯洛维克环境心理学的提出与布鲁斯·博格(Bruce Berger)的“荒野”概念不无关系。博格曾认为“荒野首先是一种加强人的意识的机遇,是一种定位与非我相对的自我的机遇。它是帮助人内省的跳板,而描写荒野的精辟话语加强了这一过程,它们鲜活地印在人们的内心,为生命启蒙。”[2](P351)在博格看来,在人与自然交往的过程中,自然会成为人反省自己,窥探内心的促进力量。持相类似观点的还有生态批评家沙龙·卡麦隆(Sharon Cameron)。他认为“书写自然就是书写心灵所看到的自然”,[3](P44)更关注到自然与心理的相互作用。环境心理学批评的出现,承袭了美国自然文学中的“心理学传统”,同时扩展了生态批评的研究视角。本文拟以易卜生创作的长诗《在高原》为个案,从生态批评下的环境心理学研究视角出发,对其中出现的具有挪威典型特征的自然意象高山、大海、森林、冰雪以及各自的相关自然意象进行分析,揭示挪威典型地理环境对易卜生诗歌创作的影响。
二、诗歌个案分析---《在高原》
斯洛维克认为,“自然是一种外部的呈现,而写作是将个人的经验变成文字的过程,二者构成作者的自我意识与非我意识。作者面对独立的自然王国,并感受到自然的‘不同性',通过这种方式,作者可以清晰地、更加深切地意识到自身所处的位置、自身形式与理解力的限度。”[2](P353)诗人易卜生亦是如此。在长诗《在高原》中,易卜生塑造了抒情主人公“我”的形象。“我”,一个生长在挪威高山峡湾环境下的小伙子,身边有一位老母,还有一名两情相悦的未婚妻。然而,“我”并不满足于在山谷中度过一生,总是想着向高处进发,去看看高处的风景,从高处俯瞰人群。在向高处攀登的过程中,“我”的母亲葬身火海,“我”的恋人改嫁他人。虽然“我”也为失去亲人、离开恋人而痛苦自责,但是什么都无法阻挡“我”向高处迈进,实现自我价值的脚步。在猎人的精神引领下,“我”终于到达了“高原”,实现了自身理想。
(一)易卜生的“荒野经验”《在高原》中大量出现的自然意象描写构成了“我”的荒野经验。纵观全诗,不难发现,“我”生长于挪威高山、深林、冰雪的地理环境之中。正是这样独特的环境,激发了“我”想向高处探寻的欲望,解放了“我”的天性,让“我”能置身自然之中,勇敢追逐梦想。“月亮把它虚幻的清光从天上洒向峡湾”,[4](P123)“我”沿着林间的小路开启了向上之旅。途中,我遇见了心仪的“她”.
我们两情相悦,携手“向上攀登,向着林莽”.[4](P123)途中休息,“我”躺在山上,想着母亲在山谷中舒适而平庸的生活,心中不免泛起思乡的涟漪。但是,“我”克服了心中的恐惧与依恋,决绝地要“直抵山顶”.[4](P127)走着走着,雾气“遮蔽了山谷”,“我”也身心疲倦。然而眼前火红的杜鹃花激励了“我”,让“我”再次“沿着山间小道向前奔去”.[4](P127)群山让“我”与南方人相逢,但南方人卷帆回溯的想法“我”不能苟同。于是我们匆匆分别,各奔东西。深夜,“我”梦回谷地,在“难道把石块从谷地田野清除出去没有好处?”[4](P131)的诘问中,找到了让自己继续向上的力量。不知不觉,秋天到了,较之温暖平凡的谷地生活,“满天雪花已经落在山脊上,像一面大的地毯”.[4](P134)然而,苦寒的自然没有让“我”低下高傲的头颅,却激发了“我”要把亲人接来携手前行的想法。“他们生活在严寒的山顶,那时候自然变得勇敢。”[4](P135)当“我”要把想法付诸行动时,“雪花飞旋,暴风雪四起!”[4](P135)所有的道路都被封闭,实践只能流产。日子就这样过去,“我”安于山上的生活,热爱那希望之星,皑皑雪原。而山谷中传来的暖曲拨乱了“我”的心弦。这时,猎人的出现重塑了“我”的信念与勇气,“山顶上的风使我变得冷静”[4](P141)。正当“我”
要鼓起勇气继续进发之时,却得知母亲房屋起火,恋人改嫁他人,这让“我”痛苦不已,再次陷入迷惘。凭着坚定的信念与超凡的勇气,“我”最终“走在高处”.“这里有自由和上帝”,“其他所有人都在谷地踱步”.[4](P141)全诗中,无论是“我”起初有了向上攀爬的心愿,还是攀爬过程中遇到了险阻,亦或是“我”身心疲惫,想要回头,又或是“我”在猎人机智的进言下重拾信心与勇气之时,高山、大海、森林、冰雪,这四类自然意象始终以抒情背景出现,作为与人类社会截然不同的“参照物”,构成了抒情主人公“我”的“荒野经验”,成为激发“我”思考人生理想的平台。这不仅是抒情主人公“我”的自我审读的平台,更是诗人易卜生自我审视,重置人生定位的平台。
在自然这个广袤深邃的平台上,易卜生重新思考人生,追寻最高理想。
(二)易卜生的“精神内核”《在高原》一诗中,不仅代表挪威典型地理特征的四类意象作为诗歌的抒情背景出现,诗人更是赋予了它们象征意蕴,成为了“我”的“精神内核”.全诗第一部分第二节中出现了“崎岖通向山中的小路,蜿蜒伸向树林”.[4](P150)“我”沿着这条小路,经过邻人的门前,穿过柔光的树林,踽踽独行,默默向前。期间,“我”拒绝了温婉的未婚妻要我回头的请求,“身后的峡湾深谷和着我月光薄雾下的梦想”.[4](P151)在第二部分,“我”躺在朝南的山谷,看着第一缕阳光,想着远处房子里的母亲和未婚妻。这时的“我”心中思量着母亲和未婚妻的辛苦劳作,心中不免有些动摇迷惘。但是“我”“瞥见峡湾、山川,看着茂密的松林”,[4](P151)便觉得受到了自然的感召,选择了告别母亲和未婚妻,继续向高处进发。这里,森林如同一片神秘幽深之地,吸引着“我”沿着通向林中的小路,不断深入。而路途中经过的峡湾与深谷,则好似“我”不断攀向高处的坚实后盾。诗歌的第三部分,“我”试图和我的未婚妻同甘苦,共患难,一起涉险,“沿着山间小道奔向前去”,[4](P139)迎向新的挑战。第四部分,南方人与“我”相遇了。“我”看着南方人的“眼睛,湛蓝湛蓝,俨然两面冰川的湖”.[4](P140)这里,诗人易卜生以“冰湖”来比喻南方人的眼睛,幽深湛蓝,透着寒气,好似能把“我”的希望吸入幽深的湖底。诗歌的第五部分,“我”梦回母亲和未婚妻居住的山谷,那里舒适温暖,让我留恋不已。但是,更令“我”心驰神往的则是真正能够接近上帝的自然,那里有“更光明”的太阳,“更动人”的暴风雨。这里的“高山”更似一种“我”追求的人生目标,“我”的理想之所在,为“我”克服重重险阻,不断向前提供力量。诗人在第六部分开篇就提到山谷里人们的生活,安逸舒适。然后笔峰一转,再看“我”所在的高山,“满天雪花落在山脊上”,[4](P134)冰冷苦寒。选择在苦寒中攀上高峰还是返回安逸的山谷过活?“我”给出了明确的答复:“我没有一丝留恋”.[4](P134)同时,“我”还想带着母亲和未婚妻一同感受“严寒的山顶”,[4](P134)在那里变得勇敢。承袭第六部分,“我”想同亲人一起生活在“山里的圣殿”,[4](P135)无奈冰雪已经把道路封闭。第八部分中的“我”,已然习惯独自在山里生活,“月亮照亮了皑皑雪原,群星开始发出希望的光”.[4](P136)“我”继续“顺着山上的小路前进”,路上听到山谷传来温暖甜蜜的曲调,让“我”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就是幸福。这时猎人出现,读懂了“我”的心思,给予了“我”激励。这时的“我”比先前更加坚定,一路向上,向山顶进发。尽管目睹了母亲的逝世,但“我”坚信她会在天堂找到更好的居所,这启示“我”更要不畏艰险,勇敢向上。诗歌最后一部分,“我”的未婚妻多年苦等无果,最终选择改嫁他人。这时“我”虽然痛心,但是也为重新属于群山而感到幸福。现在“我”终于登上了山顶,完成了自己的梦想。不同于谷地里生活的人们,“我”在山巅找到了“自由和上帝”.[4](P141)
纵观全诗,不难发现,“高山”及其相关意象总是与“我”的自由理想相联系,与“山谷”的生活相对比。可以说,“高山”就是我理想的载体,在不断攀爬的过程中,“我”得到了锻炼,收获了勇气,找到了“自由与上帝”,成为了“自己的主人”.与之相比,山谷则象征着俗世的生活,如同谷地本身的特质,安逸温暖却狭隘自封。
谷地生活的封闭性促使“我”想要走出去,想要上去,看看山上的风景。而诗中出现的森林及其相关意象,则成为指引“我”通往山顶的引导。“我”最初想上山去,就是被幽深的森林吸引。而使“我”上山成为可能的,则是林间的小路。不断攀爬的过程中,总会遇到些阻碍。诗中多次出现的阻碍都是以“冰雪”及其相关意象为载体。
这里的“冰雪”总是先阻碍“我”的去路,让我迷惘动摇。在“我”战胜了心灵的怯懦后,总会继续向前。于是,原先成为阻碍的冰雪就转化成了“我”向山上攀爬的助推器。在“荒野经验”的刺激下,“我”重新审视自己,对自己一次次进行重新定位,逐渐形成自我意识,实现独立。
这时,“荒野”成为了一种定位自我、提高意识的机遇。而在这种对自然的不断探索,人与自然的相互观照中,诗人易卜生也关注了自身的心理感受,考察了自己的心理变化,书写了心灵中的自然,达到了“荒野经验”与“精神内核”的完美结合。
参考文献:
[1]王忠祥, 杜雪琴。《外国文学研究》与多维视阈中的易卜生评论[J]. 外国文学研究, 2012(01):115-125.
[2]Slovic S. Nature Writing and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M].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ed. Glotfelty, Cheryll and Fromm, Harold. A-thens: U of Georgia P, 1996.
[3]Cameron S. Writing Nature: Henry Thoreau's Journal[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4](挪威)亨利·约翰·易卜生著, 多人译。 易卜生文集(第 8 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