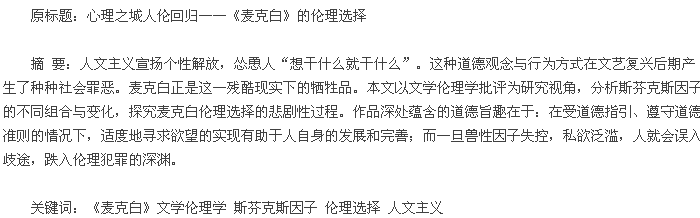
一、引言
《麦克白》写于 1606 年 ,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最后一部,也是篇幅最短、戏剧动作发展最迅速的一部。莎翁以其精妙的手笔为我们展呈了悲剧主人公麦克白受欲望和野心驱使,一步步放弃理性,沉沦堕落难以自拔并最终走向毁灭的心路历程。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将文学置于它所属的伦理环境是理解文学的一个前提,“伦理环境就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聂珍钊,2010)。 文艺复兴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人文主义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标签:它宣扬人本身的价值和尊严,鼓励人追求现世的幸福;人文主义者力图在现实世界中证明自己的能力。但人性解放的同时也出现了种种社会罪恶,人们的欲望不断膨胀,利己主义盛行。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理想与残酷的现实之间产生了剧烈的冲突,导致他由积极鼓吹和宣扬新兴的资产阶级文化,歌颂人文主义理想, 转为揭露和批判社会的罪恶和黑暗,满怀抑郁愤懑的情绪写下了一系列悲剧,《麦克白》便是这种伦理环境下的产物。
文学伦理学强调,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有机结合而成的斯芬克斯因子是理解文学作品的核心,认为“斯芬克斯因子的不同组合和变化, 将导致文学作品中人物的不同行为特征和性格表现,形成不同的伦理冲突,表现出不同的道德教诲价值”(聂珍钊,2011)。 麦克白由忠臣到叛臣的转变,正是其斯芬克斯因子不同组合和变化的结果。
二、伦理选择:不安分的兽性因子,挣扎中的人性因子
《麦克白》 的一大突出特点是大量冗长内心独白的运用, 珍妮特·狄龙认为这正是塑造麦克白悲剧形象最有力的手法(Janette Dillon, 2007)。 事实上,内心的激烈冲突充分展示了麦克白身上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角逐。 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并存于人身上,共同组成了斯芬克斯因子。 其中,人性因子作为高级因子能够控制与之相对的兽性因子,从而使人保持人的本性。 文学伦理学认为,人区别人兽的最本质特征在于人具有理性和伦理意识。《麦克白》正是大量运用表现主人公内心冲突和挣扎的独白为我们展现了麦克白伦理选择过程的悲剧性。
(一)弑杀邓肯:兽性因子初露头角
序幕刚拉开时的麦克白高贵勇敢,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为平息麦克唐华德的叛乱立下赫赫战功。 麦克白为守卫苏格兰而战,为邓肯王而战,也为自己的荣耀而战,不仅颇得邓肯王的恩宠,而且博得满朝贵族的仰慕,可谓是人民的道德楷模,周身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但英雄的麦克白身上也存在着兽性因子。 麦克白出场的第一句台词便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阴郁而又光明的日子”(莎士比亚,390),“阴郁而又光明”表明了其兽性因子与人性因子的矛盾统一。在女巫闪烁其词、模棱两可的预言之下,麦克白内心的欲望和野心被唤醒了。但此时人性因子依然占上风的麦克白信奉,“要是命运将会使我成为君王,那么也许命运会替我加上王冠,用不到我自己费力”(莎士比亚,393)。 因此,即便脑海中偶然浮起的杀死邓肯王的妄念也使他“毛发悚然”“全身震撼”,使他的心“全然失去常态,扑扑地跳个不住”(莎士比亚,393)。
当邓肯立马尔康为储君, 册封其为肯勃兰亲王时, 麦克白感到命运为其加冕的机会怕是不会来了,“肯勃兰亲王!这是一块横在我的前途的阶石,我必须跳过这块阶石, 否则就要颠仆在它的上面”(莎士比亚,394)。 他内心的欲望在膨胀,“星星啊,收起你们的火焰!不要让光亮照见我的黑暗幽深的欲望。眼睛啊,看着这双手吧,凡它做出的你都要敢于面对”(莎士比亚,394),决定要为自己的前途去奔忙。 作为邓肯王的表弟、邦国的臣子,麦克白深知,“无论从哪一种伦理关系来说, 他将采取的行动都是伦理犯罪”(陈曦,黄宁,2010)。 他更是对乱伦表现出了极端的恐惧, 认为“在这种事情上,我们往往可以看见冥冥中的裁判;教唆杀人的人,结果反而自己被人所杀;把毒药投入酒杯里的人,结果也会自己饮鸩而死”(莎士比亚,398)。
最终,“跃跃欲试的野心”和妻子的怂恿蛊惑让他决定“要用全身的力量,去干这件惊人的举动。 去,用最美妙的外表把人们的耳目欺骗;奸诈的心必须罩上虚伪的笑脸”(莎士比亚,399)。
在与兽性因子的角逐中, 人性因子不会轻易言败。 当麦克白准备对邓肯行凶时,眼前出现了一把刀子,他十分清醒这只是一个“幻象”,是“杀人的恶念”使他看见这种异象。他听到有声音喊着“不要再睡了!
葛莱密斯已经杀害了睡眠,所以考特将再也得不到睡眠,麦克白将再也得不到睡眠”(莎士比亚,403)。 麦克白夫人却只听到了“枭啼和蟋蟀的鸣声”,表明这是麦克白的想象。 恍惚中的麦克白忘了把刀子留在现场,“不敢回想刚才所干的事,更没有胆量再去看它一眼”(莎士比亚,403)。 战场上骁勇无敌的麦克白此时成了意志薄弱的懦夫,是因为他前者是符合伦理纲常的正当行为,而弑君乃是触犯当时伦理禁忌的重罪。
(二)谋杀班柯:兽性因子步步进逼
麦克白施行了伦理犯罪, 挥刀杀死了邓肯王,登上了王位。但篡位成功的麦克白却永远失去了内心的安宁,失去了“睡眠”,终日与愁思苦想、恐惧疑虑做伴。 初露头角的兽性因子开始步步进逼,麦克白在日日渐增的害怕恐惧中,为巩固王位,实施了进一步的伦理犯罪,走上了更血腥的道路,苏格兰成为了一个“在毒手压制下备受苦难的国家”(莎士比亚,422)。
按理说,登上王位的麦克白应该行使王权、富国安民、保护臣民。 班柯此时作为他的臣子,且表示“我的忠诚永远接受陛下的使唤”(莎士比亚,410), 麦克白理应待其为上宾,而非对其下毒手。 但是班柯却是他最深的恐惧,因为女巫曾预言其后裔将为王,自己坏了心术夺来的王位无法传于自己的子嗣,这是决不能容忍的。这一次,麦克白手段更为阴险,选择了借刀杀人而非亲自操刀。 当他得知班柯已死时,是多么心满意足啊, 然而当得知班柯之子弗里恩斯逃亡时,瞬间又陷入了犹疑与恐惧之中。未曾失落的人性因子又为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宴会上麦克白看到班柯的鬼魂坐于其位,吓得魂不附体,胡言乱语泄露了其内心的隐秘,“你不能说这是我干的事;别这样对我摇着你的染着血的头发”(莎士比亚,417)。 即便是非常清醒这只是“可怕的影子”“虚妄的揶揄”(莎士比亚,419),麦克白仍旧表现出异常的恐惧,因为他的伦理道德不允许他干出谋杀班柯这样的事,他深知自己的伦理犯罪天理不容。 然而,人性因子的抗争加剧了兽性因子的发作。 麦克白泥足深陷,无法自拔,认为“我已经两足深陷于血泊之中,要是不再涉血前进,那么回头的路也是同样使人厌倦的”(莎士比亚,420)。
如果说弑杀邓肯后,麦克白的兽性因子还只是初露头角,那么谋杀班柯后,兽性因子则在步步进逼中取得了进一步的胜利。 在兽性因子原始欲望的推动下, 麦克白在沉沦与堕落的伦理犯罪道路上越陷越深,难以回头。
(三)残杀妇孺:兽性因子全面失控
兽性因子在麦克白身上占据绝对优势,击败人性因子是在麦克白主动造访三女巫之后。决定造访女巫是麦克白对兽性因子的主动召唤和迎接。 “为了我自己的好处,只好把一切置之不顾。 ”(莎士比亚,420)三幽灵对麦克白“留心麦克德夫”的告诫和八代君王依次显现的幻影正中麦克白内心的隐秘和恐惧,“没有一个妇人所生下的人可以伤害麦克白”和“麦克白永远不会被人打败,除非有一天勃南的树林会冲着他向邓西嫩高山移动”的承诺进一步打消了他的犹疑和懦弱,坚定了他邪恶的道路。 当得知麦克德夫逃亡英格兰时,他意识道:
再狠毒的计划,行动一旦跟不上,也会落空。从这一刻起,我心里一想到什么,便要立刻把它实行。
没有迟疑的余地;我现在就要用行动表示我的意志:
我要去突袭麦克德夫的城堡;把法夫夺下来;把他的妻子儿女和一切追随他的不幸的人们一齐杀死。
我不能像一个傻瓜似的只会空口说大话,我必须趁着我这一个目的还没有冷淡下来以前把这件事干好。 (莎士比亚,428)可见,此时的麦克白已经被兽性因子掌控,决定不顾一切追随原始欲望。这一次,他没有半点的犹疑,迅速带领刺客踏平了麦克德夫城堡费辅。 在这个“做了恶事才会被人恭维赞美,做了好事返会被人当做危险的傻瓜”(莎士比亚,430)的世上,麦克德夫的妻子儿女及其血亲惨糟无情的屠戮,死于非命,做了麦克德夫的替死鬼。麦克白统治下的苏格兰,“叹息、呻吟、震撼天空的呼号,都是日常听惯的声音,不能再引起人们的注意;沉痛的悲哀变成一般的风气;葬钟敲响的时候,谁也不再关心它是为谁而鸣;善良人的生命往往在他们帽上的花朵还没有枯萎以前就化为朝露”(莎士比亚,434-5),简直连它都不敢认自己了 ,人民也不敢再称它为“母亲”,而只是“坟墓”。
三、肉体的毁灭,人伦的回归
伦理选择的实质是做人还是做兽。在欲望被唤醒并逐步扩展最终将麦克白吞噬的过程中,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进行了不断的抗衡,表现为麦克白内心的激烈冲突。麦克白从一个人性因子控制兽性因子的道德楷模沦落为一个兽性因子失控伦理罪人,悲剧性地完成了做人还是做兽的伦理选择。而“扔掉雄壮的盾牌,血战到底”(莎士比亚,447)这种以毫不悔改的姿态完结自己生命和伦理犯罪的行为,更增加了麦克白的悲剧性。
正如莎士比亚悲剧的所有主人公一样,麦克白最终走向了死亡,但他在其悲剧性伦理选择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度伦理自觉和难以自拔的沉沦堕落却给观众及世人带来了深深的震撼,让人不可自控地对其给予深切的同情。麦克白以其悲壮性的毁灭警示世人兽性因子失控, 原始欲望泛滥将带给人的严重后果。
尽管《麦克白》反映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现实,敲响的是当时的时代警钟,然而,麦克白却是对人性的充分阐释,莎士比亚对人伦回归的呼唤却适用于所有时代,难怪本·琼生说他“不是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所有世纪”。
参考文献
[1] Janette Dillon.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Shakes-peare’s Tragedies [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2] 陈曦,黄宁.麦克白:伦理身份的转换与自我毁灭[J].湖南大学学报,2010(3):100.
[3]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悲喜剧[M],朱生豪,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
[4]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19.
[5]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J].外国文学研究,201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