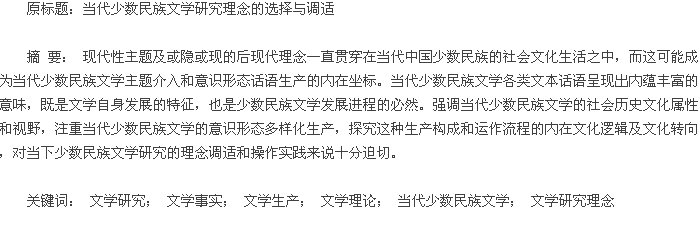
文学理论是人类文学活动规律的总结,到目前,古今中外文学理论是都能够阐释说明所有文学的性质、功能和作用的,在一定意义上说,理论是普世、也是普适的。但是,理论在运用时总是表明或流露出使用者主体选择某一理论的动机,不管是出于社会性的功利要求,还是出于民族自我的尊严或自我保护,或者是出于当代文学研究者的个人私我用心,动机决定了使用者对某种文学理论的乐此不疲操作和留恋不舍的标准。同样,文学理论其实每天面对的和需要阐释的问题是,为什么摆在我们面前的文学现象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为什么在西南、中南、华南地区是这样,而在西北的新疆就不是那样的文学事实? 就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而言,创作和批评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所有呈现,都是少数民族主体文学实践的产物,而其中的规律性特征,是需要文学理论和批评来予以阐释和说明的。
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要关注文本的内在结构变化
在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视角与内容与主流汉文学的研究确实是有点不一样的,在这个“有点”中,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异和区别。为什么会这样? 这就因为是“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由于历史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原因,具有特殊性,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的特殊性,不管作为一个汉族研究者你是否抱有对历史的承认理解和同情宽容之意,这个特殊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无法消失的。所以,当经过一段时间诸多西方理论的旅行之后; 当我们用当代中国主流文学的研究范式来打量并介入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时; 同时,当我们身处少数民族文学产生的区域性环境,把自己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理论诉诸于少数民族文学产生的区域性环境中对自己理论进行感性验证时,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习以为常正在操作的一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理论似乎不能完整地阐释说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诸多现象,也不能真正阐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为文学事实的社会文化意义的生成动因。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研究思路是从文学反映论出发,从创作与意识的关系出发,把文学活动看成是人的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认识与反映,文学是现实的模仿,文学通过语言创造反映现实,反映特定的社会历史生活和社会意识形态。而在对历史的反映呈现和叙述时,预先设置的历史进程或面貌被宏观叙事崇高化,用英雄人物代替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芸芸众生,通过疏离日常生活和非个人化的叙事来表现社会组织集团的世界观及精神价值取向,并始终与之同构。文学反映论变为主流意识形态表现论的简单传递。这是一种相对单一静态的理论范式。同汉文学一样,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长期文学反映论的决定性影响下,在创作上看,作品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少数民族生活的反映和表现,是对党和国家民族政策、各民族团结、各民族人民生活蒸蒸日上、社会主义建设等主旋律的歌颂和赞美,甚至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定历史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也成为反映时代阶级和路线斗争的直接或间接的工具。如在新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运动中,新疆有不少各民族作家和诗人,也都像铁依甫江·艾力耶夫那样:作为“战斗的无产阶级/立刻识破了敌人的鬼把戏,/向敌人发起了反击。/ /敌人吓得发抖了,/悄声的躲进了黑暗的沟渠,/用‘民族’称号来掩盖丑恶的嘴脸。/紧紧追! 我们从四面八方乘胜追击! /‘举起手来! / /赶快放下武器! /你们的失败是历史注定的……',/我们的声音震天动地。/ /我们是生活在社会主义祖国的民族。/要彻底根除意识中的地方民族主义,/有一天,人们都会把这肮脏的名词忘记。”[1]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直至现在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看,这样的作品很多。虽然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也不乏主观表现抒写的作品,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这种主观化表现的作品仍然是在反映论影响下的创作,是社会主义时代的主旋律之歌①.
然而,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和全球化不断推进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学的情况在逐渐发生变化。从创作看,对社会主义、国家、领袖歌颂和美化的少数民族作品逐渐减少,取而代之是部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对民族日常生活、民族文化和民族自我主体性的单向性强烈表达。即使是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中,也几乎没有他族的人物形象,这在多民族地区的城市生活中是难以理解的。一个城市里的某个民族居民在日常的生活中,实际上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民族的同事、职业者、邻居发生各种自在性的联系,而这种自在性的联系本身是每个民族日常生活的实质性内容。如果说是现实主义叙述的话,那么这种少数民族日常性的生活表达中应该是有“他者”民族存在的。因为“从叙事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看,虽然,叙事不同于日常生活,指称的是有顺序的虚构作品,叙事比日常生活要集中、概括,叙事要突出特别的人和特别的冲突、问题、威胁或使生活变得复杂的任何事物; 而日常生活往往被看成是真实的、自在性的、相对平凡的。这是因为日常生活存在于每一社会之中,构成了任何个体存在的基础。”[2]
所以,日常社会已成为现代性的表征或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叙事中如果有意为之地淡化或缺少这种不同个体、族群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互动,仅仅是单一性的族群个体叙事,这显然是力图用鲜明的民族主体性作为文学最高和最终的价值目标,并以此来回避、遮蔽或代替全社会的公共性。这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创作倾向对部分或个别民族作家来说趋之若鹜,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实践中并非鲜见。
另外,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实践中,部分或个别民族作家通过多种文化关系的表现对主流社会及主流意识形态进行疏离。一些作家不想让自己的本民族概念化、抽象化、诗意化,而是想让民族在自己的笔下具体起来,常常在对本民族往昔和当下的具体表述过程中,大肆赞美和铺陈具有民族文化身份意味的自然地理、故事传说和各类古今人物等等。相反,非民族文化身份在这里仅仅是作为参照物被简单地提及,当然有时也会被作为反讽的对象加以呈现和描述。在这里,不管是寓意象征还是挪揄反讽,都隐含着与“他者”文化的潜在区隔。
可以看到,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文学在今天是被生产出来的,而不再仅仅是反映表现出来的。
当然,少数民族文学的“生产”从文学制度的视角看,其实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当“少数民族文学”被提出来后,就已经被国家组织化地进行了“生产”,只不过这种“生产”是统一化的也是同一性的“生产”.这种“生产”是建立在少数民族文学必须与国家意识形态一致和反映表现社会主义国家各兄弟民族新生活的规约基础上的。在文学被高度组织化并成为社会时代的关注中心时,少数民族文学的“生产”材料来自一体化的意识形态渗透影响和灌输,这样的“生产”只能是反映表现,或者说是被反映、被表现。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当文学从社会时代的中心被挪移至别处时,被高度组织化的少数民族文学“生产”与汉文学一样,都面临着对反映表现对象的重新考量整合,文学从一体化的意识形态规约中走出,其中相当一部分就很难再重新进入。挪移至别处“边缘”化的文学很容易在多种文学生产材料和文学消费者面前另起炉灶,这同样对少数民族文学来说是一个契机。少数民族文学要借此完成本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补课”,并积极介入当代中国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中。虽然,少数民族文学也同样处于边缘境遇,但由于民族主体意识的强化,部分民族作家个体不受制于机制的约束,创作相对自由,他们可以从容地进行关于本民族进入现代进程的虚构叙事及历史想象抒写,并采用传统的口头文学样式和大数据时代文学的多种方式进行影响传播。这时,少数民族文学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少数民族文学话语所表达的知识和意义,就不再单纯是社会历史事件的被动反映或者主观意向的表现,而是一种积极生产、一种主动建构了。
如在新疆维吾尔当代口头文学中,阿凡提式的机智、幽默、辛辣,以及经过知识分子文学处理后的隐喻、反讽等意味,同时出现在一个个笑话故事或段子之中,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包含着民族知识情感共同体的表达。在新疆的少数民族或族群的当代口头文学中,时常都可以看到在不同民族或族群在场的语境中各自机智地表现本民族或族群身份意识优越性的笑话、故事、段子、扯淡等。乡村的不说,就目前城市口头文学---笑话的创作者队伍看,传统专业的“恰克恰克奇”①仍然存在,而且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加入“恰克恰克奇”的队伍,这些“恰克恰克奇”的参与使得口头文学的内涵更为丰富多彩,其中的社会政治性意味也日趋浓郁。这些口头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十分广泛普及,成为新疆各民族大众随时可以感知并融入其中的文学事实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