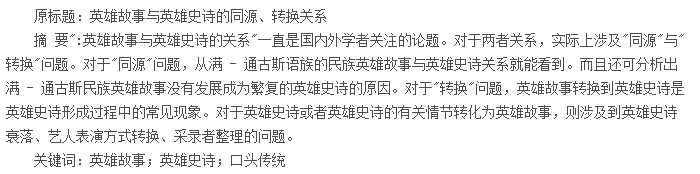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大家庭,多民族的历史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尽管如此,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却始终难以获得应有的地位,始终处于中国文学的边缘。特别是中国进入近现代历史之后,中国文学领域受到西方文化的强大冲击,这种现象更加明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甚至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由此,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遭受三重话语霸权的排挤表现为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突出特征。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保持理性的认识和思维,同时必须下大力气进行多民族文学研究,对话语霸权现象展开强烈批判,强调多民族文化共同发展,不同民族文化要互相影响、互相融合,这样才能使中国民族文学的独特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而我们的民族文学将会迎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一、少数民族文学分析
少数民族文学历史悠久,内容十分丰富,包括神话传说、民俗故事、叙事诗等等,这些都是中国文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很多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并没有书面形式,而是口头流传,但这并不能夺去少数民族文学的璀璨光芒。不少作品还被翻译成汉文字出现在中国经典的文学作品之中。比如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就是当时各民族流传诗歌的作品。虽然当时的汉民族尚未形成,并没有少数民族的概念。但是从当今的视角来看,很多少数民族的先祖正是当时分布各地的居民。比如湖南湘西土家族在婚礼之前的告祖仪式上,还要演奏诗经音乐,所唱歌词恰恰是《诗经》中的《关雎》、《桃夭》之章,而且歌词与《诗经》相同,这种遗风说明《诗经》与古代少数民族的渊源关系。
虽然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但是相对于汉民族而言在影响力上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就是文学的霸语权。
因为相比汉民族,少数民族在文化、经济、政治等各方面都存在差距,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学等社会的各个方面长期以来都是汉民族占据主导地位。从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集中,我们很少发现少数民族的作品,这是因为历代很少有学者对于少数民族的作品进行研究或者收录自己编纂的作品集中,这也恰恰是少数民族文学在多重话语霸权下影响力不足的最有力说明。[1]
二、西方话语霸权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
西方话语霸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研究,因为超过一半的文学史都建立在西方话语体系上。[2]当代文学这种特定时期下的言说方式原本反映现当代文学生存经验,同时还应该体现现当代生存背景的独特性,可是现当代文学处于西方话语霸权的压迫之下,在反映本民族生存经验的过程中表现得不够出色,出现现当代文学的失语现象。[3]
在长达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论的言说方式逐渐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评价标准各不相同,同时还立足于中国文人的生存经验,逐渐发展成具有自身独特性的阐释体系。中华民族独特的生存经验恰恰可以通过这种阐释体系体现出来,如《文心雕龙》、《诗品》、《文赋》等都能够出色地承担起反映中华民族独特生存经验的重任。可是,随着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中国文化便陷入了西方文化强势压迫的不利条件,中国长达几千年的文学经验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出现了失语现象,而它阐述生存经验的功能也很快消失,事实上,这种现象非常不正常。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逐渐向着西方的方向发展,文学生存机制本身具有的连续性不能采取强制手段人为隔断,否则只能使中国文学成为西方文化的忠实追随者,失去言说本民族独特生存经验的功能。处于这样一种不利条件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评价体系必然不能很好地传承中国传统文论的独特特征,而中国文论也就难以依照自己的标准对世界文论体系做出评判。[4]
现当代中国文学体系处在西方话语霸权的霸权之下,属于中国文学体系的少数民族文学自然也难逃西方话语霸权的压迫,这主要通过处于西方文学评价体系下的少数民族文学评价一直努力为自己争取合法化身份体现出来。少数民族文学处于被压迫的形势下,已经濒临生存的边缘,但是因为少数民族文学有自身的独特生存机制,因而也应该具有自身独特的评价标准。可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一直没有形成这种独特性,而是紧随西方文学之后,建立少数民族文学史就是这一现象的突出表现,如《白族文学史》、《苗族文学史》、《藏族文学史简编》、《少数民族文学》等,以上提到的少数民族文学史无论是在评价标准上,还是在结构体系上都体现了对西方话语霸权的追随,而且这些少数民族文学史无不采用了西方话语来阐释,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反映出西方话语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巨大冲击,而少数民族文学也在与西方话语的碰撞中失去自己的独特性。
三、汉语话语霸权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少数民族文学不但面临西方话语压迫,而且也面临着汉语话语霸权的巨大冲击,现代学者王国维曾经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中国史诗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他同时也认为,中国尽管是一个古文学大国,可是却没有一部史诗可以与西方史诗相媲美,胡适也持类似观点。[5]
可是,少数民族地区却不乏优秀的史诗,即使我们依据西方史诗标准进行衡量,它们也仍然毫无疑问被划入史诗的范围,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乌古斯传》、《格萨尔王传》,此外还有《江格尔》等。不管是《格萨尔王传》还是《乌古斯传》都应该划入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行列,可是中国文学史却并没有为这些作品提供应有的地位,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出现中国不存在史诗的结论,这也是汉语话语霸权的最根本体现。
另外,处于汉文化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文献存在非常明显的失落感,而语言失落是其最突出的表现。[6]
中华民族是由多种少数民族组合在一起的大家庭,民族之间通过各自的语言进行区别,因此中华民族的语言应该表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而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应该采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创作,并且具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点,所以对少数民族文学展开研究必须要从语言的角度来切入,而且语言也必定会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一项必备条件。如果将某一种少数民族文化转换成另一种民族文化,需要用到翻译,如人们耳熟能详的《敕勒歌》就是一首鲜卑族民族诗歌,后才被翻译成汉族诗歌,虽然我们所见到的《敕勒歌》新形式仍然带有少数民族文化色彩,比如诗句与诗句之间长短不齐,可是鲜卑语已经消失,这首诗歌真实的原始风貌是怎样的,我们并不能深入考究。由于少数民族语言和汉族语言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经常会出现互相翻译的情况,因此不同文化的碰撞应该首先表现为语言的碰撞或者思维的碰撞。由此,语言问题表现出一种新的含义,也就是汉族语言的话语霸权地位。[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