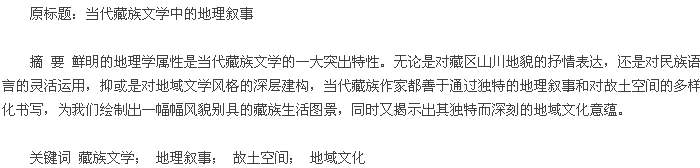
早在 1967 年 3 月 14 日,福柯先生便在一场演讲中宣称: “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我相信,世界更多的是能感觉到自己像一个连接一些点和使它的线束交织在一起的网,而非像一个经过时间成长起来的伟大生命……当前的时代是空间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布满各种性质,一个可能同样被幻觉所萦绕着的空间中。”[1]
随之,空间概念很快便在各学科领域传播开来,空间地理学也被引入到文学作品中来,成为一种研究文学的新手段,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 “如同时间问题( 在柏格森、普鲁斯特和乔伊斯那里) 成为这个世纪头几十年里主要的美学问题一样,空间的结构已经成为 20世纪中叶文化中的主要的美学问题。”[2]在此空间理论热潮的迸发下,“地理叙事”研究也应运而生。所谓“地理叙事”是指“作家运用艺术手段在叙事文本中通过地理空间如自然山水风貌、地域人文风俗、城市生活图景以及想象虚拟空间的动态建构,展开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表达思想主题、绘制或投射出一幅社会人生的认知地图。”[3]
它与我们经常使用的“时间叙事”研究方法不同,抛开了时间的维度而强调一种有机的、融和的地域文化特征,用地域空间内容来展现作家个人认知、时代变迁阵痛以及民族精神投射,无疑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当前国内叙事学研究仍以“故事”与“情节”研究为主,较少涉及到地理空间研究,因此笔者认为从“地理叙事”的角度对当代文学进行考察研究是必要可行的。其次,藏族文学的地理学属性又格外突出,无论是对藏区山川地貌的抒情表达,还是对民族语言的灵活运用,抑或是对地域文学风格的深层建构,当代藏族作家都善于通过独特的地理叙事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幅风貌别具的藏族生活图景,通过对故土风情的书写揭示出当地独特而深刻的地域文化意蕴。正是在此基础上,从人类与自然的角度对当代藏族文学中的地理叙事进行分析研究是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文章就从“地理叙事”入手,从价值外化下的地名抒情、民族语言的灵活运用、叙事风格的深层建构三方面具体分析了当代藏族文学中的地域色彩及其价值属性。
一、价值外化下的地名抒情
所谓“地名抒情”是指藏族作家在关注乡土、表现乡土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叙事抒情上就直接调用地名进行表情达意”[4]的现象。例如藏族诗人伊丹才让的诗集《雪山集》《雪域集》、格桑多杰的诗歌《玛卿雪山的名字》、松热加措的抒情诗《青海湖礼赞》、饶阶巴桑的《草原集》、达真的长篇小说《康巴》、丹巴亚尔杰的短篇小说集《羌塘美景》、阿来的长篇地理散文《大地的阶梯》都是直接以地域来命名。
在《玛卿雪山的名字》中,作者首先用雪山、岛屿、丛林、闹市、宫廷、庙堂、书斋等密集的地理名称来烘托出雪山的美名,然后用万仞银峰、蓝玉般的湖泊和七彩的虹、白色的驹、银色的风翅、白色的雪蛙……来描写雪山之美,种种自然意象铺陈开来,节奏紧密如明珠落玉盘,表现了作者对于雪山浓烈的爱恋与赞美之情。无论是这里的地理景观还是自然生物都已经被作者赋予了强烈的感情,是一种情感的物化。正如女诗人唯色所述: “在诗人的笔下,那些情有所钟的元素: 扑不起来的小小翅膀,养不大的指甲,来自天上的花朵,单单为谁而长的昂贵骨头,飞扬的尘土,秋日中落在喇嘛肩上的树叶,永恒的光芒,命中之马,紫气,水等等,当它们在诗人的手中熠熠闪烁时……这就是诗。”[5]这些普通的自然景观在作家眼中已经成为一种诗意的自然,无论是蔚蓝如洗的天空,还是广袤无垠的大地,抑或是三五成群的牛羊,在作家心中都具有独特的风情和浓浓的宗教色彩。
早在 20 世纪,德国费肖尔父子便提出了“移情”说,他们认为审美主体在审美活动中会将自己的感情灌注到客体中,使得相同的审美客体在不同的主体眼中呈现出不同的美学效应,或者不同的心境下,相同的客体在同一个审美主体眼中也具有不同的美感。例如,同样的一条红裙,在银光素裹的冬日会让人觉得精神振奋、喜气洋洋,而在一片漆黑的深夜却会让人毛骨悚然、胆战心惊。这种美学主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却揭示了“自然的人化”现象,带领我们走向物我同一的审美境界,但是却过分夸大了移情的作用,忽视了审美对象的客观性。
在此基础上,卢卡契提出了审美主体“外化及其向主观回复”的范畴,更为科学地对审美主体与客体的互动作出了研究。他认为艺术的创作就是人类通过塑造一个虚拟世界来表现其自我意识的过程,而这种主观意识的表达就是审美主体的“外化”.在他看来,外化是“审美创造中审美主体以业以形成的内部主观成分去反映、组织客观现实,它以对客观现实的模仿为基点,创造出适合于人的感性的现象‘世界'---艺术作品”正是在这种审美主体的外化作用下,文学作品中的客观世界才具有了人的感情,才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在审美主体的外化下,通过作家感情的投射,枯藤老树化身为西风萧瑟下的断肠人,芭蕉夜雨倾诉着对亲人的愁思,雪山圣湖像一位盛装出席的神女,长街雨巷则演绎了一位江南烟雨中欲语还休的青涩少女。
对于藏族作家来说,这种“外化及其向主观回复”的审美活动尤为明显。西藏地处青藏高原,边缘封闭的地理位置使得作家们受到地理基因的影响更为明显。藏族居住在寒冷干燥的高原地带,白昼有刺眼灼热的日光相伴,夜间有凛冽刺骨的寒风相陪,昼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便养成了藏民骨子里热情豪爽、淳朴直接的性格特征。再加上当地浓厚的宗教氛围,他们的性格里又多了虔诚、质朴、感恩等属性。于是,通过主题外化下的藏族文学便也多了几分时而热情奔放、时而虔诚恭敬,时而炙热如初、时而神秘莫测的特色。这种地理对作家的影响就是审美客体“向主观回复”的过程,也是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家进行“价值内化”的过程。自然地理在经过作家主体的审美观照后,由最初的作为人类生活空间的地理环境而外化为作家的写作源泉,并通过主体的观照、情感的投射、价值的内化继而升华为作家的精神家园,其间的山水、草木、花鸟都能够化身为艺术创作中的精神原型,为艺术家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与助力。在这片充满生机的高原大地,藏族作家们生于斯长于斯,故土的文化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当他们将笔端投注于家乡的地理风貌时,这种外化的价值就会使得他们笔下的自然风貌呈现出别样的风情。
二、民族语言的灵活运用
除了对自然山水的地名抒情外,地域语言的灵活运动也体现出了地理学叙事的特点。民族语言是某一民族内部的通用语言,是沟通交流信息的基本工具、传递民族文化的桥梁与纽带,也是该民族的显要标志、代表特征。通过这一地域性语言我们才能走进他们的日常生活、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认同他们的文化心理。可以说,如果没有民族语言的存在,那么我们就失去了最鲜活、最本真的民族特色,同时也失去了一个极为丰富的资源宝库。对于作家来说,合理运用地域语言更能为他们的创作提升了不少个性魅力。例如,老舍先生对北京话的运用、韩少功先生在《马桥词典》中的语言实践、田永红先生在作品中对方言的调用……这些作家依托当地的地域语言进行文学创作,使作品既鲜活又生动,对于异域的读者来说还会有一种“陌生化”的美感。正如肖太云在研究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时所述: “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自觉学习和运用这一本土或本民族资源,既拓展和提升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魅力,有效缓解了普通话写作的焦虑,又在文学地理学的向度上营造了一块颇具自足性和抵抗意义的’野地‘,开拓了一块地方话语或少数民族话语与公共话语或政治话语相抗衡的话语空间,且随时随地、自由灵活、代价极小。”
当代的藏族文学作品大体上可以分为母语写作与汉语写作两大类,这种双语并行的文学创作不但有利于藏族传统文学的继承发展,而且有益于藏族文化在其他区域的流行传播。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后,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知识的传播,一些藏族作家受到了更为系统的写作训练,他们开始思考如何在“多元化”的背景下弘扬本民族的文化,如何在坚守民族阵地的基础上构筑未来,如何在开放的环境中实现“民族”与“世界”的和谐交融……于是一部分坚持用母语创作的作家对藏族文化投注了极大的热情,他们认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只有实现民族精神内核的回归才能使藏族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他们进行了一系列文学创作实践,一改藏族传统文学镂金溢彩、精雕细琢、寓意深邃的特点,开始用朴实的语言来描写平凡人的生活,描绘族人们如何在恶劣的高原环境下辛勤耕耘、在歌谣的陪伴下四处游牧、在虔诚的朝拜之路上投地叩首、在跳跃的篝火旁载歌载舞……格德嘉的诗歌《措把》、根丘多吉的《雪山》《寻香妙歌》、奔嘉的《阿坝草原晨曲》、俄邓的小说《对仁德西》《佛灯》、奔嘉的散文《我爱这颗小草》等,都是这一时期藏族作家用母语进行创作的代表作品。
除了用藏语写作外,还有部分作家用汉语抒写家乡故土,试图让更多人了解深处祖国腹地的魅力西藏,对于藏族文学的提高、拓展有着极大的贡献。正如当代藏族诗人旺秀才丹所评价的那样: “正如一些现代语汇必将进入藏语语汇一样,用汉文字创作取得一定成就的藏族作家,无疑是可以被藏族文学史所接纳的。它的贡献就在于对藏族文学史的丰富和延展。说它丰富,是指它吸收了藏语诗歌创作目前还无法接受的许多现代技巧乃至词汇、词( 语)义,从外围楔入并加强了本民族的传统; 说它延展,是指使用汉文字可以更直接、更轻松地从汉文诗歌成就中’拿来‘,也更快地使藏民族传统文化与异文化互相交流、融合和浸润,从而挖掘、提高和拓展藏民族新文学的品位,使藏族文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学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能更宏大、更完整地走向世界。”
这部分作家有益希单增、意西泽仁、阿来、多杰才旦、孕藏才旦、丹珠昂奔、扎西达娃等。他们的作品虽然从形式上看是由汉字组成,但描绘的是藏人的多彩生活,表达的是藏人的思绪情感,刻画的是浓郁的藏族风情,散发出辛辣的青稞酒味与浓厚的酥油奶香。
以《乔庄新年纪事》为例,作家何延华通过三个小故事为我们描绘了阿尼玛卿雪山脚下一个偏僻村落的风土人情。她在讲故事的时候有意识地调用了当地的方言俗语,使作品充满了地气与活力。文中既有原汁原味的民间口语“你嫑寻茬头,也嫑打赌憋”,也有信手拈来的地方俗语“宁给狠人牵马缒镫,不给怂人出谋定计”; 既有形象的比喻“瞧,一只大哼猴,三只小哼猴”,也有贴切的排比“和面的时候,他嘴里骂着你,眼泪嗒嗒嗒,掉进面里; 擀面的时候,擀杖梆梆梆,像打鼓,赛敲锣,震得屋顶上的尘灰也落下来……”; 既有客观的释意“挨刀子这么硬的话一旦由传情达意的一方说出来,立马软得就像秋天的柿子,轻轻一捏,就能流出甜甜的汁水”,也有强烈的抒情“我这么下茬,还不是为了拉扯尕将们?还不是为了家里宽展些? 要不是你花马嘹嘴,当的甩手掌柜,我也不会这么戳腾,这么霸揽……”这些鲜活的文字一个个在页面上跳跃,为读者塑造了懦弱的小林、强势的小兰、糊涂的老王、苦命的大丽……作品语言淳朴生动,极富有地域色彩。
此类极富语言特色的藏族作品还有很多。作家们把民族语言作为自己文化的载体,将方言作为描摹世界、刻画人生的工具,以方言写作来为故土风貌和民族代言。对他们来说,这种相对封闭的表达方式,更能完美体现出他们对家乡的热爱、对故土的眷念、对神灵的敬仰、对民族文化的依服。“这种诞生于’野地‘的相对弱势的’地域语言‘,通过对’官话‘规训、宰制的逃逸和博弈,复活了被现代空间日益逼仄、挤压和机械复制的’生活世界‘,它承载着理想和寄托,传递着民间和底层的文化、政治、生活诉求,重塑和召唤着一种与’根性‘相沟通的诗意生活。”
正是在母语强力的召唤下,一代又一代藏族作家无论走得多远都始终在创作实践中显示出了对民族语言的依恋与回归,这种坚守构成了当代藏族文学创作中最为执着的精神守护,也是他们凭借浓郁的地方色彩与鲜明的种族属性走向世界的助力之一。
三、地域叙事风格的深层建构
俗话说“文如其人”,作家的风格会随着文笔在作品中逐一显现,人格决定文章的风格。同样,地域风格也能对作品风格起很大的决定作用。因此,从地域叙事风格的角度对藏族作品进行分析也是极为必要的。
从文学发生的角度来看,邹建军先生认为“任何作家的成长都不可能离开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任何作品的创作也只能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发生的。因此,我们将这种与生俱来的因素,称为’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10]当我们将“地理基因”这一概念引入到文学创作过程中来时,会发现基因的遗传功能会通过创作主体的生命体验对作品风格产生极大的影响,形成一种“艺术风格的地理约束”.正如藏族青年作家何延华在其小说集《嘉禾的夏天》中谈及创作感言时说述: “当我写下’后记‘二字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了生我养我的那个小山村……由于地处中原农耕文化与青藏高原草原文化的交会地带,这里的地域文化丰富而独特,充满魅力: 比如情真意切、朴实刚烈的”花儿“,富于智慧、妙趣横生的”宴席曲“……这些宝贵的民俗文化遗产,使县境中的大小村落从骨子里散发出一种古朴憨拙的味道,一种有别于市场经济的宁静安详……在这种人文环境中,人的心,便如养育他的自然环境一般,纯粹恬淡,质朴良善。”正是在这种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影响下,她将地理资源、生活资源与精神资源赋予自己的感思一一诉诸于笔端,将“发现真善美,表达真善美,弘扬真善美”作为自己的创作目的,作品沉静质朴、乐观向上,带有浓浓的乡土气息与地域风情。
正如作家们感受到的那样,他们的成长环境、家乡民俗对他们感受世界、认知世界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这种地理基因不但会直接作用于他们世界观、人生观的构建,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情感归宿,而且会间接影响到他们的文学创作,使作家在内心世界产生特殊的山水情结,表现出独特的美学意味。
例如,东北地处高纬度地区,多为平原地貌,资源丰富。在气候上北倚北极圈外围,西部与西伯利亚寒流相接,冬季漫长寒冷,人们无法在室外耕种,只能在室内活动,闲暇时间较长,于是相对于中部地区的民众来说,东北人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消遣玩乐,也有更多的时间聚会交流、增进了解,这就使得东北人性格豁达、豪爽、开朗、乐观、幽默、凝聚力强。东北作家在作品中也构建了属于他们的白山黑水,展现了东北的博大与冷峻,表现出一种蓬勃的野性美与张扬的生命力度。
与东北的平原地貌不同,西藏地处高原,地形复杂,既有严寒干燥的藏北高原,又有温暖湿润的藏南谷地,还有地势险峻的藏东峡谷,气候复杂多变,“十里不同天”; 早晚温差极大,“一天有四季”.在这种复杂的地理条件下,藏族文化也随着地理的变化分为三个区域: 卫藏、康巴和安多文化,更有俗语称“法域卫藏,马域安多,人域康巴”.卫藏作为藏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以佛教信仰为主,浓厚的宗教色彩和淳朴自然的民族风貌是作品的主要描写对象,代表作品有《复活的白度母》《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康巴文化属于一种多元文化融合,其间既有黄河文化、巴蜀文化,又有长江文化以及来自云南多个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康巴人将这些文化都融入到自有的藏族文化中,形成了一种热情奔放、坚毅勇敢、内涵丰富的有别于其他藏区地域文化的特殊表现,代表作品有《青藏时光》《康巴》等。
安多地区位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带,有着万里无垠的广阔草原,以崇尚马而闻名。同时这片魅力深邃的梵天净土也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诞生地,浓厚的宗教色彩随处可见,虔诚的信仰早已融入藏民的生活与艺术中来。在这里流传千年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气势磅礴、瑰丽灿烂,无疑是杰出的文学巨着。因此,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会作用于作家的审美风格和叙事风格,进而影响到该区域的文学整体风格。
从本质上说,文学作品中的地理叙事实际上就是作家对地理影像的固化描摹。作为地理基因的外化形态,地理影像的固化既包含对自然山水的书写,也包括对作家情感的把握,它就像一幅完美的摄影作品,表现的不仅仅是自然风光,更为重要的是摄影者的情感内核。以《康巴》为例,作者以康巴藏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变迁为视角,将故乡康巴作为叙事的空间和背景,试图对康巴大地上百年来的历史变迁进行史诗性的全景展现。作为茶马古道的核心地区,这里生活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多民族共居、多种文化交融的氛围在小说中得到了形象的展现:
“进入郑云龙视野的康定,房屋同川西平原的房屋相差无二,不同的是一楼一底木质穿斗屋架加了半截石头墙,唯一的变化就是底层的铺面的店主多了穿藏袍的商人; 走在一半铺鹅卵石一半是黄泥路的紫气街,街道两边有几家小小的客栈,几家米铺屋檐下的横木飘舞着米铺的布招牌; 卖土杂的店主的手抄在袖筒里在与买家讨价还价……霎时,那些藏人用宽大的袖口罩住嘴和鼻子,将头缩在皮袍里; 戴小沿礼帽的汉商则用手压住帽子,顶风前行; 偶尔一两个穿旗袍的女人连忙半蹲着用双手一前一后地压住旗袍,一脸的羞涩与无奈。这一场景是康定的风留给他俩最深刻的印象。”
在这里,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结合形成了一种隐喻的象征系统,对生活在其间的人们产生了种种制约。“汹涌而来的法国人在康定最好的地段修建了大教堂; 清真寺的唤礼楼下的穆斯林兴旺发达; 陕商、晋商、川商、滇商、徽商占据了最好的店面并疯狂地使之延伸。生意场上,这些移民拼命似地跑在了云登家族属下的几十家锅庄前面……”
在这种时空背景下,作者刻画的康巴早已超越了地理层面的意义,成为一个集地理、符号和体验三者一体的叙事影像。这种具体而又特殊的地域空间的选取与建构不但形象地反映了大时代中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现象,而且还能作用于生活在其间的民众,通过对主人公个人命运的书写来揭示出隐藏在他背后的整个族群的命运。通过地理叙事,作家为我们描画了一幅独特的康巴风光图,在这幅图画上既有高原雪山的自然美,又有热情淳朴的人性美; 既有复杂多变的地貌书写,又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刻画; 既有对故土家园的热爱,又有对精神家园的追寻……毫无疑问,作家生活的自然空间就是他进行创作的素材库,同时也是作品固化的影像来源。而作品中呈现出的空间叙事一方面是对自然地理的艺术描摹,另一方面也是作家情感与民族文化的象征系统。只要我们把握住文本地理叙事的特点,就能够以小见大,由一砖一瓦触摸到隐于背后的民族风骨和作者审美世界中的史诗大厦。总之,当代藏族文学具有鲜明的地理学属性。
藏族作家通过地理叙事来支撑起作品的框架,通过地理叙事来书写自己的所见所闻、民族的特色风情、时代的发展变迁。作为读者的我们也可以借作品中地理书写的桥梁走进作家所构建的艺术审美世界。
正如肖太云先生所述: “通过文学地理学的书写,可以窥见民族生活图景、母语文化精神和民族心理,特别是揭示地域文化表层经验和深层底蕴,这既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保持根性和个性的方式,又是民族作家坦诚面对、寻求对话、获取认同、谋求发展的一种策略。”
参考文献
[1]福柯。 另类空间[J]. 王喆译。 世界哲学,2006,( 6) .
[2]黄继刚。 爱德华·索雅和空间文化理论研究的新视野[J]. 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4) .
[3]颜红菲。 地理叙事在文学作品中的变迁及其意义[J]. 江汉论坛,2013,( 3) .
[4]肖太云。 文学地理学维度下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扫描[J].民族文学研究,2012 ,( 5) .
[5]马丽华。 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M].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242.
[6]张伟。 卢卡契对审美反映论的一个贡献---论卢卡契“外化及其向主观回复”美学范畴的思想价值[J]. 复旦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6,( 2) .
[7]肖太云。 文学地理学维度下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扫描[J].民族文学研究,2012 ,( 5) .
[8]才旺瑙乳,旺秀才丹。 藏族当代诗人诗选( 汉文卷) [M]. 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
[9]孙国亮。 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方言小说在文学地理学向度的研究[J]. 世界文学评论,2010 ,( 1) .
[10]覃莉。 关于“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的思考[J]. 世界文学评论,2011 ,( 1) .
[11]达真。 康巴[M]. 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18,8.
[12]肖太云。 文学地理学维度下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扫描[J].民族文学研究,2012 ,( 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