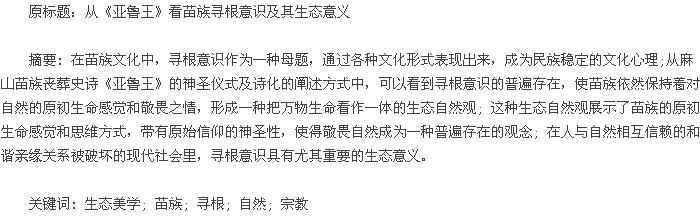
一、引言
在全球化时代,技术进步给人们带来福祉的同时,也猛烈地冲击着传统农耕文明。在向自然疯狂索取和掠夺的过程中,不仅自然生态被破坏,人自身的存在也有一种被撕裂感。正如海德格尔所言: 现代科技力量正在把人类从大地上“连根拔起”[1]。现代人就如漂浮的浮萍,心灵无所皈依。在失去存在根基的当代生活里,甚至连民族传统的精髓也逐渐消失。现代性给人造成的断裂和分化感,以及因此带来的整体性和连续性的失去,使得追寻与回归民族历史文化之根的愿望变得尤为迫切。对于人类来说,寻根是为自己寻找精神支点和价值坐标,生态意义上的“寻根”则是指对民族文化的保持及对古老记忆的延续与生命归宿的探源。寻根意识作为人类的一种古老而深沉的情感体验,普遍地存在于人类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中。老子就说过“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老子》第十六章) ,追根溯源是人类普遍的人文情怀。在现代多元文化的冲击下,“无根”所造成的焦虑与失落是现代人的精神困境的重要根源。
这种情况下,探寻苗族文化中的“寻根”意识,考察苗胞保持民族文化、延续古老记忆及探源生命归宿的方式,在人们呼吁重新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传统、现代与原始之间对话的可能性之时,就具有了为人类生存多样性提供参照的生态文化意义。
二、寻根意识与苗族文化
在苗族的日常文化生活中,有许多形象固定、代代相传、无处不在的审美意象和文化符号,它们作为苗族文化的“母题”,是寻根意识的集中体现。比如芦笙、蝴蝶、枫木、花鸟、牛角等,这些苗族审美文化中处处可见的意象和文化符号,通过代代承传的方式存在于苗族世界,是本民族历史长河中沉积下来的关于族群的集体记忆,并积淀为深远的集体文化心理。曾有人说,寻根是一种移民才具有的意识,苗族的五次大迁徙,是其历史上最重要的经历,飘泊和迁徙的记忆自然会在民族历史中打上深深烙印,成为其文化的一个母题,顽强地生长在苗族的服饰、古歌、史诗、神话里。
麻山苗族在丧葬仪式上吟唱的英雄史诗《亚鲁王》所展现的就是一次典型的寻根之旅。亚鲁王是麻山苗族心目中的祖先,一位勇猛过人、足智多谋、半人半神的英雄,一个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诗意化形象。在葬礼上唱诵《亚鲁王》,就是表现对祖宗的崇敬和追忆。史诗中不但再现了远古祖先农耕生活的幸福繁荣景象,“亚鲁王造田种谷环绕疆域,亚鲁王圈池养鱼遍布田园。造田有吃糯米,圈池得吃鱼虾”[2],也描述了亚鲁带领族人踏上迁徙之路的惨境: “亚鲁王艰难迁徙,日夜奔走。亚鲁王继续迁移,绝不回头。”在孩子们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中,亚鲁王带着妻儿老小和族人,日夜兼程走上千万里路,为族群寻找新的生活之地。而在葬礼上演唱的段落“郎捷排”,意为“返回祖先故地的路”,把回到祖先之地的路线一一向亡灵讲明,好让其能顺利回到祖先那里,同时也提醒后人要牢记祖先的苦难历程[3]。每一次演唱,每一次仪式,对于生者来说都是一场心灵的召唤和洗礼,都是在上演寻找民族之根、进行身份定位的叙事主题。
苗族有尚东的意识,对东方的崇尚也是其寻根意识的体现。在麻山苗族葬礼仪式中占重要地位的“砍马”仪式里,马倒地死去后要使其头朝东方,喻为马把死者带回祖先居住的故乡,死者的头也要朝向东方,其喻意是让逝者沿着祖先历尽艰险开辟的路重回故里。与此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在黔东南古歌中为死者演唱的《焚巾曲》中也唱道: “妈妈去东方,沿着古老道,沿着迁移路,赶路去东方。”当年苗族的祖先被迫迁徙,离开故土,故乡就成为族人心中永远的心灵归属地。东方是自己的故土,人死去也后要回归故地,在神圣的仪式和诗化的阐述方式中,一个和祖先互动的神圣世界得以生成,故土和祖先的记忆就这样被反复唱诵,成为不忘本源的象征性表达。
三、寻根意识与生态自然观
“寻根”之“根”,本来就包含着生命来自自然之义。从生态美学的眼光来看,寻根之“根”,更多地指向人类生命的本源: 自然。在苗胞看来,大自然是一个孕育、滋养万物的存在,古歌《枫木歌》中就提到苗族的始祖母妹榜妹留来自枫木的传说。维科说过,原始人依赖自然而生存,凭借原始直觉就感到自己源于自然,自身和自然是浑然一体的,而神话就是对人类起源、人与自然万物之间关系的一种幻想式解读。苗族还保持着这种神话思维方式,在他们看来,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傍、同为一体的关系。在他们的自然观里,没有人类与其他物质相区别的“自我意识”,也没有人与神灵相区别的高级宗教意识,他们依然沉浸在万物一体的原始生态观念中。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上,展现了苗人的原初生命感觉,这种感觉的本质特征在于: 人与自然是混沌不分的共同体。在苗人眼中,自然界的所有物种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存在,自然万物和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样样东西那是活的,而每一样东西都以各种方式依赖着其他的一切”[4]。《亚鲁王》中就把自然物称为“祖宗”,第一章中就唱道: “女祖宗蝴蝶寻来糯谷种,男祖宗蝴蝶找红稗种……糯谷祖宗答应蝴蝶祖宗,红稗祖宗应承蝴蝶祖先。糯谷祖宗说往后你下崽在我叶梗上,红稗祖宗讲日后你下蛋在我叶子上。”第二章中提到了“蚯蚓祖宗”“青蛙祖宗”“牛祖宗”“老鹰祖宗”等为亚鲁王做事的事情。
可见,无论是蝴蝶、蚯蚓、青蛙、老鹰、牛这些动物,还是糯谷、红稗等植物,都与亚鲁王一样,是苗人的祖宗,苗人对他们也像对先祖一样地尊重,在唱诵时也要把动植物们的祖宗身份明确地标示出来,表达自己的敬意和感恩之心。而这些动植物祖宗们,有着和人类一样的特性: 七情六欲和相同的语言、思维。当亚鲁王派老鹰祖宗考察领地,老鹰祖宗言说辛苦之后,还跟人讨价还价讲条件,索要些劳力费,最终得到了春天可以任意捕食小鸡、秋天可以随意吃大鸡的特权,并且至今一直受到苗胞的善待。其他动植物祖宗也一样,是要受到尊敬的、不能伤害的,这种观念对保持栖居地的生态完整性具有积极意义[5]。
这种对自然的归属感使苗族把万物生命看作一种互相关联的存在。生态美学强调的生命关联性不仅是指生命的孕育和成长,还指向生命的更新和循环,以维持生命的动态平衡。这种生命归宿上的寻根意识在苗族的死亡观念中也体现得很明显。既然人是大地和自然母亲的孩子,死亡就具有“归根”的含义,死亡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而不是生命的结束,因此,在麻山苗族葬礼上,并没有多少号啕大哭的场景。生命是轮回的,也是超越的,向死而生,生命存在方式在这里得到了永恒。在麻山苗族葬礼上,要给死者准备草鞋( 回归祖先的路上穿) ,回归路途中的吃喝如酒、水果、豆腐、鱼,防身用的弓箭、藤盔,装食物的饭箩,喝水用的葫芦,发展生产用的稻种等,这些东西在《亚鲁王》中都提到过。对于苗族而言,死亡是“归去祖奶奶那里”,“去往祖爷爷那方”,未来的新生命是在先祖亚鲁王故国度过的。在葬礼上唱诵《亚鲁王》,主要是因其是亡灵回归的指路歌,是苗民生死转换不可或缺的一个“节点”。这种“死亡是生命回归而不是终结”的观念在苗胞社会中普遍存在,雷山地区苗族在葬礼上唱的《焚巾曲》中就唱道死者是沿着祖先曾走过的迁徙的路线,回到东方去,“去跟蝴蝶妈,跟祖先团聚,团聚在一起”。在紫云四大寨苗族的丧葬仪式中,巫师要进行“开路”活动,当地苗语中称之为 Jangz ghad,即指通往祖先的道路[7]。这是灵魂和肉体的回归,回归到生命的本源,回到自然的怀抱。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乐之源( 接近极乐) 。故乡最玄奥、最美丽之处恰恰在于这种对本源的接近,绝非其他。所以,惟有在故乡才可亲近本源,……还乡就是返回与本源的亲近”[8]。自然是生命的根基,返回自然才是回归最本真的本源。
苗族对大自然的依恋与其农耕生活背景密不可分。农耕社会对大地有强烈的依赖,大地养育了人类,象母亲一样给予人类生命,让她的孩子在怀抱中休养生息、生殖繁衍。华夏传说中,女娲用泥土创造了人类,无疑是人类源于大地的隐喻。
这种天人相合的生态文化,是农耕文化的典型特征,对于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而言,这种生态文化具有原生性的特点。只是近代以后,现代大工业在全球蔓延开来,在对资本和利润的追逐中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被打破了,在全球化的生态危机中,偏远的苗族地区保留了这种生态文化。
在苗胞这里,自然也是包括本民族在内的万物之根,《焚巾曲》中唱道: “大地是主人,山河永存留,人生是过客,短暂一时候。”自然之道是民族共同生活的法则,因此苗胞还保持着女神信仰时代尊重大地母亲、自然母亲的古老生态智慧。它的启示意义在于告诉人们,人与自然之间要建立一种新的价值关系,一种不是对立而是对话和交流的关系,从根本上维持生态的有序化,才能走出现代生态危机的泥淖。
四、信仰与敬畏自然
苗族动人的古歌和优美的传说,都展示了苗族原初的生命感觉和思维方式。早就有研究表明,人类原始文化中,物我同一、天人同一的观念是普遍存在的,按荣格的话说,这种观念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扎根在各民族的文化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神圣的宗教之情被现代化“祛魅”的时候,苗族的这种原初生命感觉还依然延续至今。这种对自然独特的认知使他们克服了自然与人类的对立和隔绝,在性灵层面上与万物达到了沟通融合。宗教学家艾利亚德认为,在原始思维中,当石块或树木受到膜拜,“并不是因为它们是石块或树木,而是因为它们是圣石与圣树。
因为它们是神圣显象,它们显示出不是石不是树的某种圣性”[9]。麻山苗人对亚鲁王的崇拜,带有原始信仰的性质,这种神圣的对祖先的崇拜意识使亚鲁王历来倍受麻山地区苗族的尊重,重大活动中都要祭祀,并且只能在仪式内这种神圣的与祖先通灵的场合吟唱,否则就被视为对祖先不敬。学习演唱亚鲁王也是一种让人骄傲和自豪的行为,虽然学习唱诵十分不易,也有人执着坚持,因为这是对祖先的敬仰,东郎作为沟通祖先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人,也受到人们的尊敬。有学者在考察了麻山苗族丧葬仪式后分析认为: 苗族社会中对祖先灵魂和先祖世界的崇拜,已经成为一种深入其生活的信仰,而“对亚鲁的信仰是西部方言区苗人社会的精神支柱”[5]。
这种敬畏情怀在当今社会显得尤其可贵。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市场以追求利润为目的,把传统社会中神圣的宗教精神“祛魅”了,神圣的事物是微不足道的。这种世俗化进程给社会带来的是工具理性无限膨胀的时代,人们放纵自己的欲望,向着自然无限度地索取,把自然看作为己所用的工具,是满足自己欲望的手段,最终使自己的生存也陷入危机四伏的境地。针对这种危机,格里芬曾提出了对世界的“返魅”主张,要恢复万物的神圣性。而在苗胞那里,自然万物都是一种“神圣事物”( 涂尔干语) ,被加上了社会意义,“动物是不可缺少的,必要的东西……而人的生命和存在所依存的东西,对于人来说就是神”[10]。在麻山地区的丧葬仪式中,除了吟唱《亚鲁王》,还要用到猪、鸡、马等动物,它们各有其用,承担着亡灵回归路上的开路者、引路者及运输者等功能,即使是“砍马”仪式,也是马为了履行其祖先与亚鲁王的承诺,这背后体现的是万物之间关系的平等[5]。
而从生态学视野来看,保持原始信仰对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社会和谐秩序无疑是有益的。罗宾·克拉克和杰弗里·欣德利在《原始人的挑战》一书中,认为宗教和仪式这类宗教行为在原始人生活中非常重要,它们对调节人与自然及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生态整合作用,正是由于有神圣的、真诚的宗教性动机,人们才对自然充满着敬畏,正是有了敬畏之情的存在,苗族对村规寨约都自觉遵守。在《亚鲁王》中有这样的描述: “赛扬攀上马桑树去射太阳,赛扬爬上杨柳树来射月亮。”于是,马桑树和杨柳树都有了神性,都要受到敬重和保护,不能砍伐,否则如同忘祖弃祖,必被众人谴责。苗族寨前屋后的古树,也是这种信仰的直接受益者,苗族聚居的地方,生态都保持得很完好。自然万物和世俗事物并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更不是人们取来为己所用的工具,它具有一种远离尘世、指向神圣高远世界的意义。苗族的原始信仰把人与万物看成“通灵”的一体,其中的环境保护意蕴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由此可以反思,现代人缺少的就是人与自然万物相通的那种原始的“灵性”和敬畏之心。
五、结语
现代社会给人们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都市的扩张和人们向自然的过度索取,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也给人自身带来了异化的恶果,“拔根状态是各种人类社会之疾病中最危险的一种,因为它会自我增殖”[11],这和人类与传统及自然的本源性关系被切断有关,因此重建民族之根的需要尤为迫切。这种寻根,既包括延续民族文化之根,也有着回到自然之根的涵义,正如法国生态主义者莫斯科维奇所言“扎根就是从人的现有基础和独特智慧出发重建他与大地的联系”[12]。苗族同胞多居住在偏远的山地,在交通不便、生活相对贫困的大山里,他们却有着强大的生命张力,像大山一样坚韧强大,在这片神秘、悠远、厚重的土地上顽强地生存下来,保持着未被外来文化污染的纯洁、真实,保持着原初性的生态的纯朴和自然,这离不开他们紧紧抓住自身文化与自然的深层关联,牢牢植根于自然与民族之根,并从中得到精神的依托有关。在人们纷纷哀叹“文化断裂”的时候,苗胞的民族之根一直完整地保持着,没有被分化或断裂,这为在当代文化困境中苦苦寻找自我、呼唤民族文化意识觉醒的当代人寻求文化归属感和价值意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也为我们构建稳固的民族心理,在文明冲突下构建多元统一的生态文明社会提供了反思。
参考文献:
[1][德]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M]. 孙周兴,编. 上海:三联书店,1996: 1305.
[2]杨正江. 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亚鲁王》工作室内部资料[Z].
[3]梁勇. 麻山苗族史诗《亚鲁王》音乐文化阐释[D]. 陕西师范大学,2011.
[4]休斯顿·史密斯. 人的宗教[M]. 海口: 海南出版社,2002: 404.
[5]余未人.《亚鲁王》的民间信仰特色[J]. 民间文化论坛,2012( 4) : 41 -47.
[6]朝戈金. 媒体对《亚鲁王》报道不科学[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 -03 -23.
[7]吴正彪,班由科. 仪式、神话与社会记忆———紫云自治县四大寨乡关口寨苗族丧葬文化调查[J]. 贵州民族研究,2010,31( 6) : 48 -52.
[8]海德格尔. 人,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语要[M]. 郜元宝,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69.
[9]叶舒宪. 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 62.
[10]费尔巴哈哲学着作选读( 下卷) [C]. 北京: 三联书店,1962: 434.
[11]薇依. 扎根[M]. 北京: 三联书店,2003: 37.
[12]塞尔日·莫斯科维奇. 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M]. 北京: 三联书店,2005: 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