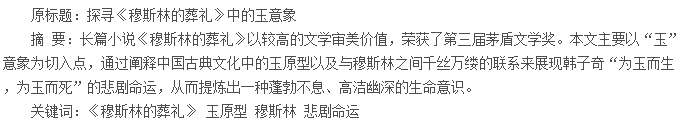
“玉”是一个古老的意象,“在新石器时代从我们日用器皿制出玉器,作为我们政治上、社会上以及精神上人格上美丽的象征物”。玉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中是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国更有源远流长的玉文化,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所谓“君子比德于玉”,所谓“古之君子必佩玉”就是很好的证明。
本文主要以“玉”为切入点,通过阐释其意象功能来展现韩子奇“为玉而生,为玉而死”的悲剧命运,从而提炼出一种蓬勃不息、高洁幽深的生命意识。
一、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玉原型及其象征意义
刘大同在《古玉辨》中说:“伏思吴国文艺之开化,以玉为最古,其他皆在其后。”“玉”体现了中华民族古老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中国文学经典中几乎都有玉的影子。加拿大的诺斯罗普 ? 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一书中谈到“原型”理论时说,“它是一种经典的或反复出现的意象。我用原型指一种象征,它把一首诗和别的诗联系起来从而有助于统一和整合我们的文学经验。”
根据这一解释,玉作为中国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体和象征,无疑可以作为中国文学中的一个“原型”。
由于玉的温润之性人们时常将它和女性联系在一起。在古诗文中,经常出现以玉比喻女子的容貌、声音、品行等等,如形容女子的声音是“珠圆玉润”,肌肤是“冰肌玉骨”,就连落泪也是“抛珠滚玉”,女子死去则是“香消玉殒”,而“佩名玉以比洁,齐幽兰而争芬”便是比喻美人高洁的品德。可见,在中国人的审美意识里,玉和女性有着太多的关联,玉原型带给人们的也是女性崇拜的远古记忆。玉从女神时代到父权社会,虽然它的阴柔之美和温润之性得以延续,但也被打上了父权文化的烙印:玉成为权利和财富、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成为规范封建社会君子之才的标准和维护封建礼制道德观念的工具。玉作为一种特殊的石头具有一种神秘的色彩,“玉从人体装饰物、馈赠礼物,到巫祀宗教的神物,都是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斗争中所用于体现人的生命意识力量的一种媒体。”在中国人心目中,拥有它就仿佛会使生命永存,玉原型被赋予一种生命意识,被视为生命力的象征,千百年来受到人们的推崇,中国人用玉去形容所有至纯、至贵、至美的事物,以至于衍生为形容君子的美德与才华,同时也是事业的象征,寓意国家昌盛。
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玉一直被人们视为内在美与外在美的统一,成为各种美的事物的象征。
二、玉和穆斯林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玉”在《穆斯林的葬礼》中是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有关“玉”的篇章是“玉”史的再现,爱玉人的故事,同时也显露出玉和穆斯林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论是受人敬仰的“玉魔”老先生、琢玉高手梁亦清,抑或是作品主人公韩子奇,甚至是作家霍达都对“玉”有着非同一般的欣赏与喜爱之情。
“玉魔”老先生是“博雅”宅的第一位主人,一生清高,以鉴玉、赏玉为乐事,但玉终是随着他的仙逝而散落殆尽。梁亦清,这位一辈子都在默默无闻地用双手创造奇迹的匠人,为了给中国的穆斯林争口气,倾注其毕生的心血精雕细刻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宝船,然而当宝船即将完工之时,他却因心力交瘁倒下了,最终玉损人亡。
回族女作家霍达对“玉”有着独特的认识与研究,她雕章琢句地将历代宝玉如数家珍,像博物馆陈列古董似的一件件呈现在读者面前。霍达如此谙熟“玉”与“玉器行”很大部分归因于她生于珠玉世家,那些在别人看来难以揣摩的东西,她却能信手拈来,熟练地当了一次“玉博会”的解说员,令人惊叹不已,由此可以看出玉和回回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韩子奇将玉视为生命“为玉而生,为玉而死”的悲剧命运
《穆斯林的葬礼》有关“玉”的篇章,看似写了“玉”的经历,实则是对主人公韩子奇一生的提炼。当他第一次踏入梁亦清家时,冥冥之中与玉有着不解之缘,于是毅然决定留下成为梁亦清的徒弟,他继承了师傅的善良品格和高超的技艺,但他比师傅更懂得玉的历史和价值,他努力去了解政治、了解生活、了解玉,他琢玉、品玉、识玉、藏玉,将玉视为生命,将玉看作中华民族的瑰宝,看作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文物,精心准备的览玉盛会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代“玉王”,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玉的世界,甚至抛妻别子、抛家舍业去英国,甚至为此放弃自己的爱情。
他的后半生,女儿新月和藏玉成为他的两大精神支柱,女儿的不幸早逝使他身心备受摧残,而当他的心爱之物被洗劫一空之后,也彻底摧毁了他的精神支柱,“玉王”没有了玉,他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这就直接造成了他悲剧性命运。临死之前他才顿悟:原来他痴迷了一生,被玉所驱使,那些“玉”不属于任何人,他同以往的爱玉人一样,只不过是“玉”的暂时守护者,“玉”最终还是要从他们手中流失。韩子奇的一生比“玉魔”老先生、师傅都辉煌,但他也经受了太多的磨难,他的顿悟是心灵冶炼的必然结果。
韩子奇一生琢玉、识玉、品玉、藏玉,“为玉而生,为玉而死”,虽然最终无法摆脱人世间的矛盾冲突,无法改变悲剧性的命运结局,但是他却有着为完善自身素质所焕发出的蓬勃不息的精神追求,小说正是通过对玉的意象探寻,提炼出一种高洁幽深的生命意识,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谈到的“我觉得人生在世应该做那样的人,即使一生中全是悲剧,悲剧,也是幸运的,因为它毕竟完成了并非人人都能完成的对自己的心灵的冶炼过程,他毕竟经历了并非人人都能经历的高洁、纯净的意境。人应该是这样大写的‘人’。”
参考文献:
[1] 宗白华《艺境》,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
[2] 杨伯达《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紫禁城出版社,2002 年版.
[3] [加拿大]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年版.
[4] 霍达《穆斯林的葬礼》,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 年版.
[5] 傅道彬《晚唐钟声——中国文学的原型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