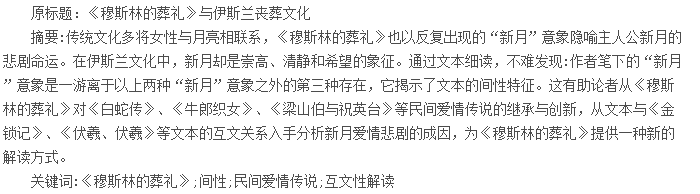
在传统文化中,月亮多与女性相关—同为阴性,表征内守、寒冷以及阴暗。在《穆斯林的葬礼》中,反复出现的“新月”意象与主人公新月构成了一种隐喻关系,其明净、清秀和凄楚与新月的聪慧、美丽与不幸异质同构。喻体、喻指浑然一体,成为联结人与物、感性和理性的桥梁,既将作者寄寓的物象提升至人生命运的高度,也加深读者于大喜大悲后的生命体验。“新月”这一意象因其不完满而令人感慨万千、更因其残缺而使文本充溢悲剧色彩。而在伊斯兰文化中,新月是崇高、清静和希望的象征,二者对“新月”的理解是截然相反的。
在文本中,与“新月”这一意象具有隐喻关系的主人公新月短暂的一生,经历了“幸福地出生—家庭的不幸—甜蜜的爱情—走向葬礼”这一悲喜交织的过程。它暗示着,作者笔下的“新月”意象是一完全游离于这两种“新月”意象之外的第三种存在。这一现象揭示了《穆斯林的葬礼》与生俱来的间性特质。间性具有居间、中间、中介等多重意义。布伯认为在“我一你”的关系中永远存在一个距离即“之间”,这个“之间”仅在于双方之间而不能在发现的双方中发现。也即,你与我可以通过对话联系在一起,但彼此都保持自我特点,不会融为一体。实际上,二者因差异而进行对话时,应始终保持各自的独立性,继而会有相互融合后的重新生成,它表现为间性特质。
一、间性视角、民间土壤
通过文本细读,我们不难发现,《穆斯林的葬礼》正是作者多重身份(回族、知识分子,女性)和艺术追求,与《白蛇传》、《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民间爱情传说“棒打鸳鸯”式悲剧模式及其文化内蕴所进行的对话的产物。当然,这一对话是在双方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融合的前提下进行的。
与生老病死一样,爱情是文学又一永恒的母题。古往今来,对爱情的思考与表现是许多艺术家乐此不疲的话题。描写爱情生活、展现爱情理想的作品也似乎层出不穷。喜剧也好,悲剧也罢,大众对这类作品的兴趣日益浓厚。然而,在文学传承中,爱情悲剧更以其撕裂人心的艺术感染力备受关注与青睐。《穆斯林的葬礼》同样关乎爱情。民间爱情传说《白蛇传》、《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所固有的“棒打鸳鸯”式悲剧模式在《穆斯林的葬礼》同样可见一斑。细心的读者甚至会发现,在文本中,男女主人公的心灵就是在梁祝空灵的旋律中紧紧地贴在了一起,新月去世多年后,她的爱人也同样以这首在中国几乎人尽皆知的曲子寄托哀思。
依据结构一功能分析模式,《白蛇传》、《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民间爱情传说大多经历了男女相爱(许仙与白蛇;牛郎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阻力产生(法海与雷峰塔;王母娘娘与天河;祝父与婚配)—劳燕分飞(以塔为界;隔河相望;违心出嫁)—幻化结合(雷峰塔倒;鹊桥;化蝶)四个阶段。
在中国,这一悲剧模式有其生长、发育的现实土壤—儒家思想及其文化。儒家思想及其文化致力于建设一个父慈子孝、兄良弟善、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社会。在这种环境下,男女婚配作为关乎种族繁衍的大事,就毫无疑问地纳入其管辖范围了。朱熹曾视“存天理、灭人欲”为儒家思想的精华,在他的理解中天理即三纲五常。受儒家思想制约的中国古代婚姻观是一种蔑视爱情、关注伦理的功利主义婚姻观。成家立业、传宗接代、维持社会稳定是其口的;强制包办是其唯一的方式;残酷无情是其最根本的特征;对美好爱情有朦胧渴望,并由此萌生追求意识的青年男女正是其压制、打击的对象。可想而知,在青年男女为争取理想爱'隋而进行的与儒家思想、文化的抗衡中,失败者只能是他们自己。古代,身为知识女性的霍达,在现代社会也同样感觉到了这种思想文化无所不在的渗透力量。在《穆斯林的葬礼》中,身为新月“母亲”的韩太太在新月高考前就曾动过为新月“聘个人家儿”的念头,在新月和楚雁潮相恋后,这种想法更为强烈:“……要是为主的能给你这条命,我就快快地找个回回人家打发你走……然而,新月的悲剧爱情在继承这一悲剧模式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以主人公的死亡落幕。在“棒打鸳鸯”式悲剧模式中,爱情的反对者一般是实有其人的,如《白蛇传》中的法海,《牛郎织女》中的王母娘娘,《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祝父,而在《穆斯林的葬礼》中,它己虚化为一种宗教力量—回族不能与“卡斐尔”结婚的伊斯兰教教规。
新月的母亲本能地反对新月与楚雁潮相爱:“你就不知道自个儿是个回回吗?回回怎么能嫁个‘卡斐尔,;喻斯兰教是以信奉“安拉”为基本特征的宗教,“安拉”是阿拉伯文音译,原意为“神”,意译为“真主”,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称为“穆斯林”,他们的“男婚女嫁”制度不允许与异教徒联姻。回族与汉族以及其它不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通婚,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即非穆斯林一方,需要坂依伊斯兰教,并在生活上无条件地跟从穆斯林,同时这种通婚一般只允许非伊斯兰教女子嫁给穆斯林,而穆斯林女子不能嫁给非穆斯林。于是回族穆斯林女孩新月与其汉族恋人楚雁潮的爱情被注定向悲剧靠拢。
对新月的爱情而言,更为可怕的事情是这种教规己内化为自己“母亲”的一种思维方式、处事原则—“我j‘可看着你死了,也不能叫你给我丢人显眼!;随正如《伏羲、伏羲》中,内化在主人公杨天青、王菊豆心底的“乱伦”伦理观念。他们二人爱情的真正阻力不是杨金山,也不是杨天白,而是这种“乱伦”思想,那鲜为人知的恐惧感、罪孽感不但束缚了他们的肉体,也栓桔着他们的灵魂。
在《穆斯林的葬礼》中,通过积淀,宗教便内化为韩太太的心理,成为造成新月不幸的外在力量,赋韩太太的干涉行为以力量和合理性,也使新月的反抗不仅针对宗教,也指向了宗教的代言人—自己的“母亲”、指向了亲情。在传统“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婚嫁语境及儒家道德观念中,反抗父母即意味J降逆、不孝。在古代,青年男女要结婚,必须通过媒婆的牵线搭桥与父母的认同才能实现。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中,虽然二人同窗多年,互相爱慕,但祝英台还是暗示梁山伯前来求婚,因为媒灼之婚才能得到父母的认同与祝福。然而,在梁山伯赶来时,祝父己经将英台许配给了马公子,爱情悲剧因为父母的意志而拉开序幕。受过新思想影响的楚雁潮也不得不遵从这一传统,请求韩太太首肯他与新月的爱情。
“您以为我和她之间还会有什么……婚事吗?我是求您答应我把她娶走,去……生儿育女吗?命运对她并没有这么宽容,人间的许多美好的事物己经很难再属于她了!她是一个病人……她需要爱,需要力量、需要希望,为了她,我一切都愿意献出来,只要她不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只希望她能活下去!
韩伯母,不要夺走她心中的这点儿希望,我求您!谈婚姻,既便是爱情也要得到双方父母的认同,楚雁潮有勇气挣脱自己母亲的束缚,但而对韩太太的强硬,“他的心、他的全身、他的灵魂都在战栗!”“一道人间天河横在他的而前,他怎么能离开新月,新月又怎么能离开他?两颗紧贴在一起的心分开了还怎么能活下去!”既使是被王母娘娘用天河隔开的牛郎与织女,也有鹊桥相会的那一天,可楚雁潮与新月的爱情却因人间这无影无形又无处不在的天河终成悲剧。既然紧贴在一起的心分开了便无法活下去,那么,死亡只能是这段爱情唯一的结局,新月由爱情走向葬礼便也在意料之中。
不过,因为这一结局与读者善良的愿望相去甚远,取得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这在实质上与悲剧就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美学特征不谋而合。
二、文本之间、互文解读
在韩太太近乎冷酷的反对与不惜一切手段的干涉中,曹七巧的影子若隐若现。这一发现提供了对文本进行互文性解读的可能。所谓“互文性”,就是指本文的“互本文”特性。在隐喻意义上,“互本文就像将原有文字刮去后再度使用的羊皮纸,在新墨痕的字里行间还能瞥见先在本文的未擦净的痕迹。;喻此巴尔特理解为: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文本—先前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互文性”解读即借助一部文学文本和其他文本相互“应和”、相互联系的种种方法,来探寻文本间的相互作用,从而找到一条通向文本意义的道路。所以,将文本《穆斯林的葬礼》放在与《白蛇传》、《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民间爱情传说和《金锁记》等文本所形成的对话场中,分析此文本与其他文本经由对话而形成的间性现象,探讨这一现象在《穆斯林的葬礼》中是怎样表现的,进而探寻文本美学价值的思路是可行的。
除了宗教因素,韩太太对新月爱情的阻碍与干涉,还基于其嫉妒心理。法海千方百计地拆散许仙与白蛇是因为他嫉妒他们甜蜜的爱情,鲁迅就曾这样说过:“和尚本应该只管自己念经。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经卷,横来招是搬非,大约是怀着嫉妒吧,—那简直是一定的。”《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也容不得无可挑剔的刘兰芝。当然,焦母的嫉妒更是其寡居多年变态心理的一种表现,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也一样。不同的是,她不仅嫉妒儿媳的幸福,也见不得女儿长安为爱陶醉的笑脸,因为她自己不曾拥有过爱情。
至于因为不得己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J性质者居多。欧洲中世的教士、日本维新前的御殿女中(女内待),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阴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一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嫉。
由于自身的情爱得不到及时的释放,压抑了的'隋爱也只能被变态、扭曲地寄寓在子辈身上,于是,纯洁的母爱便渐渐发生异变。韩太太也是一个缺失爱情的女性形象,与韩子奇之间以“合伙过日子”为口的的结合,以及婚后貌合神离的婚姻生活,加之其中的插曲—丈夫的别恋与背叛,都使本不知爱情为何物的她本能地排斥、蔑视爱情:翎桑死我了……张嘴就是‘爱’,亏你还说得出口!”‘3内在精神的失衡导致她产生人格障碍,使她逐渐不近情理、一意孤行,通过猎取管教儿女的权力填丰卜失落的情感。
《金锁记》等爱情悲剧中的权力指涉对象,她们对待干预的态度是惫忠与顺从。而对母亲的步步紧逼,长安选择了哭泣与忍让,她那些不满与委屈只能通过被压抑的曲调在夜间幽幽倾诉。“那呜呜的口琴忽断忽续,如同婴儿的哭泣。她接不上气来,歇了半晌。”,而窗外“模糊的缺月,像石印的图画,下而白云蒸腾,树顶上透出街灯淡淡的圆光。”“文本从月亮写起,又以月亮结束,加深了悲剧的深刻性与一贯性。长安是其不幸爱情的被动承受者,在曹七巧毁了她的爱情后,她只能将自己关于爱情的那些零散回忆—“她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爱”理解为“将来是要装在水b,瓶里双手捧着看的”。‘5这是一种口睹自己的所爱变成标本的无奈与疼痛。在曹七巧无所不在的控制、管束下,她己对爱情、甚至生命不再抱任何美好的幻想了,她很清楚,只要自己的母亲在,走进她感情、生活中的任何人,都不过是另一个童世舫而己。
但《穆斯林的葬礼》中,新月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反抗,直至她生命的尽头。她不明白,自己的母亲为什么要夺走她所拥有的爱情,“实在说,我根本没想到我和他的爱情还要得到您的同意,我只认为爱是自发的、天然的、无条件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难道这是命运的安排—“把给了她的再夺走,把她的心折磨的千疮百孔,再让她在清醒的痛定思痛中等待着死?”,而“没有希望,没有爱的人生还不如死,死也许并不那么可怕吧?”‘日她不愿放弃爱情,哪怕以死为代价。也可以说,新月的不幸陨落并不等同于她爱情追求的失败。谁都有权利生活,有权利爱,所以,在阻力重重的家庭、宗教环境中,她仍义无反顾、纯真热烈地去爱,去追求爱。在新月弥留之际时断时续的意识流动中,楚雁潮以及他们的爱情曾多次闪现:“天亮了,她就可以看到楚老师了。她多想早一点儿看到他!”
“……我这眼睛怎么了?再也看不见哥哥嫂子了? ……看不见楚老师了……”“‘楚……她竭尽全力呼唤他……”
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发现,由于以其母亲为代表的反对力量的强大,新月的反抗便似乎没有成功的希望,“妈妈不是说得清清楚楚吗?宁可让她死,也不……‘在情节的这一部分,身为爱情的维护者、追求者的新月和以其母为代表的爱情破坏者的矛盾冲突己达高潮。在黑格尔看来,悲剧就是两种伦理力量的冲突与和解,悲剧的产生与矛盾冲突是不可分害」的统一体。因为悲剧根源于两种对立而又各具片而性的思想、观念的冲突,且悲剧主人公总是致力于达成自己的理想,冲突的对抗性、排他性以及冲突结果的唯一性便在所难免。于是,在新月和她母亲之间必须有一方做出妥协。至于这一方究竞是谁,作者无法也不能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但吸收多重艺术养分成长起来的霍达,深谙艺术规律,懂得怎样使悲剧更富感染力。所以,新月这个美丽、无辜的女孩就如“新月”这一意象所喻指的那样逐渐暗淡,过于仓促地结束了她短暂的一生。
死亡意象是悲凉的,可作家通过死亡做出的思考却是积极的:新月的陨落,使她的悲剧在冲突双方的对立统一中,获得了一种和谐的美。“爱”的力量消解了“怨”与“恨”,韩太太虔诚地为女儿祈祷,并以自己的眼泪思念女儿,感受爱。比例适度、和谐统一是西方传统美学观的特点,在其自身的发展中,和谐美又逐渐容含了对立统一的和谐这样一种内涵。而中国人历来崇尚大团圆的结局,古代悲剧多追求团圆之趣,并侧重以象征性的美满结局赞美死者、唤醒后人。《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梁山伯与祝英台终双双化蝶、比翼双飞,《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与刘兰芝变成了双飞鸟,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则死后复生并与柳梦梅结合。
既使作品本身的结尾并不喜庆,在流传中也会被受众美化、喜剧化,读者对《白蛇传》改写与再创造便是一活生生的例证。五四以后,由于西方悲剧观的介入,我国许多作家也运用推崇以悲做结的悲剧手法,巴金《寒夜》中的曾树生与汪文宣不得不分道扬镰,田汉《获虎之夜》中的黄大傻无奈中选择了自杀……身为知识女性的霍达也不例外—中国人崇尚大团圆,《穆斯林的葬礼》却一反传统,真主赐予人爱情,可新月的爱情却以悲剧告终。
无论从文化传统、文学土壤、艺术创新,文本间的相互作用,还是从宗教因素、人物心理、作者多重身份、美学倾向入手,“葬礼”只能是新月最好的归宿了。关于爱情的战争在她的葬礼中由喧嚣走向j‘静,楚雁潮在她的葬礼中祭奠着自己的爱'隋,读者在她的葬礼中领略了悲剧艺术扑而而来的感染力,论者亦在她的悲剧中找到了文本的又一解读方式—间性视角、互文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