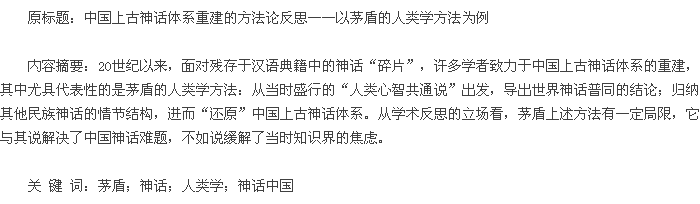
20 世纪初,随着域外神话的大规模输入,许多学者开始在汉语典籍中寻找相应的“神话”。不过,令这些学者备感受挫的是,见载于《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书中的神话资料,呈现出与希腊、北欧诸国神话截然不同的面貌。面对残存于汉语古籍中的神话“碎片”,如何重建中国的上古神话体系,成为众多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茅盾运用人类学方法对中国上古神话体系的重建。时隔一个世纪,随着中国神话学的日益成熟,如何在继承前人学术遗产的同时又能进行自觉反思,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本文即以茅盾为例,对其重建中国上古神话体系的方法作一反思性考察。
一、茅盾与人类学派
神话学作为国内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茅盾很早就对欧洲文学表现出强烈兴趣。正是在这种兴趣的促发之下,茅盾在上世纪20年代初便走上了神话研究的道路。据茅盾晚年自述,当时为了系统考察欧洲文学的发展历程,他开始研究古希腊的两大史诗;由希腊史诗出发,他进而又对作为欧洲文学源头的希腊神话产生兴趣。茅盾当时推断,既然地处南欧的希腊有着如此丰富的神话,那么北欧各民族也应当有自己的神话。于是,茅盾利用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便利,搜罗可能买到的英文书籍,果然找到介绍北欧神话的资料。接着又查《大英百科全书》中的“神话”条,知道世界各地“半开化民族”亦有自己的神话,只不过与希腊、北欧神话的面貌、风格有所不同而已。根据上述发现,茅盾进一步推断,有着悠久历史的华夏民族不可能没有神话,于是又在汉语古籍中寻找神话,从而转向了中国神话的研究[1]。
茅盾当时所接触到的西方神话学理论不止一家,不过最令他服膺的,是以安德鲁·兰为代表的人类学派神话学。茅盾曾将神话区分为“合理的”与“不合理的”两种,在论及后者时说道:“自古以来,有许多神话研究者曾经从各方面探讨这个谜,不幸尚无十分完善的答复,直至近年始有安得烈·兰的比较圆满的解释。诸君要想知道安得烈·兰的解释,请看本刊第三一九期拙着《人类学派神话起源的解释》罢。”[2]
茅盾在此毛遂自荐的这篇文章原载于《文学周报》,系对人类学派神话学、尤其是安德鲁·兰的神话学理论的集中介绍。在茅盾之前,周作人、黄石等对安德鲁·兰的神话学理论已有介绍,不过与后二者不同的是,茅盾在这篇文章中还追溯了安德鲁·兰神话学理论的来源——从攸栖比呵斯(Eusebi-us)关于异教的辩论直到爱德华·泰勒的《原始文化》,中间有斯本塞 (L. Spencer,今通译作“斯宾塞”)、封特涅尔(Fontenelle)、特布洛斯(De Brosses)、曼哈尔特 (Mannhardt)、罗培克(Lobeck)等人承前启后。自然,文章详细介绍的,是作为安德鲁·兰神话理论直接来源的《原始文化》。不过,与泰勒相比,茅盾对安德鲁·兰更为推崇。在这篇文章中,茅盾将安德鲁·兰的观点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以今证古”的方法,即借助现代“野蛮民族”的思想和生活,来印证万年以前原始先民的思想与生活;第二,从对现代“野蛮民族”的研究,推知原始人心理的特点;第三,“遗形(survival)说”(今通译作“文化遗留说”),即在流传至今的各种神话中,愈是包涵有“不合理”的元素,愈可能是原始神话的“遗留”,因而更加接近神话的最初形态[3]102-104。
当然,对安德鲁·兰理论的局限,茅盾并非没有察觉。比如,按照人类学派神话学的观点,所有神话都是早期人类出于好奇心而对周围自然界所作的一种错误的解释,茅盾却认为:“神话中也有一部分未必准是原始人生活与思想的反映;例如希腊神话的远征忒洛族的故事,今已证明确有几分历史性(至少,希腊民族与忒洛族的战争是事实),而此外关于民族英雄的冒险故事,大概也是有所本的。”[3]105这里显然是对历史学派神话解释的某种认同。不过,就当时已经流行的各种神话理论而言,在茅盾看来,更为可取的仍然是人类学派的解释:“大体而言,我们不能不说神话之起源是在原始人的蒙昧思想与野蛮生活之混合的表现。以此说为解释神话的钥匙,几乎无往而不合。这便是人类学派优于其他各派的原因。”[3]105正是出于这种原因,茅盾对于中国上古神话的研究,主要借鉴的便是人类学派的方法。
二、人类学与中国上古神话体系重建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茅盾不仅是较早向国内介绍人类学派神话学的学者,而且是全力搜集中国上古神话的第一人。后一种成绩,早在上世纪30年代已有人论及:“中国向无研究神话的专着,前人亦仅指杂记琐事而无当于大道的书为古代小说,因此神话多被掩埋。及鲁迅着《中国小说史略》,开卷即叙神话,而玄珠着《中国神话研究》,专替古代神话作发掘,于是被掩埋的神话渐被发现出来。”[4]
由于中、西方文化之间的隔膜,19世纪后期,一些西方学者断言中国没有神话。20世纪初,随着“神话”概念由西方经日本传入中国,许多人终于在中国上古典籍中找到了类似的“神话”。不过,与希腊、北欧神话相比,中国神话明显零散、不成体系,这自然引起一些学者的好奇与焦虑。当时的学者中,日本的盐谷温,中国的鲁迅、胡适、冯沅君等,均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神话“匮乏”、“零散”的原因进行过探讨[5-8]。
与上述诸人不同的是,茅盾不仅想证明中华民族亦有自己的神话,而且要从各种典籍中梳理出一条中国的上古神话体系。1924年完成的《中国神话研究》与1928年在日本东京完成的《中国神话研究ABC》,便是这种努力的体现。后者主要是根据安德鲁·兰的文化人类学方法和“文化遗留说”理论,对头绪纷乱的中国古代神话作一整理与分析,从方法来说,明显是对前者的延续,因而本文重点讨论的是前一篇文章。
在《中国神话研究》一文中,茅盾首先引述安德鲁·兰和麦根西 (D. A. Mackenzie) 的观点,说明世界各个民族在原始阶段具有大致相同的思想与信仰,所以其神话也大体相同。不过,由于各民族生活环境的差异,其生活经验也因之各不相同,这便导致各民族神话在趋同中又表现出自身特色。另一方面,茅盾又强调,现今所见各“文明民族”的神话已非其原始形态,而是经过后世文学家的加工,尽管其原始形态依旧有所保留:“神话既是原始信仰的产物,流行于原始民族社会间,则当一民族文明渐启,原始信仰失坠以后,此种表现原始信仰的故事当然亦要渐渐衰歇,尚幸有古代文人时时引用,所以还能间接地传到现代。”[9]
此外,在茅盾看来,当一个民族与某种后起的或外来的宗教相遇时,其神话也会发生变异,比如基督教传播到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时北欧神话所发生的变化。
以上所述似乎与中国神话无直接关联,实际上,茅盾是通过对世界各民族神话总体特征的归纳,为即将讨论的中国神话设定原则和标准。仔细分析起来,这些原则中隐含着三组二项对立:原始神话一文人加工过的神话木土神话一外来神话。
原始宗教神话一后起宗教神话 将以上二项对立中的右边各项剔除,剩余左边各项所反映的便是一个民族的原初神话形态。茅盾所要做的,正是重构纯正的“中国神话”(实际为“汉民族神话”)。不过,山于中国神话向来未有专书辑录,散见于占书者又十分零散,兼之占代中国与域外文化的交流十分频繁,因而重构“中国神话”谈何容易!针对这一难题,茅盾借鉴安德鲁·兰等的理论,首先区分现今流传下来的中国神话传说中,哪些属于上占先民信仰与生活的真实反映,哪些属于后世方士的伪造与发明;然后根据“生活经验不同则神话各异”这一原则,将外来神话从中国神话中剔除;最后寻求未经佛教思想改造的中国神话。经过上述剔抉,便可以看到中国神话的大致面目,用茅盾的话说:“我们如果照上面说的三层手续来研究中国神话,把那些冒牌的中国神话都开除犷,则所余下来的,川一以视作表现中华民族的原始信仰与生活状况的神话。”当然,这些神话的多寡也有差异,比如“幽冥世界的神话”,在占书中便十分稀见,见载于后代典籍的,却多少已经过道教或佛教的改造。又如“万物来源神话”,数量也极为少见,茅盾举出的只有蚕的来源神话—即便如此,这一神话是否可靠还值得怀疑。
其实,上述只是茅盾重建中国神话的第一步,因为将二项对立中属于右边各项的神话材料剔除之后,剩下的顶多是错综复杂甚至相互抵梧的汉民族神话“碎片”。如何将这些“碎片”组织成一个井然有序的“神话体系”,则是茅盾下一步的目标。茅盾的办法,依然是参照人类学派的理论,先归纳出其他民族神话的主要特点与情节结构,然后以之为参照来重构中国神话。当然,这中间有一个预设—世界各民族神话大体相同—这也是人类学派的理论基点之一。
茅盾首先注意到,中国占代记载神仙的专书如《列仙传》、《神仙传》等,虽然也载有诸神世系,但以人类学派的观点来考察,这些书中所讲述的大多是方士的“谰言”,而非中华民族的神话,理山有二:一是世界各民族神话均为对某种自然现象的解释,而上述书中载录的却是炼丹修道、长生不老之类的故事;二是原始人以自己所居住的地方为世界全体,而《十洲记》等书中所描绘的却是别处的洞天福地,因而与原始人的宇宙观不合。既然上述诸书无法采信,要建构中国的“神话体系”,只有从占史人手。与“占史辨”派的代表人物顾领刚一样,茅盾也断言中国上占史中的大部分实即中国神话。再证之以世界历史,“神话历史化”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比如占希腊学者武赫默洛司(Euhemerus )、冰岛史学家斯奴罗·斯土莱松等,就曾将希腊神话、北欧神话附会为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既然如此,后世研究者反过来从前人的历史着作中钩稽神话,当是一条可行的途径。以盘占神话为例,在《三五历记》、《述异记》和《五运历年纪》等占籍中,分别保存着这一神话的三个片断。借助于比较神话学知识,茅盾发现这儿个故事中的主要叙事单兀,如“天地混沌如鸡子”、“身体化为宇宙万物”等,在芬兰、印度、希腊乃至北美伊罗瓜族的天地开辟神话中均曾出现,因而可以确认,有关盘占的这儿条“史料”,实为中国天地开辟神话的“断片”。茅盾又以上述民族的开辟神话作为“模板”,将《三五历记》、《述异记》等书中的相关记载“连串”起来,所得结果便是汉民族的天地开辟神话。
上述结论出发,茅盾又联想到《列子》和《淮南子》等书中所载的女蜗补天故事,认为这是中国创世神话的后半段,因为参照世界其他民族的神话,只有将盘占开天辟地与女蜗补天两组J睛节合并起来,才是完整的中国创世神话。不过这又引出一个问题:在盘占开天辟地和女蜗补天之间,缺少“天崩地陷”的中间环节。木来在《列子·汤问》中,也载有共工怒触不周山而致“天柱折,地维绝”的片断,但从时间来看,这段神话是在女蜗补天之后。为明厂起见,现将《列子》与《淮南子》中的两段神话资料引述如下,并标示出其中的情节单兀:
情节单元A: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民,鹜鸟攫老弱。(《淮南子·览冥训》)情节单元B:女锅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淮南子·览冥训》)情节单元C:昔者女锅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闭,断鳌之足以立四极。(《列子·汤间篇》)情节单元D:共工氏与J“项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列子·汤间篇》)茅盾认为,上述四组情节单兀中,B与C可以视做一项。如果将这四组材料与盘古神话“连串”起来,便得到下面一组情节结构:盘古开天辟地——四极废,九州裂(A)——女娲炼五色石补天 (B,C) ——共工怒触不周之山(D)。以上结构中,其他三项均为完整的叙事,惟有第二项混沌不清,既没有“施动者”,也不知灾难发生的原因。对于这一难题,茅盾采用神话中屡见不鲜的大洪水来解释:“中国民族的神话里本来也有洪水的故事,后来不知什么缘故,竟至失传,却只剩了破坏后建设——即女娲氏炼石补天——的故事了。”[9]
其理论依据,依然来自于跨文化的神话学资料,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民族的神话都在讲述天地开辟、人类创生以后,有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洪水将世界毁灭。至于洪水的原因,茅盾援引其他学者的观点来解答:“这些洪水神话,有人解释是原始人所身受的最后一次因冰川融解而发的大水的经验的记录。这个经验,据说是温热带地段居民所共有的;今证之以凡居温热带地段的民族几乎全有这段神话,觉得这个假定似乎可以成立。”[9]
如果说异民族神话属于中国式洪水神话“外证”的话,那么,《淮南子》中“水浩洋而不息”几句记载,便是中国式洪水神话的“内证”。再根据女娲“断鳌足以立四极”的叙述,茅盾推知洪水的始作俑者为鳌。如此一来,盘古开天辟地与女娲补天之间的“缺环”终于得以弥补:“我们不妨想象我们的祖先曾把他们那时传下来的地面最后一次洪水的故事,解释作因为有鳌作怪,发大水,以至四极废,九州裂,然后女娲氏斩鳌,断其足以为天柱,把天撑住,又补了有破痕的天,乃创造第二次的世界。”[9]
经由茅盾的大胆想像与推论,载录于中国古籍中的几则神话“碎片”终于被编织得秩序井然。不过,茅盾对上述推论显然有些不够自信:“这个想像,似乎也还近理,就可惜于书无征。”[9]
三、对重建中国上古神话体系的反思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茅盾的神话研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一方面,茅盾所提出的中国神话三大区域说、西王母神话演化说等重要命题,今天依然引起许多研究者的讨论与争鸣。另一方面,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学界曾出现一次神话研究的高潮,茅盾、黄石、谢六逸、林惠祥等的神话学专着纷纷于此时面世。不过相比之下,后几位学者主要致力于西方神话学知识的介绍;论及对于中国神话的专门研究,茅盾当属第一人,其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中国神话研究ABC》一书,是第一部由国内学者所撰写的中国神话学专着。更为重要的是,茅盾借鉴域外神话重建中国上古神话体系的尝试,成为嗣后许多研究者致力的目标。从民国时期卫聚贤、孙作云、程憬直到当代袁珂、朱大可等学者,其神话研究中均可看到这种努力的踪迹。因而,对茅盾重建中国上古神话体系的方法进行反思,不仅具有学术史的意义,对于当下中国神话学的建设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笔者将茅盾重建中国神话体系的方法概括为:由原始先民“心智共通说”出发,导出世界神话普同的结论;归纳其他民族的神话模式,“复原”中国上古神话体系。打个比方,这种“神话复原”的方法如同博物馆中的拼图游戏:我们面对的是一堆色彩斑斓的史前陶片,需要参考某种模板将其复合。所不同的是,博物馆中的模板是给定的、已知的,而我们面对的神话“模板”则仅仅是一种基于“人类心灵共通说”的类比,很难在实证意义上对其加以证实或证伪。
进一步说,所谓“人类心灵共通说”,不过是19世纪心理学家的一种理论假说,而建立在此假说基础上的“中国神话体系”,则是假说的假说。因而面对同一个对象,不同的研究者可能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比如,茅盾采用人类学派的观点,认为“嫦娥奔月”并非纯正的中国民间神话,而是经过后人的虚饰,对此,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另一位重要人物钟敬文则提出质疑:《淮南子》云:“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以奔月。”……沈雁冰极否认此条为真的民间神话。他最重要的理由是,“原始人民对于日月的观念有一个特点,就是即以日月神为日月之本体,并非于日月之外,另有日月之本体。现在《淮南子》说姮娥奔入月中为月精,便是明明把月亮当做一个可居住的地方,这已是后来的观念,已和原始人民的思想不相符合了。”这话不见得很可靠。[10]
值得注意的是,钟敬文反驳的依据,依然来自人类学资料。在《楚辞中的神话和传说》一文中钟敬文依次列举墨西哥人、南非布西曼族人恩康戒湾土人、美洲墨斯喀族人、喜马拉雅ournalJfoanzhouLrniveUsity(ocialSciencesS)Vo1.34o.N1/anuaryJ,0152卡西亚族人的日月神话为例,来反证许多民族中其实都流传有日月中神系由地上凡人变化而来的神话。
茅盾和钟敬文分歧的节点,在于人类神话本来是纷繁多样的,任何一个神话学者,都无法在穷尽人类所有神话的基础上概括出其普遍的情节模式。虽然在世界神话学史上也不乏有此雄心的学者,比如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他曾借助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试图发掘出人类神话叙事背后的“普遍语法”。不过,列维-斯特劳斯的建构对象仅仅是超验层面的“深层结构”。至于神话叙事表层的情节结构,依然呈现出千差万别的样态,很难用某几种固定的模式来简单归纳。对于茅盾等学者而言,他们试图重建的,却正是神话的表层情节叙事。由于不同学者所选择、借鉴的民族志资料互有差异,因而以之为参照对中国上古神话“残片”进行“复原”时,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在笔者看来,茅盾对于中国上古神话的“重建”,与其说解决了一个学术难题,不如说缓解了当时知识界的普遍焦虑。在当时知识分子看来,希腊、埃及、印度等文明古国皆有自己的神话体系,惟独中国例外,这难免让他们产生一种“世界弃子”般的心理挫败感。而茅盾从浩如烟海的汉语典籍中钩稽出中国的神话体系,无疑是对上述心理挫折的一种补偿。在对盘古神话进行“成功”复原后,茅盾便说过一番耐人寻味的话:这便是中国神话的第一页,若照兰氏的各民族开辟神话的方式看来,中国的开辟神话与希腊、北欧相似,不愧为后来有伟大文化的民族的神话;虽然还嫌少了些曲折,但我们可以假定这是因为后人不会保存而致散佚,原样或者要曲折美丽得多呢![9]
不难看出,这段话与其说传达的是学术发现的喜悦,不如说是民族主义的激情。也许令茅盾始料不及的是,由于盘古神话的晚出,后来的一些研究者否认此一神话的中国本土发生说,而认为系由印度随佛教传播而来。
如果我们作一番考察,会发现中国神话研究中这种混杂着民族情绪的焦虑感贯穿了整个20世纪。1928年,黄诏年在《民间神话》一文中便说道:“中国的神话,也如其他的事情一样,国内很少人注意,倒被国外的人工作起来……的确的,中国的神话如果全国的材料汇起来,下一番整理的功夫编本代表集,其成绩定会惊人,以我个人看来,中国的神话的丰富伟大,决不会逊色于古希腊很多,在世界文艺史上,中国的神话,也是一朵永不凋谢的白莲。”[11]
尽管黄诏年对茅盾神话研究中过于“注重于书本”略有微辞,但其有关中国神话的判断,又与茅盾的口吻何其相似。
半个多世纪后,我们从一些学者的论述中依然可以感受到这种焦虑:“美国神话学家杰克·波德说:‘特别应该强调的是(如果把盘古神话除外)中国可能是主要的古代文明社会中唯一没有真正的创世神话的国家。’杰克·波德先生没有调查研究,这样武断,完全是跟欧洲的一些学者鹦鹉学舌。我们有理由有根据地讲:现在应当颠倒过来:中国是唯一拥有最丰富最‘真正’的创世神话的国家。”[12]100说中国是“古代文明社会中唯一没有真正的创世神话的国家”,当然失之偏颇;但又断言“中国是唯一拥有最丰富最‘真正’的创世神话的国家”,则是从一种极端走到了另一极端。
从学理的层面来看,笔者以为,茅盾等学者的主要缺失,一方面是受五四时期西化思潮的支配,以西方文化的源头之一希腊神话作为普遍性范式,先验地认定中国也有类似的神话体系存在,只是因时间的流逝或历史的原因,这种体系早在汉字记录之前就已经瓦解;另一方面,则是受其职业身份所限,将神话单纯视为“文学”的一种亚型,由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特殊性,要在汉语文献中找出类似希腊、罗马神话一样的叙事类型,只能是削足适履。
近年来,神话学者叶舒宪从中、希文化比较的视野出发,提出“神话中国”的视点,也许能给予我们一些启示,从而为“后重建”时代中国神话学的发展提供一条可能的进路。所谓“神话中国”,是相对于传统的“中国神话”而言,指的是“按照天人合一的神话式感知方式与思维方式建构起来的五千年文化传统”[13]。这一新的概念折射出中国神话学范式的根本转变:如果说后者欲借助中国典籍来重建古希腊式神话叙事,前者则意在突出中国神话自身的特殊性。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献中原本无“神话”一词,这个概念是在20世纪初由王国维、梁启超等学者率先从日本引入;其最初的源头,则是希腊语中的“mythos”(秘索斯) 一词。在叶舒宪看来,“秘索斯”(神话)概念在古希腊的出现,有着特定的思想背景:“轴心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要走出神话世界,建立理性权威,因而创造出“秘索斯”(神话) 这一概念,以作为“逻各斯”(理性)的对立面。相对于古希腊来说,中国在历史上并未出现类似的“哲学突破”阶段,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生活在神话式的思维和感知之中,因而也就没有类似西方“秘索斯”(神话)概念的创造。如此一来,要在中国典籍资料中重构类似古希腊的上古神话体系,无异于缘木求鱼[14]。叶舒宪的上述论断,自然也有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地方,比如“秘索斯”与“逻各斯”的原始意涵、二者出现的时间先后问题,以及古希腊知识界看待“秘索斯”与“逻各斯”的态度等。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思路为我们走出“重建中国神话体系”的迷宫,提供了一种可贵的视点:我们无需焦虑中国上古时代是否有丰富的神话在流传,因为我们从古至今便生活在神话构成的意义世界之中;我们也无需汲汲于重建中国神话体系,因为不同民族文化自有其特殊性,中国上古神话未必同希腊神话呈现相同的样态。
参考文献
[1] 茅盾 . 神话研究·序[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
[2] 茅盾 . 神话的意义与类别[M]//茅盾全集:第 28 卷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113.
[3] 茅盾 . 人类学派神话起源的解释[M]//茅盾全集:第 28 卷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4] 郭箴一 . 中国小说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40.
[5] 盐谷温 . 中国文学概论[M]. 陈彬龢,译 . 北京:朴社印行,1926:89-90.
[6] 鲁迅 . 中国小说史略[M]//鲁迅全集:第 9 卷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