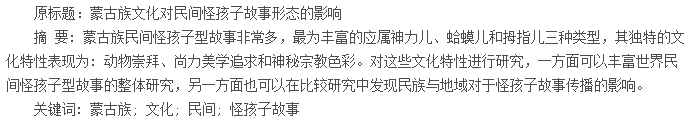
怪孩子故事,是世界民间童话故事中的一个独特类型,如枣娃、葫芦娃、蛋娃、蛤蟆儿、拇指儿、神力儿等。林继富曾对其进行过界定,认为怪孩子故事主要表现出“三怪”现象:出生怪、形体怪和行为怪。[1]因故事鲜明的幻想特质,汤普森和丁乃通都将其归入神奇故事(或者魔术故事、幻想故事、魔幻故事)进行过研究。蒙古族的这类故事也很丰富,对其进行研究,一方面可以丰富世界民间怪孩子型故事的整体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比较研究中发现民族与地域对于怪孩子故事传播的影响。
一、蒙古族怪孩子故事的主要类型
蒙古族民间怪孩子型故事非常多,前文所列的类型多有涉及,但最为丰富的应属神力儿、蛤蟆儿和拇指儿三种类型。
(一)神力儿
这类故事中的小主人公都是在出生以后几天就长大成人,并且具有特殊的能力,这种能力有时表现为具有神力,有时表现为具有特殊的技能,如捕猎、打鱼,他们往往被派去与魔怪作战,最后胜利而归。
这类故事在国内外的故事类型索引中找不到相对应的类型,属于蒙古族特有的故事类型,它很像蒙古族英雄史诗故事的精简版,基本的故事元素包括:神奇的诞生、上路、神奇的相助者、与魔怪战斗,也有的故事会包括神奇婚姻。较有代表性的有《虎王衣》[2](P25~31)、《巴尔·乌兰》[3](P94~105)、《八腿花马和乌兰巴特尔》[3](P167~175)、《神箭手》[4](P93~104)、《只有一根头发的小英雄》[5](P183~191)等。
(二)蛤蟆儿
这类故事的主要情节是:久婚不孕的夫妇祈求生育,没想到却生下一只青蛙,但这只青蛙具有人的情感和超人能力。青蛙长大以后想要娶亲,女方家庭会设置许多难题,青蛙借助神奇力量解决了难题,最终娶到姑娘。青蛙有时会变成英俊的青年参加各种活动,被妻子发现后,青蛙或生或死,或走或留。美国学者斯蒂·汤普森在《民间故事类型》中将其定为440A型,并命名为“蛙王或铁亨利”。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神奇故事”中也专门列出了“神蛙丈夫”,定为类型440A。德国学者艾伯华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中,将此类型故事划分到第四大类“动物或精灵跟男人或女人结婚”当中,将其命名为“青蛙皇帝”和“蛤蟆儿子”,定为42、43型。蒙古族较有代表性的有《青蛙儿子》[6](P701~703)、《青蛙王子》[7](P161~169)、《蛙仔的故事》[8](P181~185)、《蛙仔的故事(变体)》[8](P185~186)等。
(三)拇指儿
这类故事专指出生的孩子只有拇指大小却具有神奇力量或超人智慧的故事类型。美国学者斯蒂·汤普森在《民间故事类型》中将其命名为“拇指汤姆”并编成第700型。丁乃通先生在其《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照用了AT700型“拇指汤姆”的命名。在蒙古族的这类故事中以“羊尾巴儿子”的故事居多,故事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诞生”和“神奇冒险”。冒险部分的情节会有不同变体,但“被吞噬”、“帮小偷(或被逼)偷窃”、“从某人嘴里偷宝物”母题在很多故事中会保留。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耳朵一样大的孩子》[5](P162~166)、《拇指般大的儿子》[9](P391~400)、《山羊尾巴儿子》[10](P634~636)、《尾巴儿子》[11](P924~929)等。
二、蒙古族文化对民间怪孩子故事的影响
民间文学的流动性和变异性,一方面使世界各地的故事都表现得极其相似,另一方面又使同一个故事会存在很多异文。但是一个民族或者地域的故事总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相对稳定的元素,我们称之为民族的或者地域的文化符码。笔者认为,早期蒙古族的原始狩猎—游牧文化对于蒙古族民间怪孩子故事形态的生成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其呈现出与受农耕文化影响的怪孩子故事非常不同的文化特质,主要表现为:动物崇拜、尚力美学追求、神秘宗教色彩。
(一)动物崇拜
依据怪孩子的外形特征,林继富将怪孩子故事分为三类:植物型、动物型和蛋型[1]。但笔者认为分为植物型和动物型两类即可,蛋类属于动物型中的分支,动物型分支还应该包括人类,如神力儿故事。蒙古族民间怪孩子故事绝大多数都属于动物型。“蛤蟆儿”自不用说,男主角的形体是在蛤蟆(青蛙)和美少年之间转换;“拇指儿”的诞生多与羊直接相关;至于“神力儿”,其本身就属于广义的动物型范畴。
蒙古族民间童话故事是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故事融合的产物,汉藏语系的怪孩子故事中有很多植物型的,尤其以葫芦娃和枣娃故事居多,如果尊重故事传播史的话,相信这些故事一定同动物型的故事一同被传到过蒙古高原,但何以动物型故事会以其顽强的生命力蔓延到蒙古族的各个角落,而植物型故事却呈逐渐衰减之势?在文化的反复淘洗中,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怪孩子故事动物形态的逐渐扩大化和主流化?笔者以为蒙古族游牧—狩猎文化中的动物崇拜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
蒙古族经历了漫长的狩猎—游牧文化时期,动物崇拜在蒙古族人心中始终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猎物和畜群很多都成为蒙古族初民崇拜的对象。这种崇拜与天崇拜、家畜保护神崇拜、佛教信仰、经济民俗交织于一体世世代代绵延,同时又在文学叙述中被逐渐丰富、润泽,甚至神化。崔斯琴曾经对蒙古族动物故事进行过分类研究,仅她收集整理的动物故事蒙文版就有1957个,汉文版和日文版的就有352个[12](P468~616),动物以对手、伙伴、食物,甚至是精神的力量源泉等不同的形象被讲述和书写。相反,植物型的故事却很少,这与农耕文化开始较晚有很直接的关系。当然在蒙古族也存在着植物崇拜,但主要集中于树崇拜,以柏树、榆树、桦树、柳树崇拜居多,这与生殖崇拜密切相关。而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民族则不同,植物崇拜不仅包含树崇拜,还有五谷崇拜、茶崇拜、各类草药材崇拜。
动物型的怪孩子故事何以以青蛙小子和羊尾巴儿子形象居多?羊尾巴儿子形象是很好理解的,因为羊是蒙古族游牧文化中最重要的放养牲畜,世世代代陪伴蒙古人,是蒙古人生活富裕的象征,在五畜崇拜中马和绵羊是最重要的崇拜对象。这类故事也可能是原生的,也可能是在传播过程中为了顺应民族心理而发生了动物形象的替换。很多学者认为青蛙儿子形象应该来源于南方水乡,是农耕文化的代表形象之一,对蛤蟆儿故事的原发地域也进行过考证,但是考察蒙古族最早的宗教信仰———萨满教常用的器具图案,蛙是最古老、最稳定的形象之一,萨满在施法时手持的神鼓,其图案就是青蛙。可以断定,蛙崇拜在北方游牧民族中,尤其在信奉萨满教的古老民族中是存在的。我们不能由此妄言,蛤蟆儿故事的原发地域是在蒙古高原,但至少可以说明,在怪孩子故事传播过程中,当动物形象与蒙古族自身的动物崇拜一致时,这些形象就被完全保留了下来。由此可见,动物形象在故事的传承过程中,还是发生了自觉地选择与变更,这种选择与变更的土壤即是狩猎—游牧文化在蒙古人内心世界的潜移默化,他们按照自己的心愿选择和改造着故事的形象,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蒙古族民间怪孩子故事群。
(二)尚力美学追求
《韩非子》(卷六)中有“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的说法,“争于力”在战国时期就被认为是个体生命存在和强大,乃至一个集体、国家存在和强大的制胜法宝。考察蒙古族民间怪孩子故事,不管是降妖除魔型,还是难题求婚型,这些孩子在完成使命的过程中多表现出力大无比、勇武过人、法力神奇的普遍特点。是典型的“争于力”的生命形态。
神力儿故事中的怪孩子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可以与魔怪抗衡的形体和力量。神力儿古南不是一天一天的长大,而是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往上长。出生头一天就吃了一只整羊,第三天就能吃下一只母牛,并且打死一只老虎。他的“力量”传到可汗那里,可汗都为之震惊、恐惧(《虎王衣》)。只有一根头发的小英雄,出生第一天,一张羊皮做的皮袄就小的穿不下了;第三天,连三张羊皮做的皮袄都显得小了。他力大无比,徒手可以拧断马的脖子,还可以将马撕成两半,连蟒古斯恶魔也被他吓得魂不附体、屁滚尿流(《只有一根头发的小英雄》)。在蛤蟆儿型故事中,常常穿插难题求婚情节,蛤蟆儿往往通过哭、笑、叫、跳来显示自身强大的控制自然界的能力用以征服对方。
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内蒙古卷》中的《青蛙儿子》,青蛙儿笑能使树木枯萎、绿草燃烧;哭能使惊雷闪电,大地颤抖,暴雨倾盆,洪水泛滥;吼能使狂风大作,天地黑暗,大树也连根拔起。也有的故事在蛤蟆儿变成英俊小伙子以后会参加摔跤和赛马比赛,最终的结果都是获得冠军,如蒙古族巴尔虎地区的青蛙儿故事。其实在怪孩子故事中普遍存在着与他人争斗的情节,或者是与魔怪,或者是与国王,或者是与贪官污吏,在斗智斗勇中成就了孩子之“怪”。由于文化的不同,不同民族在斗智还是斗勇这一情节的叙述中会有所侧重,蒙古族怪孩子故事更重视以力赢人。
尚力文化作为两大人类文化基本模式之一,它与汉民族尚礼文化重视道德教化、伦理秩序和社会理想,讲求恩泽海内、以德服人,具有内省性与内敛性不同,它更倾向于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倚仗实力进行征服与扩张,具有扩张性与侵略性。法国地理学家白吕纳认为:“一地的位置、地形、地质构造和气候都可以解释一个民族的历史。”[13](P221)蒙古民族生活在蒙古高原,这里气候条件相对恶劣,生活资源相对匮乏,为了争夺仅有的资源,游牧部落之间征战不断,无论是部落还是个体,为了活下去,必须要自我强大,而这种强大一定是指向勇气和力量,所谓英雄即为具有可以对抗恶魔、天灾或者敌对的个体或部落的神力的人。蒙古民族是一个崇拜英雄的民族,这种崇拜即包含着“争于力”的原始生命观,正是这种原始生命观孕育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这样的传奇人物,也成为一代代蒙古族人骨血中深埋的生命激情和好争斗的人格特质。尤其在信仰原始巫术时期,这种对神力的崇拜,表达了蒙古族先民确信并企图通过驾驭神秘力量而对客体施加影响与控制的愿望。
(三)原始宗教色彩
并不是所有怪孩子故事都保留着原始宗教的神秘色彩,汉族的怪孩子故事就更侧重世俗生活的现实性和轻松诙谐,但在蒙古族民间怪孩子故事中却始终萦绕着神圣的宗教仪式感。生命的诞生与转换、灵魂的出壳与复归在故事中占据着重要的舞台。
这类故事普遍涉及“神奇的诞生”、“变形”和“死而复生”母题,反映的生命观即是北方狩猎—游牧部落信奉的原始萨满观念的移植和再现。
“神奇的诞生”母题在世界各地几乎所有的怪孩子故事中都保留着,从现存的文本看,“祈神而孕”和“突然怀孕”的情节相对普遍,不同物种间生命互相转换的情节相对较少。“祈神而孕”和“突然怀孕”的提法可能是原始思维观念的退化或对情节的一种简化。而不同物种间生命互相转换的情节更古老,更接近原始萨满观念对生命的认识,正像卡希尔所言,“有一种基本的不可磨灭的生命一体化(solidarity)沟通了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个别生命形式。”[14](P105)在原始人的观念里,生命被看成是一个不中断的连续整体,容不得任何泾渭分明的区别。各领域间的界限并不是不可逾越的栅栏,而是流动不定的。在蒙古族民间怪孩子故事中,不同物种间生命互相转换的情节保留得非常完好,有的是因吃了某种植物而孕;有的是山羊尾巴掉下来成为孩子;有的是往山羊耳朵放土得到孩子;也有的是肚子上长了肉瘤割掉后变成小孩儿;还有的是从身体的某个部分跳出来一个孩子,如蒙古族很多蛤蟆儿都是从老婆婆的大拇指或膝盖中生出的。
“变形”母题是民间童话最常见的母题,万建中曾对“变形”进行了界定,它“是指人与物、物与人、物与物之间因某种特殊原因,按照某种途径而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包括仙人因自身的法力而发生的种种自我变化。”[15](P248)笔者认为还应补充人与人之间的变化,比如此人变彼人、大人变小人等。
“变形”几乎是童话人物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武器,对于这种精神武器的崇拜,是建立在原始初民混沌的、综合的、非分析的、非科学的生命观基础上的,其背后暗含着对灵魂不死观念的绝对信仰。生命的形体可以死亡,但灵魂却可以在不同的物种间迁移,静止的生命变为流动,有限的生命成为无限。
羊尾巴变儿子的故事在蒙古族地区非常流行,邰银枝在《蒙古族“羊尾巴儿子”故事类型解析》就列出了11个异文[16],青蛙变美少年的故事也很多见,彭春梅在《蛤蟆儿的神奇讨婚:蒙汉“神蛙丈夫”故事比较研究》就至少列出8个异文。在神力儿故事中,变形的母题也有所涉猎,如《八腿花马和乌兰巴特尔》中就有小孩子变成小伙子参加战斗的情节。
“死而复生”是盛行萨满教地区怪孩子故事中的一种独特母题,这可能与萨满教治病驱疫的法术有直接关系。只要身体各个部位及骨骼完备,并且各个部位一一就位,施以法术便可以获得重生。新疆地区蒙古族蛤蟆儿故事就有通过起死回生方式向皇帝讨婚的情节,也有的故事在青蛙皮被烧掉以后,青蛙会死去,然后紧随着妻子用金扇子再使青蛙丈夫复活。这样的死而复生情节在汉族的蛤蟆儿故事中是没有的。“吞噬”母题是死而复生母题的一种古老形式,吞入魔兽肚中表明死亡,吐出则复活。这类母题主要出现在拇指儿和神力儿故事中,邰银枝在《蒙古族“羊尾巴儿子”故事类型解析》就列出了含有“吞噬”母题4个异文,王清、关巴编的《蒙古族民间故事》中的《耳朵般大的儿子》和《巴尔·乌兰》中也涉及到“吞噬”母题。
“神奇的诞生”、“变形”和“死而复生”母题在故事中的贯穿和渗透,使蒙古族民间怪孩子故事充满神秘的宗教色彩,灵魂不死观念是其核心,变形是灵魂转换的重要通道,怪孩子的成长是灵魂的延续。
三、结论
按照语言的语系归属,蒙古族应属于阿尔泰语系,但由于长期受到藏传佛教的文化影响,这使民间童话故事兼具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的文化特质。
在复合形态的故事中,以上所谈到的蒙古族民间怪孩子故事的三种特质,只是一种相对的文化表达,是蒙古族民间童话故事在与其它民族的故事进行比较的情况下所呈现出的相对稳定的存在形式。这种存在是民间童话故事对蒙古族文化的呈现与传承,更是一代代蒙古族人对文化血脉的坚守。这种坚守让蒙古族民间童话故事成为“这一个”,在民间文学的璀璨星河中始终保持自身的亮色。
参考文献:
[1]林继富.源于怪的力和美———中国怪孩子故事的审美艺术[J].西北民族研究,2003,(6).
[2]张锦贻,哈达奇·刚.寻找第三个智慧者[M].昆明:云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
[3]王清,关巴.蒙古族民间故事[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
[4]鲍尔吉·原野.蒙古族民间故事选[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0.
[5]德·策伦索德诺姆.蒙古民间故事选[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
[6]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内蒙古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2007.
[7]姚宝宣.新疆民族神话故事选[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
[8]哈达奇·刚主编.内蒙古民间故事全书·镶黄旗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出版集团远方出版社,2013.
[9]拉·苏和.蒙古族讽刺与幽默故事选[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7.
[10]旦布尔加甫,乌兰托娅.萨丽和萨德格[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