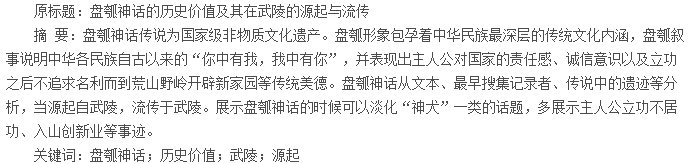
2011 年 5 月,国务院公布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下简称为非遗名录),其中湖南省泸溪县申报的“盘瓠传说”(后来补充完整为“盘瓠与辛女神话传说”)在列。在我的记忆中,这是至今为止唯一一个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载入正史的少数民族族源神话,意义非同寻常。应该说,在南方民族流传的四大族源神话(即盘瓠、廪君、竹王、九隆等神话)中,盘瓠神话情节最生动、形象最鲜明、也最富于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率先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当为实至名归。
一
盘瓠神话,根据汉文古籍一些注疏,可能最早由东汉人应劭搜集并载入所撰《风俗通义》中。而《风俗通义》,据清代卢文弨《群书拾补》云:“隋、唐《志》皆三十一卷,录一卷,至宋始作十卷,盖亡其二十一篇矣。”依此说法,此书原为三十一卷(包括目录一卷则三十二卷),至宋时仅存十卷,则肯定有不少散佚。盘瓠神话未见于自宋流传至今的十卷中,当属于散佚的篇章之一。如是,应劭当为搜集并记录盘瓠神话的第一人。
继应劭之后,三国时鱼豢《魏略》、东晋人郭璞《玄中记》及《山海经·海内北经》注、干宝《晋记》及《搜神记》等也有记述。《晋记》首次把盘瓠故事作为历史资料记载,《搜神记》开始有关于它的详细记述。
到了南朝宋,范晔或是照录《风俗通义》所载,或是综合诸家所述、加以增删整理,将盘瓠神话记入正史《后汉书》中的“南蛮西南夷列传”。尽管内容无多少增益,但一经载入正史便发生深远的影响。
在现存汉文典籍中,记载盘瓠神话最详细的是干宝《搜神记》、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其它或简略或片断。综合各家所载,大致情节为:
(一)老妇人耳中挑出顶虫,置以瓠蓠,覆之以盘,顶虫化为犬,其文五色,因名盘瓠。
(二)犬戎数侵边境,高辛氏乃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金千斤,封邑万户,又妻以少女。
(三)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盘瓠不可妻之以女。女闻之,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
(四)盘瓠得女,附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瓠死后,因自相夫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
(五)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
盘瓠神话是古代苗蛮系统内容最丰富、情节最曲折的族源神话,盘瓠形象、盘瓠事迹具多层内涵,有多重意义,值得细细体味。
神话是一种独特的叙事,要理解神话需首先了解古人独特的思维及表述方式。18 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把神话看作是“不自觉的象征”,认为神话是古人用想象的方式把内在、深刻的内心生活变成“认识的对象”。他在《美学》第二卷里写道:古人在创造神话的时代,就生活在诗的气氛里,所以他们不用抽象思考的方式而用凭想象创造形象的方式,把他们的最内在最深刻的内心生活变成认识的对象,他们还没有把抽象的普遍观念和具体的形象分割开来。[1]18就是说,神话形象与叙事是古人凭想象创造的,有时会很荒诞;但是包含着他们“最内在最深刻的内心生活”,即所经历的生活在内心留下的形影。从此出发,来看看盘瓠形象具哪些内涵,盘瓠事迹有哪些意义。
先来看看盘瓠这一形象的内涵。
在籍载的南方民族几则着名的族源神话里,盘瓠神话主人公诞生的环节是最多的,形象的内涵也是最丰富的。根据上述《魏略》、《搜神记》等的记载,盘瓠诞生的环节大致如下:高辛氏老妇得耳疾——挑之乃得物或顶虫大如茧——妇人盛瓠中、覆之以盘——俄顷化为犬、其文五色。
由此,盘瓠形象的内涵亦具有多层结构,包含多种意味。
盘瓠形象首先含有龙的因素。《魏略》、《搜神记》所载盘瓠神话里,老妇耳中挑出的“大如茧”之“物”或“顶虫”。古称动物为“虫物”,动物皆可名“虫”,《说文》谓龙为“鳞虫之长”,故此处“物”或“顶虫”与龙可联系得上。
远古上古各族群心目中的早期的龙,并非一定是“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尔雅翼》引东汉王符语)[2]329的典型形象,更多地只是动物灵性化的一种形影。因此缘由,与形态多样的动物相对应,早期的龙似乎无固定的形象。陕西西安半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彩陶瓶绘龙、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妇好墓玉龙以及其他商代古器龙纹等,都似水泽鱼虫之类;而内蒙翁牛特旗新石器时代遗址龙形瓶,却是兽头、虫身。而苗蛮系统所信奉的龙,正是原始形态的龙。
从苗蛮系统的后裔苗族刺绣、剪纸等的传统图案来看,他们心目中的龙多无前爪,无角,以鱼、虾、虫等为体,是鱼、虾、虫灵性化而为龙者。它们当与盘瓠形象有联系。
而在苗族等民族的很多口头传说中,此耳中物及所化与龙相关。贵州施洞苗族传说,一位祖母患耳疾,掏耳朵掉出一根蜈蚣龙,蜈蚣龙被盖在盘子里,七天后变为龙狗盘瓠。苗蛮系统另一后裔畲族龙的意识更浓烈。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族《蓝氏家谱》载,帝喾高辛皇后刘氏有一老妇患耳疾,请医师从中取出一虫,“如异玺,以瓠载之,将盘覆之,须臾化作一龙,身有一百二十个斑点花色,故名盘瓠。”[3]84尚存于苗族等民族生活中的风俗资料,也说明盘瓠形象带有龙的特征。
在湖南麻阳苗族居住区,至今共有盘瓠庙二十一座,其中始建于明代、重建于清代的高村乡漫水盘瓠庙,正门横梁上有“盘瓠大王云游四方”木雕。木雕上的盘瓠大王是龙头狗身,虎尾卷毛,脚下是山川云海。当地还有椎牛祭祖的活动,活动中有“接龙”(当地人们称为“接祖神”)仪式。人们唱道:“盘瓠大王是我祖”,“子孙诚心来接龙”。然后划两艘昂首翘尾的雄、雌龙舟,以之象征盘瓠大王和高辛氏公主的化身,进行意为请盘瓠大王游江的活动。
盘瓠形象含龙的因素,似乎与苗蛮系统古代居住环境有关。根据最近的民族学研究,苗蛮系统最早的活动范围在西北达丹江流域,至川东及鄂、湘、赣、皖的沿长江流域,东抵淮河流域,集结于洞庭和彭蠡(今鄱阳湖)之间。这些地区遍布江河湖泊,产生(原始形态的)龙崇拜是完全可能的。如是,从应劭开始的古代文人在搜集记载盘瓠神话的时候,可能有意无意忽略了盘瓠形象这一内涵。
其次,盘瓠名字的由来可能又与盘和瓠有关。《魏略》说盘瓠之名是因为老妇从耳中挑出的物“盛瓠中,覆之以盘”化为犬而得的;《搜神记》也说盘瓠之名来自从老妇人耳中挑出的顶虫“置于瓠蓠,覆之以盘”化为犬之故,所以又带葫芦崇拜的意味。
瓠,葫芦,“瓠”、“葫”同音通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采食和使用葫芦的历史。《诗经·小雅·瓠叶》说:“幡幡匏叶,采之烹之。”《周礼·郊特牲》说:“天子树瓜华。”郝懿行《尔雅义疏》:“是华读为瓠,瓠华古音同也。”汉代王桢《农书》说:“瓠小之为瓠勺,大之为盆盎。”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葫芦,说明最近至七、八千年以前,中国已经栽培葫芦,利用野生葫芦的历史可能更长;在浙江嘉兴大坟新石器时代遗址又出土一件人像葫芦陶瓶,可能为一象征母性的陶偶,说明其进入信仰领域也很早。葫芦与人的关系那么密切,葫芦崇拜的产生是很自然的。
在神话中,神犬名叫盘瓠,可能更多地是远古葫芦崇拜的遗留。盘覆瓠而孕育盘瓠这一情节,也明显地带有对葫芦的生殖方面象征意义的崇拜,是古代南方民族“人从葫芦出”原始信仰的演化;也有可能是一种仪式的神话化。
再次,不可避谈的是,盘瓠形象自然也含有犬的因素。《搜神记》说盘瓠是顶虫所化之犬,《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也说盘瓠是“其毛五色”的狗;在苗蛮系统后裔苗、瑶等民族口头流传的盘瓠神话、史诗中,一般均称盘瓠为“龙犬”;即使是龙的意识最浓烈的畲族,在他们《盘瓠歌》里说盘瓠是“龙麒”,但他在金钟里变人样因七日期限未到而变成的形象,也是“头像狗来身是人”。此外,一些地方信仰盘瓠的族人“向狗膜拜”和不吃狗肉等风俗,也说明了这一点。
盘瓠含有犬的因素,也当与族群居住环境和狩猎生活有关。《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此记载反映了族群居住在山区的历史情况。人们居住在山区,狩猎为主要生存手段之一。狗为人类狩猎的得力助手,又为人畜的守护者,且易繁殖,此当为族人认狗为“亲属”的主要原因。
由此可以说,盘瓠形象具有多层结构,包孕中华民族最深层的传统文化内涵。而籍载的关于盘瓠的叙事,更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独特的现实意义。
作为一则族源神话,盘瓠神话应该有历史的影子。神话里作为盘瓠“岳父”的高辛氏,按照相传为战国时赵国史书的《世本·帝系篇》(清代张澍稡集注本)所言“帝喾高辛氏”,高辛氏即帝喾,为殷商高祖。以此推论,此神话当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苗蛮系统的先民(或认为即史书所称的“九黎”)早期在北方活动时,与殷商先民有过密切的关系,包括协助作战以至立下大功、以及联姻等,由此在族源等方面也会有某些交汇点。
另外,盘瓠“岳父”的高辛氏即殷商高祖帝喾,亦即殷商甲骨文中的“夋”,《山海经》中的帝俊,是中华民族神话传说时代具有崇高地位的人物。瑶族族源神话与之联系并载入正史,说明瑶族历史的悠久,文化的源远流长,也说明中华各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密不可分。
同时,盘瓠神话又是一则表现英雄杀敌立功的神话,有战争,有爱情,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安排都相当完整。应该说,在整个神话里,人们按照当时的审美理想塑造形象、安排情节,使两位主要人物的人性突出,人格鲜明,出现一系列闪光点。
神话里,“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于是,高辛帝“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盘瓠应召,“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此处,盘瓠表现了一种对国家的责任感,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而且以勇敢与智慧战胜敌酋,立下功勋。
盘瓠立功后,“帝大喜,而计盘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此时,“女闻之,以为帝皇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王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这里,高辛女表现出一种高度的诚信,契约在先,践约神圣。
尤其是,盘瓠立功之后,不贪念官位,不追求名利,不呆在宫廷,而带着帝女 “走入南山,止石室中”,到荒山野岭开辟自己的家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而帝女也“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着独立之衣”,跟着自己的丈夫在偏僻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这些,自古至今,都当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失其灿烂光辉;而盘瓠神话作为这些美德艺术表现的载体,也具有永久的魅力!
二
盘瓠神话为苗蛮系统的族源神话,其最初起源、流传于何处,在汉文古籍记载中,可以找出比较清晰的线索。盘瓠神话载入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其书并曰,盘瓠后代“其后滋蔓,……今长沙武陵蛮是也”。依此,盘瓠神话当源起于武陵蛮。
另从盘瓠神话最早搜集并记录者的活动,也可以寻觅神话的源起。《后汉书》所载盘瓠神话,唐代李贤在其下注云:“以上并见《风俗通》也。”即此记载也同样出现于东汉应劭《风俗通义》。按照先后次序,《后汉书》所载当来源于《风俗通义》。唐时《风俗通义》尚未散佚,李贤说法当有根据。
此事宋代罗泌《路史》也有记述,其书“发挥二”称:应劭书遂以高辛氏之犬名曰盘瓠,帝妻之女,乃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妻,是为南蛮。[4]19如是,《风俗通义》最早记载此则神话,当为不虚。
从应劭经历考察,根据《后汉书·应奉传》记载,应劭的祖父应彬、父亲应奉都当过武陵太守,应劭少从父游,生活在武陵,其搜集记录的盘瓠神话亦当来自“武陵蛮”。根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东汉初期,由于民族压迫加深,武陵山脉以及附近地区民族起义接踵而来。建武二十三年(公元 47 年),“武陵蛮”各氏族各部落联合起来反抗汉王朝,与汉王朝派来镇压的军队发生激烈的战斗,使对方一再受挫,坚持数年,直到建武二十五年(49)才归于失败。在战斗中,武陵蛮各氏族各部落为了团结内部,对抗敌人,广泛传播自己族类的族源神话——盘瓠神话,以在盘瓠的旗帜下形成一个整体,应劭当是在这种情势下接触并记录下这则神话的。
记录下来的盘瓠神话讲述的是传说中高辛时代的事,但从其中一些提法来看,似乎带有后世添加的东西。前人早已指出,神话中所谓“吴将军”、“封邑万户”等,均属后世的提法。周朝才有吴姓,周末才有将军之职;三代以前以土分封,自秦汉才以人分封,高辛时代不可能有万户之封……。[5]5042如是,也为此则神话为后世的东汉时应劭在武陵所记提供了佐证。
自东汉以来,一些汉文古籍在记述盘瓠神话的同时,还提到武陵一带传说中盘瓠的遗迹。北魏《水经注·沅水》条云:武陵有五溪,……悉是蛮左所居,故谓此五溪蛮也。水又经沅陵县西,有武溪,源出武山,于酉阳分山。水源石上有盘瓠迹犹存矣。[6]534而更着名的,是李贤注《后汉书》所引的南朝齐黄闵《武陵记》所云:武陵,山高可万仞,山半有盘瓠石室,可容数万人。中有石床,盘瓠行迹,……望石窟大如三间屋,遥见一石,乃似狗形,蛮俗相传云是盘瓠像也。[7]2830在武陵一带特别是泸溪民间,有更多的盘瓠传说及遗迹,不一一列举。
而盘瓠的形象所涉及到的神犬崇拜,在武陵一带也源远流长。近年,考古工作者在武陵地区沅水中游一个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里发掘出一批文物,其中有一座约三十多厘米高的“双头连体带器座”的神犬塑像。这种与原型有较大差距并带较大底座的塑像,极有可能是供人祭祀的神器。伴随出土的玉器中有一件玉斧、一件玉环,也极有可能是当时的酋长或大巫表示神权的宝器。这表明,早在当时,武陵地区已产生神犬崇拜。
与此相对应,武陵地区至今还流传着不少神犬神话和神犬崇拜的风俗。而《搜神记》等书所记载的关于“盘瓠种”的衣食住行等习俗,如“为仆竖之结”(结婚后椎髻),“织绩木皮”(织麻布),“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腰巾垂结于后似尾形),“饮食蹲踞”(饮食时屈膝臀部不落地),“糁杂鱼肉”(以米屑杂拌鱼肉腌制成酢鱼酢肉),“赤髀横裙”(裸露股腿,横披短裙)等,也都是武陵山区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这也说明盘瓠神话与武陵山区少数民族的联系。
综上所述,盘瓠神话源起自武陵,流传于武陵,当有充分的根据。盘瓠神话属于武陵,在武陵有正史的记载,又有口头的流传,还有相关的“遗迹”,可以说形成了一个立体的“盘瓠与高辛女神话传说”的形态。盘瓠形象包孕中华民族最深层的传统文化内涵,关于盘瓠的叙事说明中华各民族自古以来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表现出主人公对国家的责任感、诚信意识以及立功之后不追求名利而到荒山野岭开辟新家园等传统美德。盘瓠神话是中华民族族源神话的精品,也是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非遗项目的精品!
三
不可避谈的是,盘瓠神话的认同与传播遇到一个很大的障碍,即异物、特别是一个带神犬因素的异物进入祖先的形象,会使一些现代人在感情上接受不了。
其实,此类问题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一直困扰着人们。根据现存的汉文文献,早在《诗经》“商颂”、“大雅”一些带史诗性质的篇章里,商人、周人就分别把简狄吞燕卵、姜嫄践巨人迹的神话化入其中,开辟了化神话为史的风气之先;到了西汉司马迁,则沿袭此路把殷、周、秦的始祖神话作为正史一部分记载于所撰《史记》里的《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中。《殷本纪》曰:“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8]91《周本纪》曰:“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姜嫄为帝喾元妃。姜嫄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8]111《秦本纪》曰: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8]173这些,都是极不“雅驯”的感生神话,司马迁将其载入堂堂的正史,当时确实需要勇气,也引起后世一些学者不同的意见。最为人们所知的是东汉王充对“感生说”的批判,他在《论衡·奇怪》篇里写道:儒者称圣人之生,不因人气,更禀精于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契母吞燕子而生契,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迹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此或时见三家之姓,曰姒氏、子氏、姬氏,则因依放,空生怪说,……或时禹、契、后稷之母,适欲怀妊,遭吞薏苡、燕子、履大人迹也。世好奇怪,古今同情,不见奇怪,谓德不异,故因以为姓。世间诚信,因以为然;圣人重疑,因不复定;世士浅论,因不复辨;儒生是古,因生其说。……夫如是,言圣人更禀气于天,母有感吞者,虚妄之言也。[9]19-20从自然科学角度来看,这样说可能没错,但从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角度来看,有很大的可商榷之处。19 世纪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他的名着《原始文化》里曾经指出:“被某些人当作虚假的无稽之谈而抛弃的真实的神话,以其创作者和传播者几乎未梦想过的方式,证实着它正是往事的源头。……作为思维发展的证据,作为很久以前的信仰与习惯的记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各民族历史的素材,古老的神话在历史事实中都已合理地占有一席之地,具有这种见识的当代历史学家,就能够放下架子,重建历史的真实面目。”[10]282从此出发,应该对两千年前的司马迁做出崇高的评价。司马迁正是这样的有见识的历史学家,他在努力地揭示神话蕴涵的历史真实内核,以一种独特的记录“以前的信仰与习惯”的方式“重建历史的真实面目”。
回到我们的盘瓠神话,就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看待此类问题,理解历史上很多民族都有过的动植物崇拜阶段,如是,或许能够坦然面对。还应该明确一点的是,此类崇拜不是对具体的某个动物或某株植物的崇拜,而是对主宰整个某类动物界或植物界的兽灵、或植物之灵、或神灵的崇拜。
事实上,盘瓠神话产生以后,在苗蛮系统世代子孙中一直得到尊崇,他们一直以盘瓠神话的叙事作为自己民族的历史。《隋书·地理志下》载:“长沙郡又杂有夷蜒,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11]898其根据就是盘瓠神话。
唐代,诗人刘禹锡到连州(今粤北一带)任刺史,他在《蛮子歌》里描述“莫徭”的狩猎生活时就写道:熏狸掘沙鼠,时节祭盘瓠。[12]343说到犬,忍不住多说几句。别说古代狗是最早被人们驯化的动物,就是到了今天,“狗是人类的朋友”的观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起码在国内外许多城市,狗几乎成了动物里“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宠物,档次越来越高,待遇越来越好,不少人对其宠爱甚于对人;至于说到威猛,孰能超越藏獒?狗已经是骄傲的小公主、威武的将军,形象早已今非昔比。不然,为什么前段时间广西玉林“狗肉节”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对浪潮?
当然,为了避开目前的某种不适应,展示盘瓠神话的时候可以淡化“神犬”一类的话题,多展示主人公立战功、不居功、入深山、创新业等事迹。
这同样与武陵山水武陵风俗等相吻合,同样会有极大的吸引力。许多人同样会怀着极大的兴趣来此“所处险绝,人迹不至”的南山探幽,寻觅这位高辛帝“驸马”及帝女的踪迹,体味他们的襟怀,接受灵魂的洗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