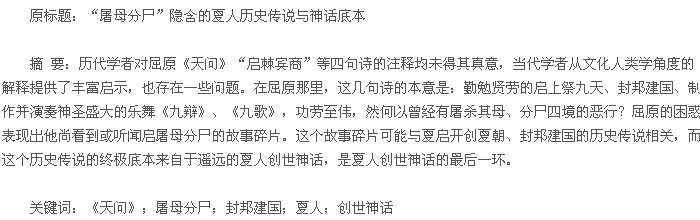
屈原《天问》充满令后人摸不着头脑的疑问,如下面一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1982 年著名学者游国恩等搜集从王逸 《楚辞章句》到当代学者有关《天问》的诸种注释,编成《天问纂义》一书,关于这四句诗,历代注家不同的注解居然有 34 种之多,游先生就此感叹道:“此条旧解无一能尽通者。说愈多而愈歧,解弥异而弥远。大抵后先相袭、执其一端,以求强事贯通,卒之左支而右绌,捉襟则见肘,于全文辞义,未有以见其合也,……。”〔1〕(P211)综观《天问纂义》所集古今注家之说,信游先生所言不诬也。
本文将从评析若干古今学者有关研究入手,展开对这几句诗本意的探讨。
一、已有研究成果的困难与不足
从《天问纂义》所集资料看,对于“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二句的解释,尽管分歧者也众,但朱熹、洪兴祖等十多位注家都认为它与《淮南子》所载启母化石、石破生启的故事相关,值得辨析。据古本《淮南子》:禹治水时,自化为熊,以通环辕之山,涂山氏见而惭,遂化为石。时方孕启,禹曰“归我子!”于是石破北方而生启。
〔2〕(P60)清人马骕在《绎史》中亦引有《随巢子》的相关故事:禹娶涂山,治洪水,通环辕山,化为熊,涂山氏见之,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启。
〔3〕(P168)认为“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与上引《淮南子》资料相关的见解最早可追溯到朱熹的《楚辞集注》:屠母,疑亦即《淮南》所说:“禹治水时,自化为熊,以通环辕之道,涂山氏见之而惭,遂化为石,时方孕启。禹曰:‘归我子!’于是石破北方而启生”。其石在嵩山,见《汉书》注,竟地,即化石也。此皆怪妄不足论,但恐文义当如此耳。
〔2〕(P60)朱熹之后,注家多从此说。今人姜亮夫先生的《屈原赋校注》亦从朱说,认为“所谓屠母者,即谓石破乃生也。死分竟地者,犹言尸骨分裂委地也,即指石破事言。”
〔4〕(P311)但游国恩先生在集合了这些相关注解后评论说:“言启能上宾于天,得《九辩》、《九歌》之乐,以奏于下,已属荒谬绝伦,又何以有其母化石,石破而启生之事乎?疑其说之不经也。”
〔5〕(P212)游先生的怀疑是有代表性的,若用理性观点看待启母化石生启的传说,那一定要认定虚妄不足信。其实当年朱熹就认为“此皆怪妄不足论”,但朱熹同时又谓“但恐文义当如此耳。”意谓屈原看到了这个荒诞不经的传说。游先生认为诸位注家未合适释读屈原那四句诗的判断是对的,但他自己囿于传统的学术视野亦未合适解决古代注家存在的问题。
人们很少质疑屈原看到的是否《淮南子》中的这个故事,因为,这个“石破北方而生启”的故事中,启非主动者而是被动者,谈不上“屠母”,更谈不上“分尸”抛撒四境(“死分竟地”),故以《淮南子》、《随巢子》所载启母化石、石破生启事解屈诗是否合适大可存疑。
若从今之神话学和人类学视野窥视,上引《淮南子》和《随巢子》叙述涂山氏离禹原因并不可信。禹化熊以通环辕山化为图腾神的行为,一如《天问》谓鲧治水而“蚩龟衔曳”乃获图腾神帮助的行为,显带图腾崇拜时代印迹,并非不可思议。得图腾神帮助,或化为图腾神,在神话时代恰是具有神圣性的证明,涂山氏见丈夫禹化图腾熊,如何会“惭而去”呢?此显系文明人类看法:人比动物高级,故必非原初神话中涂山氏离禹原因。如涂山氏见禹化熊惭去的关目不可信,则其避禹追化石生启的关目自然亦不可信。尽管其所本神话为何现今不得而知,但从屈原所问可以推测,屈原曾看到或听到关于启屠戮其母、分尸四境的神话碎片,故有那样的困惑与问题,而《淮南子》中的那个启母化石生启的故事,正是后世对屈原看到的神话故事的虚化性改编结果。关于这个问题,下文还将论及,此处仅仅提示而已。
90 年代以来,关于《天问》这几句诗新的释读注解又有若干,其中,具有人类学视野的学者萧兵、陈建宪先生的训释最值得注意。
萧兵先生在《楚辞新探》、《楚辞全译》、《楚辞的文化破解》等著作中,都曾经涉及这四句诗的解释,他认为这四句诗表述的事实与夏启暴巫求雨的仪式相关。概括其结论如下:(1)“棘”,急,亟;“商”,上帝;“宾”,即《山海经》中“开上三嫔于天”之“嫔”,即作为牺牲的女性;(2)夏人地处西北,自然气候缺水少雨,干旱经常发生,因此王朝的统治者主持求雨仪式、奉献牺牲给上帝祈雨乃常事。启在一次求雨仪式中,杀了三个美女奉献上帝,最后甚至屠杀了自己的母亲(女巫),将其分尸四境,以求上帝赐雨;因此,“启棘宾商,《九辩》、《九歌》”的意思是,“旱情危重,夏启急(亟)需杀死三嫔而‘宾商’(帝),换取祈雨巫术乐舞《九辩》、《九歌》以解燃眉之急。”
〔6〕(P198-229);(3)“勤”当作“堇”,《老子》“用之不勤”帛书乙本作“用之不堇”,而堇有旱义,“勤子”即“堇子”———即“旱子”———即“晴子”———即启。夏启之“启”正有“晴”义,与“旱”义合,因此,“勤子”即主持求雨仪式的启;4“.死分竟地”之“死”同“尸”,“竟”通“境”,这样,“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两句诗可以理解为:启(勤子)把母亲涂山氏杀死并分尸埋于四境,“以使雨水更加充足,庄稼格外丰盛”。
〔7〕(P538)所以,对上面四句诗相关的历史事件,萧兵先生做了这样的解读:“夏启初年,遭遇旱馑,以牺牲换取《九歌》求雨不成,只好杀死母亲———作为女巫,她更便于上天请雨。
涂山氏化石,石破而生启,当是此事的神话反映。”
〔8〕(P85)萧兵先生的解释中,确认“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应解做“夏启屠剥其母,将其母的尸体分割开来埋于四境”,我以为是合适的,他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解释这种屠母分尸行为,拓展了理解的视阈,很有启发性。但其解释也有可讨论的地方———首先,训“勤”为“堇”,在“勤子”—“堇子”—“旱子”—“晴子”—启之间建立语义上的同一关系,尽管未为不可,但建立在过多转义引申基础上的训释其可靠性大打折扣,这也是治古文献学者忌讳的;其次,古文献学者对文字训释大都奉行三证原则,即对一个字义的新训释,至少应有三条以上资料佐证才为有效,而要训“勤子”即堇子———旱子———晴子———启,一条佐证资料也难找到;再其次,将“勤子屠母”解为“暴巫求雨”的仪式性行为,固然有文化人类学理论支持,但却在有关夏人的神话传说资料中找不到任何依据,仅靠文化人类学的一般理论做这种推断,甚不可靠。且古代传说化的历史资料中,夏人面临的问题是水患,而非天旱,谓启屠剥其母、分尸四境为“暴巫求雨”的行为,与夏人传说资料殊不相合。故尽管萧兵先生对“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一问核心的内容做了正确的解读(启曾经屠剥其母、分尸四境),但启何以如此的原因并未得到揭示。
陈建宪先生《一个失落的上古神话仪式———<天问>“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解》一文,从文化人类学视野提出这四句诗可能关涉的是启主持的一种农业社会的祈丰仪式。其观点主要概括如下:
1. 他认为“《天问》中的‘启棘宾商,《九辩》、《九歌》’可以肯定是指祭祀仪式。”〔9〕(P89-90)夏启改变了传统的禅让制度,用暴力夺取并且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建立华夏第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对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他需要通过祭天的方式证明;
2. 他不同意将“勤子”释为“堇子”、“旱子”、“晴子”。他指出“堇”的本义乃是粘土之意,可引申为板结的土地,“力”乃古代翻土工具“耒”的象形。“要之,‘勤’之本义似为一会意字,由于粘(黄)土难治,故当勤劳耕作。”〔9〕(P93)“‘勤子’可能是古代祭仪中主祭者的称号,他主持一年一度的播种祈丰典礼。”〔9〕(P95)
3. 通过文字训诂,他确认:“母”字的意义,“不仅指人类的母亲,也指一切雌性的、能生育的动物,如母羊、母牛等,同时也指能结果实的草木。”〔9〕(P93)所以“‘何勤子屠母’的‘母’,未必就是指启的母亲,也有可能指的是‘草木有实者’”。〔9〕(P93)他参照世界各地神话碎尸化生母题,从逻辑上推断,夏启屠母碎尸仪式,恐怕更有可能是播种而非求雨仪式。“启代表国家举行的播种节祭,所屠之‘母’是用真的人殉,还是用‘尸’代替地母,尚不得而知。如果是‘死’,则可能是一些称为‘母’的植物种子(如《山海经》中提到的)膏稻、膏黍、膏稷等)。主祭者将这些种子的穗揉碎,象征性地分埋进不同地方,就是所谓‘尸分竟地’。到了后世,人们对这一仪式的意义已不能解,于是产生‘语言的疾病’———启母石神话,用来解释这一仪程。再到屈原时代,对这一仪式和神话更不甚了了,于是乃有《天问》中的这个问题。”
〔9〕(P95)陈建宪对这四句诗的解释别开生面,颇富新意,但有几个问题:
首先,将“勤子”解作古代祭仪中主祭者的专有称号,无有二例,在训诂学上存在和萧兵先生训“勤子”为“晴子”一样的问题;其次,解“屠母分尸”为将结实之植物穗子揉碎分埋四境的播种仪式虽别开生面,但即使屈原不知这种祭俗,也不至于如此惊讶困惑。屈原感到惊讶困惑的显然是在他的时代不合血缘伦理的行为,即启屠剥自己的母亲分埋四境的行为。对此窃以为萧兵先生解释甚确,惜其未能在一个合适的框架中解释这种行为;又其次,他认为屈原因对夏启时代祈丰祭仪不甚了了而产生《天问》中“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的疑问,也难服人。中国作为农业国家,夏商周经济生产方式并无根本不同,祈丰祭仪三代都有,何至根本不知;最后,仅视启为历史人物不能解释今见资料中其作为和神性。
综上,尽管陈建宪先生提供了多有启发性的解释,但仍未窥破这四句诗隐含的原初本相。
此外,闻一多和何新先生对这四句诗的释读值得一提。闻先生曾以太康五子之乱训“勤子”作“奸子”(指五子):“案勤、奸声近,勤子即奸子。乱在内曰奸(《九歌》惜贤注),五子家讧,故曰奸子也。屠读为瘏……,瘏,忧劳也。……盖五子叛父而挟其母,使母忧劳,故曰‘奸子瘏母’也。”
〔10〕(P572)闻先生训释上承清人朱亦栋和张惠言,但古来取此说者寥寥,盖因这几句诗与太康和五子实无关联;且以“屠”为“瘏”、勤、奸音近为义同的理由,很难服人,古人运用音声训义十分慎重,除非所训之字它法无解,才可勉强使用。而“勤”“、屠”词义明晓,实不必用同音转义的方式训释。
今人何新先生在《宇宙的起源》一书接受闻先生的训释:“勤子,勤读若奸(闻一多说);屠母,舜族与莘族世为婚姻,后益之族即有易,有莘之族。禹母涂山女亦为莘氏,故为启之母族。启杀益,故曰‘屠母’。”
〔11〕(P96)据此,他对本文开始引录的那几句诗这样释读:于是启大颁赏又歌又唱———为何奸子淫母的家伙竟能封国建邦?
〔11〕(P96)何新训“勤子”为“奸子”存在与闻先生一样的问题。同时,在正文中“勤子屠母”释作“奸子淫母的家伙”,但在注释中,“淫母”被指认为启屠杀母族之后益的行为,两者也殊不统一;何况启“屠母”可否解为杀母族之后益,大有疑问。
而且,“奸子淫母的家伙”这个词组本身就不通。此外,“死分竟地”其字面意思就是尸分四境。这种行为可能与封邦建国的行为相关联,但需要放在一个特定框架中解释才可能。故何先生训释亦有问题。
综上,迄今对这四句诗的众多训释,尚未有一种无懈可击。
二、“启棘宾商”诗句群的本意再释
我认为,对“屠母分尸”诗句群的解释,要分三层次进行还原性处理方可窥见其原意原貌。首先是还原性推断屈原所可能见到的资料,对这几句诗在屈原那里的本义本貌进行训释;其次是从历史分析角度,揭示屈原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但隐含在这几句诗相关故事后面的历史信息;第三个层次,则是从人类学和神话学角度对这种历史信息进行还原性处理,以窥探其背后隐藏的夏人神话原初形态。
本节从文本构成自身推断屈原看到的故事片段,并解释屈诗本意。
首先,就文本本身而言,无论从语法关系还是内容角度讲,这四句诗的主体都是启。游国恩先生辑录的 34 家注释中,有学者将前两句的主体和后两句的主体确认为不同的人(如前两句的主体为启,后两句的主体为禹或天帝或五子等),均不合适。
其次,笔者认为,屈原见到的资料或听到的传说中,有启屠戮其母,分尸四境的故事关目,这也是屈原“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一问针对的故事情节。
再其次,“启棘宾商”之“棘”,多位学者训同“亟”,可从。但学者们续训“亟”为“急”,则不妥。今按:“亟”字本意乃是“极”也,甲骨文作 ,象形字,像人() 在天地()之间,表示人之上与人之下的天地两极。名词“极”因此衍生出“最”、“极其”、“无以复加”之意,可作程度副词。所以,“启棘(极)宾商”,亦可作“启宾商棘(极)”,意谓启举行极其盛大隆重的“宾商”仪式。
又其次,“宾”字训释,歧见纷呈,窃以为陈建宪先生作祭仪之一种解较为合适。据甲骨文,商人诸种祭仪中有“宾”,如甲骨卜辞有“庚子卜贞:王宾日,亡尤”、“贞:咸宾于帝”、“乙巳卜,王宾日”等。《尚书·尧典》也有羲仲“寅宾出日,平秩东作”、舜“宾之四门,四门穆穆”的记载。这里的“宾”,均为祭日仪式。商人祭日仪式和称谓有很多,如“出日”、“宾日”、“既日”、“入日”、“御日”等,一天不同时段祭日仪式都有不同称谓,据“寅宾出日”一句,则“宾”大约是早上(寅时)这一时段祭日仪式的称谓。日在天上,且是天的代表,祭日就是祭天,故古人又有“宾天”的祭礼。由此推断夏人祭天之礼的名称之一可能也是“宾”。“启棘宾商”,之“商”,有作“帝”解,认为是“帝”字误写,这是可能的;但“商”亦可同“上”,上即天,宾商即宾天,即祭祀上天。陈建宪先生将“宾商”做祭天仪式解是合适的。启棘(极)宾商,其意谓启举行极其隆重盛大的祭天仪式。启这次宾天仪式显然有不同一般的特殊意义,故被代代相传,直到屈原,仍然有深刻的记忆。启何以要举行盛大的宾天仪式?陈建宪先生认为这与启封邦建国的历史活动相关,启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第一次建立了国家政权,这自然是开天辟地的重大历史事件,通过祭天仪式,证明自己政权和行为的合法性(君权神授),我以为是很可能的。
启举行祭天仪式,不仅是想通过这个活动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还是封邦建国的盛大庆典活动,这一点十分重要。
还其次,关于“勤子”的训释:窃以为历史化的文献中,启作为夏之开国君王,承父志、征三苗、讨有扈、宾天制乐(《九歌》、《九辩》)、铸造九鼎、封邦建国,其勤勉辛劳自不待言,故屈原称之为“勤子”是很恰当的。今人姜亮夫先生训“勤子”作“贤子”:“勤子犹贤子,犹勤劳之为贤劳也。……启能承禹之位,有征有扈安国家之功,故曰贤子。”
〔4〕(P310-311)姜训甚是。正因为启为贤子,故其屠母分尸、抛埋四境就不能令人理解。“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一句意即“言启有宾天之德,何以有屠母之说也。”
〔4〕(P310)其前提当是屈原在他的时代尚能看到或听到启杀死其母、屠剥分尸、撒埋四境的故事碎片。因为到了屈原的时代,文明社会的宗法血缘伦理规范已经确立,儿子屠母并分尸四境的行为自然是不能理解、不能饶恕的、罪大恶极的行为,所以,他才对启的行为感到困惑不解。
“死分竟地”一句,多数学者训“死”同“尸”,是合适的;“竟”有学者训同“境”,可通。但亦可训作“尽”即“所有”、“全部”“,竟地”即“尽地”,即所有的地方,大地四方。“死分竟地”即将其尸体肢解抛撒大地四方。
最后,启封邦建国举行隆重的祭天仪式,制作并演奏盛大的祭天乐舞(“启棘宾商,《九辩》、《九歌》”)的行为,与他屠剥其母、分尸四境(“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并不是同时发生的行为,应该是封邦建国的祭天仪式在后,而屠母分尸的行动在前。屈原是基于启封邦建国、建立不世之功的伟大事业,而追问其从前何以有屠母分尸这样违背基本伦常的忤逆行为。
依据上面的分析,屈原那四句诗的本意可以作如下释译:启为封邦建国举行盛大的祭天仪式,制作并隆重演奏了神圣乐舞《九辩》、《九歌》。这样贤劳的儿子(从前)何以会屠杀自己的母亲,并将其尸体肢解抛埋大地四方?
三、“启棘宾商”携带的历史信息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启祭天仪式的性质。这种讨论的前提是将夏启当成一位传说中的历史人物,从今见有关夏启的传说资料中去探寻可能的历史信息。
启举行隆重盛大的祭天仪式在《山海经》中有特别突出的记载: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
大运山高三百仞,在灭蒙鸟北,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在大运山北。一曰大遗之野。
《山海经》中这两条资料已参进后人的许多细节性改变(如原初启“宾商”祭仪变成“上三嫔于天”的行为,启自己制作并演奏盛大的乐舞《九辩》与《九歌》,变成他从天帝那里“得《九辩》与《九歌》以下”的行为,等等),但当初祭天仪式的盛大与隆重场景依然在这两则资料中保留。所谓“大乐”,即“天乐”、神乐,”大乐之野”,就是演奏天乐神舞的地方。《九辩》、《九歌》即神舞神歌,今天看到的屈原《九歌》是祭祀以楚人天神东皇太一为首的诸神之歌,屈原《九歌》是否夏人《九歌》原本体制,尚难确认,但夏人《九歌》当是夏人以天神启为首的诸神之歌,应可推定。“九”为夏人创世神话宇宙圣数,①夏人以“九”命称之物基本可以“神”字替换,如“九州”、“九鼎”、“九龙”等,亦可作“神州”、“神鼎”、“神龙”,其《九歌》、《九辩》、《九招》、《九代》等神乐神舞之“九”亦可以“神”替换之。因此,《山海经》特别突出记载的夏启在大乐之野举行的这场祭祀仪式,正是祭天的仪式。
为何祭天?从历史化的层面,那应该与传说中夏启开创夏朝、封邦建国的庆典仪式相关。陈建宪先生认为这与启将一个部落联盟转换为古代中国第一个国家政权这一重大的历史活动有密切关系。启为了通过这种祭天仪式方式证明自己的权力来自上天的赐予。以强化对所建立的王朝和自己权力合法性的确认。我认为这是十分重要而正确的见解。同时,从历史的层面讲,我觉得更准确地说,启举行的祭天仪式应该是封邦建国的庆贺大典。因为他建立的王朝是旷古未有、开天辟地的,所以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注定会在中国文化史上保存特殊记忆,上引《山海经》关于这场庆典祭礼的关键性碎片,就是这种记忆的证明。
接下来的问题是,启举行的这个封邦建国盛大隆重的祭天庆典,和启“屠母分尸”的行为有何关系?难道是说这场庆典仪式上启屠母分尸了?如果仅仅从文化人类学角度,也许可以给出这种解释,且亦可通,但我认为事情并不是这样的。我认为屈原的诗歌中,前二句与后二句所指之事,并不是同一个时间发生的事情,就是说启屠母分尸是举行封邦建国的盛大仪式以前的事情,屈原所以要放在一起提问,可能是觉得启既勤勉贤劳、制舞作乐、封邦建国、建立夏朝,是不世功业,如此杰出伟大的英雄为何先前做出屠母分尸这样大逆不道的恶事呢?
那么,启真的屠母分尸了吗?屈原的设问让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我推断,屈原当时看到的是一个类似“有神十人,横道而处,女娲之肠所化”这样一个无头无尾、令人莫名其妙的关于启屠其母分其尸的故事碎片,现今所见的中国古代神话资料中有不少这样无头无尾、莫名其妙的碎片,我相信它们遗落于遥远的上古神话系统,由于它所在的神话系统在后世要么湮灭,要么转化成历史传说,被严重地伦理化和合理化了,这种极少数保留着其原生形态的神话碎片因失去原初的文本、历史和文化语境,遂成为怪异的、不可理解的神话硬块。屈原“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一问所见到的神话碎片,应属此类。
启为何杀母分尸?现有文献未见任何交代。从后世已虚化原初真相的涂山氏离禹化石生启的传说推断,应是涂山氏因为什么问题和禹发生严重冲突(袁珂先生曾经也这样推断),在这场冲突中,启坚决地站在父亲一边,屠母分尸。那么,因何问题涂山氏女娲与禹、启发生冲突?现有资料无法断定。从人类历史进程角度推断,这场冲突很可能与两个原因相关:一是与中国上古社会由母系转向父系有关,即与恩格斯所说的那场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有关。二是与禹与涂山氏女娲分别代表的西夏族团与苗蛮族团的分合冲突相关。
我们知道,传说中涂山氏是禹在南巡路途主动向禹示好因而与禹“通之台桑”、结为夫妻的,这种结合方式说明那还是一个女性十分主动、有相当自主权的时代。涂山氏与禹不和,断然离去,这也印证女性在那个时代的独立性和自由性,意味着这还不是完全的男权社会。同时涂山氏离去而禹大叫“归我子”的关目,透露了父亲对儿子所有权的争夺、强调和确认(儿子是父亲的)。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子女从随母到随父的过程,对应的正是人类社会由母系到父系的发展过程。故涂山氏从携子离去到禹夺回儿子的神话故事,极具象征性地表达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性转折。在这两性权力由平等向男性主宰过渡的关键时刻,他们的儿子启站在父亲一边,打败了母亲,决定性地完成了男性对女性的历史性胜利。
启屠母碎尸的故事还可以从社会历史角度解读。关于原始神话的历史寓意论认为,神话中讲述的某些故事,是真实历史事件的象征性表达。若以此理解启屠母分尸的神话故事将会发现,它很可能折射着远古中国西北夏人族团与南方苗蛮族团之间交往和冲突的历史过程的某些环节。
涂山氏作为女神,按照闻一多等学者的研究,源自南方苗蛮族团。后世附会性的传说中涂山所在的四个地方分布在今四川、重庆、安徽、浙江绍兴等地,均在南方长江流域,在远古属南方苗蛮族团居地。上古中国来自东北的东夷族团、来自西北的夏人族团和来自南方的苗蛮族团,在中原地区曾有长期交往和冲突的历史过程。曾经强大的南方苗蛮族团先败于西方夏族,后败于东方夷族,最后退守到长江流域的中上游区域散居。这个历史过程在夏人和商人的神话中都有象征性表述。在这种形式中,胜利者的族团形象主要是以强大的男性神祇形象出现的,而失败者的族团形象则被女性化,其身份和地位,在神话中是从属性的。西北族团的领袖禹娶南方族团的涂山氏为妻,它象征性地表述了苗蛮族团与西夏族团交往中的失败者形象和历史。从此可窥见启屠母分尸事件象征性地表达了夏人对南方苗蛮族团的征服和屠戮,是这个历史事件和过程的折射。
至此我们对《天问》中“启棘宾商”四句诗的文本语义和历史信息做了基本的还原性清理,但这并非最终还原。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屈原所见的那个启屠剥其母、将其肢解并分尸四境的神话碎片来自何处?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才能对屈原《天问》四句诗后面隐含的夏人神话原始形态及其本意作出最终的解释。
四、“勤子屠母”隐含的神话底本
若从历史层面解读,启举行的祭天仪式指向的是夏人封邦建国的历史庆典,但这个历史庆典是否是历史上真实举行过的活动?有可能,但不一定。关于这个庆典的传说应是从更远的夏人创世神话中转化而来,它原本是夏人创世神话的最后一环。
20 世纪初以来,学术界关于鲧、禹、启传说的研究经历过三个阶段。一是继续接受司马迁《史记·夏本纪》最后完成的叙述,将他们当成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二是自上世纪初日本学者白吉鸟库开始,至 30 年代由顾颉刚、杨宽等古史辨派学者完成的,将他们从历史人物还原为神话人物;三是上世纪中下叶从日本学者大林太良开始,叶舒宪、胡万川、吕微等学者完成的,将他们从一般神话传说人物还原成创世神话人物。②本人也认为鲧、禹、启都是原初夏人创世神话主神。③启是夏人创世神话中的天神、光明之神,是他完成了世界最后的创造。屠母分尸的情节,正是创世完成的最后一环。
关于启屠母分尸的情节,并不是说真实存在的夏人建邦立国的第一个统治者(假设他叫启),真的曾经屠戮过自己的母亲,还将她的尸体剁碎抛撒四境,这个情节当是夏人自己编织的创世神话中的一个部分,只是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曾经是想象性的神话故事,被当成了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后世关于夏启封邦建国的庆典,只是从这个终极底本中转化出来的历史传说。当然,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夏人最初的建国者也可能按照自己的创世神话来设计和真实地举行封邦建国的祭天大典。
涂山氏在远古神话中应该就是山的人格化形式,山的主要构成成分是石,在根本上它是大地的一部分。所谓土之精为石,石之精为玉的说法,正表达了这种普遍的认识。
涂山氏,山神、石神也。关于山、石与女性的内在联系,西方学者埃利希·诺依曼在他的名著《大母神———原型分析》一书中有明确指认:洞穴,与兼具容器、峡谷和大地特征的山峦相联系,也属于下界黑暗领域。岩和石作为山和地,也具有同样的意义。如前所述,受到崇拜的不仅仅是作为大母神的山,也是代表她和它的石头。〔13〕(P43)石作为女性的象征,总是对应于晚上、西方、北方等昏暗的时空方位,故涂山的本义即昏蒙之山。从神话的平面时空角度讲,鲧所代表的是西北方位的黑暗时空,而禹和涂山氏则代表的是由北向东转换的黎明时空,故石破北方而生启,启代表的是从东方开始的光明时空。启明、朱明、东明,都指的是东方初生的太阳。故启是光明之神无疑,夏人神话的生殖世系暗含的正是世界由黑暗走向光明的过程。
从这里来看“勤子屠母,死分竟地”内含的神话故事,就不难理解了,它内含的是光明世界与昏蒙世界的斗争和前者对后者的胜利。在鲧禹完成了从原始大水中创造大地的工作后,涂山氏通过生殖的方式完成了创造天空的工作,启则通过屠戮其母、分尸四境,其尸体碎片化生众神万物的方式,最后完成了世界的创造。
佐证这一推断的另一个证据是涂山氏与女娲的关系。
涂山氏何人?大约产生于秦汉之际的《世本》谓涂山氏即女娲,即禹的妻子。闻一多、孙作云、郭沫若、王孝廉、龚维英等学者都予以采信,笔者也深以为是,并认为她就是夏人创世神话中的原始大母神。
④在原初夏人创世神话中,涂山氏女娲是创世神禹的妻子,启的母亲。涂山氏女娲在夏人创世神话中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她生了光明天神启,她创造了人类并制定了人类婚姻规则,她炼石补天、和禹启一起战胜了由原始黑暗水神共工氏(鲧)发动的宇宙大灾难。
最后,她在和丈夫禹与儿子启发生的冲突中,被儿神启屠剥分尸,满世界抛撒,尸化众神万物(今见《山海经》“有神十人、横道而处,女娲之肠所化”的记载,正是夏人神话在后世遗落的碎片之一。许慎《说文解字》中谓女娲“古神圣女,化为万物者也”的本义即此)。
古老的创世大母神在创世神话中何以最后会被儿子屠剥分尸?这似乎令人不能理解。但这几乎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在巴比伦创世神话《埃利希———恩努马》中,光明天神马尔杜克为首的新神与他的曾祖母、原始黑暗的创世海神提阿马特为首的老神发生冲突,最后打败、杀死并肢解她,将其尸体分为两块,创造天地。很多民族古代神话中,屠神碎尸、尸化万物,是创世神话的重要关目,由此,神话学家们专门归纳出一种创世神话类型:尸体化生型创世神话。该型神话另一典型案例是印度《梨俱吠陀》中原人布尔夏尸体被诸神肢解化生天地日月星辰万物的故事。在日本学者高木敏雄看来,这正是中国盘古尸化万物神话的来源。这一观点获得吕思勉、何新、叶舒宪等一大批中国学者的认同。
⑤在我看来,尽管不能完全否定盘古神话“印度来源说”,但早已存在的夏启屠母碎尸神话这个本土元素的来源尤其值得重视。
至此我们应该揭示了屈原《天问》有关“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一问的终极神话底本所在。本文前引启母化石、石破生启的故事,应是前文本中启屠戮母亲、分尸四境故事的置换形式。据此对这个神话故事的碎片进行还原性处理,当能窥见它其实是远古夏人天神启屠母创世神话遗落的碎片之一。
由此看“启棘宾商”的仪式,将发现它的终极底本很可能是夏人创世神话中启在完成创世工作后举行的诸神庆典和狂欢。在这个庆典上,创世诸神(很可能是九神)排定座次,启亲自为诸神分别创制并率领诸神演奏盛大的神乐神舞《九辩》、《九歌》、《九招》,并命人铸造九鼎以为天下九州象征,诸神配享。《山海经》中所特别记载的启与诸神在“大乐之野”、“天穆之野”演奏《九歌》、《九招》或《九代》,当是创世神话中这个盛大庆典在后世遗落的碎片。后世这个神话变成历史传说,启历史化为夏朝开国之君,创世神话中他率领诸神庆贺创世完成的盛大庆典,也转换成了封邦建国的历史庆典。
[参考文献]
〔1〕游国恩主编、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补辑.天问纂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宋)朱熹集注.楚辞集注〔M〕.引古本淮南子(今本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马骕撰.绎史(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4〕姜亮夫校注.屈原赋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5〕游国恩主编、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补辑.天问纂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解〔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