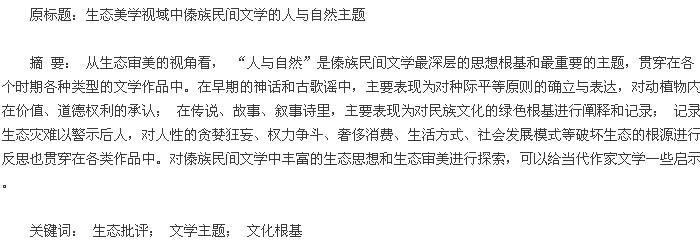
傣族是一个绿色的民族,其文学和文化都是充满绿韵的。在历史长河中,傣族人民创造了歌谣、神话、传说、故事、叙事诗等一大批优秀的文学篇章。翻开这些作品,那种浸满生趣的绿色气息总能使你在回归自然中体味到生命之美。从神话、歌谣中对人与自然万物的平等和谐关系准则的确立与表达,对动植物内在价值、道德权利的思考,到各种传说、故事、叙事诗中对民族文化根基的绿色阐释、感恩自然,对人类生命存在和精神需求的双重看护,对生态灾难的人性根源与社会发展模式的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傣族民间文学最深层的思想根基和最重要的主题。
一、对人与自然万物平等和谐关系准则的确立与表达
在各民族的文学中,歌谣和神话都属于起源较早的文学样式。歌谣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民众日常生活情感的表达。神话则是初民综合的意识形态,“包含着他们对世界起源、宇宙模式、万物关系、民族历史、宗教观念乃至各类日常生活知识。”因此,歌谣和神话中的基本精神往往是该民族文化的核心所在,对该民族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傣族的早期文学古歌谣和神话,以种际平等原则作为思想根基,表达了傣族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
《生死果》是一篇富有热带森林气息的创世神话,其中深刻的生态思想可以作为傣族绿色文学的一个标志。故事讲述英叭神创世之初曾立过 “万物都应该各有各的住处、各有各的吃处”的原则,但他忘记了让人有生有死,所以人越来越多,把森林里的果子树叶都吃光了。动物们很害怕,就去找英叭论理,英叭神于是告诉动物们神果园里有生果和死果,等人类吃到死果后就会死了。动物们汇集在一起商量对付人的办法,最后由聪明的蛇引诱人类吃下死果,人类才有生有死,不再无限膨胀。很显然,人与动物之间的矛盾是贯穿这篇神话的主题,最高天神英叭作为宇宙正义的象征而存在,他的旨意就是傣族先民所信奉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准则。从生态视域的角度解读这篇神话,至少包含这样三层意思: 1. 限制人口过度发展以避免对其他非人类存在物构成威胁; 2. 英叭在创世之初就已立法 “万物都应该各有各的住处,各有各的吃处”.因此,人与非人类存在物之间乃是处于平等地位,动植物不是因为对人类具有工具价值而存在,他们的生存发展权力与人类一样得到了神的许可。3. 如果人类社会无节制的发展,最终将遭到自然界的反击和报复,故事中的蛇引人类吃下死果,实际上象征了自然对人类的强制性限制。
这种人与自然万物平等的原则并非凭空而来的奇异想象,而是根源于先民们一个更古老的思想: 万物有灵,人与自然有着亲情血缘关系,应该与自然万物睦邻友好相依相存。在傣族文学里: “日月星辰、飞禽走兽、花草树木、一切都跟人一样有知觉、有感受、有灵 魂、有 追 求。”图 腾 神 话 《雀 姑娘》、《鸟姑娘》、《象的女儿》、《神牛之女》等篇章追溯了人与各类动物的血缘亲情关系。
而古歌谣 《挖井歌》、《祭树神歌》、《叫雨魂歌》等表达人们日常生活愿望的诗篇中,在向自然索取生活资料时,先民们总是心存感激,要为自己的需要的合理性进行说明。还有许多传说和故事,如 《动物帮助桑木底盖房》描绘了一幅人与乌龟、穿山甲、麻雀、燕子、大象等各类动物互助互爱的欢乐场景;《竹竹必的故事》讲述人在险境中因得到竹鼠的帮助而获救; 《含羞草》、 《柠檬姑娘》中的主人公则在困顿失意中从含羞草、柠檬树身上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最终重获幸福。类似的篇章还有很多,它们从不同的侧面演绎人与自然万物在各类情形中互相依存的关系,从而为人与自然平等和谐关系的立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对民族文化根基的绿色阐释
在生态系统中,人类作为纯粹的消费者,维持其生命存在所需的一切物质均来自于自然,不仅如此,如德谟克利特所言: “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 天 鹅 和 黄 莺 等 歌 唱 的 鸟 学 会 了 歌唱。”人类的精神文化亦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形成,并从大自然中获得启示。以感恩的方式,对民族文化的绿色根基进行阐释和记录,铭刻大自然对人类的赐予,是傣族民间文学的重要内容。
吃、穿、住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但从何种角度看待自身需要的满足,是决定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基石。水稻是傣族社会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农作物,在关于水稻的一系列传说故事中,谴责懒惰、反对奢侈消费、感恩自然是其主旨所在。 《雀屎谷鼠屎谷》、《向鼠王借谷种》追溯人类发现和种植稻谷的历史,始终不忘记雀、老鼠的功劳,并愿意与他们一起分享成果。 《尝新节的来历》、《为什么谷子那么小粒》是告诫后人关于人类奢侈消费而导致生态灾难的一个警醒。
《谷魂奶奶》是保护生态与崇拜权威之间的一场斗争,是关于 “天地之间,谷子最大”的一个宣言。花筒裙是傣族具有标志性的民族服饰, 《筒裙的由来》对这种民族服饰的来历、风格特征等做了绿色的说明: 人类看到孔雀、白鹇、野鸡等禽类身上华美的羽毛时,才产生了要将自己也打扮得更漂亮一些的想法,最终做成了有 33 种颜色的花筒裙。在有关傣族民居建筑的传说 《竹屋的由来》、《动物帮助桑木氐盖房》等篇中,其发明创造者桑木氐两次为傣族人民建盖房屋都得到鸟类、兽类、水族的帮助,而竹楼上的许多部件如白鹭翅、象舌头、狗脊背等名称的由来也正是为了纪念这些动物对人类的帮助。
宗教信仰在傣族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至今瑞丽地区的傣族人家仍保留着供奉祖先神柱和早晚在佛龛前念经祈福的传统。与宗教信仰有关的作品在傣族民间故事中有很多,且大多以人类与自然的亲和关系为根基。
与原始宗教信仰祖先崇拜有关的故事如《帕雅桑木底》、 《坠落在龙宫中的木柱》、《沙都加罗》、《追寻金鹿的故事》《景洪---黎明之城》等,其主人公猎神沙罗、寨神桑木氐、英雄帕雅拉吾作为部落首领兼神只,都是能领悟自然之爱的人,他们对傣族人民的贡献都是在自然的启示或帮助下完成的。
以解释自然崇拜为内容的 《山神树》,讲述傣族人祭祀山神树神的由来,是因为在洪水灾难中,大树不仅使傣族的祖先逃脱被洪水淹死的灾难,为人们提供了遮风避雨、躲避野兽侵袭的家园和美味的果实给人类养命充饥。
佛教信仰对傣族文学影响深远,佛教思想中众生平等、万物皆有佛性、轮回转世等观念原本就有着丰厚的生态思想内涵,与傣族珍爱自然的传统相结合,使得傣族文学作品中的绿色更加深层。系列叙事长诗 “阿銮故事”是傣族文学的辉煌成就,作为佛本生故事与傣族英雄神话故事的融合,“惠及以至于动植物的人道主义底热忱方面,实在找不到有比这更好的范例”也是同样适用于此的。以轮回转世为结构要素的作品如 《皇帝与罕云》、《会唱歌的菩提树》、 《檀香树》等篇中,反面人物的贪婪、残暴往往殃及各种动物植物; 正面人物在遭受迫害时,常常转变为荷花、缅桂花、菩提树、檀香树、芒果树、梨树或者鱼、乌龟、鹦哥、鸭子等动植物的生命形态,与自然融为一体从而能够历经迫害而生命不息。劝善惩恶的道德评价往往与亲近自然的态度相联系。
音乐歌舞是傣族精神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与之相关的各种传说故事,始终注目于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赞美大自然给人类带来的光明和欢乐。有关民族歌手赞哈的故事 《滴水成歌》、《诺嘎兰托和赞哈》、《赞哈的始祖》、《唱歌驱魔贺新房》等基本上都包含着两层意蕴: 一是音乐起源于自然天籁;二是音乐在傣族人民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
关于赞哈来历的两种传说都强调了自然之音鸟鸣、泉水之声给人类心灵带来的愉悦。尤其是在 《诺嘎兰托和赞哈》中,诺噶兰托与玉嫩之间那深厚的感情、奇妙的生命联系,都昭示着玉嫩与自然的融合。 《象脚鼓的传说》、《葫芦笙的由来》、《竹竹必的故事》等追溯民族乐器的创制,其主人公总是处于困境或贫苦状态,作品的重心在于乐器的发现给主人公带来的欢乐和安慰,并由此歌颂了自然对人类的恩赐和启示。在讲述民族舞蹈的故事 《金鹿舞的传说》、 《孔雀舞的传说》等篇中,与自然亲近的倾向更加明显,金鹿、孔雀都被幻化成美丽善良的姑娘,人们因喜爱和思念而模仿它们的神态动作,创制了独具特色的民族舞蹈。
三、对生态灾难的警示及其根源的反思
在歌谣 《攀枝花调》里,傣族人自述自己的民族性格 “爱花又爱树”,从 《傣族文学史》、《傣族民间故事集成》、《德宏傣族民间故事》、 《傣族古歌谣》等文献记载来看,里面有许多篇章都与某个时期发生的自然灾难有关,贯穿着对家园的珍爱,对生态灾难的警示告诫,对生态破坏的人性根源和社会发展模式等进行反思的主题。
傣族人民珍爱自己的家园,在神话中他们对世界的来源给予了优美的想象, 《木细过》、《混散造天造地》讲述神只们三次创造天地的经历,寓含着人类美好家园的来之不易,在以荷花、荷叶比喻天地的想象中,流溢着对自然家园的细腻感受和深爱之情。《伐木歌》、《破篾歌》、《龙女神》、《点水雀》等很多篇章中均有对家乡美景的描绘和自豪与珍爱之情。
正因为意识到家园的来之不易和美好,对其受到破坏和毁灭的记忆也就愈加鲜明。
歌谣 《大火烧天》、 《洪水泛滥》,不论是与西方挪亚方舟或黄河流域汉族的大禹治水等传说相比,对灾难场面的记录都更详实、精确、细腻,焦点始终对准灾难中各类物种的悲惨命运,记录灾难并告诫后人的意识非常明确地在作品的结尾处提出。《骑石树》是一篇用神话思维谱写而颇具现代色彩的故事,但记录灾难的意识一脉相承,山清水秀的漫岭冲在森林被破坏后,变成了一个风沙肆虐的场所。《毁灭森林,宫殿倒塌》里,宫殿在肆虐的狂风中荡然无存,最终为后人得出“毁林自毁勐”的惨痛教训。
大自然是人类的家园,是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立足点和根基,一旦大自然的生态循环系统被破坏,无尽的灾难必将接踵而至。从这种意识出发,傣族民间文学中许多作品对引起生态灾难的原因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反思。内容涉及到人性中的贪婪、自我中心而引起的对自然的背离,人类世界的猜忌、权力争斗、狂妄、奢侈消费等,有的作品甚至还对人类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模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芒棒蛙的传说》和 《神鹿》等篇借用兽性对比人性,讲述人被自身的贪欲主宰,恩将仇报,背离与自然万物平等和谐相处,最终招致恶果的下场。故事中,老熊在知道猎人对自己的出卖后,仍不加计较和怨恨,大度地送对方离开险境。金鹿多次救助人类,明知有生命危险,仍涉险营救采药人岩温。
与之相比,猎人鄂嘎塔却由于贪欲,对于自己有救命之恩、朋友之义的老熊心起歹意。
《神鹿》中除了对岩温贪欲的批判外,还更深一层揭示了上层社会奢侈需求的影响。因为王后想要金鹿的皮做装饰,作为一国之主的国王竟悬赏十万两黄金捕猎金鹿。有了上层社会需求的引导和刺激,岩温才对于自己有两次救命之恩的金鹿心存杀意。两篇作品的结尾均寓意深远,猎人鄂嘎塔被地缝吞没,其血液变成一个热水溏,用来洗去人身上不干净的东西。岩温第三次落水终致身亡,被欲望之海吞没,神鹿顺着阳光照射的道路走进森林,将思考留给后人。
《抛弃国王的狗》、 《毁灭森林,宫殿倒塌》中既有对人类狂妄无知的批判,也有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朦胧思考。 《抛弃国王的狗》中,借一条正受国王宠爱的狗,在听了牛骨头、猫骨头们的谈话后,对自身作为工具而存在的命运幡然醒悟,毅然离开国王回到森林,对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
《毁灭森林,宫殿倒塌》中的国王身上,人类中心主义和集权主义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国王帕雅龙极希望能与太阳平起平坐,为了凸显自己的名声地位,不顾大臣的劝谏,砍倒上万棵树去盖比所有高山还高的宫殿,为了让宫殿显得更加高大雄伟,又命令把境内所有大树全部砍光。在涉及到人与自然背离和生态灾难的多篇故事中,国王都扮演着主要角色,这或许并不是偶然。国王是人间世界的主宰,人类是地球的主宰,两者之间本是相通的。
《金孔雀》则通过象征与对比手法将反思深入到人类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层面,其思想的深刻性和前瞻性,几乎就是对当代社会的一个预言。在河床干得露底,树木花草全部枯死的绝境中。致富和致穷两兄弟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出发寻找能够解救人间苦难的金孔雀。故事将两兄弟的选择、生活方式、结果等一一对比,在三岔路口,致富选择了 “发财致富”之路,得到大量的金银财宝,最后整天吃喝玩乐,对兄弟和母亲也不理,两个老婆都在吃光变穷后离开他,而他自己也被自己懒惰培育出的大黑蛇吓死;致穷选择 “艰险难行”之路,得到能使河水涨满的绿宝石、能使山坡变绿的红宝石和葫芦种子,他勤恳劳作,帮助贫困的人们,最后娶了窝蒲坝子最美的姑娘,生活越过越美满。表面上看起来发财致富、富贵繁华的道路,最终走向了死亡,而与自然和谐共存之路虽然看起来艰险难行,却能获得长久的幸福。关于两条道路的思考,美国学者瑞秋·卡逊也曾发出过严厉的警示: “现在我们站在两条路的交叉路口上,这两条路完全不一样,……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行驶的这条道路使人们容易错认为是一条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这条路的终点却有灾难等待着。这条路的另一个岔路---一条很少有人走过的岔路,为我们提供了最后唯一的机会让我们保住我们的地球。”
西方学者的睿智洞见与东方民间智慧竟有着惊人的相通。其实从灾难发生开始,“致富之路”就已经变成了空中楼阁。没有致穷对山河的治理和修复,致富找回再多的金银财宝也无法换回一滴救命的活水,解救自己和窝铺坝子于绝境。
傣族民间文学中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存关系的描述和思考是全面、丰富而深刻的。自然不是一个被动接受主体情感投射的无生命符号; 对自然的亲和与尊重不是名利场中的失意者在社会主流价值观外实现其生命价值的替代形式,不是从个体的一己之感偶尔升华和触摸到人类生存的本相。它是整个民族对自然万物所共同持有的关系准则,是一种为该群体共同认可的伦理道德观念,是对其民族文化根基的阐释与对青年一代的教育,是对理想生活的展望与对家园的守护。植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中,傣族民间文学用神话的思维表达来自日常生活中的朴素道理,融地域色彩与民族风情为一炉,在艺术上亦取得较高成就。
参考文献:
[1] 章培恒,骆玉明。 中国文学史[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2] 岩峰,王松,刀保尧 . 傣族文学史[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
[3]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 . 古希腊罗马哲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1.
[4] 雷奈·格鲁塞着 . 印度文明 [M] .常任侠,袁音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56.
[5] 瑞秋·卡逊着 . 寂静的春天 [M] .吕瑞兰,李长生 译,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