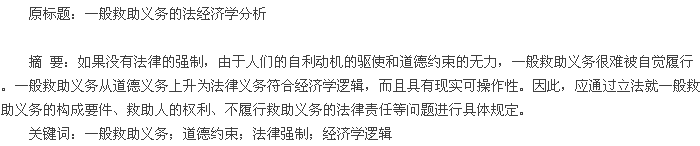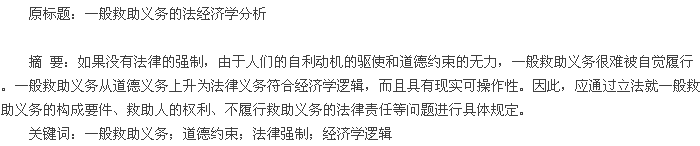
“小悦悦事件”过去已久,但至今仍值得我们反思。笔者以为,导致“小悦悦事件”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法律没有确立一般救助义务规则。传统观点认为,救助义务只是一种道德义务,而法律是不能强制执行道德义务的。“任何人都不能要求某人扮演乐善好施的角色去为一个流血不止的陌生人包扎伤口,或是在见到有人走向危险的机器时向他发出警告。”
“纵然见义勇为者会受到群众们英雄般的礼遇,但是袖手旁观者也不会被提传到法庭上受审。”法律坚持一般无救助义务规则,主要缘于作为与不作为的根本区别。个人没有积极作为,只能说明他没有将某种利益给予受害人,而并未使受害人的处境变得更糟。
美国学者艾姆斯在着名的“溺水假设”演讲中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倘若你从桥上经过正好有人溺水并大声呼救,你没有义务顺手扔给他一条绳子来救助吗?”在他看来,法律是功利的,是为了满足社会的合理需要而存在的,所以法律只有这样才是令人满意的:如果一个人在不会给他自己造成任何不方便的情况下,拒绝救助他人以免其生命或身体受到更大损害,那么他应该受到惩罚并对受害者或其家属进行赔偿。
艾姆斯的观点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美国法中一般无救助义务规则也因此而经受两方面的侵蚀:一是扩大产生积极义务的特殊法律关系的范围;二是通过制定法律承认行为人救助陌生人义务的例外情况。
受此启发,笔者拟从法经济学视角对一般救助义务规则进行探索,期望能对解决社会上广泛存在的见死不救现象有所助益。
一、一般救助义务缺失下的冷漠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人口流动也随之提速。由于城市用地的紧张,市民大多蜗居于高楼大厦的单元房中,人际之间的联系水平大大降低。电视和网络更是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人们在茶余饭后与左邻右舍交谈的兴致逐渐减少,一种“宅”的生活方式逐渐盛行。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社会已经逐渐演变成一个陌生人社会,我不知道你是谁,你也不知道我是谁,这样的陌生人社会是滋生普遍冷漠的适宜土壤。在传统的乡土社会,友爱互助是无须讨价还价而成的自发现象。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近乎永久性的生活圈子将人们之间的互动自动纳入无限次重复博弈中,互惠行为无疑是优于见死不救的策略。而在陌生人社会,人们之间的互动基本上是一次性博弈,容易刺激机会主义行为。此外,陌生人社会容易导致道德约束力下降,因为道德约束要发挥作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不道德之事必须要让人知晓;二是行为人因为不道德之事受到社会的否定性评价。
互不熟识的陌生人社会具有匿名效应,道德约束发挥作用的条件无从满足。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容易将自己承担的道德责任分解到他人身上。同时,我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慎独”和“君子不欺暗室”等道德要求不再为普世信奉,内在约束日渐式微。再考虑到没有法律的强制作用,见死不救几乎无须承担任何成本。主动为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提供救助可能给救助人带来乐于助人的好名声,但也可能引起“沽名钓誉”的质疑。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救助行为带来的收益是不确定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救助人在救助过程中自身权益受到损害,由于国家补偿义务的缺失,救助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当前,救助人可以利用的法律规则主要是 《民法通则》 第93条,该条文规定:“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贯彻执行 〈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第132条,“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管理人或者服务人可以要求受益人偿付的必要费用,包括在管理或者服务活动中直接支出的费用,以及在该活动中受到的实际损失。”表面看来,上述规定为受到损害的救助人提供了有效的救济,实则不然。假设受益人不愿意补偿,救助人只得通过司法途径寻求救济,但这会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是否能够完成举证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而且,即使官司胜诉,依然面临执行难问题。如果遇上受益人无能力补偿,救助人只能是欲哭无泪。在有承担侵权责任的第三人时,情况同样如此。总的看来,救助行为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利己是所有生物基因的一个普遍特性,人类也不过是自私的基因所创造的保存自己的机器。“它们存在于你我身体里;它们制造了我们的肉体和灵魂;保存它们乃是我们存在的终极原因。”自私的基因间接地最终控制了每个人的行为,决定了爱的差等性。“自爱必多于爱人、为己必多于为人。”
在利己动机的驱动下,通过道德规范并不能促使人们遵守一般救助义务,人们对他人危难所表现出来的冷漠与无情已经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病态,各大媒体报道中的见危不救行为更是不胜枚举。当人们处于从恶能得到好处的制度下,要劝人从善是徒劳的。因此,为了遏制冷漠现象的蔓延,必须将一般救助义务从道德规范的范畴纳入法律规范的范畴,惩罚冷漠行为,将道德层面的“应当实施救助”转化为法律层面的“必须实施救助”。一般救助义务的法律化可以增加不予救助的成本,也可以用来保证救助人在救助活动中的所有成本得到补偿,甚至获得一定的报酬,增加救助行为的净收益。如此一来,不救助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而实施救助无须自己承担成本,两相比较,利己的行为人也会选择实施救助。最终,在法律强制作用下人们便可能由习惯冷漠演变为习惯救助,达到行为养成的目的。
二、一般救助义务入法的正当性
长期以来,一般救助义务被认为是道德义务,不履行它只是道德不佳的表现应受到道德谴责而已。因为学者认为应尽力把法律强制限制在最小范围之内,并且不断寻求减少使用它的机会,而不是增强强制的机会并且把它当做挽救一切道德败坏的药方。
同时,“只有在不使用社会的强力来保障遵守这种道德规则,则社会连带关系就会受到严重危害时才成为法律规则。”基于以上两点考虑,一般救助义务一直未能在我国法律中有所体现。海曼认为,当道德义务被转化为与权利相对应的义务或社会的义务时,它才能被强制执行。而作为社会的一名成员,处于危险中的人享有被救助的权利,救助者负有救助的义务。在此意义上,一般救助义务已经由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
对此逻辑,也许有读者会提出质疑:处于危难中的人享有被救助的权利,而旁观者也有选择救助或不救助的自由权,而且危难状况并不是后者所造成的,法律为何要作出倾向于前者的选择?通常,限制自由是因为存在着与自由的价值同等或比自由的价值更高的价值。
当他人的生命可能因为旁观者的冷漠而消亡时,无视他人生命的冷漠相当于杀人。法律是无论如何都不会保护变相地剥夺他人生命的自由权的。无疑,在任何时候,生命权的价值高于自由的价值。除了生命权的价值高于自由的价值外,法律规定一般救助义务也是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考虑。按照科斯定理,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权利的初始配置只对收益的分配构成影响,而不会对效率的实现产生影响;而存在交易成本时,权利的初始配置却对效率的实现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合理的法律制度必须能够减少或消除私人协议的障碍,使得交易成本最小化。现在假设一般救助义务仍然停留在道德层面,这相当于赋予民众自由观望的权利,让我们来看看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假设落水者大声呼救吸引了路人的注意,不一会儿就聚集了一大群围观者。路人甲表示可以下水救人,如果落水者愿意支付令他满意的报酬的话。落水者觉得路人甲的报价太高,冒死还了一个自己能够承受的价格。路人甲不满意落水者的报价,扬长而去。
紧接着,路人乙、路人丙、路人丁……众多路人重复着路人甲的行为,落水者最终在讨价还价中淹死。众所周知,合作盈余越大,为了瓜分合作盈余的谈判过程就越是艰难。生命权是无价的,救助者和遇难者之间的交易因此注定要费一番周折,协议失败的风险甚高。一旦交易失败,一条生命可能就此陨落。因此,在法律上应该构建起一种制度安排,以便私人协议失败造成的损害最小化。显然,比起让有能力救助的人享有选择救助或观望的自由权,让处于危险中的人享有被救助的权利是一种更好的制度安排。
如果法律制度缺乏可操作性,其立法目的依然难以实现。国内有学者曾撰文提出“见死不救”不能被设定为犯罪的观点,其中给出的一个重要理由便是这种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因为,如果见死不救是犯罪的话,由于犯罪嫌疑人没有采取积极行为去侵害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那么见死不救只能是不作为犯罪。但不作为犯罪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求行为人能够履行特定义务而未履行。而就是否能够履行救助义务而言,法律无法给出关于“能救助”或“不能救助”的明确标准,增加了司法实践的难度。同时,大部分见死不救发生在公众聚集场所,人员密集且流动性较大,责任人的范围不好确定,公安机关在实践中也面临取证难题。再者,如果有人见义勇为,是否还需要对见死不救者以犯罪论处面临两难境地。
撇开刑事惩罚的严厉性不论,立法规定一般救助义务确实面临制度的操作性问题,但这不应成为一般救助义务的立法障碍。首先,就当事人是否具有救助能力的判断而言,可以考虑其智力、体力、生活经历以及当时的特定环境等因素,在必要时还可以借助于类似陪审团的机构来帮助判断。其次,如果需要救助者的危险状况因为有人履行救助义务而消除,那么可以不追究其他在场者的救助责任。这样做不会误导公众在以后的事件中消极等待“英雄”的出现。毕竟,观望存在很大的风险。一旦无人实施救助酿成大错,观望者都将因此而承担责任。最后,由于天网工程的存在,取证问题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难。而且,即使只能将部分见死不救者绳之以法,法律制裁的威慑作用依然能够迫使大多数人去履行一般救助义务,尤其是有目击者在场时。有学者更是宣称,即使这种仅仅停留在书面上的法律也将通过增强人们的道德责任感使履行救助义务的人增多。
三、一般救助义务规则的建构
救助义务的产生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基于合同引起的救助义务。例如,受雇照看婴儿的保姆在工作期间对处在危险状况中的婴儿负有救助义务。第二,基于先行行为引起的救助义务。行为人的先前行为制造了一个典型的继续性的有形损害危险时,行为人对处在这种危险中的人负有救助义务。第三,基于特殊关系而产生的救助义务。行为人与他人之间具有特殊关系,那么行为人应在该种特殊关系的范围之内就所出现的危险对此人承担救助义务,这些关系包括但不限于公共承运人与乘客之间、旅店与其顾客之间、因商业目的或其他原因而占有土地并将其场所向社会开放的人与合法进入该场所的人之间、雇用人与受雇人之间、学校与学生之间、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医生与病人之间以及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第四,基于职业或业务而引起的救助义务。例如,正在巡逻的警察对正在遭受暴力攻击的受害人具有救助义务。第五,基于自愿履行而引起的救助义务。如果一个人原先没有义务向他人提供救助,但自愿提供了援助,提供援助者必须善始善终而不能半途而废。不履行上述几种原因引起的救助义务而造成他人损害的,义务人可能因此而承担侵权责任。
笔者所主张的一般救助义务,是完全不能归入上述情况的一种新型救助义务,其目的是通过法律强制为身处险境的人提供及时的救助。
一般救助义务构成要件有三:第一,他人身处险境的紧迫性。他人身处险境的事实本身并不足以产生一般救助义务,如果有充裕的时间供其脱离险境的话。只有当这种危险具有紧迫性,不立即进行救助可能带来巨大的财产或者人身损害时才会对他人施加一般救助义务。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险境可能是由于受害人自己的无知或者过错、他人的过错或者自然灾害等原因所造成,但绝不是由于行为人的过错所造成。第二,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身处险境之人需要立即得到救助。对危险的认知是采取救助行为的前提,因此对于险境状况的判断直接决定着行为人的选择。对此,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判断。身处险境之人的亲人可能会夸大其词,而陌生人则可能不以为然。为了避免行为人以各种藉口故意规避救助义务,除了考虑行为人自身的特殊情况外,还应结合客观的“理性人”标准来判断。
按通常理解,理性人是某类人群中具有该人群通常的或普遍的智力水平、认知能力和知识经验的人。如果理性人能够认识到危险的紧迫性,通常可以认定行为人也可以认识到,除非行为人能充分证明他确实不能认识到。但是,并不能因为理性人不能认识到危险的紧迫性而认定行为人也不能认识到,如果考虑到行为人所具有的特殊能力的话。
第三,对行为人具备救助的期待可能性。行为人必须具有实施救助的能力,并且,救助行为本身不会给行为人带来过大的危险。这意味着救助方式的选择可能是多样的,亲自实施救助不是唯一的方式。在特殊情况下,将他人需要救助的信息传递出去也可以被当作是履行了救助义务。法律不强人所难,当救助行为的代价过于巨大时,可以免除行为人的一般救助义务。
立法确认一般救助义务是为了鼓励社会互助的道德风尚,弥补意思自治的缺陷,体现了对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兼顾。在上文比较救助义务人的自由权和危难之人的获得救助权时笔者已经指出,赋予救助权优先地位能够更好地保护危难之人的利益,避免权利交易失败带来的危害。与此同时,一般救助义务因此可能产生一个不值得期望的效果:减少人们活动的积极性。人们外出活动的频率越高,承担一般救助义务的概率也就越大。如果救助行为产生的成本无法得到补偿,必然导致人们活动水平的下降,甚至引起正当行为的萎缩。为此,在确认一般救助义务时必须考虑救助者获得补偿的权利。由于受助人从救助中获利,由他们承担这种补偿责任充分体现了权利义务的平衡。
如果仅将在救助过程中花费的成本支出看作是受助人对救助人的负债,则受助人赖账可能导致救助人无法得到充分补偿,从而降低了救助人的积极性。因此,国家应采取必要措施协助救助人向受助人的追讨行为。在必要时,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履行代为划扣财物等手段来实现。如果因为受助人没有财产可供执行,那么国家应承担补充责任,使得救助者的状态恢复到履行救助义务以前的状态。当然,国家补偿始终是救助人获得救济的最后保证,救助人不得一开始就找国家寻求帮助。
在履行救助义务的过程中,一旦行为人开始救助就必须继续履行救助义务,不得半途而废,尤其是当中途放弃救助行为可能使受害人处于一个比行为人当时没有救助更糟糕的境地时。因为行为人所实施的救助行为使得受害人丧失或减少了获得其他人救助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受害人的获得救助权。
所以,行为人中途停止救助给受害人造成损害的,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除此之外,如果行为人是本着诚信的心态对受害人实施救助而没有从此救助活动中获得报酬或不期望获得报酬,那么他就对在此过程中因其非重大过失的行为而导致的被救助者的损害免责。受害人的危险状况通常具有紧迫性,留给行为人进行判断的时间非常有限。而且,大多数行为人没有受过严格的救助作业培训,不具备专业的救助技能。在救助过程中出现意想不到的过失行为给受害人带来损害就在所难免。
免除行为人因轻过失而造成的损害是必要的,否则,行为人可能因为害怕承担责任而放弃救助。为了保证行为人认真履行救助义务,必须规定不履行义务的法律责任。对于故意不履行救助义务的行为人,必须赔偿受害人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同时,可以将案件处理情况向全社会通报,对见死不救者形成一般性威慑。在必要时,可以对行为人施加刑事责任,这在古今中外的立法例中都有所体现。例如 《法国刑法典》 223-6条第二款就明确规定:“任何人对于危险之中的他人,能够自己采取行动,或能够唤起救助行为,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无危险,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处五年监禁并科五十万法郎罚金。”
再如 《唐律疏议》 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救助者,速告附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但是,为了避免公民行为萎缩的可怕后果,“即使行为侵害或威胁了他人的生活利益,也不是必须直接动用刑法。可能的话,采取其他社会统制手段才是理想的。可以说,只有在其他社会统制手段不充分时,或者其他社会统制手段(如私刑)过于强烈、有代之以刑罚的必要时,才可以动用刑法。”
因此,笔者建议,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课加刑事责任:第一,不履行救助义务导致他人因此而失去生命或者身体受到严重伤害的;第二,通过冷嘲热讽等手段为他人履行救助义务制造障碍的。
四、结论
步入陌生人社会以来,人性冷漠日益泛滥,社会上见死不救现象也屡见不鲜。完全寄望于道德控制去改变这种状况明显是在自欺欺人。因为主动履行救助义务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是得不偿失的,有违人类行为利己的天性。为此,必须将一般救助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利用法律的强制作用来保证它得到履行。事实上,这种规定也完全符合经济学逻辑,能够减少社会救助过程的交易成本和无人救助引起的损失。早有学者预言,“或许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帮助处于严重危难中的人的义务,会在某个适当的限制范围内从普通的道德领域转入强制性法律的领域。”也许,现在是时候了。
参考文献:
[1][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596.
[2]李响.美国侵权法原理及案例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380.
[3]郑丽清.美国无救助义务规则的修正[J].北方法学,2012,(3).
[4]James Barr Ames.Law and Morals[J].Harv. L. Rev.1908,(22).
[5]Steven J.Heyman.Foundation of the Duty to Rescue[J].Vand. L. Rev. 1994,(47).
[6]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0.
[7]朱道坤.“田园将芜”时代的法律文化———对“小悦悦事件”的反思[J].法治研究,2012,(1).
[8]朱力.旁观者的冷漠[J].南京大学学报,1997,(2).
[9]王海明.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85.
[10][英]威廉·葛慎文.政治正义论[M].何慕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560.
[11]狄骥.宪法论[M].钱克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91.
[12][美]史蒂文·J·海曼.民事救助义务的理论基础[G]//张民安.民商法学家(第2卷).王迎春,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188-227.
[13]王振东.自由主义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0.
[14]Ken Levy.Killing, Letting Die, and the Case forMildly Punishing Bad Samaritanism [J].Ga. L. Rev.2010,(44).
[15]朱勇,朱晓辉.“见死不救”不能被设定为犯罪[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5,(5).
[16]Jay Silver.The Duty to Rescue: A Reexaminationand Proposal[J].Wm. &Mary L. Rev. 1985,(26).
[17]Sungeeta Jain.How Many People does It to Save aDrowning Baby? A Good Samaritan Statue in Washington State[J].Wash. L. Rev. 1999,(74).
[18]赵万一,蒋英燕.论不作为侵权及其法律完善[J].河北法学,2010,(1).
[19]徐国栋.见义勇为立法比较研究[J].河北法学,2006,(7).
[20][法]卡斯东·斯特法尼.法国刑法总论精义[M].罗结珍,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217.
[21]黎宏.不作为犯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32.
[22][日]平野龙一.刑法总论[M].东京:有斐阁,197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