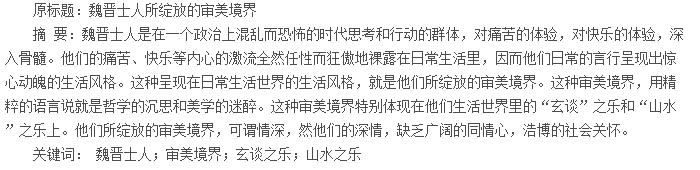
魏晋士人遭遇的是一个政治上混乱而恐怖的时代,曹操篡汉,司马氏篡汉,士人动辄被杀;思想上儒家信仰全面崩溃,已经无法安顿他们的精神;老庄哲学、佛教义理、道教神仙信仰异军突起。
魏晋士人遭遇的可谓是一个思想巨变的时代,魏晋士人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思考和行动的群体,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幽愤,他们的行为惊世骇俗,他们的思想离经叛道。他们遭遇的混乱而恐怖的时代,使他们对痛苦的体验,对伤心的体验,对孤独的体验,对快乐的体验,深入骨髓。他们的痛苦、伤心、孤独、快乐等内心的激流全然任性而狂傲地裸露在日常生活里,因而他们日常的言行呈现出惊心动魄的生活风格。这种呈现在日常生活世界的生活风格,就是他们所绽放的审美境界。这种审美境界,用精粹的语言说就是哲学的沉思和美学的迷醉。这种审美境界特别体现在他们生活世界里的“玄谈”之乐和“山水”之乐上。
一、魏晋士人的“玄谈”之乐
魏晋士人没有不“玄谈”的,“玄谈”是魏晋时代的风尚。庄子、老子、易经是他们玄谈的资源,被称为“三玄”,而“三玄”的核心范畴是“道”,而“道”是闻不到其声、看不见其形的,是我们感官无法把握的存在。这就是所谓的“玄”,“玄”就是远的意思,就是和日常生活世界没有关系。例如“有无之辩”就是当时玄谈的中心命题之一,这是很高妙的抽象思辨,也可以说是纯粹理性思辨。
“有”可以说是现象世界,“无”可以说是本质世界。“有”是通过我们的感官可以把握的,而“无”是我们的感官无法直接把握的。他们认为“无”是“有”的“本”,“有”是“无”的“末”,故要“崇本息末”或“举本统末”。他们沉醉对“无”的思索,崇尚对“无”的谈论,故他们的发言吐辞,谓之玄妙。他们对“玄”的沉思,对“玄”的谈论,给遭遇混乱和恐怖时代的他们创造出了一座快乐至极的精神高原。他们在这个远离政治漩涡的抽象思维的精神高原上,纵横争锋,彼此俱畅。
他们“玄谈”,“玄谈”得何等沉醉:“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
他们“玄谈”,“玄谈”得何等忘我:“林道人诣谢公,东阳时始总角,新病起,体未堪劳。与林公讲论,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后听之,再遣信令还,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妇少遭家难,一生所寄,唯在此儿。’因流涕抱儿以归。”
他们“玄谈”,“玄谈”得何等尽兴:“后正值王(王羲之)当行,车已在门,支(支道林)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
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魏晋士人的“玄谈”,是魏晋士人的智力游戏。
他们沉醉在如此自由的游戏中,忘我而尽兴,获得了精神的解放,体验到了逍遥至极的快乐。可以说,他们真的快乐,快乐的要死!他们的快乐,不是生色欲的低级快乐,而是纯粹抽象思辨的快乐,是高雅的快乐,故他们在玄谈中体验的快乐是纯粹的审美的快乐。“玄谈”可以说是魏晋士人节日般的狂欢,给他们痛苦的心灵短暂的慰藉,让他们体验到幸福的狂喜。
“玄谈”给他们的审美一种纯度,洗尽了尘滓,独留一份神明;“玄谈”给他们的审美一种高度,远离了质实,独留一份空灵;“玄谈”给他们的审美一种深度,远离了枯淡,独留一份风韵。魏晋士人的“玄谈”,是哲学的沉思和美学的沉醉。哲学的沉思,是他们精神自由逍遥至极的绽放;美学的迷醉,是他们心灵自由快乐至极的绽放。
二、魏晋士人的山水之乐
魏晋士人的“玄谈”,净化出了魏晋士人澄明的胸襟,给他们一个空灵的心灵;训练了出了魏晋士人妙赏的能力,给他们一双晶莹透彻的眼睛;涵养出了魏晋士人的性情,使他们渗透了深情。在政治激流与漩涡的时代,如此的魏晋士人与有灵山水相遇,随成千古知己。没有空灵的心灵,就不能朗照云兴霞蔚山水的神明;没有妙赏的眼睛,就不能捕捉窈窕山水的倩影;没有深情的性情,就不能和山水甜言蜜语、相亲相爱。澄明的胸襟、妙赏的能力、深情的性情,缺一不可。妙赏没有深情,就是繁彩寡情,味之必厌;深情没有妙赏,就是繁情寡彩,没有风韵。妙赏、深情没有空灵,就不能清,不能远,不能高,不能神,不能明;空灵而没有妙赏、深情,就是枯,就是寂,就是空。只有这三者完美结合的人,才是真风流、真风韵。魏晋士人就是真风流真风韵的人,故魏晋士人才是窈窕山水千载难逢的知己。窈窕山水与魏晋士人的相遇相亲绽放出中国美学史上最令人心醉神迷、神魂颠倒的美。
《世说新语》说: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世说新语》说: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魏晋士人与山水相遇,相遇而妙赏,妙赏而陶醉,陶醉而物我两忘。这就是他们的山水之乐,是魏晋士人所绽放的生活风韵,他们发言吐辞莫不风流蕴藉,美不胜收,精彩绝艳,都成妙谛。魏晋士人用“玄谈”给他们的那双晶莹透彻的眼睛,目视了蓦然相遇的山水,山水是如此的晶莹,如此的俊美,如此的多情,如此的窈窕。窈窕山水,是魏晋士人相遇的美人。这位美人是如此远,如此高,如此清,如此淡,如此神,如此明,如此韵,真可谓超尘绝俗,风尘物外!魏晋士人在这位千情万趣、媚态横生的窈窕美人的逗引下,神思荡漾,快乐,快乐的要死!
《晋书》里说:“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戈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
读之,令人绝倒。这种惊心动魄、刻骨铭心、心醉神迷的至极体验,是审美的最高境界。真可谓“乐莫乐兮新相识”!“新”,“新”美人,超尘绝俗;“新”,“新”名士,风流蕴藉;“新”,“新”相遇,“新”相识,“新”相爱,“新”相亲;“新”,“新”感觉,“新”体验,“新“快乐”,“新”陶醉。人生之乐,莫过于如此!如果说人生的最大幸福,就是得一知己,那么魏晋士人就是最幸福的人了,尽管他们所遭遇的时代令人郁闷不已。
魏晋士人以他们之玄心,朗照山水之灵心,山水又以他们之灵心,鉴照魏晋士人之玄心,两心相映,真情斯现。魏晋士人用心灵和激情开拓了美的“新”天地,创造了日月清朗,鸟兽禽鱼自来亲人的“新”天地。他们把他们最纯真的“新”痴情泼洒在池塘上,池塘上就生出了“新”春草;泼洒在千岩万壑上,千岩万壑就有“新”回响;泼洒在鸟兽上,鸟兽就来“新”相亲。魏晋艺术最大的魅力,就体现在这个“新”字上。王羲之的书法,“新”飘逸;顾恺之的绘画,“新”传神;谢灵运的山水诗,“新”体验。
然读:“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又令人黯然伤魂,再读就令人心疼神驰。他们所谓克复神州,只不过是无用之空话而已。在杂花生树,莺歌燕舞之江南,此复何忧!乐不思蜀,而非卧薪尝胆。今日激赏魏晋时代之饱学之士,时时要穿越他们快乐,揭开快乐要死的面纱,目睹神州陆沉的大悲剧。
魏晋士人山水之乐的另一表现,就是人物品藻。他们对人的品藻也精彩绝伦。他们对人的妙赏其实是对自然美的妙赏。故这种妙赏就是纯粹审美的,而不是伦理道德的。这也是魏晋人物品藻的一大特点,人成为纯粹的审美对象,赋予人一种山水美。
三、魏晋士人的审美缺失
我们欣赏一个时代美的同时,也要看看它的丑。人世间的事物往往有多重的存在特性,也可以说是特征的集合体。灯光在黑夜里不仅能带来光明,也能形成更厚重的黑暗,也许形成的黑暗比带来的光明要多。所以在目视光明的同时,也要自觉地消解黑暗的厚重。魏晋士人对快乐的体验是如此惊心动魄,同样他们对痛苦的品尝也是深入骨髓。
没有痛苦,也就没有快乐,最大的快乐,是最大的痛苦孕育而成的,没有品尝最深的痛苦,也就体验不到最大的快乐。魏晋士人之所以快乐,快乐的要死,是因为他们深入到最痛苦的深渊,信仰破坏后的沉沦,人之为人尊严和价值的丧失。在那样一个政治龌龊黑暗的时代,不需要他们拥有济世志,没有人理解他们,没有人尊重他们,他们动不动就被杀,就被宰。他们快乐至极的玄谈里埋藏着他们的理想毁灭的痛苦,他们快乐至极的山水妙赏里时时流露为人尊严丧失的悲痛,有些魏晋士人完全沉沦为禽兽!
阮籍是魏晋时代的大名士。反复阅读他的隐晦曲折的咏怀诗,能感觉到他是一个有大孤独感的人,是一个充满苦闷的人。他“夜中不能寐”,睡不着;就“起坐弹鸣琴”,消磨时间。他“独坐空堂上”,面临“谁可与欢者”的寂寞。他的这些诗,虽然不容易理解透彻,然而是一等一的好诗。也许他遭遇的那个时代,就是他忧思、伤心的根源。故他胸中的垒块,须酒浇之。他肆意酣畅,可谓酒池。
他用酒浇的是他的孤独,他的寂寞。他坐上牛车,让牛漫无目的的走,到路的尽头,痛哭而返。他母亲死了,他埋葬的时候喝酒吃肉,然临诀吐血。这是怎样的沉沦之痛?!然而那些沉醉于酒池,丑态百出、完全堕落的士人,他们并没有创造出像阮籍那样好的作品,他们心中也没有垒块,他们是十足的恶棍,羞耻心荡然无存!抱朴子在《讥惑》篇有描写:“世人闻戴叔夜、阮嗣宗傲俗自放,见谓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学之,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亲。”
时代风气,令人咋舌。那些激扬魏晋名士的后来人,想必也不能宽容溲便于人前之禽兽行为吧。可谓礼教破碎,傲慢成俗。千年后读之,也令人恼怒。人总不能以作禽兽而傲俗。
嵇康也是魏晋时代的大名士,可谓朝阳之鸣凤。他活,活得光明磊落;死,死得从容不迫。《世说新语》说:“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这就是淡定的极致的绽放,然而“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发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
这就是神色狼狈的丑态,也令人唾弃。魏晋时代,名士……被屠杀极为惨烈。曹爽、何晏、李胜、丁谧、邓飏、毕轨、恒范等同日被杀,有名士减半之叹。晋人虽发现了人之形体美和精神美,也用惊采绝艳的词藻形容之、赞叹之,然晋人对人却唯独不爱,对人也没有深厚的同情心。
余嘉锡先生说:“嵇、阮虽以放诞鸣高,然皆狭中不能容物。如康之萁踞不礼钟会,与山涛《绝交书》自言‘不喜俗人,刚肠嫉恶,轻肆直言,寓事辄发’,又《幽愤诗》曰‘惟此褊心,显明臧否’,皆足见刚直任性,不合时宜。籍虽至慎,口无臧否,然能青白眼,见凡俗之士,辄以白眼对之。则亦孤僻,好与俗忤。特因畏祸,能衔默不言耳。康足掇杀身之祸。藉亦为司马昭之狎客,苟全性命而已。
涛一见司马师,便以吕望比之,尤见赏于昭,委以腹心之任,摇尾于奸雄之前,为之功狗。”
这可谓高见,和那些片面啧啧赞扬魏晋名士的人不可同日而语。
魏晋士人虽沉醉于玄谈,迷醉于山水,他们所绽放的审美境界,可谓情深,然他们的深情,缺乏广阔的同情心,浩博的社会关怀。
参考文献:
[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余嘉锡.晋书(第七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0.
[3]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