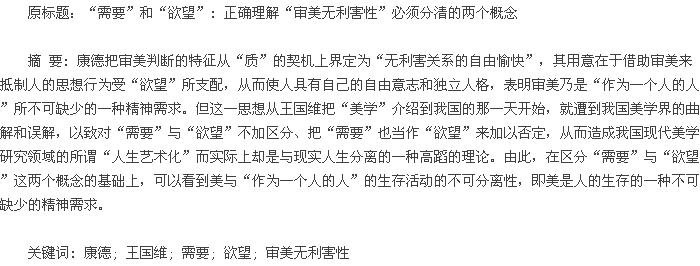
一
“无利害关系的自由愉快”被康德视为“审美判断”的第一契机,他把“美”与“快适”和“善”加以比较,认为“在这三种愉快里,只有对于美的愉快是唯一无利害关系的自由愉快,因为它既没有感官方面的利害感,也没有理性方面的利害感来强迫我们去赞许”。他把这种观赏方式称之为“静观”,认为“它对一对象的存在是淡漠的”,而不会引发人们占有的冲动,[1]( P.46) 因此它既不属于理智,也不属于意志,而只能是属于情感的对象。
“静观”这概念源于古希腊哲学。古希腊哲人认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的善”就是“幸福”的生活,“幸福应伴随快乐”; 而在各种快乐中,最大的快乐也就是合乎智慧的活动,“因为它是思辨活动,它在自身之外别无目的追求,它有着本身固有的快乐,有着人所可能有的自足、闲暇、孜孜不倦。……如若一个人终身都是这样生活,这就是人所能得到的完美幸福”。[2]( PP.225 -226) 所以到了斯多亚主义那里,就把与“自足”相对的、追求外在目的的意志活动,以及作为意志的内驱力的“欲望”分离开来,而对欲望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自然的东西都是容易获得的,毋须刻意追求。它把因欲求而生的内心冲动称之为“激情”,认为“激情是由错觉而生,是灵魂中的不合理的,不自然的运动”,“它在‘钱是好东西’的信念下贪图钱财、酗酒、挥霍无度而使人内心不得安宁”。所以“有智慧的人是没有激情的”,“良好的情感就是愉悦、谨慎和希望”。“愉悦”与“快乐”相对,是“理性的兴奋”; “谨慎”与“恐惧”相对,是“理性的避免”; “希望”与“欲求”相对,是“理性的追求”。从而表明幸福的生活就是一种不受欲望所困,远离激情冲动的一种淡泊、宁静的生活,亦即是以“静观”的态度去对待的生活,它带有强烈地否定意志的倾向,[3]( P.618) 以至到奥古斯丁那里进一步根据《旧约》圣经中的“原罪”说而视“意志是罪恶的根源”。[4]( P.128) 埃里根纳就是按这一思想来解释审美的特性的,认为“智者在心中估量一个器皿的外观时,只是简单地把它的自然的美归于上帝,他不为诱惑所动,没有任何贪婪的毒害能够浸染其纯洁的心,没有任何欲念能玷污他”。他反对仅仅以感官的愉悦性来判断美与不美,批评“视觉被以欲求的心理看待可见形态美的人们滥用了。因为上帝在《福音书》中说: ‘谁以贪婪的目光注视一个女子,谁已在心里犯了通奸罪’”。[5]( P. 126) 到了近代,鉴于资本主义发展而导致的对社会风气的败坏,又被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夏夫兹博里和哈奇森引入到对美的解释中,如哈奇森认为,美所给予人的快乐“不同于基于对利益的预期而源于自爱的那种喜悦”,它使人“除了获得令人愉快的美的观念外,在美的形式上毫无对利益的任何其他预期”,“我们源于对象的美的感官把对象构造得有益于我们,完全不同于对象被如此构造时我们对于它的欲望”。[6]( PP.10 -11) 经过这一思想演变,到了康德那里就被概括为“无利害关系的自由愉快”而作为“审美判断力”的“质”的契机而明确提出。
“审美判断力批判”是康德《判断力批判》的基础部分。他的《判断力批判》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为了沟通“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亦即道德理性而作的,他把“无利害关系的自由愉快”作为“审美判断力”的“质”的契机,和与之并存的“量”、“关系”、“情状”这三个契机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实践理性”排除内部和外部的强制而使人的道德行为进入自由的境界。所以与斯多亚主义不同,这里并没有否定意志的意思。因为意志作为人的追求一定目的活动,它的合理与否不在于意志本身,而在于它所要达到的目的。而这一点却被叔本华忽视了,这使得他不仅完全倒退至斯多亚主义,而且还按古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学和佛教的思想,不加分析地把意志看作是造成人生痛苦的最终根源。叔本华美学思想的出发点也是把审美看作是一种静观( 直观) 的活动,它使人不再与自己的利害关系联系起来而使人在观察事物时“不再是‘何处’、‘何时’、‘何以’、‘何用’,而仅仅只是‘什么’……代替这一切的却是把人的全副精神能力献给直观,沉浸于直观,并使全部意识为宁静地观审恰在眼前的自然对象所充满”。[7]( PP.249 -250) 他把人生的本质视作为“无”,认为在平时生活中“我们之所以这样痛恶这个无,这无非……我们是这么贪生,表现着我们这贪生的意志而不是别的,只认识这意志而不认识别的”。所以一旦随着“意志的放弃,则所有那些现象,在客体性一切级别上无目标无休止的,这世界由之而存在并存在于其中的那种不停的熙熙攘攘和蝇营狗苟都取消了,一级又一级的形式多样性都取消了,随意志的取消,意志的整个现象也取消了”,[7]( P.562) 这时,人们也就“自失于对象之中”,也就“忘记了它的个体,忘记了它的意志”,而作为无私无欲的“纯粹的认识主体”而存在,从而使自己与对象的关系成为“纯粹的观审,是直观中的沉浸,是在客体中的自失,是一切个体性的忘怀,是遵循根据律的和只把握关系的那种认识方式的取消”。[7]( P. 274) 这时“我们所看到的就不是无休止的冲动和营求,不是不断地从愿望过渡到恐惧,从欢愉过渡到痛苦,不是永未满足永不死心的希望,那构成贪得无厌的人生大梦的希望; 而是那高于一切理性的心境和平,那古井无波的情绪,那深深的宁静,不可动摇的自得和愉悦。”[7]( PP.562 -563) 这就是人生的解脱,一种静观的审美境界。
在我国近代美学史上,把西方美学引入我国的第一人王国维就是按叔本华的这一思想来理解康德的审美是“无利害关系的自由愉快”的,他认为生活的本质“‘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痛苦是也”,“故欲与生活与痛苦,三者一而已矣”,[8]( P.744)“人之所以朝夕营营者,安归乎? 归于一己之利害也。人之生矣则不能无欲,有欲则不能无求,有求则不能无得失……于是由之发生于心者则为痛苦,见之于外者则为罪恶”,[9]( P.150) 而“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10]( P.147) 这样,他就把审美境界视作为一种“无希望、恐惧、内外斗争、无人我之分”的“生的意志”灭绝的状态。[9]( P. 153) 这解释似乎为我国现代审美理论定下了基调,以致其后将近半个世纪之中,我国的美学界大多是按这一观点来解释审美,而把对审美的理解引入误区。
之所以会作出这样的解释,在笔者看来,就在于王国维对“欲望”与“需要”这两个概念未作区分而加以混淆,把“需要”都当作“欲望”来加以否定而陷入到悲观主义和xuwuzhuyi之故。“需要”是人为了求得自身生存和发展所必然会有的对于外部世界的各种需求的总称,它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人作为血肉之躯,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有生命的个人存在”,总需依赖于一定的物质资料才能生存下去,所以物质的需要乃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如果按王国维的理解,把人的一切需要甚至“生的意志”都混同于欲望予以否定,那么人活在世上本身岂不就是一种罪过? 后来,朱光潜在阐述他们提倡的“人生艺术化”时,又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认为:
“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问题,大半由于人心太坏”,“人心之坏,是由于‘未能免俗’”,“现世只是一个密密无缝的利害网,一般人都不能逃脱这一圈套,所以转来转去,仍然被利害两个大字系住”,不能超脱,“像蛆钻粪似的求温饱”,“这种人愈多,社会愈趋腐蚀”。这无疑是把人生的基本“需要”也当作“欲望”来予以否定。
联系当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人民大众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度日的现实社会,这种回避现实、掩盖矛盾的分析就不仅是一个思想认识的问题,而视为政治立场的问题也不以为过。所以在基于这一认识基础上他所提出的“美感世界纯粹是意象的世界,超乎利害关系而独立,在创造或欣赏艺术时,人们都从有利害关系的实用世界搬到无利害关系的理想世界里去”,因而可以达到“怡情养性”、“净化人心”的作用,[11]( P.466) 就像当年黑格尔批评伊壁鸠鲁学派时所说的,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圆满无亏、纯粹自我享受”的“养心术”。[12]( P.13) 所以他提出要改造社会先得要求人心净化,而“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的主张,[11]( P.446) 所反映的实在是当时那些既不甘同流合污,又远离人民大众、惧怕现实斗争的士大夫阶级的消极避世的心理。这不仅与改造社会无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使美学在我国成了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高蹈的理论。这也就是从 20 世纪初以来,虽然对于审美教育我国有不少人都在积极提倡而实际上却没有产生多大社会影响和社会作用,如同当年蔡元培所感叹的“我以前曾经很费了些心血去写文章,提倡人民对于美育的注意。当时很有许多人加入讨论,结果无非纸上空谈”,[13]( P.214) 而鲜有功效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所以,笔者认为要正确理解审美是“无利害关系的自由愉快”这一思想,首先就应该分清“欲望”和“需要”这两个概念。
“欲望”在古希腊哲学中各家的认识并不一致,在柏拉图那里一般以其自然性与非理性对之采取批判否定的态度,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则作一个中性的概念来使用,并不含有褒贬的倾向。如他认为人的灵魂有三个方面: 感觉、理智、欲望。“感觉”受制于对象,是个别的; “理智”存在于灵魂自身,是普遍的,是“灵魂中用来思索和判断的部分”; 而“欲望中有所追求和躲避”,因而是指向一定目的的,“如果没有任何欲望,我们决不可能看到心灵会产生运动”,[14]( P. 87) 因此他把欲望归属于意志的活动,只不过他认为欲望应该受理性的制约而取其中道、有所节制,若是“离开了德性,将是最肮脏、最残暴的最坏的纵欲者和贪婪者”。[15]( P.586) 到了中世纪,尽管受禁欲主义的影响,对欲望一般都采取排斥的态度,但即使在经院哲学家托玛斯·阿奎那那里,还是沿袭亚里士多德的理解而视其为人的固有本性之一部分,并未与贪欲直接等同而完全予以否定;只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由于一些人文学者如彼得克拉、爱拉斯谟、薄迦丘等人对于人的感性需要和现世享乐的片面宣扬而导致人的欲望日趋膨胀,以致在霍布斯那里才从“性恶论”出发,视欲望为一切罪恶的总根源。他认为人性本恶,它使得人天生就有强烈的权势欲、财富欲、知识欲和名誉欲。而“这几种欲可以总括为一种欲望,也就是权势欲: 因为财富、知识和荣誉不过是几种不同的权势而已”。[16]( P.54) 这种权势欲造成了“作为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就是“得其一而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争夺,从而“使人倾向于争斗,敌对和战争”,处于“互相为战的战争状态”。[16]( PP.72 -73,96) 这样,也就把欲望与恶、贪婪、野心、争斗联系在一起,使“欲望”这一原本是中性的词演变成一个贬义的词。这才引起学界的强烈反对,而认为它与审美是完全对立的。首先在英国本土,它就招来了剑桥柏拉图主义和夏夫兹博里、哈奇森等人的批判; 其后在法国又受到卢梭的严厉斥责。但在对“欲望”的理解上,卢梭又与夏夫兹博里等人不完全相同,他所沿承的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就像当年伊壁鸠鲁那样,他把欲望分为“必要的”和“不必要的”。认为“自然的又必要的欲望可以解除痛苦,例如渴的时候想喝水; 自然而非必要的欲望则是指仅能使快乐多样化而不能消除痛苦,例如奢侈的食品”,“所有尚未满足却不会产生痛苦的欲望都是不必要的”。[17]( P.85) 并指出人出于生存的目的,他必须爱自己,所以不可能没有欲求,但应该区分“是为了维护我们生命所必须的物质需要”和“为了我们生活的舒适,快乐和豪华排场的需要”这样两种不同的需要,他把前者称之为“真正的需要”而后者为“虚假的需要”,亦即欲望。[18]( PP.240,246) 认为与文明人相比,“野蛮人由于缺乏各种智慧只能具有因自然冲动而产生的情感,他的欲求决不会超出生理上的需要”,而且“这种需要也很有限”; 只是到了文明社会,“每个人都开始注意别人,也愿意别人注意自己。于是公众的重视具有了一种价值”,从而使得人“一方面产生了虚荣和轻蔑,另一方面产生了羞惭和羡慕”,[17]( P.118) 人人都想超过别人而争当第一,这样才导致理性代替了本能,智巧代替了良知,自然的需要也就开始演变成欲望,从而使“虚荣和享乐之心,邪恶和萎靡不振之风迷漫”,“一方面是竞争和倾轧,另一方面是利害冲突,人人都时时隐藏着损人利己之心,这 一 切 灾 祸,都 是 私 有 财 产 第 一 的 结果”。[17]( P.125)经历了这样一番思想演变之后,人们对于这两个概念开始有了比较客观而辩证的认识和鉴别,并使卢梭的观点逐渐为人们所认同和接受。
在考察人的意志活动的时候,就逐渐把“欲望”从“需要”中分离开来。如霍尔巴哈在谈到人与动物的区别时认为: 动物的活动只是“满足于本能”,它的需要是“有限的”,它“既然没有人的那些需要,又没有人的那些欲望”; 而对于人的活动来说,由于他的“想象、偏见和脑力活动”的作用和推动会使得需要无限增长而成为欲望,这样“随着这些需要的增长,人的痛苦随之也加深了”。[19]( P.84) 这一区分也为当今不少西方学者所认同,如弗洛姆认为“只有依据于认识到真正人的需要是植根于人的本性的,才能区分真正的需要和虚伪的需要。……社会分析学家的任务正是要唤醒人们认识什么是梦幻的虚伪的需要。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目的就是实现人的真正的需要,而只有当生产为人服务,资本家不再创造和利用人的虚伪的需要时,才能达到这一目的”。[20]( P.73) 而丹尼尔·贝尔则对两者作了更明确的区分,认为“需要是所有人作为同一‘物种’成员所应有的东西”,“欲望则表现不同个人因其趣味和癖性所生的多种喜好”。他引用凯恩斯的话说明它不是一种必需的而意在表明自己地位的优越,“满足人的优越感”,以使自己“超过他人感到优越自尊的永无止境的那一类的需求”,它会“驱使人追求满足时可以达到凶猛的程度,足以使人丧失理智而走向犯罪”,他认为“资产阶级社会与众不同的特点就在它所要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望”。[21]( PP.22,68)这种情况并非完全没有引起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关注,并考虑如何予以改变; 但他们大多是在讨论什么是“幸福”的问题时,从“感觉论”和“自爱论”的观点出发来加以分析和评判,像 18 世纪法国启蒙主义和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尽管都不赞同霍布斯的人与人之间是豺狼之说,认为人与社会是不可分离的,“美德只能理解为追求共同幸福的欲望; 因此,公益乃是美德的目的,美德所支持的行为,乃是它用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 但由于它的出发点是感觉论、是人的“肉体感受性”,认为“人是能感觉肉体的快乐和痛苦的,因此他逃避前者,追求后者”,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爱,乃是我们身上感觉能力必然的结果”,这就必然导致“个人利益是人们行为价值的唯一而且普遍的鉴定者”的结论。只是由于在社会中任何个人的幸福都是需要别人的幸福来保障,这才要求在自爱的同时还必须顾及别人的利益,所以“爱邻人在每个人身上只不过是爱自己的结果”,[22]( PP.63,64) 这就是他们所宣扬的“合理的利己主义”的理论依据。从这一思想基础出发,他们在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上似乎都沿袭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试图通过制定人的行为规范从外部来控制人的欲望,而视道德的人为按照社会制定的规范准则行事的人。这样“德行”就不是源于“德性”,而只不过是在外部规范强制下的一种行动。
这些理论使康德颇为不屑,他转向从人的“德性”、从人的内部原因去寻找当时社会道德沦丧的根源以及人生“幸福”的道路,认为那种从经验的“现实性的快乐”出发的“从属自爱或个人幸福的普遍原则”是不能成为道德原则而给人以真正的快乐和幸福的。他从基督教的“原罪”说所引申出来的把有罪的体验看作是道德的基础中得到启示,因为《圣经·约翰一书》里说: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凡是虔诚的基督徒都认为自己是有罪的人。这“罪”在康德看来就是源于“欲望”。但他又不同于禁欲主义者,他承认人的感性需要存在的合法性,并不认为“幸福原则”和“德性原则”是完全对立的,如他在其伦理学的代表作《实践理性批判》中表明: “纯粹实践理性并不希望人们应当放弃对于幸福的要求而只是希望一旦谈到职责人们应当完全不瞻顾幸福。”因为感性毕竟只是个体的、生理的、经验的,如果以个人幸福为目的不可避免地就必然会导致欲望的无限膨胀,所以若是“以个人的幸福原则成为意志决定的根据,那么这正是德性原则的对立面”。[23]( PP.101,37) 如何在满足人的感性需求的同时又使人在生活中避免完全受感性的支配,而不使自己成为欲望的奴隶? 这在康德看来也就成了人在走向自我完善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的人的过程中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他把“欲望”看作是培养个人德性的最大的障碍,强调德性必须建立在职责的基础上,只有当人们摆脱一切利己主义,建立在对道德法则的膺服的基础上的自由意志驱使下,才会有真正的道德行为的发生。那么如何使“德性原则”和“幸福原则”两者不再相互对立而有机地统一起来呢? 他发现审美正好可以完成他所希望的沟通两者的目的,因为审美判断作为一种“无利害关系的自由愉快”,虽然是在感性的层面上发生的,但它不同于“感觉快适”,因为快适是一种“促使主体停留在原状态的情感”,[24]( P. 155) 它“只是属于单纯的享乐”而“没有教养作用”;[1]( P.107) 而审美作为一种“理性的兴奋”,在满足人的感官享受使人从对象中得到愉快的同时,不仅不为占有欲所支配,而使人始终保持一种平和、宁静的心态。所以他认为只有当人排除利害关系“不顾到享受而行动着……这才赋予他作为一个人格的生存以一绝对的价值”。[1]( P. 45) 这就是康德把审美看作是“无利害关系的自由愉快”的真意所在。他的目的就是试图借审美来抵消自资本主义社会以来所无限膨胀的“欲望”,恰恰是为了维护和完善人自身人格的“需要”。
三
但是我国美学界,在阐述和理解审美是“无利害关系的自由愉快”这一命题时,由于自王国维以来一直没有分清“需要”和“欲望”这两者的区别,以致为了抵制“欲望”而把“需要”也一起予以否定,不是把审美放在人的需要系统中来进行考察。这样,有意无意地把美看作像戈蒂叶所说的是一种奢侈品,似乎它只是有钱人的专利。所以直到今天,当我们在谈论普及审美教育时,还常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质疑: 当广大劳苦大众还为衣食奔波时,我们来提倡审美,乃是一路高蹈的、不切实际的理论。为了澄清这一认识上的混乱,笔者觉得在说明了审美对于完善人的人格的重大意义这一普遍道理的基础上,还有必要再针对这一具体观点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这就要从人的需要系统以及不同需要层次的内在关系和联系的分析入手。
需要是人的活动的内在动机,是人的活动的积极性的源泉,要是没有一定需要的驱使,人的活动就不可能产生。而需要是一个层次的系统,一般可以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层次。
这是由于人作为“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它的生命包括肉体生命和精神生命两个方面。肉体生命是依靠物质生活资料来维持的,相对于精神需要来说,物质的需要是第一性的,要是连基本的物质需要都不能得到满足,人也就难以存活。所以,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在一个尚存在着贫穷、失业,许多人还在为温饱的生活奔波的社会里,审美在国民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总是要受到限制。因此为了提倡和普及审美教育,首先应该解决的就是经济生活和文化教育领域中的公平正义问题; 但若是仅仅从物质的层面上考虑问题,不仅很难划清需要与欲望的区别,而且很可能把需要引向欲望。所以这里还需要我们从人学和伦理学的观点来进行思考。因为社会学是一门实证的科学,它看重的是必然律,是外部因果性,所以在社会学的视野中,人总是被外部的环境和条件所决定的; 而人学、伦理学所强调的是自由律,认为人不同于动物,他不是消极地听命于外部关系,受外部条件所决定,他有自己的志趣和意向,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这就决定了在同样的客观条件下,每个人在行动上还有自己不同选择的自由。正如从当今不断揭发出来的许多高官的贪污、受贿的事实所表明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优裕不能保证人就不犯罪那样,反之,物质生活贫穷也不一定就会使人们放弃自己的志趣、爱好、独立人格和精神上的追求。这里就突显了精神生活在人的生存活动中的重要地位。要说明这个问题,还需要我们从什么是精神生活说起。
精神相对于物质而言,指的是人的心理活动和意识活动,这是人类进入社会以来不断社会化的积极成果,是人不同于动物的根本特征,它体现在人的认识活动、意志活动和情感活动之中。
精神生活的特点就在于奥伊肯所说的“超越性”:
认识是为求理性对感性的超越,它使人的意识进入普遍的领域而不再直接接受个别的、感觉经验的限制,唯此人的认识才能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意志是为求理想对现实的超越,因为意志是人追求一定目的的活动,它不同于认识在于通过自己的活动使对象世界按自己的目的加以改造而实现自己的理想。如果说,认识与意志都是人的后天智能发展的成果,它们旨在求得对外部世界的超越; 那么,情感则源于人先天的自然本性,源于人的内部世界,而使人的活动超越一己之利害关系,而获得普遍的社会意义。这正是马克思认为的是“人的活动”的基本特征,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所着重阐述的问题。尽管自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来,由于私有制和社会分工,使人的活动向着与之相反的方向发展,丧失了它原本所固有的特性,而成为仅仅是个人谋生的手段,使劳动人民的劳动成为“外在的”、“不属于他本质的东西”,以致“他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成为“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25]( PP.50 -51) 这在马克思看来是不应该当作我们应认同的,而恰恰是需要予以改变的现实。而理论的作用正是为了给我们变革现状指明方向,探寻道路。所以为了消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实现人的自由解放,马克思在从物质层面上提出消灭私有制和社会分工所造成的对人的强制和奴役的同时,还着重研究了如何使人由于异化劳动所导致的“人的机能”变为“动物的机能”的状态下解放出来,而“把劳动作为体力和智力的游戏来享受”。[26]( PP.368 -369) 这里的“游戏”一词显然是借用了康德和席勒的概念。康德把人的活动分为“自由活动”和“雇佣活动”两类,认为后者“只是由于它的结果( 例如工资) 吸引着”,它对工作本身并不感兴趣,所以是“被迫的”、“痛苦而不愉快的”,[1]( P.149) 而前者则仅仅是为工作自身所吸引,它对工作本身就感到愉快的。马克思提出“把劳动作为体力和智力的游戏来享受”的用意也就是认为发展生产“决不是摒弃享乐”,而是在发展力量,发展生产能力的同时也必须顾及“发展享乐的能力和手段”。[26]( P.371) 这就充分说明了“享受”与“人的劳动”的不可分离性,唯有劳动者把乐业的精神与敬业的精神统一起来,把工作同时看作是一种享受,他才会全心致志地投入其中,使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这种超越利害关系的精神享受,就是一种审美享受。
正是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审美作为一种确保人格独立和人格完善的精神享受对于每个人的生存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它是人的一种“精神食粮”,就像梁启超所说它并非什么“奢侈品”,而像“布帛菽粟一样”是人所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须品之一”。[27]( P.22) 所以那种认为当劳苦大众尚在为温饱奔波的时候,来提倡审美是一种脱离现实的高蹈的理论之说,只能说是一种导致人们放弃对于“应是”生活的追求而去认同那些屈从于现状的奴隶哲学。虽然我们这里所做的都是一些理论上的探讨,但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即使在广大劳苦大众所从事的艰苦劳动的生产中,也不是就与审美绝缘的。这种审美的因素使得劳动对他们来说不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同时也从中获得一种精神享受的方式,就像高尔斯华绥在他的小说《品质》中所描写的那位老皮靴匠格斯拉那样,尽管他非常穷困,但从不把制作皮靴仅仅当作谋生的手段,一旦投入制靴工作,他就感到是一种享受,总是自得其乐、乐在其中,从不草率从事、粗制滥造。从而使得他的工作不仅成了展示他的技艺、实现其自身价值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且也使得他在精力上的付出能从工作所得到的愉快中获得补偿,并始终对工作怀有一种敬业的精神,从不因穷困而丧失自己的人格; 所以他制作的靴子总是最精美、最耐穿的。他对工作是那样的虔敬,让人感到“进了他的店铺那心情仿佛进了教堂”。罗丹更是把对工作忠心耿耿、精益求精、以工作为乐的工人称之为“艺术家”。[28]( P. 118) 也正是由于审美对于人的生存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从历史上来看,尽管广大劳苦大众挣扎于温饱线之下,进入不了艺术的殿堂,与一切高雅的艺术无缘,但以各种形式流传于民间的艺术在他们的生活中却从未消失,这不仅使得他们在自娱自乐中获得精神的抚慰和激励,缓解生存的压力,而且还从中获得思想品德的提升,如同恩格斯在谈到民间故事时说的,民间故事使一个劳累的农民“忘却了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 使一个疲乏不堪的手工业学徒感到自己的“寒碜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 民间故事书“还像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29]( P.401) 这都说明审美作为一种精神生活乃是人的生存的需求,是任何人的生活和工作所必须的。尽管实际上离这样理想的状态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理论从来不只是说明现状而是为了改变现状的,所以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就特别需要理论来予以正确的引导。
参考文献:
[1]康德. 判断力批判: 上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4.
[2]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3]第欧根尼·拉尔修. 名哲言行录[M]/ /苗力田. 古希腊哲学.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4]奥古斯丁. 论自由意志[M]/ /恩典与自由.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5]塔塔科维洛.中世纪美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6]哈奇森.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7]叔本华.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