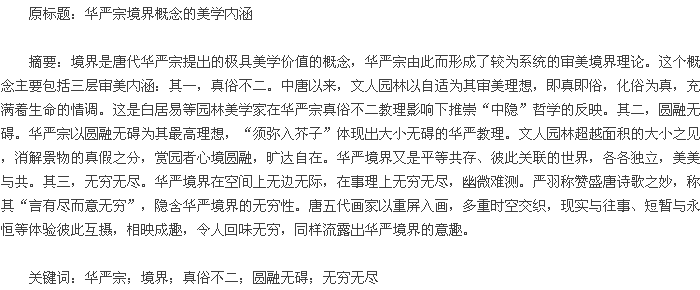
华严宗是隋唐时期盛行的佛教流派。《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唐代华严宗的理论基础,也是他们从事佛教义理建构的总纲法门。关于中国哲学与审美境界的关系,学界已有丰富而深入的探讨。然而,以往的研究多强调道家和禅宗对审美境界的影响,殊不知中国佛教各宗其实都很重视境界问题,特别是唐代华严宗形成了系统的境界理论,境界是最具美学价值的华严宗哲学概念。华严宗的境界概念不仅为中国美学意境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思想支持,而且在唐代艺术审美领域也常有华严境界的意味。本文从唐代华严宗境界概念出发,阐发其美学内涵,以便深化对中国美学境界问题的认知。
结合唐代美学和艺术的实际情况而言,华严境界主要包括三层内涵:一是真俗不二,二是圆融无碍,三是无穷无尽。以下依次论述。
一、真俗不二
唐代华严宗人普遍重视大乘佛教的般若空观。般若空观即源于印度佛教的中道思想,真俗不二是般若空观对事物真实性的基本体认。华严宗四祖澄观说:“色不异空,明俗不异真。空不异色,明真不异俗。色空相即,明是中道。”[1]澄观强调事物的真俗不异,这在唐代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法藏那里则被表述为真妄双融。法藏说:“又明真该妄末无不称,真妄彻真源体无不寂,真妄交彻二分双融无碍全摄。”[2]大致而言,华严宗讲真俗不二、真妄双融,继承了大乘佛教的般若空观,特别是在法藏这里,又注入了圆融无碍的华严理想,这与当时中国佛教其他各宗的真实论区别开来。与禅宗相比,华严宗的真实论更强调事物形相与体性的交互圆融,而禅宗的真实论则更侧重事物形相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作为佛教的一对关系概念,“真”与“俗”对举,如一体之双面。这里的“俗”是指事物因缘所生,其存在的体性虚幻不实。佛教所说的“真”也不属科学认知或逻辑推理之真,它源于般若空观的真如本体。在大乘佛教看来,“俗”为幻有,它是对事物虚幻存在状态的概括。“真”即真如,这是对事物体性真空的指称。依据般若空观,真不异俗,俗不异真,真俗不二,即俗即真,方为正道。印度佛教的真实观念通过高僧僧肇等人的介绍与阐发融入中国佛教,并得以发展。僧肇说:“是以圣人乘真心而理顺,则无滞而不通。审一气以观化,故所遇而顺适。
无滞而不通,故能混杂致淳。所遇而顺适,故则触物而一。如此,则万象虽殊,而不能自异。不能自异故知象非真象。象非真象,故则虽象而非象。然则物我同根,是非一气。”[3]这表明,世间万物并非先天而在,它是一气的显发流行,所以说“象非真象”。同时,他有强调事物形相虽然有别,却又彼此关联,归于本根之气。僧肇借道家象论切入大乘佛理,论证万象与一气(即“道”、“一象”)的不二关系,为隋唐五代佛教探讨事物的真实性做好了理论准备。
天台宗立教,即以真俗不二为其基本教理。“空谛”、“假谛”、“中谛”三谛相即,是其基本理论构架。华严宗也讲真俗不二,这与天台宗没有本质差异。然而,华严宗没有设置三谛结构,只列“世谛”和“真谛”二维,这是一大区别。法藏说:“幻有现前,是世谛。了尘无体,幻相荡尽,是真谛。今此世谛之有,不异于空相,方名世谛。又真谛之空,随缘显现,不异于有相,方名真谛。又空依有显即世谛,成真谛也。由有揽空成,即真谛成俗谛也。由非真非俗,是故能真能俗。即二而无二,不碍一二之义历然。”[4]在华严宗看来,世谛之有与真谛之空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真谛虚空,世谛幻有,称为俗谛。二者相待而存,空幻不异。华严宗承续了大乘佛教的般若空观,并将它运用到真俗关系的讨论领域。从最高的境界来说,真源超绝筌蹄,妙观超越言象。妙观是华严宗的觉悟法门,尽管妙观强调真俗双泯,空有两亡,但这并不妨碍真俗二谛的体用相即。或者说,真空未尝不俗,即俗以体真空。幻有未始不真,即真以明幻有。破除对空/有、常/断的执念,才能呈现真空如如的本来面目。天地万物,无不缘起而在,自性为空,真俗不二,合乎般若精神。
此外,华严宗既然主张真俗不二,其中含有真俗圆融的意蕴,这也是天台教义所不具备的。法藏说:“是故空有无碍,名大乘法。谓空不异有,有是幻有。幻有宛然,举体是空。有不异空,空是真空。
真空湛然,举体是有。是故空有,无毫分别。”[5]这里主要讲了两层意思:一是空有/真俗不异,二是空有/真俗无碍。这段话很能代表唐代华严宗真实观的基本见解。真空幻有,圆融无碍,这是极为微妙的华严境界。
华严境界的真俗不二,在唐代文人园林审美中有最为突出的体现。中唐以来,文人园林普遍出现了以自适为审美理想的倾向。这种审美理想的出场可以看作是白居易等文人推崇“中隐”的人生哲学在园林审美领域的落实。白居易说:“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6]490这里的“中隐”,既不同于“大隐”,又不等于“小隐”,它介于二者之间,或兼得二者之长,而避二者之短。白居易提出“中隐”,这是一种“儒玄道两全”的生存方式。作为中唐以来出现的新的人生哲学,“中隐”集中体现出居士式的人格理想。白居易既不放弃世俗生活,同时又想保持心境的旷达、精神的洒脱。这对中唐以来文人审美理想的生成有过极大的导引作用。
“中隐”是作为一种官吏的处世哲学而被提出来的。一旦身为世俗官吏,就会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需要担当,有较为繁杂的政务事务需要处理,他不可能避世,也不可能逃世。但是,在白居易、刘禹锡等看来,文人虽然身为官吏,难以摆脱世俗社会的约束和限制,但政务事务的处理不能成为个人生活的全部内容,这种功利的、世俗的生活状态不能在人的整个生命活动中占据过大的比重。因此,白居易主张官吏应该具有洒脱的性情,从政不能趋炎附势,不能盲从流俗,不可疲于名利升迁,失却本真天性。这样,“中隐”似乎成为最理想的处世方式与人生理想。他们在政事之余,往往忘返于山水园林,可以游览,可以痛饮,可以吟诗,或独处,或会友,或享乐,政务料理与性情愉悦毫不相碍。
按照白居易的规定,“中隐”之士应该不计贵/贱、穷/达、闹/静,过着悠游逍遥的生活,在出世与入世之间自在回旋。这显然是一种诗意化的处世态度,也是一种审美化的人生理想。白居易的难得之处在于,他将“中隐”的处世态度落实到园林审美领域,经营他的“官舍”世界:“高树换新叶,阴阴覆地隅。何言太守宅,有似幽人居。太守卧其下,闲慵两有余。起尝一瓯茗,行读一卷书。早梅结青实,残樱落红珠。稚女弄庭果,嬉戏牵人裾。是日晚弥静,巢禽下相呼;啧啧护儿鹊,哑哑母子乌。岂唯云鸟尔,吾亦引吾雏。”[7]157依照白居易的设想,官舍可以办理政事,也可以恣情休憩,世俗性的公务活动与休闲性的审美化生存并行无妨。于是,官舍成为白居易等人舒卷性情的理想居所,成为既有社会担当又作超然之想的文人寄寓隐逸情趣的诗意空间。这是华严真俗不二教理对文人处世哲学、生活态度乃至审美理想的影响所至。
中晚唐不少退隐的文人雅士,晚年生活在青苔院落之中,享受暖日和风的滋润,品味幽兰松香的雅意。虽然时光已老,岁月蹉跎,但他们并不感到孤独,而是尽情享受平生未了的田园之乐。如此闲适的心境,如许平淡的情怀,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世界原来并不冷酷,人间真情如故,栖息之地不大,却具无限妙意。风轻云淡,月落乌啼,一切尽在不言中。他们将园林居所作为护养闲适生命情调的道场。通过园林审美活动,传达出华严哲学真俗不二的意趣。在这样的园林意境之中,人的心性既舒卷自在,景物的存在价值也得以彰显,可谓各张其天,各尽其性。园林审美者没有脱离日常的生活世界,却又能从世俗的生存中突围出来。唐代园林为文人的精神突围提供了极佳的场所和氛围。私家园林经常成为文人雅士聚会交流的诗意居所,处处充满着即真即俗的氛围。天光云影,飞潜动植,无不洋溢着生命的情调,无不愉悦着悠闲的性情。
尽管唐代园林注重审美者的精神超越,但终究没有走上与世隔绝之路,而是在平常的生活世界里构筑一方自在的精神栖息之所。唐代园林美学认为,生活世界处处充满着诗情画意,而园林正是生成这种诗情画意美的重要场所。王维述其田园之乐:“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春烟。花落家僮未扫,莺啼山客犹眠。”[8]258这种任运自然的乐生情调、现世情怀在当时园林中颇为普遍。花前月下,池畔溪边,处处充盈着生活的气息,弥漫着人间的情味。这种活泼泼的园林生意,是普通的日常生活的写照,又何尝不是生命真趣的留影。
唐代园林建造讲究活泼泼的生意。苍苔挂绿,野草成茵,幽鸟时鸣,竹影婆娑。这是园林的生命精神所在。杜甫咏庭院之草:“楚草经寒碧,逢春入眼浓。旧低收叶举,新掩卷牙重。步履宜轻过,开筵得屡供。看花随节序,不敢强为容。”[9]1598杜甫观赏春草,领略到普通庭院的盎然生机。李德裕的平泉园林之所以充满生意,是因为它与周围的世界息息相通。在这里,可以赏芳草,品梨花,观新苔,玩落照,望夕亭,戏游禽,生命是何其充盈而自在!
唐代园林追求活泼泼的生意,造园家多将园林建造成充满诗情画意的居所。飞潜动植,无一不在传达园林的生意。池水绿,清荷开。蛙声阵阵,蝉声丝丝。黄昏更兼细雨,微风迎来凉意。身处这样的园林情境,你会感受到生意充盈,体验到生命充满。这是唐代艺术家化俗为真,点俗成真的工夫。
二、圆融无碍
法界圆融是唐代华严宗的核心理论。在华严宗看来,理法界与事法界、事法界与事法界之间彼此互摄,交融自在。“须弥入芥子”,是华严宗为了体证事物之间的圆融关系而提出来的。这一学说源于印度佛教。“须弥”,原指古代印度宇宙论中位于世界中央的须弥山,转喻为极大之意。“芥子”,本为芥菜之种子,其体积细微,佛教以此喻示极微之物。维摩诘言:“唯!舍利弗!诸佛菩萨有解脱名‘不可思议’。若菩萨住是解脱者,以须弥之高广内芥子中无所增减。须弥山王本相如故,而四天王、忉利诸天,不觉不知己之所入,唯应度者乃见须弥入芥子中。是名住不思议解脱法门。”[10]这是印度佛教关于“须弥入芥子”的代表说法。这教理引起了唐代华严宗人的关注。
华严宗以缘起的法界理论起家,以圆融无碍为其最高理想和境界。华严宗人在说法时,常引印度佛教的“芥子”之喻来宣讲法界的圆融无碍。“须弥入芥子”,体现的是华严宗事物之间大小无碍的教理。华严宗宣称事物之间的圆融关系,通常就从事物的大小无碍入手。法藏说:“大小者,如尘圆相是小。须弥高广为大,然此尘与彼山大小相容,随心回转,而不生灭。且如见高广之时,是自心现作大,非别有大。今见尘圆小之时,亦是自心现作小。非别有小,今由见尘,全以见山,高广之心,而现尘也。
是故即小容大也。”[4]在法藏看来,事物形相的大小差异,只是世人肉眼所见,或为自心妄想诈现,不外乎心识的杂念所生。尽管如此,事物的真相并不因人的感触而改变,它超越形相分别之见,是纯净心源之映现。同时,事物的形相和真相又相即而存,圆融自在。
华严宗用“须弥入芥子”指称法界的广大而不可思议,无所不包而又大小无碍。一须弥山纳入一芥子中,须弥山不为之缩小,而芥子亦不因此膨胀。这表达出事事无碍之理。如果人能超越事物之间的大小、真幻之见,即能处处圆融,事事无碍,交融互涉,各适其性。
同样以唐代园林美学来说明问题。中唐以来的园林美学家常以小言大,流露出适意的审美理想。这与华严宗“须弥入芥子”学说有关。园林是诗意栖居的场所,也是文人安顿生命的法门。隋唐以来,中国园林常能超越面积的大小之见,消解园林景物的真假之分,流露出圆融无碍的华严意趣。
白居易说:“为爱小塘招散客,不嫌老监与新诗。山公倒载无妨学,范蠡扁舟未要追。蓬断偶飘桃李径,鸥惊误拂凤凰池。敢辞课拙詶高韵,一勺争禁万顷陂?”[11]561“一勺”之地,便有“万顷陂”之势。
园林贵在精神,而其精神不在物理空间的大小,也不在园林景物的真假,而在于它能否以有限的空间表显出无尽的风光。唐代园林是中国人圆活生命情调的映现,它处处充满着生活的气息,流露出人间的情味。
法界圆融的意趣如此,华严法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华严境界之别称。华严法界与心境相关,指向融通自在的心灵世界。法藏说:“心境融通门者,即彼绝理事之无碍境与彼泯止观之无碍心。二而不二故不碍心境,而冥然一味。不二而二故不坏一味,而心境两分也。”[12]法藏将理事圆融的精神融入到境界论领域,其中他对心境之间互不相碍关系的思考最具美学价值。
关于华严法界观、宇宙观以及心境关系,现代学者唐君毅有一段论述,颇为中肯。唐君毅指出:
“华严法界观,亦即华严之宇宙观也。然此宇宙观即宇宙唯心观,此宇宙唯心观,非如天台之重观心而可说其重在观宇宙或观境。然华严之观境,又非如唯识宗之观境之非外,以破外境之执,而是观外境是一真法界之显现,一心之显现。心之所以异于境,在心之能摄。然依华严法界观以观法界中之一切法,皆能相摄,即皆是心。如境是法,亦即是心,万境相摄如众心相摄,我心观万境,即我心观万心之互摄,于是充塞宇宙皆成一透明之心光所照耀,更无外境可执,无执可破。”[13]18-19唐君毅将华严法界观与华严宇宙观等同起来,将华严法界与华严境界等而视之,认为依华严法界观,心与境依互而存,空灵通透,心境互摄,无执无破,这的确是华严宗极为高深的心灵境界。
依据唐代华严宗的教理教义,华严境界与华严法界密不可分。因此,要体证华严境界,当从华严法界谈起。法界是华严宗的核心概念,法界观则是华严宗立教的基础。法界的体性如何?裴休对此有精要概括。他说:“法界者,一切众生身心之本体也。从本已来,灵明廓彻,广大虚寂,唯一真之境而已。无有形貌而森罗大千,无有边际而含容万有昭昭于心目之间,而相不可覩。晃晃于色尘之内,而理不可分。非彻法之慧目离念之明智,不能见自心如此之灵通也。”[14]一真法界是众生身心之本,是人的心源。法界是事物的真实本体,是万物之本源,事物真如实相的显发离不开这一真法界,即“一真之境”。法界不是客观存在的物理世界,它是本源心境,是世间万象之体。“往复无际,动静一源,含众妙而有余,超言思而迥出者,其唯法界欤!”[15]法界超越语言文字境界,而源自本心;法界没有具体的形相,却森罗大千;法界无法衡之以固定的边际,却含藏万有。法界昭明于心目之间而无相可睹,往 复 于 色 尘 世 界 而 理 不 可 夺。这 就 是 华 严法界。
探讨心与境的关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华严宗法界观的重要内容。从华严宗的规定看,一真法界是本觉之心的映现。华严法界不异世间万象,华严宗人探讨心与境的关系时反复强调这一点。华严法界是心境融通的境界,是物我自在的境界。体证华严法界,须开启离念之智,洞见本觉之心,体验一真之境。这就是华严境界。它不离法界,没有形貌,漫无际涯,“灵明廓彻,广大虚寂”,而能容纳万有。这就保证了事物之间自在无阂,纳须弥入芥子,掷大千于方外。
华严法界观的重心在于观宇宙或观境,华严所观之境即是华严境界。它是人心之本体,指向心境的广阔无垠、寥廓无边,且不可思议。生活于尘世之中,众人妄想迷执着,故步自封,画地为牢,迷惑而不知自拔,更不了心体广大神妙,不能体证心灵境界的寥廓无垠。在华严宗人眼里,一真法界是人人具足的真如智慧,实质上就是人的创造精神。佛见人迷惑不悟,不能体证法界,因此说《华严经》,令其回光返照,反求诸己,妙观如来广大智慧,体证心境圆融无碍。华严宗初祖杜顺和尚着《法界观》,赞叹法界精深,主张开三重门:“一曰真空门,简情妄以显理。二曰理事无碍门,融理事以显用。三曰周遍含容门,摄事事以显玄。使其融万象之色相,全一真之明性,然后可以入华严之法界矣。”[14]这三重门对应着华严宗的三重境界。开三重门,即可证入华严法界,即心境融通的自在之境。
中国哲学常以心镜对举来揭示心灵与世界的关系。《庄子·应帝王》曰:“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在佛典中,也有很多以镜像、影像喻示事物虚空体性的论述。包括佛法在内的一切事物,犹如镜面映照而成的影子,不必追逐,也无须断除。真正体证佛理微妙,就能心明如镜,随缘遇合,无取无舍,触境自在。既不与物合,又不与境离,即能深领华严境界之奥义。唐译《华严经》说:“譬如净满月,普现一切水。影像虽无量,本月未曾二。如是无碍智,成就等正觉。”[16]满月当空,倩影普现。处处皆圆,在在即真。影像圆成,这是华严宗理事圆融论的支点,也充满着心境融通的华严智慧。
唐代华严宗还认为,心境融通需要处理好“境”与“智”的关系。真谛和俗谛是所依之境,而贯通之心则是能依之智。对于所依之境而言,能依之智并无能取与所取之分。经由事物而彰显的智慧,才是真正的智慧。脱离具体的事物,则无能分别之智。
智慧通过事物得以彰显,才有境界可言。如果事物脱离智慧,也无所分别之境。心智虚空,故照而常寂。境界随缘而有,虽空寂而恒用[4]。这种心境融通的境界,是华严宗处理人与世界关系的智慧,它流溢着审美化、诗意化的色彩。由此,也体现出华严宗境界概念的第二重内涵,即华严境界是圆融无碍之境。
在广阔的社会美、生活美领域,也处处流露出华严境界的审美精神。宗白华说:“空寂中生气流行,鸢飞鱼跃,是中国人艺术心灵与宇宙意象‘两镜相入’互摄互映的华严境界。”宗白华提到的这种华严境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几乎无处不在。风雅君子临水闲观望,这是人与水面的互摄互映。如花少女对镜贴花黄,这是人与镜面的互摄互映。华严境界是一种和谐共存、彼此相关的世界。
宽泛地说,人与他者、人与世界、人与万物无时无刻不处在这样的彼此关联之中。
在这个华严世界里,事物之间平等共存,和谐相处,互不取扰,各各独立。人人都能实现自我,物物都能各尽其性。这就是本真的存在境界,彼此关联,美美与共。华严宗构造的美的世界既是遍在共存的,又是广大和谐的。这对于理解美的和谐性、审美活动的多样性、审美形态的丰富性等都有启发。和谐美并不是美的杂多或堆砌,不是美的铺张绚烂,而是审美形态或要素的和谐化合,交互共存而圆融自在。和谐美不是要抹杀事物的个体性和丰富性,而指向审美形态或要素之间的和谐共存,它是在尊重差异基础之上的和谐共存。
隋唐五代审美领域呈现出丰富多彩、多元并存的格局。就审美风格而言,既有声色交错、流光溢彩之美,也有风骨嶙峋、自然清新之美。在绘画审美领域,既出现过色彩绚烂的壁画、青绿山水、仕女服饰,“唐三彩”更是光彩夺目,令人目不暇接。同时,也存在以平淡天真、闲情逸趣见长的水墨山水。
唐代艺术雅俗并存,和谐发展,形成了多元化的审美风尚。这种多元化的审美风尚的出现,这种不同审美风格并存不碍的局面,一方面与唐代自由开放的社会背景分不开,另一方面也与当时思想领域的文化气象有关。提起盛唐气象,今人多会发出会心的微笑,既而心向往之,这就包含着对盛唐时代开放多元、繁荣昌盛而兼容并包的文化气象与审美精神的神往。
三、无穷无尽
华严宗境界概念还有一层特别重要的审美内涵,就是它在空间上无边无际,在事理上无穷无尽,在事物之间则相容互摄。唐代华严宗人也有相关表述,如:“境界者,即法,明多法互入犹如帝网天珠重重无尽之境界也。”[18];“若据一乘,总别与十一法相应,是佛境界。一佛境界,齐如虚空,此是总也。”[19];“事事无碍,法如是故十身互作自在用故,唯普眼之境界也。如上事相之中,一一更互相容相摄,各具重重无尽境界也。”[20]因其虚空,故能无碍。因其无碍,故能无边无际,无穷无尽。这是杜顺、智俨、法藏等华严宗人对华严境界的普遍体认。
在唐代华严宗人构造的无穷无尽的华严境界里,事物自在,互不干涉。这种圆融含摄的境界,不是杂乱无纪,而是万象宛然。法藏说:“十总圆融者,谓尘相既尽惑识又亡。以事无体故,事随理而圆融。体有事故,理随事而通会。是则终日有而常空,空不绝有。终日空而常有,有不碍空。然不碍有之空,能融万像。不绝空之有,能成一切。是故万像宛然,彼此无碍也。”[4]在法藏这里,圆融自在的精神贯通于华严教理的每个角落。事物无体,故虚空无碍而随理圆融;随体成事,故真理遍在而缘事会通。会通即是含摄,圆融无外中道。唐代华严宗构造出这样一种境界:空幻相依,万象宛然,和谐相处,互摄交融。
华严境界是一种无穷无尽、幽微难测的世界图景。这为中国美学理论建构提供了思想支持,中国艺术的审美意境也常具有华严境界的意味。唐人徐安贞题画:“画得襄阳郡,依然见昔游。岘山思驻马,汉水忆回舟。丹壑常含霁,青林不换秋。图书空咫尺,千里意悠悠。”[21]咫尺之间,便有千里之意。美感无穷,令人回味。
学界普遍认为,“境界”作为一个成熟的美学概念是唐代王昌龄提出的。对于审美境界的阐释五花八门,但多数学者都指出境界具有虚实相生、有无一际等特征,这些特征并不只是道禅哲学的影响,唐代华严宗也有其历史贡献。宋人严羽论诗:
“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22]严羽称赞盛唐诗歌之妙,称其“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是指审美意境的无穷性,同样让人体验到盛唐诗歌的余味。严羽的概括是准确的,盛唐时代正是华严宗的繁荣时期。可见,无穷无尽的华严境界已经渗入当时的诗学领域,且在王昌龄、司空图那里结出了智慧之果。
唐五代以来的艺术也时常流露出无穷无尽的华严意趣。当时绘画常以重屏入画,这种重屏入画现象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屏风等物象的设置固然不能排除画家基于物质材料的运用和艺术媒介的特殊性等方面的考虑,但是,这种重屏入画现象背后的审美观念也颇值得玩味。重屏入画,最直接的视觉效果是促成审美时空的交织,而这种时空交织的效果在中国艺术中具有特殊的意味。对此,可结合唐代华严宗的境界理论做出阐释。例如,五代画家周文矩有《重屏会棋图》(现藏故宫博物院),该图卷中央为一扇巨型屏风,屏风上面绘制的是白居易《偶眠》诗意,这是第一重屏。就在这扇屏风之中,还画有一扇山水屏风,这是第二重屏。这种屏中有屏、大屏套小屏的构图,被称为重屏。很明显,画家在这里着意创造一个多重时空交织的审美世界,现实与往事、短暂与永恒、屏中人与屏外人彼此互摄,相映成趣,令人回味无穷。这幅画体现的就是华严境界的意趣。
法藏谈到的“圆音”也同样体现出盛唐时代对至高音乐境界的追求。圆音不是世俗之乐,它是合乎华严教理的音乐审美形态。华严宗以圆融无碍为其立论宗旨,圆音即圆融之音,它是华严宗的最高音乐境界。圆音并不意味声音的数量众多,众声喧哗可能是出于杂乱的排列,显然不具备圆融的精神。何谓圆音?“镕融无碍名作圆音。若彼一音不即一切,但是一音非是梵音。以彼一音即多音故,融通无碍名一梵音。若此等音,不即无性同真际者,是所执故非如来音。以彼音等离作故,无性故如响故,所以法螺恒震妙音常寂故也。”[23]法藏认为,圆音不等于一音,只有一音含摄一切音而圆融无碍,才能称作梵音,这就是圆音。圆音位居中国佛教音乐的极高境界,它寂寥无声而韵味具足,无声无响而又振聋发聩,圆音是中国佛教的真如之音,华严境界的无穷无尽在圆音这一审美境界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圆音空无所有,却遍布微尘世界,它无知无识,却智慧充满。圆音超越具体声音的大/小、虚/实、真/假、有/无等分别,极微而又至妙。圆音同样也具足“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华严教理。甚至可以说,圆音是佛教即声以显教、会事以明理的妙具。
一音挥奏,呈现重重无尽之境。耳闻之声难免有漏,不能体证声音的大全微妙,难以领略其圆融周遍的妙意。圆音不以耳闻,而应开启圆融之心,需听之以心:“此一音上,由机有大小,令此法门亦复不一。一切诸声,各各如是。乃为如来无碍圆音法轮常转尔。”[4]按照法藏的规定,圆音遍在一切处所,虽然人的天机有深浅之分,觉悟程度有高低之别,但只要心境清虚,听众感受到的声音必然圆满自足,都是圆音的真实显现。
唐代艺术具有圆融无碍、卷舒自在的审美风韵,化俗为雅,多姿多彩,而华严宗正是促成唐代审美风韵的重要原因之一。与华严宗哲学最为契合的是盛唐审美境界。盛唐艺术美得繁富,美得绝伦,又美得那般世俗。这种繁富而世俗的美却又如意流转,温婉尔雅,广大和谐。这种美在当时的诗文、书画、雕塑、工艺等审美领域都有突出的体现。
这是一种属于盛唐时代的美,美的时代性与社会性在此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展现。作为一种宗教哲学,深刻的华严教理之中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智慧,华严宗境界概念更是对中国美学意境理论的生成产生过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唐]澄观.华严法界玄镜[M]//大正藏:第四十五卷.高楠顺次郎,等,辑.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昭和二年(1927).
[2][唐]法藏.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M]//大正藏:第四十五卷.高楠顺次郎,等,辑.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昭和二年(1927).
[3][后秦]僧肇.肇论[M]//大正藏:第四十五卷.高楠顺次郎,等,辑.东 京:大 正 一 切 经 刊 行 会,昭 和 二 年(1927).
[4][唐]法藏.华严经义海百门[M]//大正藏:第四十五卷.高楠顺次郎,等,辑.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昭和二年(1927).
[5][唐]法藏.华严经探玄记[M]//大正藏:第三十五卷.高楠顺次郎,等,辑.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十五年(1926).
[6][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第二十二[M].顾学颉,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79.
[7][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第八[M].顾学颉,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79.
[8][唐]王维.田园乐七首其六[M]//王右承集笺注:卷之十四.[清]赵殿成,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
[9][唐]杜甫.杜诗详注:卷之十八[M].[清]仇兆鳖,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