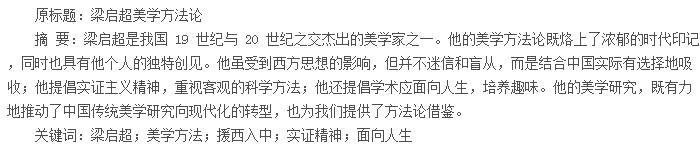
梁启超是我国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最为杰出的美学家之一,他的美学思想既深刻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色,也体现了他个人对社会的思考。他在接受西方思想的同时也融合了自己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构建。因此,他的美学思想既呈现出科学的实证精神,也洋溢着关注人生的热情;既蕴含着新的美学意识的萌芽,也体现了新的美学范式的创建,对后来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援西入中
尽管梁启超接受了西方的现代理论和学说,并且借鉴康德的思想、柏格森的生命意志说、立普斯的移情说、西方的悲剧论以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等重要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但是,在对西方理论的消化、吸收过程中,梁启超却不盲从、不迷信,而是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观点,形成了自己独到的方法。
首先,梁启超在分析中国文论的过程中,始终将“情感”放在首要位置,他非常重视情感对于文学艺术的意义。在梁启超看来,“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而且情感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
因此,梁启超总是以情感作为衡量艺术作品的重要准则,这与康德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康德是西方第一位明确将人的心理要素分为知、情、意三个部分并给予情感以本体论地位的人。从康德开始,美学才开始走向情感,他对梁启超的哲学思想和美学建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梁启超开始注意“情感的陶养”,并将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
其次,梁启超吸纳了柏格森生命哲学中的生命力理念,形成了自己的审美之“力”。梁启超曾在《欧游心影录》中写到:“直觉的创化论,由法国的柏格森首创,德国倭铿所说,也大同小异。柏格森拿科学上进化原则做立脚点,说宇宙一切现象,都是意识流转所构成。方生已灭,方灭已生,生灭相衔,便成进化。
这些生灭,都是人类自由意志发动的结果,所以人类日日创造,日日进化,这‘意识流转’就唤做‘精神生活’,是要从反省直觉得来的。我们既知道变化流转就是世界实相,又知道变化流转的权操之在我,自然可以得个‘大无畏’,一味努力前进便了。这些见地,能够把种种怀疑失望,一扫而空,给人类一服‘丈夫再造散’。”
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以小说为对象,将“力”分为四种:“熏”、“浸”、“刺”和“提”,认为正是这四种“力”的作用最后才可以做到“支配人道”。而“熏”、“浸”、“刺”与“提”又有所不同,“熏”即为熏染,“浸”即为浸透,“刺”即为刺激,这三种“力”都是从外部去影响别人,是被动的,而“提”则不然,接受者从起初的被动接受转化为积极能动的审美主体,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与审美对象融合成为一体,从而产生全新的审美体验。
此外,梁启超还受到西方“移情说”理论的影响,并且将之改造使它更加丰富和发展起来。立普斯的“移情说”是西方现代心理美学影响较大的一种学说,在立普斯看来,“审美的快感是对于一种对象的欣赏,这对象就其为欣赏的对象来说,却不是一个对象而是我自己。或则换个方式说,它是对于自我的欣赏,这个自我就其受到审美的欣赏来说,却不是我自己而是客观的自我”。而“这一切都包含在移情作用的概念里,组成这个概念的真正意义”。简而言之,就是主体在观照对象时,将自己的情感和情趣渗透到对象中,使对象呈现出主体的情感色彩。因此,美感的产生不是由对象本身是否美来决定的,而是由主体的感知和投射来决定的。西方的“移情说”强调主体对对象的改造,“移情”效果的实现必须通过对对象的作用来实现。而梁启超改造之后的理论与“移情说”有某种相同之处,他也强调主体在审美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但是梁启超的理论更希望通过对象来改造主体,通过特定环境中的情感共鸣去影响主体的精神世界。在此,梁启超对西方的“移情”说加以改造,并且将其纳入到自己的美学思想中加以融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
梁启超还吸收了西方的悲剧思想。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认为,小说“最受欢迎者,则必其可惊、可愕、可悲、可感,读之而生出无量噩梦,抹出无量眼泪者也”。在《情圣杜甫》中,梁启超写杜甫中年以后,多灾多难,家庭变故,历经很多的辛酸,那时写出来的作品“真情愈发得透”。因此,梁启超认为杜甫的作品“自然是刺激性极强”,而且透露着“真美”。他还说,“美的作用,不外令自己或别人起快感。
痛楚的刺激,也是快感之一。例如肤痒的人,用手抓到出血,越抓越畅快”。在此,梁启超将痛感与快感联系起来,就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说的,悲剧是“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在《屈原研究》中梁启超的这种观点表现得更加明显,他认为屈原本就是一个悲剧人物,正是因为屈原关心民生、独立不羁的性格使其无法面对社会的黑暗,最后他才自投汨罗,屈原的悲剧精神使其作品洋溢着悲剧的美感。由此梁启超受西方悲剧思想的影响可见一斑。
受欧洲近代文坛将文学二分为浪漫派和写实派的影响,梁启超也用这种分法来分析中国古代文学。虽然在古代并没有出现将作品划分出浪漫派和写实派这样的做法,而且各大家的作品路数也不相同,但是梁启超还是看到“很有些分带两派倾向的”作品。然而,梁启超并不完全按照西方分法去简单地区分这两派。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他就根据中国古代作品的所谓具体情况将之分为五种“表情法”,即“奔迸的表情法”、“回荡的表情法”、“蕴藉的表情法”、“浪漫派的表情法”和“写实派的表情法”。
虽然梁启超在对西方思想的吸纳上存在简单化、生硬化的现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时中国文化转型的过渡时期,对纷至沓来的各种西方学说和思想,因初次接触而造成生吞活剥的现象也在所难免,但正是由于早期梁启超等人的勇于尝试和推动,开风气之先,才奠定了后人的美学研究基础。
二、实证精神
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中,梁启超提出了对文献的研究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他强调,不仅要用谨严的态度仔细选择,把前人的误解修正,看出真面目,同时还要将同类或有关系的事物网罗起来进行比较,注意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样才可以通学。这种科学的实证精神也被运用到他的美学研究中,他或者从作家作品入手进行考察,或者列举大量的史料,或者在中外比较中得出差异,用科学的态度进行梳理,有理有据。
梁启超在对古代文学进行阐释的过程中,首先注重分析作品的产生缘起,考察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作家个人的成长环境,“先要把他所生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略叙梗概,看出他整个的人格”,再从作者的生平去解读作品,对作品的整体进行把握,这样才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作品的时代背景和创作动机。
其次,梁启超为印证自己的观点,总是会列举出大量的论据。在他看来,提出问题后就应该以问题为中心去搜集材料,而且要勤于收集,这样在以后的阐释过程中,才能有理有据。他还强调要多做笔记,多做笔记所要的资料自然就会聚拢起来,以供提出新见解。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里为了举例论证这些情感,梁启超从《诗经》、《楚辞》起,连乐府歌谣、古近体诗、填词、曲本乃至骈体文都包括在内,范围不可谓不大。而且梁启超“所征引的,都是极普通脍炙人口的作品,绝不搜求隐僻”,所举出的例子都最能代表这些作品的基本精神。
在对翻译佛典过程的阐释中,梁启超也是以史料为依据。他所依据的史书有《尚书》、《史记》、《后汉书》等,还有大量的佛典,所取范围也非常广泛。但是,他并不是完全迷信史料,而是有取舍地对史料进行鉴别。对史料的鉴别,梁启超还总结出了一个大原则:“鉴别史料之误者或伪者,其最直捷之法,则为举出一极有力之反证”。但不是所有史料都能够找到反证资料去推翻,对于这种史料,梁启超认为,“第一步,只宜消极地发表怀疑态度,以免真相之蔽;第二步,遇有旁生的触发,则不妨换一个方向从事研究,立假说以待后来之再审定”。
同时,梁启超也注重将其他民族的文化与中原文化进行比较,指出其他民族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以中国古代艺术作品为例,他认为《三百篇》以温柔敦厚为主,完全表现了诸夏民族的特性,而《楚辞》是后来南方新加入的一种新民族的作品,它们已经被诸夏同化,用诸夏的文化手法来写情感,掺入他们固有思想中那种半神秘的色彩,因此文学界添了一种新境界。到了“五胡乱华”的时候,西北方又有好几个民族加入进来,渐渐成了中华民族的新分子“,他们民族的特性,自然也有一部分溶化在诸夏民族性的里头,不知不觉间,便令我们的文学顿增活气”。这也是文学史上的关键。温柔敦厚与亢爽真率相结合,使中华文化表现出不一样的面貌。
梁启超在整理中国艺术时,也非常重视与西方艺术相互参证。例如在《书法指导》中,对于书法之美,梁启超就从线条、光线、力道与个性方面进行阐释。在阐释过程中,梁启超就将西方美术与之相较,认为中国的书法与西洋的美术相类,因此中国的书法就是一种特别的美术。同时梁启超也从书法内部进行梳理,针对临碑还是临帖、六朝碑和唐碑哪一种更好等问题进行了详尽而细致的论述。梁启超对书法有很高的趣味,有很多的收藏,因此对中国书法可谓烂熟于心,如数家珍,所以其分析极有条理且全面,让人不得不叹服。
梁启超将科学的实证主义精神带入美学研究之中,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作家作品的重视上,同时还表现在他对中国美学与其他民族、西方文化的区别比较上。这种方法不仅对当时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当代的美学方法论研究也有深远影响。
因此他“既是‘文献学’又是‘中国文献学’概念的最早提出者”。
三、面向人生
梁启超特别注重面向人生的学术和艺术追求。
他提倡“内省及躬行的方法”,也就是他所谓的“德性学”研究方法。梁启超从儒家哲学中汲取了这种方法,并将它运用于他的美学研究中。
在梁启超看来,欧洲哲学更注重科学方法,但由于其不太贴近人生,所以只能用于研究人生以外的问题。他说“西方哲人精神萃集处之宇宙原理、物理公例等等,倒都不视为首要”,或者是归于宗教“,是纯以客观的上帝来解决人生,终竟离题尚远”,最终也没有落实到人生的实处。他认为,最后直到柏格森等人出现才算是有了改变,“但是果真拿来与我们儒家相比,我可说仍然幼稚”。
在这篇《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中,梁启超将中国儒学与西洋哲学进行了对比,他几乎是完全站在国学这边,认为中国的儒家哲学始终讲究知行合一,知识的获得与扩充不仅要从知识方法上求得,还应该从自身的实践和躬行中实现,因此儒家不仅从纯学术的角度去研究,还提倡将学术与人生联系起来,这是与西方人不一样的地方。
在梁启超看来,儒家的观点是宇宙人生是不可分的,宇宙的进化在于人类的努力,因为宇宙的不完满,才使人们不断努力向前创造,因此人类每天进步,那么宇宙也会不断进化,而这些也是人类自由意识发展的原因,而这变化流转的主体在于我自身。因此,生活的乐趣就在于不断发展和创造,不要为了它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就失去做这件事的乐趣,因为你所做的都是在推动宇宙的发展。其次,由于儒家不承认人是可以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的,个人的人格和整个社会的人格息息相关,所以,想要让自己的人格积极向上,也就要求整个社会的人格积极向上,反之亦然。因此,不管做什么,都要想到自己是和整个社会相关联的。从而,梁启超提出了“知不可而为”与“为而不有”主义,主张去功利化,主张趣味为本,主张“生活的艺术化”。“生活的艺术化”就是“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成艺术的、情感的”。
这切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维新变法失败,民国又处于动荡之中,梁启超一生起伏,对国事时局的关注和参与从未间断,和处在这个动荡变革时期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他当然更看重“学以致用”的经世之道。五四以来的一批学者、知识分子,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胡适、陈独秀、茅盾、徐复观……无不受到这股潮流的影响。而在梁启超那里,他将对人生和生活的思考融入到学术中,主张学术需要落实到人生、人生要活得艺术化这样的辩证观点。一方面,他提出对现实功利人生的批判,对那种只重眼前利益而不顾艺术生活的人的嘲笑;另一方面,他也反对将学术与人生社会脱离。他曾在《外交欤内政欤》中说:“我的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浓些。我常常梦想能够在稍为清明点子的政治之下,容我专作学者生涯。但又常常感觉,我若不管政治,便是我逃避责任。”
由此可见,“生活的艺术化”也是他改造现实、关注人生的一种方式。
那么如何实现“生活的艺术化”呢?梁启超认为,“趣味”是最重要的实现方法。“趣味”,在梁启超看来是生活的基本价值和根本动力,人们只有生活在“趣味”之中才有价值,同时,“趣味是梁启超美学思想中最有特色的核心理论范畴”。只有趣味才可以激发生活的热情。人只有在生活中、在实践中才可以获得趣味,“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因此,他提出文学、音乐和美术是诱发趣味并且使之不会迟钝的三种利器。以美术为例,对美术作品欣赏之后,对于它们的记忆会留存在脑海中,留存的时间越长,趣味也会随之越长久;其次,我们看画的时候,也像是在看自己的心情,因此画中人快乐,自己也像是增加了快乐……最后,美术可以将我们平常想构建的理想都实现了,于是在看画的时候,也像是进入了一个超越的自由世界。
在这样的基础上,梁启超提倡“趣味教育”,倡导“趣味主义”人生观,这既是对人生的趣味态度的培养,更是对好的纯正的趣味态度的培养。在梁启超看来,趣味教育的积极意义就是唤起学生对生活、学问的兴趣,所以教育家应该让学生懂得为学或生活的目的在于其本身,而不是谋求利益。梁启超的“趣味教育”理论对中国现代美育思想也影响深远。而这样的“趣味”理论、“生活的艺术化”,集中体现了梁启超面向人生的学术态度和美学研究方法,也启发我们将美学研究落到人生社会的实处。
总而言之,梁启超借鉴西方视角,将西方的思想和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相互阐释,援西入中,在借鉴的基础上创新,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思想,并能求新求变、融会贯通。同时,他重视科学的实证方法,结合史料、多重比较,使学术研究更有说服力,也促进了中国传统美学向科学化、系统化方向的发展。他还提倡面向人生的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以现实和人生为出发点,提倡为人生的学术,和“生活的艺术化”,将学术与人生有机地统一起来,让美学研究落到人生的实处。这种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襟也给我们当今的美学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和启迪。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委员会.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8 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45.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3.
[5]彭树欣.梁启超———“文献学”的最早提出者和阐释者[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7,(5):66- 76.
[6]金雅.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