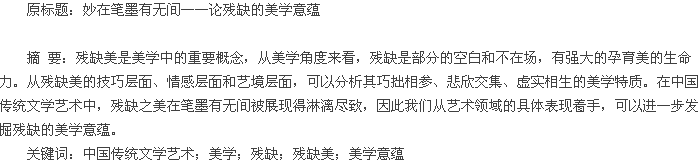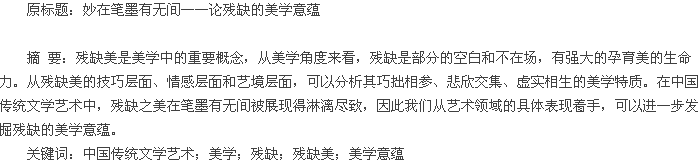
残缺是部分的空白和不在场,是一种“未完成”或“已失去”的状态,是一种不稳定、不清晰、不完全、不完整的形式,这种形式恰恰因为隐藏或丢失了一部分,无中生有,使那个潜在的不存在的或未视觉化的部分反而有更强大的孕育美的生命力,从而具备更鲜活的审美活力和审美张力,具有无限的美学意蕴。艺术是人类美学思想最集中、最直接的体现,要探讨残缺美这一美学框架内的问题,必须从艺术领域内的具体分析入手,找出残缺之“美”在艺术中的具体表现。
一、巧拙相参——残缺美的技巧层面
江西诗派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说:“宁拙勿巧,宁朴勿华,宁粗勿弱,宁僻勿俗,诗文皆然。”在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形式层面,有以朴拙来拗圆熟、以险僻以纠俗烂的艺术追求,中国文学史上文风、诗风的转捩往往因应这种艺术追求的变化,而从艺术效果来说,恰恰是以拙参巧、以拙显巧、以拙衬巧,即老子所言“大巧若拙”,是真正的巧夺天工,而不是处处落于痕迹,时时显出匠气。
中国从最初就并不排斥丑,老树、怪石、病梅这些所谓丑怪之物,在艺术家眼中却有别样的审美价值,深得艺术家和收藏家的追捧。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充满野趣和逸情,残缺与美的辩证表现,同时彰显出纷层叠出的艺术个性。
以绘画为例,绘画的取材大有讲究,什么东西值得入画?是美轮美奂、完美无瑕,还是与众不同,充满活力,与绘画原初的材料大有关联。“瑞士艺术史家乌而夫林在他那部研究艺术风格问题的名着《艺术风格学》中提出过一对概念:“入画”与“不入画”。在他看来,整洁美丽的东西,比如一间装潢一新、纤尘不染的房间是“不入画”的,因为缺乏生气。而不是那么美丽整洁的东西,比如斑驳的墙壁,有裂缝的地板、缺损了一块的水壶等等,才是“入画”的,因为正是那些不完美的地方颤动着“生命之光”。
唐代诗人李白曾说“丹青能令丑者妍”,意思是说丑怪的事物经过画家的神笔挥就,可以使形象获得审美的意义,即化丑为美。生活中枯树、丑石都给人一种病态、消亡甚至不祥的意味。但在艺术家眼中,却是珍品,通过艺术创造,能挖掘出它们的情趣、神韵和生机,赋予其新的精神内涵和生命力、表现力。丑陋的对象经过艺术创造与提炼,获得了美学的价值,拓宽了绘画思路与审美领域。明代唐志契在《绘事微言》中说:“写枯树最难苍古,然画中最不可少,即茂林盛夏,亦须用之,诀云:‘画无枯树,则不疏通’,此之谓也。”苏轼就画有一幅《枯木怪石图》流传于世,怪石盘踞左下角,盘旋如涡,石右之枯木,屈曲盘折,气势雄强,米芾《画史》说:“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黄庭坚在《题子瞻枯木》中说:“折冲儒墨阵堂堂,书人颜扬鸿雁行。胸中原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风霜。”《题东坡竹石》中又说:“风枝雨叶瘦士竹,龙蹲虎踞苍藓石,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笔法看似草率,实为写意为之,飘逸间吐露胸臆,恰是苏轼本人人格魅力的折射。这又不禁让人想起《庄子·人间世》说:“匠石家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其大蔽数千牛,挈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观者如市,匠伯不顾,遂行不辍。弟子厌观之,走及匠石,曰:‘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视,行不辍,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樠,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枯木并不枝繁叶茂,怪石不是玲珑圆润,在角落里却别具自然之趣,没有功利,没有欲求,无用之用,反而更具欣赏价值,而不是作为工具被占用。也因为有了更长久的生命,“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另外,作为四君子的梅花,也深得画家倾心,它们的枝干那样疏影横斜,却更显苍劲古雅,千姿百态,变化多端,“岩坳深雪病枝蟠,骨傲天生耐得寒。得意自开花一树,不曾开与世人看”“砚水生冰墨半干,画梅须画晚来香。树无丑态香沾袖,不爱花人莫与看”,都是说枝干虽丑,却自有高洁的品格。园林盆景中的梅花有些还经过了人工的压弯处理,就是为了追求特有的姿态美。
美术创作中又分无意或有意导致的残缺与瑕疵。而儿童画,由于创作者的技巧还不成熟,对于事物的描摹可能不尽完善,与现实事物有一定的差距,但却往往显得纯洁率真而且充满意趣,稚拙、天真、朴素这些美学因素使这些儿童画体现了一颗颗童心的真挚与强烈的艺术激情。也许他们会把天空绘成绿色,把小鸟画有 4 只腿,给奶奶添上胡子,也许反常、夸张、颠倒黑白、无中生有,但往往是个充满想象力的、自由的童话王国。
而成人常常被各种规则、各种技巧和技术束缚,不能自由发挥,有过多的修饰和做作的痕迹,反而失却了天性和本真的美。当然,成人如果具备“童心”,也是可以真率的创作出充满童心童趣,而不带功利色彩的佳作。
二、悲欣交集——残缺美的情感层面
黑格尔曾说:“这不死之鸟,终古地为自己预备下火葬的中柴堆,而在柴堆上焚死它自己;但是从那劫灰余烬当中,又有新鲜活泼的新生命产生出来。”无论是浴火的凤凰,还是扑火的飞蛾,在冲向烈火与光明的一刹那,视死如归,无怨无悔。它们的残缺是彻底的,悲情的,毁灭性的,但美也是极致的,因为可以重生或完成追逐。在艺术中,残缺美融化在各种艺术中。是凤凰,也是飞蛾,让我们扼腕叹息,让我们悲欣交集。
中国的文学中对于残缺形象的塑造最经典的应首推《庄子》。《庄子》中的一系列畸人群像,身负残疾,没有健康完整的体魄,却有高尚理想的人格,或有特殊的才能去弥补自身身体上的残缺。他们并不脆弱,超越形骸之外,有一颗至善至美的心。但他们总归与平常人不一样,样子也有点怪异,庄子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群人作为他说道的对象呢?正因为他们起作用的方式也是怪异的,反而更有效果。研究庄学的美国学者爱莲心把这群残疾人叫做“怪物”,而“怪物”却能达到必要的效果。原因在于:“打破我们意识的固定性,要求在一个突然和有时候是不愉快的震惊。在我们恰当的理解达到以后,更高的认识是:怪物(在我们的意义上)是最大的赐福,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就既不能在心灵的方向上有所进步,也不能有这种进步的经常性的提示与体现……对于我们之中的‘怪物’的完全接受,意味着在我们经验层面的怪物范畴的消失和哲学层面的更高水平的意识的取得……怪物之运用有两种哲学上的功能。首先,怪物是标准(norm)的一个活生生的反例,不管这个标准是文化的或者是生物的,或者是两者兼之的。在特定的哲学路线上,怪物变成了哲学家。怪物型的哲学家是一种哲学原则的化身,这种原则是常人害怕的和要避开的。这就是自然(spontaneity)。那么,怪物的第一个哲学意义就是以一种非常精妙的方式让我们知道:由怪物所代表的价值——自然——是一种为常规社会所害怕和避开的价值……正如在西方文学中,疯子或愚人的话是受到尊敬的,在庄子里,怪物是受到保护的。因为他们是不同的,他们可以说一些普通人不能说的话而被处分。他们有顺其自然的自由,并且当他们是可怕的时候,这是一种可怕的哲学特质。反过来说,但我们有勇气成为怪物或者同意怪物的观点的时候,我们也能顺其自然了。以顺其自然的方式行事,我们就会非常接近能够理解的真理。”爱莲心以深入浅出的道理说明了庄子采用怪物这种形象的智慧所在,化腐朽为神奇。
在中国的古典诗词中也有很多残缺的意象,却异常得美,马致远的散曲名篇《天净沙·秋思》就运用“枯藤”“老树”“昏鸦”“瘦马”这一连串残缺的意象来表现断肠人独立夕阳下莫名的怅惘。残缺意象最典型的有残阳、缺月、残荷、落花,诗人往往将感时伤世、感物伤怀融入物哀的情怀中,将伤春悲秋与人生的体验相结合,对残缺意象演绎得美轮美奂、如泣如诉、长歌当哭。
黄昏意象被称述为落日、残阳、薄暮、夕阳、余晖等,最让人消魂,也最凄美。钱钟书先生说:“盖死别生离,伤逝怀远,皆于昏黄时分,触绪纷来,所谓‘最难消遣。’”再如诗词中有“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怕黄昏忽地又黄昏,不销魂怎地又销魂”“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晚霞红,看山迷暮霭,烟暗孤松。动翩翩风袂,轻若惊鸿。心似鉴,鬓如云,弄清影,月明中。漫悲凉,岁冉冉,蕣华潜改衰容”;李白“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境界何其雄浑;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情感何等凄清。无论是血色黄昏,还是晚霞残照表达的多为怀人、伤别、叹逝的主题,这都是人生的残缺,在黄昏这个将暗未暗的时候将悲情挥洒到极致。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荷花妖娆,亭亭玉立,碧叶连天,夏荷何等销魂。当秋风一扫,荣华殆尽,只剩残荷还在萧瑟秋风中婆娑摇曳;“留得残荷听雨声”,这是一种情怀,也是一种意境;“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尽管是残荷,却仍有淡淡的芳魂在寒塘萦绕不去,这是静谧,是神韵,是高洁,它的美在于残,在于枯,更在于它的成熟。
谈及残荷,便自然联想到落花。花开富贵,花好月圆,笑靥如花,花的盛开总是给人美好圆满的感觉,那么,花的凋谢与飘零,则让人无限感叹惋惜。“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花落逐水去,何当顺流还,还不亦复鲜”“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满月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一朝春尽红颜老去,花落人亡两不知”“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落花飞絮茫茫,古来多少愁人意”“花自飘零水自流,一处相思,两处闲愁”“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落花不语空辞树,流水无情自入池”“春欲暮,满地落花红带雨”“满院落花春寂寂,断肠芳草碧”“更被春风送惆怅,落花飞絮雨翩翩”“高阁客竟去,小园花乱飞。参差连曲陌,迢递送斜晖。肠断未忍扫,眼穿仍欲归。芳心向春尽,所得是沾衣”,等等。
最脍炙人口的应是曹雪芹《红楼梦》中《葬花吟》:“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粘扑绣帘。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着处,手把花锄出绣帘,忍踏落花来复去?……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愁煞葬花人,独把花锄偷洒泪,洒上空枝见血痕。……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美丽的爱情却无果而终,美梦惊醒以后无路可走,既然风刀霜剑严相逼,还不如质本洁来还洁去。这是黛玉写给自己的一阙凄美的挽歌。一个纯洁柔弱的女子,扛着花锄,望着落花流水,黯然落泪的形象跃然纸上,是何等哀婉动人,荡气回肠。虽然感到凄楚,却美轮美奂。
中国的古典文学中不乏各种残缺美意境。例如郊寒岛瘦,贾岛的苦吟,“诗僻降古今,官卑误子孙。栏寒月色,人哭苦吟魂”。一味苦吟是贾岛做诗的最大特色,虽然苦,但是仍然不乏佳作,如:“长江人钓月,旷野火烧风”“乌归沙有迹,帆过浪无痕”“棹穿波底月,船压水中天”“樵人归白屋,寒日下危峰”“夕阳飘白露,树影扫青苔”,等等。皆为反复推敲而得,写得精致,有骨感,也有风格,清奇雅正。
三、虚实相生——残缺美的艺境层面
说到有意创作,不能不说中国的水墨画。水墨画的空白,是故意留白,宗白华先生评价大痴山人的画“苍苍莽莽,浑化无迹,而气韵蓬松,得山川的元气;其最不似处,最为得神。似真似梦的境界涵浑在一无形无迹,而又无往不在的虚空中”。空白的地方看似缺了什么东西,其实是别有用心的特殊的构图和章法,虚实相生,有更多的韵味,是有意味的形式,无形象的意味,美不在有形处,而在无形处。空体现了禅的精神,中国画以淡为宗,而空为淡的极致,也就是佛法相宗所说的“极迥色、极略色”(明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和禅宗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最能说明空的精髓,不是停留在物的表象上,而是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去把握生命的意义和精神,从而达到形神相融、物我两忘、澄怀观道、明心见性,在拈花微笑里领悟色相中微妙至深的禅境。《老子》四十章云:“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有无,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虚而万景入,空白处能让人联想到雪、水、天空、云等。无中生有,虚实相生。留白,使主体更突出、更清晰,也使空白本身有了更多的活力和灵气,同时扩大了画面的意境,可谓形式的延续。它留有余地,是意到笔不到,让读者有所想象,使艺术家突破了时空的束缚,实现超越现实、构造出新的形象意义组成的世界。空白处常为活眼,所谓活眼,即画中之虚也,这个活即气眼,具有解结、提神妙用,虚中有气,气韵生动。此气乃天地万物的源泉,生命的流动之处。如果一幅画,每处都被填满,不免有单一、沉闷、堵塞的感觉,但是留出空白,就使画面有了节奏感和层次感,意味深长,海阔天空。柳宗元的《江雪》一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试想这是一幅画面,一叶扁舟之上一个独自垂钓的老人,万顷寒波,轻烟淡霭,皆是空白,这种意境让人感到荒寒、洒落,同时却有一种生命的情调。宗白华先生对空白之道阐释得非常精辟:“中国画很重视空白。如马远就因常常只画一个角落而得名‘马一角’,剩下的空白并不填实,是海,是天空,却并不感到空。空白处更有意味。中国书家也讲究布白,要求‘计白当黑’。中国戏曲舞台上也利用虚空,如‘刁窗’,不用真窗,而用手势配合音乐的节奏来表演,既真实又优美。中国园林建筑更是注重布置空间、处理空间。这些都说明,以虚带实,以实带虚,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结合,这是中国美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妙在笔墨有无间。
四、结语
当我们有意无意地触摸残缺的形象时,似乎被一种无形的锐器刺痛心灵深处,反思这种心灵阵痛,我们会若有所悟,或许我们的灵魂会打开另一扇窗口,它展示的却不是月白风清、柳岸莺啼,而是残荷滞水、瞽目残臂,给我们的心灵一种震颤,随后是窥见美学另一张脸的无比愉悦,这种审美愉悦是经过深沉的反思得来的,超越了一切肤浅、表面的情感;它是一种洞见,来自于哲人的睿智与深沉博大的审美心胸,是佛祖的拈花一笑,是楚狂的引吭高歌。让我们一同来品味与享受其人生和美学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高小康.丑的魅力[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60.
[2] 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64.
[3] 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144.
[4] 爱莲心.向往心灵转化的庄子:内篇分析[M].周炽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57-59.
[5] 宗白华.美学与意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