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勒对康德的道德美学思想重构
时间:2014-07-18 来源:未知 作者:小韩 本文字数:8602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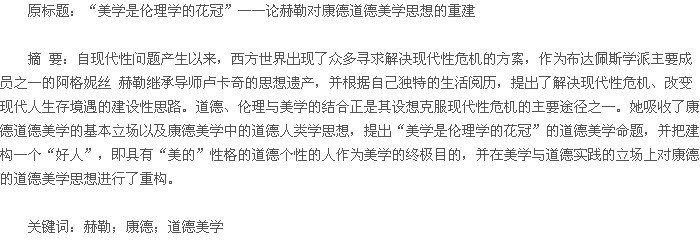
自现代性问题产生以来,西方世界出现了众多寻求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方案,作为布达佩斯学派主要成员之一的阿格妮丝 赫勒继承导师卢卡奇的思想遗产,并根据自己独特的生活阅历,提出了解决现代性危机、改变现代人生存境遇的建设性思路。道德、伦理与美学的结合正是其设想克服现代性危机的主要途径之一。应该说,赫勒以美学切入现代性命运的视角及探索途径均来自于卢卡奇的视域。衣俊卿教授曾这样评价卢卡奇,“卢卡奇对于哲学和艺术(审美)的关注毫无疑问根植于这种文化守望和家园意识。他所关注的并不是作为给定知识形态的哲学和艺术,而是作为文化批判的哲学和艺术”中译者序19。无疑,赫勒追随老师的思想轨迹,试图通过审美、通过艺术作品,来寻求解决现代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戴维德 罗伯茨(David Roberts)曾对赫勒的《美的概念》一书进行了分析,认为赫勒正在追随卢卡奇关于美学切入文化命运的构想,完成卢卡奇生前没有完成的任务。赫勒指出美的概念在现代面临着无家可归的困境,即美的概念与艺术分离,但是如果不是在艺术中,那么无家可归的美的概念到哪里去寻找它的位置呢?卢卡奇曾经试图在伦理学中寻找答案,但没有完成。而对于这个“空位”,赫勒将此与康德联系起来。
赫勒在她的论着中经常提到康德,并给予极高的评价,“对世界知识有着充足的个人体验、有道德责任感、严肃、有怀疑精神、幽默、理解人类的愚蠢、有实践智慧——所有这些品质都在哥尼斯堡这个矮小的人身上体现出来”。赫勒从19岁时为了参加卢卡奇的讨论会而翻译《判断力批判》以来,就极为喜爱这本书,经常翻阅,而且每次重读都能发现一些新的东西,这些东西深深地吸引着赫勒。在《碎片化的历史哲学》中赫勒认为康德是对世界认知最优秀的领航者,并称康德为她的“维吉尔”。基于对康德美学思想的赞同,赫勒吸收了康德道德美学的基本立场以及康德美学中的道德人类学思想,把建构一个“好人”,即具有“美的”性格的道德个性的人作为美学的终极目的,并在美学与道德实践的立场上对康德的道德美学思想进行了重构。于是,赫勒在康德道德美学思想的积极内涵中找到了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方案。
一、“美学是伦理学的花冠”是对“美是道德的象征”的发展
“美作为德性的象征”是康德对道德与美的关系的思想的完美表达:道德是最终的目的,美只是道德的“象征”,只是道德理念的“类比”。康德认为,一切先天概念都需要有直观来显示,可以是图型式的也可以是象征性的。象征借助于某种类比,对理性概念进行间接演示。
比如,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用一些可经验的自然事物来象征以道德评判为基础的超验的理性概念,比如,用青松、大厦、原野、白色来象征伟岸、雄伟、热情、纯洁。古诗文中常常用梅、兰、竹、菊来象征谦谦君子,因为“它们激起的那些感觉包含有某种类似于对由道德判断所引起的心情的意识的东西”。在康德看来,只有把美作为德性或善的象征,美才能伴随着“对每个别人都来赞同的要求而使人喜欢,这时内心同时意识到自己的某种高贵化和对感官印象的愉快的单纯感受性的超升”。
这里我们看到,美作为一种普遍的审美共通感与作为普遍性规范的道德之间的关系。康德认为,人虽然是“一种动物”,但是是被赋予了理性的,理性是保证人从自然走向自由的动力。那么,如何把自由和自然统一起来?如何超越横亘在理性的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感性的自然和超感性的自由、自然界和自由界之间的巨大的鸿沟?
康德找到了判断力、审美判断力、艺术作为一种中介、一座桥梁。它“通过自然的合目的性概念而提供了自然概念和自由概念之间的中介性概念”,使得纯粹理论理性向纯粹实践理性的过渡成为可能。
康德通过对美和崇高的分析,阐述了在审美领域认识向道德、自然向自由过渡的表现。康德认为,人天生就有鉴赏判断的能力,即“评判美的能力”。他从四个方面对美作出规定:第一,在质的方面,鉴赏和美是无利害的愉悦;第二,在量的方面,美是无概念的普遍愉快;第三,在关系方面,美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第四,在模态上,美是无概念的普遍必然性愉快。分析了美之后,康德把目光转向了崇高,因为在他看来,崇高更接近于道德。康德区分了三种崇高,恐怖的崇高、高贵的崇高和华丽的崇高、或数学的崇高和力学的崇高。他仔细探讨了崇高和道德的关系:“实际上,对自然界的崇高的情感没有一种内心的与道德情感类似的情绪与之相结合,是不太能够设想的;虽然对自然的美的直接的愉快同样也以思维方式的某种自由性、即愉悦对单纯感官享受的独立性为前提,并对此加以培养,但由此所表现出来的毕竟更多的是在游戏中的自由,而不是在合法的事务之下的自由,后者是人类德性的真正性状,是理性必须对感性施加强制力的地方。”
康德对美和崇高的分析,凝结了一个命题,即“美是道德的象征”。“真正的德行只能是植根于原则之上,这些原则越是普遍,则它们也就越崇高和越高贵。这些原则不是思辨的规律而是一种感觉的意识,它就活在每个人的胸中……如果我说它就是对人性之美和价值的感觉,那么我就概括了它的全部……唯有当一个人使他自己的品性服从于如此之广博的品性的时候,我们善良的动机才能成比例地加以运用,并且会完成成其为德行美的那种高贵的形态。”
可见,最高的美乃是与善相结合、相统一的美,最高的善亦是如此。美,说到最后,“更其是一种道德美而不是什么别的”译序。
在道德与美的关系上,赫勒采取了与康德相同的立场。在康德美学中,美是一种“象征”,道德的“象征”,这预示着美的功能,也显示了美的界限。据于此,赫勒提出“美是伦理学的花冠”。
与康德类似,“花冠”在此可被理解为一种“象征”、一种“形式”,即美是形式,伦理学是内容。人们通过外在的美的形式,达到更高的道德的目的。
在赫勒看来,美学不能取代伦理学,它只是伦理学的花冠。正如赫勒所说:“人们能够粗鲁地做正确的事情,也能够优美地优雅地完成正确的事情。”
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当我们馈赠或收到一份礼物的时刻,我们如何去做,这不是“漠不关心的”。机智而适时地赠送礼物,注意不要触犯他人的情感,这不仅是一个具有道德意义的道德问题,更关乎到美的问题。它们不仅体现了“是什么”,而且关涉“怎么样”。这里有空洞的仪式,然而也有充满意义的礼仪。“它们是我们行为的形式。更进一步说,这里有‘美的’个性,也有‘崇高’的性格。”
美的或崇高的性格带给我们的不仅是道德上的满足,更有感觉或心灵的愉快。“道德判断本身就具有审美的因素,因为感觉是构成一个好的道德判断的一个条件。”我们对待他人的情感和情绪也是审美地形成的。
从美是伦理学的花冠这一立场出发,赫勒塑造了以“美的性格”为代表的道德美学的理想个性。赫勒认为,美的性格是“音乐的”,是极其简单的心灵的和谐的日常感觉。无论面前的树木和花草、天空和太阳、气味和声音是否协调,音乐式性格的人都会感到和谐和美。美的人,类似于一道和谐的风景,当然和谐的风景也不意味着侍弄较好的花园,和谐并不意味着实现某个目标或理想。相反,和谐类似于无忧无虑或跳舞或模糊的自我肯定所带来的轻松,这种模糊的自我肯定使得人心情愉快,而心情愉快才有开放性,才有自由,才有可能性。于是,赫勒把美与音乐式的和谐、自由、开放性、可能性等联系起来,“音乐式的和谐模型更适合现代人的描述”。
这一点与康德不同,康德更加欣赏崇高的性格,而赫勒尽管认同崇高的性格仍然是现代人的理想性格,但是她认为拥有崇高的个性的人容易成为忧郁的人。在赫勒看来,崇高的人正直、正义、伟大、权重,但是这种性格容易给自身带来痛苦,不能获得普通意义上的幸福。而美的性格是一种和谐的性格,这种和谐的性格能够在行动中提供一种形式的美,从而达到道德的目的。“然而对于康德,正是美而不是崇高提供了道德的象征,正如赫勒所观察到的,美不用受到审判就指向了道德律。”
美的个性提供了人与人交往的可能性,这种社会的、分享的和交往的快乐加强了人类间的共通感,实现了赫勒的“交往的共和国”,即赫勒所称的“新的道德的”世界,激进乌托邦的理想。这个“理想的交往社会”,是民主观念的实现,而且这个未来社会的道德承认并充分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最终马克思的人类的最高价值在这里体现,个体与类实现了统一,类的物理的、心理的和精神的能力的发展同时是个性和个体的物理的、心理的和精神能力的运用和发展。
二、道德审美人类学是赫勒与康德道德美学的共同目标
道德审美人类学是赫勒与康德道德美学的共同目标,他们都试图在生存与自由的关系中思考美学。康德的“美是道德的象征”,不仅是《判断力批判》的主旨,而且体现了康德一生思想体系的建构理想:审美的最终归宿是走向道德,人类通过审美会由自然走向自由。可以说,美与道德的统一是康德毕生的祈盼,从早期的《论优美感和崇高感》,到《判断力批判》再到晚年的《实用人类学》,都渗透了康德对美的、道德的人生的追求,都体现了康德对人的存在和使命的关注。在康德看来,在自然向人生成的历史长河中,人在由自然走向自由的过程中,审美只是一种过渡,人的最终目标和最高境界是道德境界,是形成文化的、道德的人。审美的最终目的服务于道德的目的,最终为实现自由的人、实现人的解放奠定基础。
康德关于鉴赏判断的四个契机都是围绕着人的自由而阐述的。第一个契机特别强调美的无利害,因为唯有“对美的鉴赏的愉悦才是一种无利害的和自由的愉悦”。第二个契机中,美是无概念地作为一个普遍愉悦的客体被设想的。第三和第四个契机,美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以及美是无概念的普遍必然性愉快,是从自由情感的普遍性方面来规定鉴赏力的。鉴赏这种主观感性的愉悦何以可能而又是普遍的呢?康德的先验哲学向我们揭示了这种可能性,即人们先天具有的共通感。它可以使我们的鉴赏愉悦超出个人的感觉和判断,扩展到全人类。在这里,“康德立足于人类学的高度,紧紧地抓住了审美过程中人类‘共同情感’这个带有本质意义的事实”,由此,人们发现通过审美愉快可以发现自己是自由的,它因而指向了人类本性当中共同的、普遍的东西。
同时,康德通过崇高与道德的关系的论述,向人们启示了自由的道德性,崇高感本身就内在于人的本性中。
但是,这种个人的愉快感、自由感如何具有普遍性呢?于是,康德在人的审美心理上寻找到了人的社会性的“共通感”,即一个共同感觉的理念。它能够在“自己的反思中(先天地)考虑到每个别人在思维中的表象方式,以便把自己的判断仿佛依凭着全部人类理性……通过我们只是从那些偶然与我们自己的评判相联系的局限性中摆脱出来,而置身于每个别人的地位”。正是这种共通感,人的审美判断才具有普遍有效性,但这种普遍有效性又是如何在人类中普遍传达的呢?康德又在人类的审美经验事实中,在艺术中寻找审美判断和审美愉快普遍传达的途径。在康德看来,人的情感以及对自由的认识要想获得普遍传达的有效性,除了具备先天的普遍的共通感外,还应该有一种经验的、现实的传达手段——艺术。正是艺术传达着人们共同的心灵的感悟。
在艺术中、在审美经验中,人意识到自己作为普遍性自由的存在,从而意识到自由的道德必然性,最终走向道德的人。由此,康德完成了道德审美人类学的最终目的:人是整个世界最高的目的。
以此为目标,赫勒的道德审美人类学是对现代性困惑和挑战的思索,同时对美的理想的社会构成的新现代解读成为驱使赫勒道德人类学思考的动力。赫勒试图在古代理论的生存智慧中找到现代价值生长的契合点。赫勒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中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文化、艺术、政治等状况进行了考察。在她看来,美的理想是文艺复兴日常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时,只要城市共和国能够通过形成道德习俗和规范人类行为,美就不需要成为一种理想的抽象表达。但是,随着城市共和国的衰落,产生了一种多样化和个体化的需要,人们的道德、伦理、美与自由的观念呈现出与传统社会不同的特点。她承认,人的类存在展现的每一时刻都是个体、阶级、民族和种族异化的时刻,但是文艺复兴确实缩小了类的发展与个体潜力的差异,而且文艺复兴时期个人主义也不像现代自我中心主义那样带有病态的特点。
于是,赫勒试图从道德审美人类学的视角对现代价值、自由进行重构,建立了适应现代生活的个性伦理学。在《个性伦理学》中,赫勒对罗莎 卢森堡个性伦理的简单描述体现了她对崇高的看法。卢森堡是道德崇高的典型,但其是一种悲剧性的崇高,在赫勒看来,苏格拉底、浮士德、卢森堡都是悲剧价值的典范,这里她暗示了一种对悲剧价值的间接的强调。尽管她提出美的个性是理想的性格,但她对崇高的性格的分析也展现了她对崇高的热爱,只不过崇高的个性不会获得普通大众意义上的幸福,会过痛苦的一生。但她还是含蓄地提出了一种悲剧的视角,价值概念本身应该显示出与悲剧命运的一致性,这是一种个人的存在性选择。康斯坦丁诺认为,“正是赫勒的悲剧价值视角——与后现代构成主义的悲剧立场或怀旧情绪不同——决定了她的道德人类学,在她看来,崇高的美的性格不是悲剧性的”。
在赫勒对美与道德的关系的论述中、在对美与崇高的生存选择中,我们可以看出,赫勒通过外在的美的形式,建立了以自由为目的的道德美学个性。她对美的性格的阐述是同自由、道德、价值、生存联系在一起的,她吸取了古代的智慧,认为美的性格就是和谐的性格,而和谐的性格是“许多种或者甚至说所有种不同的开放性和自由的并存”。同时,“自由是美的一个有机的因素,但是作为自由的选择,它也是一个道德事件”。康斯坦丁诺极为赞赏赫勒的审美人类学建构,“比较而言,赫勒对道德承诺的美学的强调,最重要的是,她根据自由的和谐的协调来理解美,暗示了对现代性的宇宙视域的重新发现。通过把和谐设想成为完美的存在的花冠,赫勒对个性伦理学进行宇宙论的重塑”。
可以说,赫勒的道德美学是基于对人的存在状况的认识、对现代日常生活危机的认识,她试图在日常生活中解决生活和自由的问题。正如她自己所言:“我不用普遍的箴言开始我的讨论;相反,我选择跟随正派的人的生活方式。正派的人,同我们其他人一样,在日常生活中开始他们的生活。更确切地说,他们首先在基本的日常决定中区分正确和错误。”
由于对现代性的否定,道德人类学把自己的命运指向了生活世界的人文主义的社会可能性,在那里,能够产生出个体真理与自由的美,那里可以作为真实存在的预设。康斯坦丁诺认为,赫勒的道德美学应该被视为一种试图修正在康德着作中明显反思的现代性人类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赫勒已经用道德美学与敏锐的意识来调和现代性的人类学想象。
赫勒植根于日常生活的道德美学个性的形成,应该说是对康德道德美学的发展。因为对于康德先验的道德人类学来说,自由概念在感性世界的显现要想变成现实,必须有经验的参与。在赫勒看来,美向日常生活总体的扩展体现了一种文化价值。而这恰恰是超验的康德美学所不具有的。“对康德来说,艺术不是‘日常’意义上的判断对象,艺术也没有‘日常’的效用。”赫勒认为,艺术品的价值不在于它的“有用性”,而在于它具有某种唤醒人的美的力量的东西。
在日常生活中,美使人们走向了道德。赫勒的道德美学把康德超验的道德美学拉回到了人们生活的世界,保障了共通感的共和国的实现,正如罗伯茨所认为的,“如果审美判断力与理解力和理性相比,不拥有自己的领域,如果它保持着超验的地位,那么它就不能够提供通向主体间性的共同领域的桥梁。‘反思判断力的社会的、共同分享的和共有的特点以及它的快乐’打通了被赫勒称之为康德的超验的政治人类学,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共和国”。
三、赫勒道德美学对康德道德美学的超越
赫勒道德美学是在差异性范畴下选择的,更多的是个体的伦理,而康德道德美学却是在普遍性范畴下所作的选择,具有一种普遍的道德律令。
我们可以从“美是伦理学的花冠”与“美是道德的象征”这两个命题看出其中的不同:康德的道德注重的是普遍性的道德,而赫勒关注的则是个体的伦理。赫勒认为,普遍性范畴下所作的选择是一种基本的道德选择,是选择自己作为一个道德的人。而差异性范畴下所作的选择就是服务于个性伦理的模型,这里单个人不选择自己作为体面的人,而是选择自己作为某一种职业的人,或者哲学家或者诗人等等。但是现代人应该做哪一种选择呢?
赫勒认为,康德的普遍律令强调了对他者的责任,是对他者命令和要求的回答。在赫勒看来,康德的道德律令不能满足一种纯粹的个体伦理,在纯粹的个体伦理中,一个人不能把自己的行为或决定屈从于任何标准,甚至是普遍的道德法则。
康德的道德哲学只是一种形式,因为它先验地为人性设定了一种普遍遵守的道德法则,追求完美的存在方式,这在现代多元主义价值体系下是不可行的,或者即使在传统社会,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按照普遍的道德法则行事。道德选择情境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常常是两难困境的,此时康德的普遍道德律令不能给我们任何指引。
如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所举的那个学生的例子,他或者陪伴在母亲身边使她坚强地活下去,或者参军为哥哥报仇,但是“不管他乞助于任何道德体系,康德的或者任何一个人的体系,他都找不到一点点可以作为向导的东西;他只有自己发明一法”。正如赫勒所指出的,康德的绝对律令“是所有他者对你的要求,因为在我们看来,人类不仅包括所有曾经活着的人,也包括现在活着的人,还包括没有出生的人。
但是这个道德律令并不能充分地引导我们。因为它只是一种箴言的选择,而不是我们应该采取的行动,我们不可能回答所有可能的他者的命令;在行动上我们不能”。
康德有关道德的绝对命令在伊格尔顿、尼采、福柯等后现代哲学家、美学家看来,其伦理道德是高度的形式主义的,其道德主体是一元的、普遍性的,是必然要被抛弃而以美学主体来代替的。
伊格尔顿曾说:“康德的道德法则是一尊原始偶像;因此,道德法则并不是人类统一的坚实基础,这恰好表明了其意识形态的贫乏……人们需要‘在主体性的基础上促进个体间的统一’,但政治和道德都无法满足这种需要,美学却能满足这种需要。”但是赫勒在这一点上与这些后现代思想家是截然不同的,她没有放弃康德的道德美学观点,恰恰吸收了康德的审美文化观,并对当代道德美学的发展提出了建构。
赫勒认为,一个单个的个人可以在普遍性范畴下选择自己,也可以在差异性范畴下选择自己,然而有一种甚至只有一种选择是最基本的选择。
立足于现代的多元主义价值观,赫勒在伟大的传统叙事中找到了更多的美的主题:个人的独特的美的体验、自然之美、友谊之美、艺术创造之美、生活形式之美等等多种美的维度。康斯坦丁诺认为:“阿格妮丝 赫勒的道德美学极为重视自我形成的维度,完全按照个体存在选择的情感强度来决定,而不是由社会环境或遗传天赋来决定。她的指导原则是在个人的能力中发展道德资质的存在选择是自己的选择。”可见,赫勒极为强调个体选择对于现代人生存和自由的意义,强调了个体化、多元化的利益和价值。赫勒的道德美学是适合现代背景的,她对于道德美学的解释学想象抵制了普遍主义的范畴。
尽管赫勒的道德美学思想关注于个体的感受、个体的态度,剔除了普遍性因素,但是赫勒认为,现代人只有个性伦理学是不够的,必须有道德哲学。在《个性伦理学》中,赫勒用学生约希姆的口吻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果我们拒绝了康德的道德哲学,而沉湎于一种个性伦理学,我们就会失去一切,我们不能区分好与坏、善与恶。
如果我预见到康德的死亡、预测到道德律将分享老上帝的命运,那么我会万分感谢我不可能生活在下个世纪。我比过去更加恐惧未来。”
在赫勒看来,一种个性伦理是冒险的,因为在行动上它更多地从个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相比之下,“普通伦理学或道德哲学,比如说康德的道德哲学,根本就不存在冒险”。所以,尽管康德的道德性具有强烈的形式主义特征,但是赫勒保留了绝对命令的存在,并把它作为一种普遍有效的道德标准,因为他的人类学和道德美学的探索使得自然和自由的调节成为可能。
由此,赫勒把美学放到了当代历史哲学及时代的背景下,建立了体现个性伦理和道德哲学的道德美学,其思想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完整的、自由的人,就像所有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一方面,它同西方一些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流派一样,致力于人的存在和本质的探讨,致力于对现存世界的批判和对人类存在困境的反抗;另一方面,它又特别关注现存社会主义的民主化和人道化问题”中译者序10。可见,赫勒所理解的美学困境不只是美学自身的问题,而更是时代的问题,即现代性危机的重要方面;赫勒强调要在多元的文化语境中思考美学的重建,实际上也不只是解决美学的危机问题,而是克服现代性危机的一条途径,因此,赫勒的美学同伦理和道德问题紧密相关。赫勒在审美和道德领域的思考成果使得扬弃异化和恢复人的自由生存的问题成为可能,它体现了对卢卡奇“文化可能性”问题的回归,“在卢卡奇那里,文化的问题就是人的存在和命运的问题……就是对文化危机的批判,就是扬弃异化、恢复人的自由生存的问题”中译者序16。或许赫勒的思想只能算是冰山一角,但是,她的道德美学思想提出了对现代人改变生存境遇的建设性尝试。
参考文献
[1]阿格妮丝 赫勒.卢卡奇再评价[M].衣俊卿,等,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2]Roberts David. Between Home and World:Agnes Heller’s the Concept of the Beautifu[lJ]. Thesis Eleven,1999.
[3]Agnes Heller.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Fragments[M]. Blackwell,1993.
[4]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康德.论优美感和崇高感[M].何兆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6]傅其林,阿格妮丝 赫勒.布达佩斯学派美学——阿格妮丝 赫勒访谈录[J].东方丛刊,2007,(4).
[7]Fu Qilin. On Budapest School Aesthetics:An Interview with Agnes Heller[J]. Thesis Eleven,2008.
- 相关内容推荐
- 路易斯美学观的道德根基综述2014-12-22
- 康德对文化艺术所持的历史发展观2015-09-21
- 康德以秩序为根据的审美自由观2014-07-18
- 康德关于崇高美学的分析及其现代价值2014-11-01
- 以康德的目的论判断力思想解答“科学美何以可能”2014-09-29
- 探究康德的审美愉快的结构2014-09-29
- 本雅明对新康德主义美学家的反驳2014-09-20
- 纯粹美与依存美的区别与统一2015-0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