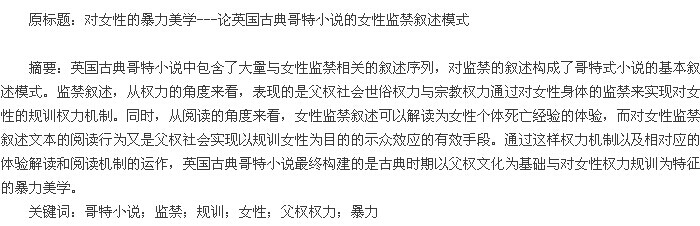
哥特小说诞生于英国 18 世纪后半叶。之后直到 19 世纪初的几十年是英国古典哥特小说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英国古典哥特小说中,监禁是小说不可或缺的叙述模式,离开了监禁整个小说叙述将无法持续,恐怖的悬念无法形成。因而,从沃尔普尔的开山之作《奥特兰托城堡》,到马修·刘易斯的《修道士》,到安·拉德克里芙的《尤道弗的神秘》等等哥特小说,对女性的监禁,不论是女性为主要角色或是次要角色,被不断地运用相同的叙述模式进行复述,成为一种常态。发生女性角色身上的常态化监禁叙述可以是对肉体的现实监禁,或是以精神桎梏为特征的隐喻监禁,既可能被定义为合法的行为,也可能被确定为非法,而衡量合法与否的标准本身也并非既定,而是具有相对的浮动性。
一、女性监禁叙述的基本模式
从叙述的角度来看,英国古典哥特小说中以女性为主的叙述一般呈现下面的基本叙述序列: 美丽动人的女性角色,遇到恶人,陷入危险之中,然后逃脱。这一叙述序列的施动者通常为男性,而受动者通常为女性,其中还会包含一些其他的辅助者或者阻碍者。一般情况下,叙述过程中女性角色遭遇到恶人之后,基本可归纳为三种结局: 被恶人监禁,然后设法脱离监禁( 叙述序列完成) ; 或是恶人的监禁意图还未实施,女性便已出逃( 叙述序列终止) ; 或是女性被恶人所监禁但最终未能脱离监禁的处境,而是在监禁中香消玉碎( 叙述序列失败) .安·拉德克里芙的《尤道弗的神秘》中的以女主人公艾米丽为对象的叙述序列就是属于成功逃离恶人的叙述序列完成模式,在父权式恶人芒托尼将其诱拐尤道弗城堡进行监禁之后,她设法脱逃; 在拉德克里芙的另一部哥特小说《森林罗曼司》中,对女性角色艾德琳的叙述就出现监禁的意图没有实现这类叙述序列终止模式; 关于监禁之内的逃脱叙述序列失败的模式在马修·刘易斯的《修道士》中最为典型,小说中安东尼娅在被恶人关入墓室后最终在墓室中悲惨地死去。当然,由于哥特小说中的人物繁杂多样,因此,这三种模式也可能重复或者是叠加出现在同一部小说中。
基本的“恶人-危险-逃脱”的叙述序列,可能是发生在单个女性角色身上,如《奥特兰托城堡》中就集中于叙述女性角色伊莎贝拉如何逃脱恶人的监禁意图; 也可能是出现在多个女性角色的经历中,如安·拉德克里芙的《西西里罗曼司》就分别出现了对女主角茱莉亚、其母亲路易莎以及其姐姐艾米利亚的监禁叙述。同时,古典哥特小说可能由多个相同的基本叙述序列链接而成,如在安·拉德克里芙的《森林罗曼司》中女性角色艾德琳的经历就是不断遭遇危险和逃脱过程的循环,特别是在涉及到德·蒙特尔特侯爵的叙述部分,分别涉及到叙述序列完成、终止和失败这三种模式。当然,在英国古典哥特小说中也可能出现多个叙述序列模式的混合出现,刘易斯的《修道士》当中就包含了多个女性被监禁的叙述序列,最主要的两个女性角色安东尼娅和阿格尼丝所就分别代表着叙述序列失败和叙述序列完成两种模式: 安东尼娅死于修道士安东尼奥的监禁,而阿格尼丝在被监禁后得到了男性的帮助逃脱了监禁。
二、女性监禁叙述的权力运作机制
( 一) 父权社会世俗权力与女性的监禁
在英国古典哥特小说中,按照叙述中监禁行为的发生地点,对女性的监禁叙述主要可分为世俗范围的监禁叙述和宗教范围的监禁叙述。世俗范围的监禁叙述的施动者常为男性,这一类男性施动者的个人品德通常恶劣,为邪恶的代表,但却可能是女性的合法所有权人,如父亲或兄弟,也可能是非法的所有权侵占者,如强盗。从权力的关系上来看,不论是合法的所有权人还是非法侵占者,都代表了父权文化中的男性权力,而二者对女性监禁行为的实施实则为权力的争夺。通过实施监禁,他们展示实现父权文化所赋予的权威,也将女性沦为没有主体性存在的客体,将权力转化以暴力为特征的现实。
作为监禁行为的受动者,哥特小说中的女性常为无主体性的客体性存在。就个体形象而言,她们的形象千篇一律,并不具备表征个体性的具体特性,而只是作为单一刻板的客体符号群体存在。在安·拉德克里芙写的四部哥特小说《西西里罗曼司》、《森林罗曼司》、《尤道弗的神秘》、《意大利人》中,四位主要女主角除了姓名不同,分辨不出她们作为个体的差异,因为用来塑造她们的语言仅仅涉及“美丽”、“善良”、“天真”等等泛泛之词。在其他作家的作品,如《弗兰肯斯坦》、《修道士》等,女性的塑造也是依赖于单一刻板的词汇。单一刻板语言支撑的女性形象塑造成了哥特小说重要的特征性符号,当然,追根究底,刻板符号的构建正是以父权社会理想女性形象为模板,正如,女性主义批评家托里尔·莫瓦就指出在父权社会中“‘不朽的女性气质’被认为是如天使般的美丽和温柔”.
依据拉康的镜像理论,哥特小说中的男性施动者是父权象征秩序代表着权力所指的主体性能指。在父权象征秩序中,只有“父亲”这一主体性能指符号才能被认同为“一种法或规范的代表”,因而,只有男性具有进入父权象征秩序,实现与父亲一样作为主体性能指的可能性,而通过成为“父亲”,男性“从而自己成为代表法的权威”.女性是不具有实现主体性认同的可能性的,只能作为父权象征秩序链条中浮动的客体性能指,对整个象征秩序的权力所指的表征不起任何决定性作用,只是可有可无的辅助。因此,在父权社会的权力机制中,女性个体被解读为具有置换性的客体。这种权力机制的存在,映射到哥特小说世界中,也就足以解释《修道士》弗吉尼亚代替安东尼娅成为男主人公妻子的结局,“安东尼娅的形象从他的心中消失了; 弗吉尼亚终于成为了他最珍爱的妻子”.这种女性个体的置换按叙述者所述应是源于男主人公洛伦佐对弗吉尼亚和安东尼娅符号化的认识,他“欣赏她美丽的身体、优雅的举止、横溢的才华和温柔的性情”.
这种置换行为的随意性及容易度也是源于女性个体在父权象征秩序所主宰的权力机制下的客体性能指地位。
由于女性的客体性能指地位,在哥特小说中男性对女性实行权力控制就具有了合理性。据此,按照父权权力体制,叙述中的世俗范围内男性对女性的监禁意图或行为就被赋予合法的意义。女性只是物品,“她本身就是某个男人的世袭财产的一部分:最初是她父亲的,后来是她丈夫的”.如前所述,在英国古典哥特小说中,对女性的合法监禁暴力的实施者通常是女性的父亲或具有父亲涵义的父权角色。对女性拥有所有权,因此虽然监禁对女性个体会造成的暴力损害,也不会改变不了暴力的合法性。
父权角色合法的监禁行为,常是出于维护父权权威或利益的必要性,如《奥特兰托城堡》中曼弗雷德对伊莎贝拉实施的监禁无非是为了延续家族的统治权; 《尤道弗的神秘》中,芒托尼对艾米丽的监禁则是为了能摄取艾米丽的财产。同时,英国古典哥特小说中的合法监禁也被父权人物作为规训女性的暴力手段,主要针对的是不遵从父权权力机制的女性个体。这种监禁暴力叙述,对女性个体进行压制,除了宣示男性作为女性的合法所有者的权威外,更重要的是将监禁作为规训的权力技术学,即通过对身体的监禁技术,甚至是惩罚,以摧残肉体的方式,意图对女性实施从肉体到精神的征服,最大化父权权力机制中的男性权力,将女性彻底地磨灭成毫无个性而言的个体符号,成为机械地遵从父权权力体系所发出的信号的傀儡。如《西西里罗曼司》中茱莉1茱莉亚屈服于其权威,遵从其意愿,嫁给公爵。
除了合法的父权权力的监禁叙述,英国古典哥特小说中,在世俗范围内对女性的监禁叙述也涉及非法的暴力行为。当女性逃离合法所有者的监禁意图或脱离监禁,女性并没有因此而获得个体自由。
远离以合法男性权力为主导的父权社会后,哥特小说中的女性通常会陷入另一类男性权力的暴力威胁。这类男性权力处于父权制家庭之外,以非法的形式,在父权社会正统权力之外的地域构建男性权威,统治着父权社会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空白地带。
强盗就是这一类男性权力的典型形象。哥特小说中的离开家族监禁的女性,往往会遭遇这些被父权社会边缘化的男性权力的暴力。他们对女性个体的监禁甚至侵犯的权力行为更具暴力性。《森林罗曼司》中的艾德琳就在密林中被强人所虏去关押监禁。对女性进行的非法暴力监禁,不再只是简单地进行规训,这里女性个体被彻底地客体化,沦为这些男性非法欲望的对象。当然,哥特小说中的这些非法男性权力者对女性的监禁暴力本身可以理解为对父权秩序中合法男性权力的对峙挑衅。对女性的“侵犯首先是对男性财产权的侵犯”.因而,通过对原属于父权社会合法男性权力的合法财产进行暴力侵犯,破坏合法父权社会的权力机制的运作,体现了父权社会权力机制合法与非法男性之间的权力斗争。当然这种权力斗争实质上与女性个体无关。这种权力斗争本质上还是以女性客体化及两性权力关系不对等的二元对立为基础,不论合法还是非法,在监禁叙述中,女性都仅被认同为男性权力暴力的实施客体,并不涉及女性个体的主体性权力的构建,因为在父权社会中,“我们大多数人能够想象得到的唯一的合法的公众权威是成年男性”.
( 二) 宗教权力与女性的监禁
除世俗范围内的监禁叙述,英国古典哥特小说对女性的监禁叙述也涉及宗教权力方面。宗教权力实施的监禁常发生在修道院或修女院等宗教场所。
多数情况下,女性进入修道院或修女院是由于遭受了强迫性的暴力侵害,如《修道士》中的阿格尼丝是在父母的压力下被迫进入修女院的。暴力胁迫行为叙述遵循的是正统父权社会文化中家长制权力的运作机制。但女性进入修道院有时并非是遭受强迫性权力的监禁,而是出于逃避世俗父权权力暴力侵害的需要,如《尤道弗的神秘》中逃离尤道弗堡的艾米丽为了躲避芒托尼的迫害曾一度藏身修道院。
从性别的角度来看,修道院进行的修道行为实质是构建在传统男尊女卑观念为基础的两性二元化建构之上。进入修道院或修女院的修女们,受到以基督为中心的宗教权力的控制,包括对精神生活的限制对个体身体的监禁。修女们要宣誓效忠于基督。传统的宗教中,基督的性别为男性,作为上帝之子而存在,是上帝权力的化身以及继承者。基督作为宗教意象的权力获得与世俗社会父权权力的继承方式如出一辙,遵循由父及子的原则,以男性作为传承的基础。在进入修女院时,修女们入院要经历配带面纱的仪式。一方面,授予女性的面纱象征着教会对女性身体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另一方面,面纱也将女性监禁到宗教权力的控制范围之内,将女性沦为了宗教权力的实践客体。修女在修道院内的日常生活也表现为监禁的形式,接受一系列的父权权力对女性个体进行的规训,如必须穿上统一规定的修道服; 未经允许,不得擅自离开修道院。本质上,父权社会中进入修道院的女性的所有权只是从父权家庭转移进入了父权教会,对女性监禁暴力的实施从世俗家庭内部转移到了修道院。
在修道院中,修女们对男性神灵的任何亵渎行为都会招致严厉暴力惩罚。暴力惩罚往往是对个体身体进行单独监禁的形式出现。通过从集体监禁升级为单独监禁,意图对女性彻底地隔离磨灭女性个性的独立性,实现对不服法行为等的规训。作为惩罚的单独监禁暴力具有示众的功能。对不服规训的女性的惩罚常在修道院的公开场所进行宣布,并且当即实施,如《西西里罗曼司》中修女院院长因茱莉亚拒绝成为修女而对其实施的监禁惩罚的叙述。福柯在论述古典时期断头台的场面时所提及的: “公开处决并不是重建正义,而是重振权力”.通过监禁惩罚的示众性实施,宗教权力巩固了其对女性个头的父权权力,使其他在权力范围控制之内的女性意识到宗教权力机制的无限存在,以达到警示、威慑以及规训的作用。
在哥特小说世界中以修道院为实施场所的宗教监禁暴力,与世俗监禁暴力的同质化,但还存在着权力的冲突。当出逃的女性进入修道院寻求暂时性庇护时,世俗父权权力的拥有者必然会要求修道院将女性移交到世俗父权权力的监禁之下。通常情况,作为宗教权力最高象征的修道院院长会进行拒绝,但这种拒绝行为并非为了维护女性权益,而是为了回应世俗权力的挑衅,维护宗教的权力权威。如,在《西西里罗曼司》中,修道院院长拒绝将茱莉亚交还给马次尼伯爵考虑到的并不是女性个体的福祉,而是因为移交女性个体就意味着宗教权力对世俗权力的屈从。
宗教在某些英国古典哥特小说中也为恶魔式的人物对女性监禁暴力的实施提供了便利。这些恶魔式的人物借助宗教权力,利用宗教的合法外衣,遮蔽其暴力行为,对女性实施监禁暴力,以达到满足自身欲望的目的。这种监禁暴力的实施常表现为对世俗父权权力的非法篡夺。宗教权力滥用的叙述以安瑞德克里夫夫人的《意大利人》和刘易斯的《修道士》最为典型。《修道士》中的修道士安东尼奥就是以其伪善面目欺骗了世俗众人,并且将神圣的修道院降格为安东尼娅的监狱。
三、女性监禁叙述的体验与阅读
( 一) 女性的监禁与死亡体验
英国古典哥特小说中对女性监禁暴力也经常和死亡体验联系在一起。对女性个体的暴力监禁所导致的死亡,并非一定是女性个体肉身的消亡。时常是通过男性话语宣布女性的死亡来构建的体验,女性的死亡体验仅仅具有死亡意象的象征性涵义。这种通过话语构建女性死亡体验的行为,源自于女性作为客体的社会存在妨碍了男性权力拥有者的利益。《西西里罗曼司》中茱莉亚的母亲一度被宣布死亡,成为城堡的“幽灵”,正是由于她暴虐的丈夫想要娶年轻的玛利亚为妻。而《修道士》中,修道士安东尼奥将安东尼娅进行监禁也是通过制造了安东尼娅死亡的假象后,将她关了修道院的墓地,使她沦为墓地里的活死人,并且最终香消玉碎在安东尼奥的淫欲之下。同样是在《修道士》中,修道院的院长将阿格尼丝关入地牢之后,也是对外宣称她已经死亡。制造女性死亡的意象,杜撰女性死亡的体验,成了英国古典哥特小说叙述当中代表邪恶的男性权力暴力实施的惯用伎俩。
女性对监禁暴力所实施的死亡体验有时还会有其他类型的死亡一起出现。在《修道士》中,阿格尼丝的监禁除了被宣布死亡之外,还伴随着其与男性角色所孕育的孩子的死亡。这个婴孩原本是阿格尼丝与男性非法结合的结晶,并非是属于父权制度下合法婚姻的产物,是阿格尼丝体验女性逾越世俗和宗教权力的限制追求个人幸福的结果,因此,无论对父权制度下的宗教权力还是世俗权力,婴孩本身是不可能进入父权权力的象征秩序,不能成为父权权力的合法继承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婴孩的死亡是阿格尼丝注定经历的体验,因为它本身无法获得男性主导的父权权力的认同。婴孩的死亡象征着阿格尼丝作为女性个体主动追求个人幸福经验的失败,表征了女性个体对监禁暴力抗争的不可能性,也为她重新进入父权制权力运作机制扫除了障碍。经历了个体死亡体验的阿格尼丝,已经不再是抗争的女性个体,在父权制权力的干涉下,她回归了父权制的婚姻,成为了接受社会世俗权力机制规训的客体。
像阿格尼丝一样,与男性结合的父权制婚姻是大多数英国古典哥特小说中大部分女性个体体验经验的最终结局。英国古典哥特小说从沃尔普尔的《奥特兰托城堡》开始,就确定了女性幸福地与心爱的男子结为连理为结局的基调。表面上看,这样的结局描述了哥特小说中部分女性抗争体验经验的最终胜利。但从深层次来看,对女性角色而言,这种以男性为主导的父权制婚姻并没有带来胜利,其意义等同于死亡。父权制婚姻并不能给女性带来自由的体验,而是将女性又重新带入了新的监禁机制,受到以丈夫为中心的父权制家庭的权力机制的监禁。
“走向婚姻的恋情,往往是个人欲望与社会规范的妥协”.因而,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古典哥特小说中作为结局的父权制婚姻对女性来说具有死亡涵义,隐喻了女性体验作为个体的主体性存在可能性的彻底死亡。
( 二) 对女性监禁暴力的叙述与作为规训的阅读
作为一种文学文体,英国古典哥特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情色暴力叙述为父权社会主流文化所不耻以及非难,并没有被英国主流文学传统所接纳。刘易斯的《修道士》就被柯勒律治等人斥责为“违背道德、亵渎神灵”,但主流文学批评的非难却没有阻止哥特小说的传播与阅读。到 18 世纪 90 年代哥特小说发展成为英国最流行的小说,并且一直持续到了 19 世纪,虽然这一切都是在“批评家的怒号声”当中进行的.因此,在 18、19 世纪的英国,对哥特小说的阅读可以被认同为一种不为主流文学所接纳的非法活动。
在 18 世纪的英国,随着经济的繁荣,女性被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了出来,特别是中产阶级女性,有了更多的闲暇时光。因此,小说成为女性阅读的主要对象。作为一种通俗化的读物,“由于当时作为阅读主体的中产阶级女性人生阅历有限,哥特小说为她们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她们可以与女主人公一起体会历险的刺激”,哥特小说在中产阶级女性中也颇受欢迎。在简·奥斯丁《诺桑觉寺》中,就有对女性阅读哥特小说行为及影响的叙述。
英国主流文学对哥特小说虽然进行了斥责以及边缘化,但并没有完全对其写作传播以及阅读进行禁止,其原因在女性阅读哥特小说的行为具有一定的规训作用。这种规训作用对于主流文学的规训作用是一种有效的补充。一方面,这类通俗化的读物被主流文学边缘化的地位与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边缘化地位相映衬。这种被主流文学传统斥责为毫无价值的读物,正好迎合了 18 世纪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教育需求,女性不需要学习知识,“女性教育唯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取悦他人”.另一方面,哥特小说以女性的个体经验为主要叙述对象,构成了一种“全景敞视正义”的权力运作机制。福柯在谈到监狱的建构时提出了“全景敞视正义”权力机制的存在。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全景敞视结构中的被监禁者“被一种权力局势所制约,而他们本身就是这种权力局势的载体”.受父权社会权力所制约的女性读者通过阅读哥特小说中被监禁女性的个体经验,深谙女性越界抗争可能带来的不幸与艰辛,使得哥特小说具有了父权社会“全景敞视正义”权力机制下权力暴力的“载体”作用,同时,哥特小说也通过“全景敞视正义”的权力机制展示家庭之外世界的罪恶暴力的存在,通过对这些罪恶暴力所带来的恐怖进行叙述,规训进行阅读的女性,使得女性读者安于父权制家庭范围之内的暴力监禁,实现示众效应。
总的来说,英国古典哥特小说,除了文本内的监禁叙述之外,又通过女性对监禁暴力叙述进行阅读的现实行为构建了一种文本外的规训机制,通过文本内外的权力运作机制的构建,最终形成了英国古典文学时期,哥特小说独特的以父权文化为基础与对女性的权力规训为特征的暴力美学。
参考文献:
[1]Troll,Moi. Sexual/Texual Politics: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M]. NewYork: Routledge. 2003: 57.
[2]黄作。 不思之说: 拉康主体理论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5: 23 - 29.
[3]马修·格雷戈里·刘易斯。 修道士[M]. 李伟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365.
[4]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M]. 陶铁柱,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78.
[5]苏珊·布朗米勒。 违背我们的意愿[M]. 祝吉芳,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417.
[6]柰奥米·R·高登博格。 神之变: 女性主义和传统宗教[M]. 北京: 民族出版社,2007: 10.
[7]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53 -226.
[8]苏耕欣。 哥特小说---社会转型时期的茅盾文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17.
[9]钱青。 英国 18 世纪文学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257 - 259.
[10]陈榕。 哥特小说[J]. 外国文学,2012( 4) : 97 -106.
[11]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女权辩[M]. 谭洁,黄晓红,译。 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