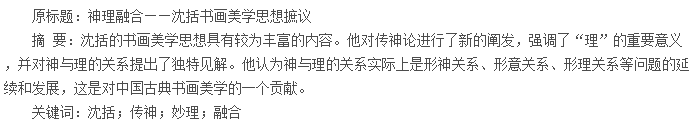
宋代书画美学较唐五代有了新的进展,如郭熙、苏轼、黄休复等人的艺术思想更加受到重视;大约同时期的沈括,在书画理论方面亦有一定成就,可以与宋代其他理论家相互参照,但对其研究还非常薄弱,本文将就此展开探讨。
沈括是宋代科学家,晚年所著的《梦溪笔谈》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宋史·沈括传》评他:“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沈括在艺术理论方面亦有所阐发。乐学方面有《乐论》《乐器图》《乐律》等著作,均佚。书画理论虽未臻系统,但往往探幽发微,见解独到,其书画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传神”观、“妙理”观及二者的融合方面。
一、书画之妙,当以神会:沈括的“传神”观
自东晋顾恺之提出“四体妍媸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世说新语.巧艺》)以来,“传神说”成为一条重要线索,但当时只体现在人物画上。南朝谢赫六法中的“气韵生动”可以说是对传神说的发展,突破了人物画的限制。同时的王僧虔在《笔意赞》中论道:“书之妙道,当以神彩为上,形质次之”,把“传神”延伸到书法品评上。沈括以敏锐的视角,继承了传神说,并将书画传神之说合而为一“,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
理论源于实践。沈括在四十五岁时绘过有关契丹道里险要的图(见《宋史·沈括传》),四十六岁开始,到五十七岁编成《天下州县图》[2]992。他所作的《图画歌》就是题画诗,计五百六十六言,叙述各家画派种类、特色。可以想见,他书画收藏颇丰,达到了“予家所有将盈车,高下百品难俱书”的富有程度。这些都说明沈括有可能从事过书画创作,至少在书画收藏方面付出了很大精力。他的传神观正是在他的审美实践中得以应用和展开的。如《图画歌》中有“花竹翎毛不同等,独出徐熙入神境”句,又如赞扬徐易画鱼“鳞鬣如生颇难学”,曹霸画马“驭人相扶似偶语”,张僧繇画龙一点双目,“即时便有雷霆驱”等,这些都说明他在论画中对传神的重视。论书法亦然。沈括的传神主张强调“活”“生动”“栩栩如生”,反对死板无生气,“譬若三馆楷书作字,不可谓不精不丽;求其佳处,到死无一笔,此病最难为医也”。三馆(一般指昭文馆、集贤殿和史馆)楷书精丽有余,追求整饬、匀称,这是形质上的特点,实际类似于明清时期的“馆阁体”。由于风格僵化,缺少生机,在明清及以后的书坛上备受诟病。而早在宋朝时期的沈括对此已有深刻的认识,足见其思想之敏锐超前。“到死无一笔”的批评可谓尖锐。值得一提的是,他拈出一个“笔”字———当指“笔法”“笔意”“笔趣”之类———无笔即笔法单调,笔意笔趣缺失,实际就是有形无神。黄庭坚亦说“盖字中无笔,如禅中无眼,非深解宗理者,未易及此”[1]357。沈括正是从其传神观的主张出发,与黄庭坚之说异曲同工,见解可谓精当。
传神与气韵是密切相关的,或可合称为“神韵”。沈括说:“最爱王维画《黄梅出山图》,盖其所图黄梅、曹溪二人,气韵神检,皆如其为人。读二人事迹,还观所画,可以想见其人。”[2]544无论书法还是绘画,如果片面追求形质,都有可能导致神韵的不足或丧失,成为难医之疾。神韵是一种活泼泼的生命律动,是灵魂,能体现作者的情感、意趣和美学追求,沈括对此有深刻的体认。
二、理须有别,迥得天机:沈括的“妙理”观
两宋时期的文论、书论、画论多涉及“理”这一范畴,在沈括的书画思想中也有着清晰的反映:画牛、虎皆画毛,惟马不画。余尝以问画工,工言‘:马毛细,不可画。’余难之曰:‘鼠毛更细,何故却画?’工不能对。大凡画马,其大不过盈尺,此乃以大为小,所以毛细而不可画;鼠乃如其大,自当画毛。然牛、虎亦是以大为小,理亦不应见毛,但牛、虎深毛,马浅毛,理须有别。……若画马如牛、虎之大者,理当画毛,盖见小马无毛,遂亦不画此,此庸人袭迹,非可与论理也。———《梦溪笔谈·书画》为什么画老鼠要画毛,而画牛、马二虎则不需要画毛呢?沈括的解释非常清楚,即因为画牛、马、虎,都是“以大为小,理不应见毛”,“鼠乃如其大,自当画毛”;那既然牛马大小相类,为什么牛画毛而马不画,沈括的回答是牛色深马色浅之故。哲学上的“理”用以解释宇宙人生之大道,而艺术上的“理”往往就在生活本身。哲学上的理被“生活化”后将为现实事物提供一个“合理”的阐释。结尾处沈括提到了两个“理”字(“理当画毛”“无与论理”),皆指生活之理。再如:……山水之法,盖以大观小,如人观假山耳。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见一重山,岂可重重悉见,兼不应见其溪谷间事。又如屋舍,亦不应见其中庭及后巷中事。若人在东立,则山西便合是远境;人在西立,则山东却合是远境。似此如何成画?李君盖不知以大观小之法,其间折高、折远,自有妙理,岂在掀屋角也。———《梦溪笔谈·书画》沈括拈出“妙理”一词,“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美,妙理即超越物理之上的艺术真实。在评价僧巨然的画时,沈括也说“祖述源法,皆臻妙理”。这里提到的“妙理”,实际上闪烁着道体的光辉,如《周易集解》所言:“天地万物皆有形质。就形质之中有体有用。体者,即形质也;用者,即形质上之妙用也。言有妙理之用以扶其体,则是道也”。
在绘画上,理不仅指生活、自然之理,还有艺术之理。理须有别,故能迥得天机。以“佛光乃定果之光,虽劫风不可动,岂常风能摇”的道理来说,“佛身光”应是常圆的。所以沈括说“,画工画佛身光,有匾圆如扇者,身侧则光亦侧,此大谬也。渠但见雕木佛耳,不知此光常圆也。又有画行佛,光尾向后,谓之顺风光,此亦谬也。”
王维将桃、杏、芙蓉、莲花同布一景,在雪中画上芭蕉,这显然不合“理”,但在沈括看来,却是“得心应手,意到便成”之作,并认为“此难可与俗人论也”。在事理(物理)和画理(艺理)之间,或说在自然规律和艺术规律之间,沈括显然倾向于后者。
关于书法的“理”,沈括亦有明确论述:“世上论书者,多自谓书不必有法,各自成一家。此语得其一偏。譬如西施、毛嫱,容貌虽不同,而皆为丽人;然手须是手,足须是足,此不可移者。作字亦然,虽形气不同,掠须是掠,磔须是磔,千变万化,此不可移也。
若掠不成掠,磔不成磔,纵其精神筋骨犹西施、毛嫱,而手足乖戾,终不为完人。杨朱、墨翟,贤辩过人,而卒不入圣域。尽得师法,律度备全,犹是奴书;然须自此入。过此一路,乃涉妙境,无迹可窥,然后入神”[2]955。这段话对“书不必有法”提出了批评,对当时过分“尚意”书风起到了辨正纠偏的作用。书法可有不同风格,可以抒不同的情,写不同的意,但根本的法是“不可移”的,这里强调的法就是理,或者说是通向理的。
三、神超理得,造理入神:沈括的“神理融合”观
在沈括的书画美学思想中,涉及到“形”“神”“理”“意”等基本范畴。形乃自然之形,神是作品之神,理为合艺术之理,意为发作者之意,因而沟通了作者、作品和外部世界的联系。沈括对理的重视与对神的强调一直联系在一起,在处理神理关系时具有明显的融合倾向,“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是突出“神”的重要性,紧接着又说“世之观画者,多能指摘其间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于奥理冥造者,罕见其人”,这与苏轼的“而至于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的观点如出一辙,都说明“理”是难的,能领会其中奥义的人很少。沈括尤爱王维画,并称《袁安卧雪图》中雪中芭蕉画,“其理入神,迥得天意”。这个其理入神的“理”是沈括本人对王维画所理解的“理”,俗者不懂其理,自然无法领会“其理入神”的境界。沈括讨论书法时作了一个形象比喻,“譬如西施、毛嫱,容貌虽不同,而皆为丽人;然手须是手,足须是足,此不可移者”,这是基本之理,然后“过此一路,乃涉妙境,无迹可窥,然后入神”,这显然是由理通向神的主张,强调理与神的统一。沈括试图沟通作品的“神”与观者所能悟出的“理”,从而达到神超理得、造理入神。理是以自然形质(形象、位置、彩色)为基础的艺术之理,神则是理的色彩或表现状态。神与理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二者的沟通须建立在“形”的基础之上;无形之理与无理之神是没有意义的;而突出传神往往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作品的形———比如绘画中大写意作品、书法中的大草作品———但“失形”而不“失理”,超于形后而合于理,合于理后而达到神。理既是对形的超越,也是对神的约束;神既是形的灵魂,也是理的升华。形、理、神本质上是统一的。而“世之观画者”往往不能理解于此,就是不懂神理相融的道理,这正是让沈括感慨的原因。
中国书画美学思想是建立在一系列审美范畴基础之上的,诸如道、气、形、神、理、意等等,东晋顾恺之就提出了形神关系的命题,此后关于各种范畴关系的讨论一直延续下来。沈括在继承“传神论”的基础上,对神与理的关系提出了独到见解,他认为形与理的关系实际上是形神关系、形意关系、形理关系等问题的延续和发展,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古典书画美学的一个贡献。
参考文献:
[1]黄简.历代书法论文选 上[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2]胡道静.梦溪笔谈校正[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