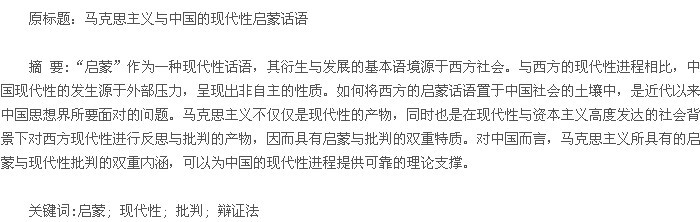
“启蒙”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其衍生与发展的基本语境无疑是西方社会,它是西方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逻辑必然。与之相比,中国现代性的发生缺乏商品经济的基础,呈现出非自主的特征。如何将西方自主语境下的启蒙文化话语置于非自主性的中国现代性进程中,解决自主性与非自主性相冲突的理论困境,是我们需要思考和追问的关乎中国现代性的重大理论问题。这一问题与如下问题相关,即中国现代性语境下的启蒙具有何种性质? 这种启蒙到底是需要以历史辩证法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蒙,还是需要以个体理性主义为主导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启蒙? 本文拟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中国现代性的理论资源进行梳理,以期思考与回答这一问题。
一、自主性与非自主性:中国与西方现代性启蒙话语的差异
在西方近现代的社会转型进程中,在纷繁复杂的思想与意识形态思潮的背后存在着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就是所谓的启蒙精神,它在哲学上表征为理性主义的思潮。正如卡西尔所指出的,“18 世纪喜欢自称为‘哲学的世纪’,也一样喜欢自称为‘批判的世纪’。这两种说法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刻画出那渗透了启蒙时代并造就了伟大的启蒙思潮的基本精神力量的特征。”
①卡西尔正是把握到了启蒙运动的核心,即理性与批判,这二者不仅构成启蒙精神的两方面,同时也是启蒙运动的价值所在。只有从启蒙理性的内核即批判理性和反思意志出发,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启蒙的进程是启蒙思想的自我批判进程,它不断地推动着现代社会的思想进程,这也是我们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在思想层面需要面对的问题。不过,由于东西方历史境遇和语境的不同,二者之间的启蒙文化在话语性质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差异。1. 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理性主义自主性阐释:西方现代性启蒙话语的性质康德在《何为启蒙》一文中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①在康德看来,人借助于理性,可以逐渐摆脱那些外在的东西,从而达到自由自主的状态。康德认为,启蒙运动首先要造成一种对自我理性价值的认可,相信理性的认识能力,同时坚持理性自我立法的意志。康德这一对启蒙运动的判断是深远的,他不是将启蒙运动当作一场只有历史意义的运动,而是认为其有永恒的价值,因而将其作为独立的哲学问题来处理。康德的批判哲学是启蒙运动的结果,而启蒙运动也由康德的批判哲学而完成了从历史活动到精神活动的跨越,康德哲学也由此而成为启蒙运动的象征。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哲学则从自我意识的角度来强调理性,这种“自我意识”的理性是指一种破除宗教、神学、权威不可质疑地位的独立判断。
需要注意的是,康德之所以能开启西方哲学史上的“哥白尼式革命”,就在于他独具慧眼地宣告了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这个新的时代就是人们的存在方式与认知方式发生质性改变的时代:一种全新的、由资本驱动的机械化大生产所带来的商品世界的发生。
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革命性继承者,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重大贡献是,指出启蒙运动所带来的思想与意识形态不过是经济利益冲突的结果;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使得理性得到哲学家的肯定,使得个体形而上的自我意识得以确立。这一判断是马克思的哲学远远高于启蒙学者天赋人权论的地方。因为在商品经济的世界中,交换价值成为统治这个世界的“真正的共同体”,这为个体自我意识的萌发以及自由、平等之观念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马克思指出,“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在所有方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这种基础而已。而这种情况也已为历史所证实”。
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指出,现代性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恰好是古代的自由和平等的反面。古代的自由和平等恰恰不是以发展了的交换价值为基础,相反地是由于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毁灭”。
③由此可见,西方的启蒙运动之所以发生,是有其现实和客观的社会基础,它是西方市民社会(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建立在商品经济交换价值之上的一种普遍性的自我意识。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理性主义主导下的自我意识就不会出现,启蒙运动也就不会发生。
基于这一认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启蒙运动的“天赋人权论”进行了批判,认为其中“天赋”的“天”其实是经济基础,但是启蒙思想家却对这一现实基础缺乏自觉意识。马克思因此对其展开批判,指出离开了经济基础,孤立地去探讨包括政治法律关系和人权观念在内的任何上层建筑,必然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就可以不必去研究在政治上表现为特权的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在政治上表现为权利、平权的现代的生产方式,以及这两种生产方式和与它们相适应的法律关系之间的关系了”④。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强调指出:“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权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
①在马克思看来,平等、自由等法权观念是有其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经济的交换过程,经济交换过程使得主体之间的关系在表面上看起来平等了,平等和自由的价值观在交换过程中形成并被尊重,启蒙运动所主张的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理论化、观念化表达,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而被启蒙思想家津津乐道的人权一旦“脱离了作为它们基础的经验的现实,就可以像手套一样地任意翻弄”②。
2. 非自主性的被动应对与中国现代性意识的觉醒
从马克思所指出的西方启蒙运动得以发生的基本语境———自主发生的商品经济进程———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与西方相比,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历史差异。源于西方的现代化对于东方民族来说,意味着打破非世界化的封闭观念,与世界同步。中国的现代化根本动力虽然来自中国社会内部,但它的诱发原因毕竟是源于外部力量。毛泽东对此有过精彩的论述:“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③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带有浓厚的被迫色彩,外国力量的入侵破坏了中国现代化趋势的自主性,使得中国无法采用渐进的、稳健的现代化发展模式。1840 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遭遇现代性的转折点,中国第一次见识到了“现代化”的巨大威力。自此以后,中国开始了代价沉痛的现代化历程。
实事求是地说,清王朝的统治精英已经意识到了中国社会正面临着强大的外部威胁,并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变革,他们试图模仿采用西方技术和部分模仿采用西方制度,以求恢复或者提升其在世界中的地位,由此而成为中国社会对现代化回应的开端。中国社会由此经历了一系列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现代化探索之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立宪运动”、“辛亥革命”等主被动交织的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但由于许多内外部原因,这些运动不但没有取得显着成绩,反而在内外交困的环境中丧失了国家统一这个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因此,“救亡压倒了启蒙”成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更为迫切的现实问题。
在一般意义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被视为开启中国现代化历史的“启蒙运动”。与滥觞于西方商品经济下的启蒙话语不同的是,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是一个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封建经济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主导经济形态,社会个体的自我意识在客观上并不具备。缺乏了必要的社会基础,在外部因素作用下的启蒙话语自然就带有极大的非自主性质,这决定了中国的现代性具有与西方相异的特性:“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启蒙不仅匮缺市民社会的根基和动力,而且没有西方式的孕育了现代性的传统资源可资利用”。④ 为了抵御外侮,中国知识分子期望以文化为武器,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因而“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扬弃,仍然是为了国家,民族,仍然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所有这些就并不是为了争个人的‘天赋权利’———纯然个体主义的自由、独立、平等”。
⑤这就使得五四运动以来的启蒙运动与西方的启蒙运动相比,在效果上,“‘五四’时代……‘人的觉醒’的运动并没有真正形成那种与‘自由主义’文化,即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自然地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个人主义’文化”,“中国启蒙思想始终是中国民族主义主旋律的‘副主题’,它无力构成所谓‘双重变奏’中的一个平等和独立的主题”。
①“救亡压倒了启蒙”的社会历史境遇提醒我们,一种由外部因素推动下的启蒙注定是被动的、不完整的,因而也就很难成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自由主义思潮所主导的启蒙与现代性运动没有成功,而由马克思主义所主导的社会主义启蒙却最终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二、启蒙与现代性批判: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双重哲学意蕴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思想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严厉的批判,指出了资本的抽象统治将导致人的异化;但同时又肯定现代性资本主义的巨大历史意义。众所周知,马克思用其毕生精力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但这并没有限制住马克思的视野而使其走向文化保守主义。马克思认为,未来那个实现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实现,是以现代社会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资本的发展是为资本的灭亡准备条件,没有资本的充分发展,就没有资本的最终消亡。然而在当下,马克思的这一历史辩证法思想却没有获得完整的理解。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许多人承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意义,却看不到马克思的这一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建立在对西方现代社会研究的基础之上。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理论深刻地指出,试图将人从神话中解放出来的启蒙运动,又重新成为压制人的神话,启蒙最终走向其反面。在对理性逻辑进行全面审视之后,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提出了“启蒙辩证法”,以一种消极的态度宣告了异化逻辑的总体性质并得出这一断言:理性的狡计就是一种欺诈,启蒙成为神话;原初的启蒙理想已经破碎,残酷的现实已经窒息了许久以前那个美好的理想。阿多诺因此认为,“启蒙超出了自身的传统的自我理解:启蒙是非神话化。它不再仅仅是人性的复归,而是一种复归的人,一种关于自称为绝对的主体的幻想的见解。”
②然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那个强加于资本主义自身的抽象性置之不理,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导性力量抛到一边,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罪魁祸首就是启蒙自身,启蒙所展望的美好理想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实际生活境遇之间的巨大落差是由启蒙自身造成的。
由于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思想是建立在这一基本的判断之上,从而忽视了资本逻辑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忽视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人的自我意识和思想观念的塑造;于是,现代社会与启蒙自身被当作陈腐的洗澡水倒掉。殊不知,启蒙的历史意义并没有结束,而是绵延持续在当下的历史事件中。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理论除了对现代性同一性话语的全面拒绝与悲观之外,在现实上并没有找到有效摆脱资本抽象统治的路径。这种全面拒绝现代性资本主义与悲观的理论在现实中必然无所作为。乔治·拉伦因此指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意识形态的一面:它那顽固的悲观主义使政治改革活动松懈和瘫痪。”
③启蒙观念成为一种普遍性意识,是现代商品经济滥觞与商品拜物教盛行的结果。如果缺乏对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层剖析,那么,启蒙精神所倡导的自我意识终究是一种无法自圆其说的物化意识。换言之,仅仅以启蒙来探究现代性的本质,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自身矛盾运动的机制避而不谈,是无法从根本上把握现代性的实质的。从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现代性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到,启蒙无法成为现代性的基础和动力,毋宁说,一种真正的启蒙是需要前提的。因为推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力量是以资本的扩张和剩余价值的实现为主轴的市场,绝非单纯的意识与思想观念层面的启蒙。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思想意识无论如何辩证与激进,都无法摆脱社会生产关系的统治。因而可以说,“拒绝概念拜物教与拒绝市场拜物教实质上是拒绝同一个东西:资本同一性———现代性”。①相对于启蒙辩证法理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面拒绝,中国社会则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以社会主义实践付出重大代价的方式诠释了启蒙得以发生的现实条件与社会基础。晚年的毛泽东采取了一种较为激进的现代化推进方案,他想要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在中国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实现美好与富足,为此,他用一种民族的特性来代替现代社会发展的一般性原则,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观念夸大为对抗贫穷的突出因素,逐渐远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十年“文革”的惨痛教训使得我们不得不再度思索: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现代性与客体性维度对中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抽空了社会基础的单维的文化启蒙是否能够真正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
马克思虽然出生在启蒙思想占据主流的时代,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启蒙思想的深刻影响;然而,马克思在与社会现实接触的过程中却发现,自己曾经信奉的启蒙思想却受到现实无情的冲击。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通过接触现实经济问题,引发了他对经济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从而超越了脱离现实的、停留在纯粹观念层面的启蒙理论。马克思认为,哲学不能仅仅在脱离现实的思想王国中发生作用,还必须充分关注现实本身,“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② 随着马克思思想的不断发展成熟,他获得了更加敏锐与深刻的洞察力,开始对曾经影响自己至深的启蒙思想进行全面的反思与批判。
马克思认为,从本质上说,启蒙精神是人类思想谋求解放的精神。这种精神要求对一切压迫人的力量展开无情的批判,首当其冲的便是批判资本对人精神的统治与束缚,将人从“自我异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③,从而真正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正如戴维·弗里斯所说的,“马克思在资本主义中确认现代性体验的‘起源’,他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当事人对于这些‘起源’本身并不清楚”。④ 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思想之悲观、失落与绝望意识不同的是,马克思从对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分析中发现了启蒙理性的自反性质,并自觉地从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基本矛盾的分析中寻找超越困境的道路。
马克思在论及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时曾经指出,评价任何一个历史事件,应当坚持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相结合的基本立场。印度、中国等古老的东方民族被西方列强所践踏的悲惨命运应当被置于现代性的总体历史进程中来认识,这才是更为合理的现实选择。西方列强对东方民族的侵略在道德评价上是恶的,但是在客观上,它打破了东方民族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落后状态,使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呈现新貌。虽然在主观上,资本主义对落后民族国家的侵略并非想结束这些国家的长期发展停滞状态,但我们却不能忽视这一历史事实的客观效应。马克思对此说道:“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正是在这一立场上,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①。这是我们在对启蒙与现代性思想进行批判时需要明确意识到的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维度来看,启蒙的本质是人从异化的“神圣形象”中摆脱出来,使人自身的个性得到更为全面的发展。吊诡的是,启蒙运动在历史进程中,却走向了其反面,曾经的解放力量成为了新的束缚,人陷入了资本的“自我异化”中。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超越启蒙的力量并不在于对启蒙思想的批判,而是在于对现实资本的批判。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始终关注的是人的地位这一启蒙的核心精神,因此马克思的工作可以说是对启蒙精神的继承与超越。马克思超越启蒙思想对天赋人权的看法,将人从资本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的努力,将资本的统治地位还给人,将本来属于人的人类历史从资本的历史中夺回,以实现人的个性和真正自由,这是一种真实的启蒙与解放。我们看到,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但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是人类的主导生产方式。
如果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而是重新回到对自由和平等抽象观念的崇拜,这在马克思之后是一种思想史的倒退。
总之,马克思主义超越了启蒙,但是并没有彻底否定启蒙;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但是并没有彻底否定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换句话说,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与启蒙并非是一体的。马克思实现了对启蒙的超越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汲取了现代社会发展的一切文明成果之后才得以确立的。当前中国的启蒙运动要想得以充分展开,必须建立在对现代社会文明成果的充分汲取之上,要在开放、对话与包容的立场上,最大程度地发展自己,为启蒙赢得足够的社会基础。如果脱离了启蒙的语境,启蒙的愿望很可能在忽视现代性经验的基础上沦落为一种抽象性的存在。正如福柯所说,启蒙是一种汇集了“复杂的历史性进程的总体”的“事件”,真正的启蒙是一个“总体性”事件,既表现为社会历史现象,又内隐为支配这一历史现象与社会矛盾的根源。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批判的理论,本身就是对启蒙的继承、改造与超越。马克思主义保留了启蒙思想的人道主义与理想主义精神,将对资本逻辑的剖析与批判深入到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当中,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抽象性本身的破除。因而,这是一种真正既继承又批判启蒙精神的“总体性”启蒙,是真正科学的、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启蒙话语。
就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最需要的启蒙思想,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最根本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还在于对落后国家与民族的理论指引。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目的是为了给人类指明一条通向自由的解放道路,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反思过去、批判现实与展望未来中鲜活地与我们同在着。在此,德里达所说的“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②,值得我们牢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