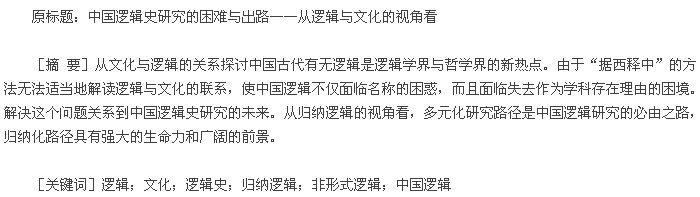
中国古代有没有逻辑?“中国的”逻辑是否存在?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困难是什么?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出路究竟是演绎化还是归纳化?这些重要问题近年来逐渐成为逻辑学界和哲学界争论的热点。在这里,我们将基于逻辑与文化的关系,从归纳逻辑、非形式逻辑等视角探讨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困难与出路。
一、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困难
上世纪 30 年代,逻辑学界的前辈曾以欧洲传统演绎逻辑是唯一和普遍的逻辑学观念,对中国逻辑的研究提出了“中国逻辑”的名称能否成立的问题。逻辑学界前辈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先秦诸子有论理,这一论理是普遍的呢?还是特殊的呢?”[1] 627近几年来,又有程仲棠教授提出了中国文化能不能产生“逻辑”的问题[2] 152。程教授认为,“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中国文化的终极关怀,是不能产生“逻辑”的深层原因:其一,在“内圣外王之道”的支配下,由道德与政治结成的价值体系的霸权,与逻辑学的价值中立的本性不相容;其二,在“内圣外王之道”的支配下,逻辑思维没有充分发展的余地。程教授从中国文化与中国逻辑关系的角度探讨中国古代有无逻辑的问题,这是深刻而富有启发性的。
程仲棠教授观点的深刻之处在于注意到中国逻辑与中国文化的密切联系,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由此得出符合中国逻辑和文化实际的结论。他坚持认为,人类只有一种逻辑,即演绎逻辑。中国古代既没有现代(演绎)逻辑系统中的永真式、有效式,也没有变项,因此中国古代没有逻辑学。按照他的演绎唯一性观点,以现代演绎逻辑系统为标准,去衡量我国古代的逻辑学说,自然会发现,中国古代(先秦)逻辑学说中的主导推理类型乃是推类,它根本不属于演绎推理,当然也找不到演绎逻辑系统中的永真式、有效式了。于是,解构中国古代逻辑的结论就顺理成章、呼之欲出了:第一,逻辑学是唯一的,也是全人类的;第二,这唯一和全人类的逻辑学就是欧洲逻辑,即欧洲演绎逻辑;第三,没有其他不同的逻辑,中国古代无逻辑。如果逻辑唯一性的前提成立,如果逻辑即演绎的前提也成立,那么程仲棠教授的中国无逻辑结论无疑可以必然地推出。平心而论,程仲棠教授的论证是严密的,结论的推出是必然的,相比而言,对程教授的反驳反倒显得不够强有力。这是因为,这些反驳大多没有从中国无逻辑结论的基本前提和基本假定入手,主要是站在逻辑一元论的立场上提出反驳。没有从文化的视角出发,没有从逻辑多元论的广阔视野看问题,这才是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真正困难。
二、中国古代逻辑研究遭遇困境的历史原因
中国古代逻辑研究遭遇这种困境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知道,西方逻辑自明朝末年经李之藻译介《名理探》传入中国,后又经严复译着的《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再度传入。于是,中国学者很自然将西方演绎逻辑与中国名辩学加以比较,顺理成章地参照西方演绎逻辑解读中国逻辑。即所谓“据西释中”的研究方法,这里的“西”主要指的是西方演绎逻辑,“中”主要指中国古代名辩学。
客观地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采用这种研究方法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许多学科在早期研究中都存在类似的情况。例如,认知科学研究初期,认知科学家往往把一些利用现成的数学和逻辑工具所容易解决的问题作为优先考虑的研究对象。对于这种状况,一位认知科学家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警察问一个在路灯下找东西的人:‘你在找什么?’‘我在找钥匙。’‘你的钥匙丢在这儿了吗?’‘不是。’‘那你为什么要在这儿找呢?’‘因为这里比别处亮。’”这个故事本来是针对视觉认知的研究现状来说的,它实际上也符合许多学科研究发展的规律。在研究初期,研究者限于当时的条件,只能借鉴当时研究相对成熟的成果和其他数学工具,搞出一些一经努力即可见效的成果;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是研究出来的东西往往脱离学科发展的实际。
尽管“据西释中”的研究方法在当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随着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深入,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逐渐显现出来。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一些前辈,在研究中国先秦名辩学说的论着中,以演绎逻辑学说为样本,把名辩学说按照现代逻辑学说标准加以解释,从主观动机上看是要拔高中国古代逻辑,其目的是要得出中国古代有逻辑的结论,但是他们撰写的有关中国古代逻辑学说的论着,与中国古代逻辑学说的实际相背离,最后只能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程仲棠教授的“中国无逻辑”论让我们冷静下来理性地思考,也让大家从迷梦中惊醒:中国逻辑研究应该改弦易辙了!
就像休谟提出的归纳问题在客观上推动了归纳逻辑的发展一样,程仲棠教授提出的“中国的”逻辑问题客观上促使中国逻辑学者重新深入思考中国古代逻辑研究和发展的可能出路。当然,也有不少中国逻辑学者在情感上对程仲棠教授的观点持抵触态度。
我们乐见的是,对中国古代逻辑的解构和质疑使人们渐渐意识到,这种“据西释中”的研究方法将会面临由逻辑学研究对象、逻辑学学科性质以及逻辑史所展示的事实所引发的诸多困惑与质疑,甚至产生中国传统文化中究竟有没有“逻辑”的疑问。如果认可中国古代无逻辑,那将是对百年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最具颠覆性的否定[3],甚至可能引致中国古代逻辑研究“无疾而终”的困局。为了破解这种困局,一些具有敏锐眼光的学者[4]认识到,必须解决以下问题:
1.钥匙到底丢在哪了?
2.那里为什么暗?
3.如何让暗变亮?
就中国古代逻辑研究来说,这三个问题就是:
1.中国古代逻辑研究困难的根本症结到底是什么?
2.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症结或问题?
3.克服这些困难的出路在哪里?
中国古代逻辑研究偏失的根本症结或根源是什么?有学者指出,否认逻辑与文化的联系,或者曲解逻辑与文化的联系,使得“中国逻辑”不仅面临名称的困惑,而且面临失去作为学科存在的理由的困境[4]。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症结或问题?中国古代逻辑研究学者认识到,迁就甚至比附西方演绎逻辑,忽视对中国文化相对性和传统思维方式特殊性的考察,漠视中国传统逻辑样式的特异性,必然造成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偏颇,从而不能对“中国的”传统逻辑历史作出合理的解读[3]。
三、多元化: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出路
克服这些困难的出路在哪里?我们的回答是:需要对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逻辑观念、研究方法进行深刻反思,阐明逻辑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的辩证关系,而且要研究文化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的关系,准确理解和诠释逻辑与文化的关系。只有通过这样的思路调整和纠偏反正,中国逻辑历史的研究才有宽广的出路和光明的前途。
为了克服困难寻求出路,崔清田先生探讨了逻辑与文化的关系。他指出,在西方,正是因为有了不同于古老东方文化的古希腊文化的孕育,才有了亚里士多德演绎逻辑的硕果。这种演绎逻辑系统的建立,以及这一系统的发展和演化,都与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背景相关[4]。
在中国,先秦文化不同于古希腊文化。它的核心是伦理政治与社会人事;它的主要内容是伦理尺度与治国纲纪的构想、建立和实践;它的基本思维取向是现实的需要以及实践中的经验。先秦文化的总体特征、核心内容和思维取向,没有像古希腊文化那样对科学证明的方法提出强烈的需求,因而难以产生与亚里士多德逻辑相同的传统演绎逻辑。中国文化重类推,西方文化重演绎。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不同文化类型的差异,导致了逻辑类型的差异。
如果我们转换思路,从中国文化的视角看待中国古代逻辑,在这种研究中不仅要求同更要求异,并对研究对象的异点给出制约因素的分析,即“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只要我们关注中国逻辑的特异性,就会发现,中国古代逻辑中不仅仅包括演绎的(外延)逻辑思想,而且包含内涵逻辑的思想、非形式逻辑和论证逻辑,还包含丰富的归纳逻辑思想。中国逻辑不是唯一的演绎逻辑,是多元化的逻辑,有无中国古代逻辑的困境是可以消解的。
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前辈温公颐[5]、汪奠基[6]和崔清田[4]等早已意识到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困难,试图探索中国古代逻辑的固有特征和特殊性。但不幸的是,他们的探索在当时并没有得到逻辑学界的广泛认同,甚至在今天,这种观点仍然没有成为中国逻辑学界的共识,也没有成为中国逻辑研究的主流。我们可以把他们对中国古代逻辑的特征的洞察表述为以下三点:
第一,中国古代逻辑具有内涵性特征。中国古代逻辑既然是逻辑,当然具有外延性特征,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是,中国古代逻辑具有内涵性特征的观点却往往被忽视。而且,这一特征在中国古代逻辑中比西方逻辑更为突出和明显。这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注重内涵的特征是相吻合的。因此,中国古代逻辑不仅具有外延性特征,更具有内涵性特征。
第二,中国古代逻辑具有非形式特征。中国古代逻辑尤其是墨辩逻辑中已经有了初步具有形式特征的推理,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代逻辑具有更多的非形式特征。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类似于西方欧几里得几何的形式理论,当然也不可能发展出西方的形式化逻辑,但是这恰恰使得中国古代逻辑的非形式推理研究得以发展。所以,中国古代逻辑只是初步的形式逻辑,但是具有非常显着的非形式逻辑特征。
第三,中国古代逻辑具有归纳逻辑特征。众所周知,西方逻辑的主体是演绎逻辑,是形式逻辑,中国古代逻辑中不乏演绎推理的模式和方法,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代逻辑具有更多的归纳逻辑特征。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讨论的论证和推理主要不是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理论,而是类推法、比喻法、排除法、枚举法等并非必然推出的推理模式。这显然不可归之于西方的可必然推出的演绎逻辑。
然而,在这一方面,中国古代逻辑的归纳推理研究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所以,中国古代逻辑中有演绎逻辑的模式和方法,但是在归纳逻辑方面,中国逻辑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要远远超过演绎逻辑。中国古代逻辑不仅具有演绎逻辑特征,更具有归纳逻辑特征。
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困境启示我们,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不应该仅限于演绎主义和外延主义的进路,应当开展多进路多视角的研究,这些研究进路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内涵主义研究进路。在我国,首倡并尝试从内涵逻辑的视角研究中国逻辑的学者是温公颐先生。在谈到公孙龙的名学思想时,温先生指出,这里有内涵逻辑思想[5]。温先生提出这一论点时,许多学者并不接受,其理由是中国古代逻辑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内涵逻辑。我们认为,尽管中国古代逻辑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内涵逻辑,但是它包含了现代内涵逻辑的思想萌芽。对现代内涵逻辑颇有研究的李先焜先生则认为,公孙龙子的正名理论属于语义理论中的指称论[7]。陈道德教授则从内涵逻辑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陈道德教授等在《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1 期撰文指出,“类”是逻辑学的一个基本范畴,通过“类”的关系进行推理正是逻辑学要探讨的问题。“演绎”、“归纳”都离不开“类”,不知“类”,就不能进行推理,就不懂得逻辑。《墨经·小取》中提出“以类取,以类予”,就是要求依据类的关系进行推理。陈道德教授等认为中国古代的“类”与西方逻辑所谓的“类”有些不同,中国古代的“类”着重于内涵,西方逻辑讲“类”着重于外延。这就表明,中国逻辑研究学者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古代逻辑并非纯外延的逻辑,更多地表现为内涵的逻辑[8]。这就表明,中国古代逻辑研究并非“自古华山一条路”,非外延研究方向是可行的。
第二,非形式逻辑或论证逻辑的进路。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阮松在《西方非形式逻辑运动与我国逻辑学的走向》[9]一文中强调了非形式逻辑的重要性。在阮松看来,非形式逻辑的兴起对于中国逻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文化的特征非常适合于非形式逻辑的发展。王克喜在《从古代汉语透视中国古代的非形式逻辑》一文中指出,中西思维方式上的不同,具有文化背景上的根源性,作为中国文化最本质方面的古代汉语对中国古代的思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而产生了中国古代特有的非形式逻辑[10]。显然,从非形式逻辑视角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同样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研究路径。
陈道德教授等指出,汪奠基先生在中国逻辑非形式特点这一方面提出了许多创造性见解,值得认真学习、继承与发展[8]。这些创造性见解可归结为以下几点:(1)中国逻辑史具有人类共同的思维形式,但它同时具有人类不同语言即不同的民族历史类型的表达形式。(2)“名辩”问题属于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名辩”具有一般逻辑的基本内容。过去有些中国学者过多地按西方形式逻辑的模式探索名辩问题的“形式”属性,而从现代逻辑发展的趋势看,名辩问题包括了“名”,也包括了“辩”。“名”主要是定义和分类,而“辩”则主要是论证与反驳,它们都属于非形式逻辑的范围。(3)“推类”是中国传统推理的主要形式。中国传统中的“类”概念,与西方的“类”概念不尽相同,“推类”过程也很难用类比、演绎或归纳简单地加以概括,它具有非形式逻辑的特点。
在陈道德教授等学者看来,中国古代逻辑推理主要是“推类法”[8]。运用到辩说中,它是很有说服力的。这种推类法,实际上就是亚里士多德所创、后来没有得到很好发展的“论辩的逻辑”,是一种非形式逻辑。很多修辞的论证手法,如隐喻等等,皆属于这一类推理,它是与演绎和归纳都有区别的推理。比利时逻辑学家佩雷尔曼就是专门研究这类推理的专家,我国逻辑界早有介绍。研究中国逻辑史,不妨从这个角度进行探索。汪奠基先生[6]、陈道德教授[8]等学者发现,中国古代善辩者往往使用这种方法,把对方置于必败之地,在《墨子》、《孟子》、《荀子》、《吕氏春秋》等着作中都有很多这类推理的实例。这种“推类”方法最适用于人文现象的辩论,在自然科学中使用起来则受到一定的限制。汪奠基先生在《略谈中国古代的“推类”与“连珠式”》一文中已经较深入地讨论了推类问题[11]。他将“假物取譬”、“引喻察类”,即现在人们所说的“隐喻”都包括在“推类”的范围内。
第三,归纳逻辑的研究进路。把中国古代逻辑看作是一种归纳逻辑的观点,在我国逻辑学界鲜有认同。主要是由于我国归纳逻辑研究的落后以及人们对归纳逻辑的忽视进而在理解上有偏差。在研究者的心目中,归纳逻辑不过是从个别、特殊过渡到一般的推理理论。实际上,这只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归纳逻辑的一种狭隘的理解。目前国际上通行的理解是:归纳逻辑中不仅包括枚举推理和排除推理,还包括类比推理甚至溯因推理(类似于科学哲学中的“最佳说明的推理”)。现代归纳逻辑中还包括了贝叶斯统计推理、概率推理、因果陈述句推理等丰富的内容。简言之,一切非必然的、或然的推理都属于归纳逻辑。从这个视角看中国古代逻辑,就会发现,中国古代逻辑的大多数推理都属于这种非必然的、或然的推理。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逻辑最辉煌的成就在名辩学中,墨辩显然是中国古代逻辑最重要部分。而墨辩中处处体现推类的思想。中国古代的逻辑经典《墨经》,将推类定义为“以类取,以类予”就是依据一类事物与另一类事物存在的某些共性,可以由一类事物推知另一类事物,即依类相推。所谓推类,即“依照类的同、异关系进行的推论”[5] 110。例如,《小取》提出四种不同的推类方式:辟、侔、援、推。辟,是举出(类同的)他物以明此物。侔,是类同的辞作连缀并列的推论。援,是说:既然你有这种论点,我为何不可有类同的论点?推,是以对方不赞同的论点类同于所赞同的论点为由,把前者给回对方使之赞同。十分明显,墨辩逻辑是推类的逻辑。崔清田先生认为,中国古代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是推类[4]。显然,这种推类在本质上不同于西方演绎推理,是一种并非必然推出的推理类型。既然如此,中国古代逻辑的主体不是归纳逻辑又是什么呢?
易学逻辑也以“推类”为自己的主导推理类型。中国古代文化并没有发展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字母符号,但是易学中的符号,诸如阴阳、八卦、五行、干支是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最具抽象意义的符号,它们都是按照“方以类聚”和“取类”(《系辞》)的方式获得的,它们之间的推导是遵循“与类行”(《坤·彖传》)的原则进行的。因此这些符号是类的最高层次的抽象,符号与符号之间的推导是在类与类之间的推导,由这些符号构成的是易学逻辑中的推类逻辑[12] 1~40。同样,以“推类”为主导推理类型的易学逻辑不是演绎推理,它只能是一种广义的或然性的归纳推理。
周山等学者的研究表明,《黄帝内经》是一个以阴、阳为核心概念建构起来的推理系统,只是在这里并没有用符号建构系统,而是引入“金、木、土、水、火”这五个概念即“五行”,组合成一个独立的概念系统;通过阴、阳平衡和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构建成一个类比推理系统。除了运用类比推理之外,尽管它还包含有演绎和辩证等推理方法,但是阴、阳平衡和五行生克原理决定了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学理论系统的逻辑属性只能是类比[12] 41~104。
我国逻辑史研究者发现,“四柱八字”推演系统具有归纳推理的属性。他们指出,古代先人将决定人生命运的探索重点放在人的出生之时,并且用甲、乙、丙、丁等十个“天干”和子、丑、寅、卯等十二个“地支”加以定位,即出生的年、月、日、时各取一个天干一个地支,由此形成所谓的“四柱八字”推演系统。在推演过程中,先将天干、地支配置于“五行”即木、火、土、金、水,再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结合四时旺衰等因素,推论人的生死寿夭、贫富贵贱、顺逆祸福。这种借助五行生克与四时旺衰等文化元素来构建系统同样是类比推理系统[12] 41~104。
在我们看来,推类也好,类比推理也好,都不是必然推出的演绎系统,都是具有或然性的推理,属于归纳逻辑的范畴。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古代逻辑的主体是归纳的而不是演绎的。而这一特殊的归纳逻辑是由中国古代文化的特殊性所决定的。难怪着名逻辑史学家杜米特留说,中国逻辑是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逻辑的“渗透性归纳”(penetrating induction),这一观点是很有见地的[13] 35~36。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国古代逻辑研究面临的困局表明,中国古代逻辑的演绎化研究进路已经是困难重重。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多元研究路径是中国逻辑研究的必由之路。只有开展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多元研究,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困境才可以化解,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强大生命力和广阔前景才会充分展现。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内涵主义进路、非形式和论证逻辑进路以及归纳逻辑进路是克服困难的出路,其中归纳逻辑进路是最有希望的出路之一!
[参 考 文 献]
[1] 金岳霖.金岳霖文集:第一卷[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2] 程仲棠“.中国古代逻辑学”解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 周山.逻辑多元性的历史根据[J].哲学分析,2011,(3).
[4] 崔清田“.中国逻辑”名称困难的辨析[J].逻辑学研究,2009,(4).
[5] 温公颐,崔清田.中国逻辑史教程:修订本[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6] 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7] 李先焜.公孙龙《名实论》中的符号学理论[J].哲学研究,1993,(6).
[8] 陈道德,李先焜.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四题[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
[9] 阮松.西方非形式逻辑运动与我国逻辑学的走向[J].南开学报,199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