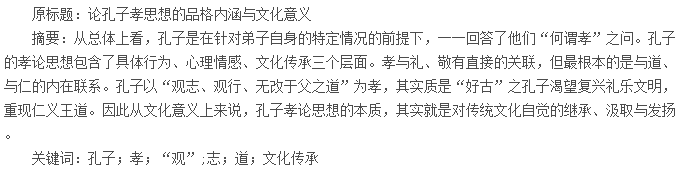
一、礼敬之孝
“孝”字在《论语》文本中一共出现了19次,其中出自孔子之口的有11次,关键的论述有以下几条:
1.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2.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而》)3.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4.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为政》)5.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6.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 生馔,曾是 以为孝 乎?”(《为政》)7.或谓孔子曰:“子 奚 不 为 政?”子 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从形式上来说,第1、第2条是孔子自己独立的陈述,而余下的则是孔子对弟子们所提之问的回答。区分这个的目的在于,要探究孔子孝论思想的本质,必须首先确定最有说服力的文本根据,从孔子的本意出发。
之所以对文本分类,是因为孔子作为“至圣先师”,其教育思想中最根本的原则之一就是因材施教。针对弟子们的不同性格特征,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回答同样的问题,这一点在《论语》文本中有多处体现,学界对此达成共识。就本文而言,孔子对弟子“何谓孝”之问的回答,也不例外。
孔子对孟懿子问孝的回答是,“无违”,即“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孔子为何要如此回答孟懿子,答案其实就在于问者自身。
孟懿子姓仲孙,名何忌,是鲁国大夫之一,“懿”实为其死后之谥号。孟懿子父亲名为孟僖子。根据《左传·昭公七年》记载,孟僖子其人十分重视礼,曾有“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之言。孟僖子在“将死”之际,命令孟懿子向孔子学礼,“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可见,孟懿子其实是遵父亲“遗嘱”(杨伯峻语)之命,来向孔子当面求教问孝。孔子以侍奉父母之生、死、祭均不违背礼节,来回答孟懿子之问,无疑是针对孟懿子当时所处的特别情形而言。也就是说,孔子此处的解答,并不是在专门论述孝,解释“何谓孝”,而是告知孟懿子在他当时所处的情况下,应当如何行孝。可见,孔子在这里谈到的“孝”,是基于特定的对象,其内容也具有一定的指向性。尽管这也道出了孝的内涵,但它并不是分析孔子孝思想的最佳文本。
再看孔子对孟武伯的回答。孟武伯是孟懿子的儿子,在《论语》中与孔子有过两次对话。一次是《为政》篇中的问孝,另一次是《公冶长》篇中的问“子路仁乎”.他本人的历史记载很少。学界对“父母唯其疾之忧”一句中,“其”的指代意义有不同看法。王充《论衡·问孔》云:“孟武伯善忧父母,故曰,唯其疾之忧”;马融则注曰:“言孝子不妄为非,唯疾病然后使父母忧”.然而不论“其”指代何者,按照孔子回答弟子的一般原则,“父母唯其疾之忧”之孝,必与孟武伯的自身处境相关。
最后看孔子对子夏、子游的回答。子夏与子游均是孔子晚年收的知名弟子。根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记录,子夏小孔子四十四岁,子游则小孔子四十五岁,二者年龄几乎相同。此外,子夏、子游的名字也经常前后连贯地出现在《论语》篇章之中,并且同样以“文学”着称,即《先进》篇所说的“文学:子游、子夏”.然而在《论语》文本中,却并未见孔子对子夏、子游作出正面 、积 极的评价。
子夏在《论语》中出现了21次之多,并且绝大部分是对子夏话语的记录。据此有学者推断,子夏可能是《论语》的编纂者。有如此之多的独立记载,证明子夏在“文学”方面确有过人之处。孔子称赞子夏,“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诗已矣”(《八佾》),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孔子主张的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所以孔子还是认为“商也不及”(《先进》),并且当面提醒子夏当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笔者以为“无为小人儒”很可能是孔子对子夏过度地擅长于文献辞令、重言轻行的警示。
如此善文之子夏,也谈到了对孝的认识,即“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学而》)。对于“贤贤易色”,传统上一般都把“色”理解为“美色”,如“以好色之心好贤则善”[1]31(孔安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贤”[2](皇侃),“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诚也”[3]57(朱熹),“当以好德易其好色”[4](康有为),“对妻子,重品德 ,不重容貌”[5]5(杨伯峻)。然而,当代有学者通过对“易色”二字在先秦至汉、魏、晋文献中惯用体例的搜集和研究指出:“’易色‘均是指’改变容色‘或’改变颜色‘,并没有将’易色‘之’色‘释作’女色‘的用例,因此不能把’贤贤易色‘中的’色‘字理解成’女色‘.”[6]同时也有研究者从思孟学派的代表文献---简帛《五行》中,“强调面对君子、贤人时需要’色然‘,否则便是不聪不圣和不明不智”[7]的观点出发,指出“’贤贤易色‘应解为’尊重贤人,改易容色‘”[7].
此外,《公羊传·哀公六年》曰:“诸大夫见之,皆色然而亥”,色然即指面容惊骇的样子;《孔子家语·正论》亦曰:“季孙色然悟曰:’吾诚未达此义‘”,“色”也作容貌神色解。就《论语》本身而言,“色”字虽出现了21次,但是作女色解仅仅一例,即“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卫灵公》)。“色”在《论语》中的主要意思是指面容、神色,如“巧言令色”、“色取仁而行违”等等。因此概而言之,“易色”的确当指改变神态、容色。
可见,子夏在谈到如何对待君子贤人时,特别指出应当改变容色。然而孔子对子夏问孝的回答却是,“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本文以为,“色难”很可能是孔子针对子夏所讲的“易色”而言,而且孔子在这里谈到的其实是某种师生关系(“弟子”与“先生”),而不是父子关系,这也似乎是针对子夏所说的“贤贤”而言。孔子认为,弟子在侍奉先生时,经常保持愉悦的容色是不容易的。孔子还进一步指出,在师生关系中,如果仅仅只是有事让弟子代劳,有酒食由先生享用,这并不能称之为“孝”.孔子言下之意即认为弟子对先生的“孝”,应当以内在的敬重为本,而不能停留在程式化、表面化的行为上。这就如同如果对父母没有发自内心的尊重,就很难对其始终保持愉悦的容色一样。
孔子以十分温和的口吻,反对子夏仅仅在行为层面对孝进行一种简单化、程式化的解释(子夏认为“事父母,当竭其力”)。“曾是以为孝乎”,其实是要求子夏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反思、纠正,而非对孝的本质的论述。孔子这种以含蓄的方式表达的孝以敬重为本的观点,在对子游的回答中则比较明确地表现出来了 ,即所谓的 “不敬 ,何以别乎”.
二、独志之孝
在前文所引的原文中,第二条(“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无疑是孔子直接对“何谓孝”的正面论述。宋代朱熹《集注》曰:“父在,子不得自专,而志则可知;父没,然后其行可见;故观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恶。然又必能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乃见其孝,不然则所行虽善,亦不得为孝矣。”[3]54然而笔者以为这样的理解,存在矛盾。
孔子的原话是“父在,则观其志”,而朱熹在注解中却添加了“子不得自专”一句。从该句中语词的前后关联来看,孔子显然旨在道明“孝”包含了父子相继的内涵。换言之,孔子认为在父存、父没两种不同的情形下,对子之为孝与否有不同的观察方式,但是无论是子之志,还是子之行,实质上都与其父有着内在的承袭关系。子之志、子之行二者并不冲突,它们都根源于其父。这也正如宋代另一学者---范祖禹所言:“为人子者,父在则能观其父之志而承顺之;父没,则能观其父之行而继述之。”[1]43可见,子之志与子之行的关系,其实是前后相继、内在统一的。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孔子此处完全是以子的表现方式(志、行、无改)为着眼点,来阐释“何谓孝”.并且孔子特别强调的是对子的“观”,“观”其志、“观”其行、观其“无改”.就“观”字而言,我们不仅看不出孔子有任何的父亲命令、强制儿子之意,而且相反,孔子的态度听上去十分的淡然、冷静。“观”一字含蓄却又清晰地表明,在父亲面前,儿子并非毫无选择、行动的自由,并非毫无独立性,否则“观”从何来。孔子最后所说的也只是“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既然是“无改”,那说明孔子也看到了存在“有改”的情况和可能。
孔子在这里的主旨的确是儿子对父亲之志的顺承,而非儿子的独立意志或是自由程度问题,但是这种顺承主要是基于儿子的自由意愿和主动行为,绝非受父亲强制。因此儿子在志向、行动上的实际自由,仍然是“观”的应有之意。总而言之,“观”虽然不能说明儿子所拥有的自由程度,但是它至少表明了自由的可能性,表明了儿子之志的相对独立性。因此承接前文所论,子之志与子之行之所以能够达到内在的统一,也正是因为它们在本质上均是子对父的主动追求和自愿行为。只有当儿子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依据自己的意愿去行动时,才有孔子所谓的“观”.
然而朱熹的注解,不仅有可能割裂这种父子承袭的内在逻辑,而且其致命错误就在于,它也可能完全改变子之志的性质与内涵。这个错误的根本之处就在于,朱熹所说的“子不得自专,而志则可知”一语。“不得”即是指不允许,是严禁、禁止之意,“自专”是说自己选择、决定。“子不得自专”其实就是认为当父在之时,子不能独自决断,而是要完全听命于其父。显而易见,这是在强调父对子的绝对权威(今人杨伯峻对此文的注解是“因为他无权独立行动,所以要观察他的志向”
[5]7,“无权”一词也充分证明了这种单方面的权威)。不过尽管儿子不能自己做主,没有独立行动的自由,朱熹却仍然认为可以“知其志”.
朱熹此解遮蔽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儿子凡事不能自由决定,而是要向父亲请命,那么朱熹所谓的“而志则可知”之“志”,在多大程度上,还是儿子自己的主观意愿?在“子不得自专”的前提下,朱熹所说的“而志则可知”之“志”,就可能包含两种完全不同的内涵。
一种情况是,因为儿子不能独立决断,所以即使是他的精神、志向问题,也必须征求父亲之旨意,或是直接听从于父亲。子之志因此有可能变成是对父亲之命的完全顺从,而非他的自我之志。另一种情况如范祖禹之言,当父在之时,子主动、自觉地“观其父之志而承顺之”,以此实现子之志对父之志的承接,从而使二者达到一致。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保证子在其父身殁之后的“行”,亦与父同,达到“无改于父之道”.
反过来说,就第一种情况而言,如果子之志完全是遵从父命甚至是父亲强加而来的,那么在父亲身殁之后,子之行很可能会背弃先前的非己之志,那就不可能做到“无改于父之道”,孝也就无从谈起。这应该不是朱熹“子不得自专”一说的本意,故而对“志”的这种理解不能成立。因此只有第二种情况是合理的,即在朱熹看来,子之志与父之志本就是同一的。也只有这样,子之志与子之行才能真正统一起来,孝才有可能。显然,这种同一性恰恰根源于子的主动意愿。正是子对父生前之志的积极观察和主动继承,才保证父殁之后,能够做到“无改于父之道”.这正是前文所阐释的,孔子使用“观”字的深刻用意。
尽管朱熹默许了父子之志的一致,但是他首先强调的显然是父对子的绝对权威,和子对父之命的无条件听从。然而从历史上对《论语》的注疏来看,朱熹此解显然是直接借用了孔安国的说法。西汉经学家孔安国注曰:“父在,子不得自专,故观其志而已。父没,乃观其行也。孝子在丧,哀慕犹若父在,无所改于父之道也。”
[1]44孔安国虽然在注解中沿用了孔子所讲的“观其志”一语,但他所说的“故观其志”,并不具有在孔子那里所拥有的自然、冷静的意味。“故”字的使用,凸显的是“观其志”的原因---“不得自专”,这就从根本上偏离了孔子强调子之主动意愿的主旨。孔安国此解的逻辑过程是,因为子在父前没有行动、选择的自由,所以要判断他孝或不孝,只能(“故”)去观察他的志向。可见,观志在孔安国那里似乎变成了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消极行为。从孔安国注解的语词顺序也可以看出,他首先是在对父子关系本身进行申明,“父在,子不得自专”,而非论述“志”或孝。本文以为,孔安国此解实质上一方面是受自身孝论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来自董仲舒的启示。“自专”一词,很可能是直接源自董仲舒的着作---《春秋繁露》。
史学界对孔安国确切的生卒年表仍有争议,但是基本确定孔安国的生活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50年至公元前90年。《孔子家语》书末附有两篇序文,其一曰:“孔安国字子国,孔子十二世孙也。……子国少学《诗》于申公,受《尚书》于伏生。
长则博览经传,问无常师。年四十为谏议大夫,迁侍中、博士。天汉后,鲁恭王坏夫子故宅得壁中诗书悉以归子国……子国由博士为临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于家。”学界一般遵从序文所言,把孔安国视为西汉重要的儒家学者、经学大师。董仲舒则是汉代儒学的集大成者,生于公元前179年,卒于公元前104年。据此而论,董仲舒约长孔安国30岁,孔安国是与董仲舒同时代的晚辈学者。
史载汉武帝笃好《公羊春秋》,“于是(上)武帝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8].汉武帝还任用治《公羊春秋》的公孙弘为丞相,国家大政也多采《公羊春秋》大义。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且被汉武帝采纳的董仲舒,也正是通过对《春秋》作注,成为西汉经学宗师。《史记》认为“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清人评价董仲舒之《春秋繁露》时曰:“西汉大师说经,此为第一书矣”[9],“汉人之解说春秋者,无有古于是书,而广大精微,比伏生大传、韩诗外传尤为切要”[10].综上所论,孔安国在注解儒家经书时受到董仲舒思想的影响,既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
董仲舒于《春秋繁露·基义》篇中云:“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阳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董仲舒认为“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天有阴阳,阴阳参合而生万物。董仲舒特别强调的是阴阳不能独行。阴、阳不是独自存在,而是共生于天地之始初,并且合力化生万物。如“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独阴不生,独阳不生,阴阳与天地参然后生”(《顺命》),“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五行相生》),“天之道,出阳为暖以生之,出阴为清以成之”(《暖燠孰多》)。由此可见,“在董仲舒的思想中,阴阳二气不仅被视为天的具体落实与具体表现,而且也是万物生化的实然基础”[11].
因此董仲舒此处以阴阳之道,来喻指君臣、父子、夫妇等人伦关系,也是要强调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妇,他们彼此之间是和合而生的关系,即所谓的“无所独行”、“其始不得专起”.以父子为例,二者的关系其实是,无父便无所谓子,无子亦无所谓父。父之所以为父,乃在于其有子。子之所以为子,乃在于其有父。换言之,父子关系的本质是相伴相生、彼此依存。由此可见,董仲舒所提出的“其始不得专起”,是基于特定的思想背景---阴与阳的和合化生。“专”字的内涵等同于“独”.与此同时,董仲舒还指出“其终也不得分功”,这就是在说天地万物之所成,有赖于阴阳之合力,而非独阳、独阴之功。概而言之,“不得专起,不得分功”的理论前提是阴阳和合化生。它表明的道德、伦理意义是阴阳的共在、互助与和谐。换言之,“不得专起,不得分功”其实是孔子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一说中所表达的,君臣、父子之间应当各遵其道,各守其礼,“双向互动”,彼此共存之意。
董仲舒在阴阳和合的思想中,的确主张“贵阳而贱阴”,认为“阳为德,阴为刑”,“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但是需要明确的是,董仲舒此时所讲的阴阳已经不是化生天地万物的、形而上的阴与阳,而是阴气与阳气。《春秋繁露》一书中有关于阳气、阴气的大量论述,这也是研究者把董仲舒视为中国思想史上气本体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原因。然而,研究者一定要区分形而上之阴、阳与形而下之阴气、阳气。如董仲舒所说的“阳常居大夏,阴常居大冬”,这里的阳阴显然是指阳气、阴气,所以他也有“阳气暖而阴气寒”一说;而论述宇宙之始初的“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阴阳与天地参然后生”等句中的阴阳,则具有形而上的本体论意义。这里的阴阳,合力共同构成了天地万物。它们是中性而不带有道德判断的,因而也就无所谓贵阳而贱阴。
由此可见,董仲舒在阴阳和合思想前提下所提出的“不得专起,不得分功”,是指阳不能无阴,阴不能无阳,二者不能独自化生万物,故而其功也无法区分。这也正是董仲舒所说的,“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的内涵。因此,“不得专起”,是不能够独自存在,无法独立完成之意。也就是说,阴、阳对彼此的需要源自它们本身,阴阳之合是内在的必然与既定的和谐。“不得专起”是指不能够独立生成,而绝非从客观上禁止其独存。然而孔安国所谓的“父在,子不得自专”之“不得”,恰恰含有禁令之意。那么孔安国为何要强调父在世之时,子不得独自决断、行动?
孔安国于其所着之《古文孝经》中曰:“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天子章第二》),“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纪孝行章第十》)。孔安国把敬亲看作是道德、礼制的基点,强调在日常生活之中,子与父相伴时的细节表现。孔安国十分看重父子关系中子对“敬”的认识和表达。“敬”不仅是父子关系之本,而且也是君臣之义。故而孔安国亦曰:“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士章第五》),“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广扬名章第十四》)。由此可见,“敬”其实是孔安国孝论思想中最根本的内容,正所谓“孝莫大于严父”(《圣治章第九》)。此外,从文字频率上看,“敬”字在《古文孝经》中总计出现了21次之多。这无疑是对“孝以敬为本”的有力证明。
既然如此强调子对父之敬,那么孔安国的注解---“父在,子不得自专”,就在情理之中。只是他所说的“不得自专”已经完全不同于董仲舒所讲的“不得专起”.董仲舒是在论述天地之开端,一种宇宙生成论的意义上,提出的阴阳不可独生、独行。孔安国则把这种形而上的元理论,下降为日常生活中可见的、具体的、禁令性的规定。“不得自专”一说,就是父在世之时,对子的言行举止进行了明确的总体性限定。这种变化其实反映了自秦汉以来,三纲五常思想的逐步推进。董仲舒虽然把父子列为三纲的内容之一,但他只是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他并未表述三纲的具体准则和关系,更没有“父为子纲”一说。《白虎通义》也只是把君臣、父子、夫妇列为三纲的内容范围,未规定其具体关系。真正明确地把三纲界定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是《礼纬·含文嘉》,“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矣”.[12]
董仲舒所说的“求于天”,也只是要明确“万物非天不生,独阴不生,独阳不生,阴阳与天地参然后生”.可见,董仲舒是在天地万物生成之本---阴阳和合---的思想前提下使用到“三纲”一词,而绝没有对子当如何孝父之纲纪进行具体规定。
综上所论,孔安国之注解并不吻合孔子之原意,而是附着了自身的孝论思想,而且也可能受到了三纲五常思想的影响。朱熹直接采用了孔安国“子不得自专”一说,这其实是“三纲五常思想受到理学家的青睐并被大力张扬,其在理学思想理论体系中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和强化”[13]的体现。
今人杨伯峻的译解,“无权独立行动”,也是值得商榷的。
三、传承之孝
接前文第二部分所述,孔安国与朱熹的“子不得自专”一说,会导致子之“志”产生两种相矛盾的内涵。但是从句子整体的旨意来看,孔安国、朱熹之解又只能允许“志”的内涵唯一性,即子之志对父之志的完全继承。然而前文的论证已经表明,只有当儿子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依据自己的意愿去行动时,才有孔子所谓的“观其志”.换言之,儿子的志向其实主要是其主观之志,有其相对的独立性,而非对父亲之命的遵从,或是简单地与父亲之志相同。那么孔子为何要暗示、默许儿子的独立意志和主观意愿?
从“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一整句话来看,考察子之孝或不孝的根本,就在于子对父之道的继承和发扬。道显然是孔子思想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这就足以证明道是孔子所追求的最高价值,是“孔子理解的本原存在或最高本体”.[14]
然而,如果仅仅从形而上、本体论的角度来理解孔子所说的道,就会南辕北辙,反而走向了老子之道。
老子明确地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四十二章)。可见,道在老子那里就是世界万物的本原。然而老子之道的基本特性是自然而然,因此老子所谓的道虽然是存在的,但它只是它自身,它以自身的本性为根据。同时由于天地万物生于道,所以道也必然区别于万物。因而道无法以任何一种物的形态存在,在这个意义上,道是虚无的,即“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于是,要领会这样的道,就只能遵老子之言,“致虚极,守静笃”,“绝圣去智”,否则只会“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孔子之道则迥然不同。孔子虽然也把道视为最高真理,但是他并不认为道如何的“惚兮恍兮”,“恍兮惚兮”.孔子之道完全没有任何的神秘色彩,因为他直接指出“人能弘道”(《卫灵公》),并且要求弟子们“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显然,孔子之道不同于老子的以自然为导向的道,他明确地导向了仁。“人因为仁而成为人,仁也因为人而成为仁,这是一个人、仁相即不离而相互成全的过程,贯穿这一过程始终的那种祈向,和其所指的至高而虚灵的境地即是孔儒之道。”[15]
正是因为道以仁为导向,所以孔子才提出以“无改于父之道”为孝。
在孔子那里,这种可以成为志向追求的 道(“志于道”),需要“敏以求之”,需要学习,“学以致其道”(《子张》)。那么如何做才能被孔子称之为好学?史载孔子有三千弟子,且“受业身通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然而在如此众多的弟子中,能够得到孔子“好学”之评价的却只有寥寥一人,即颜回。并且在颜回死后,孔子认为“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据《春秋公羊传》记载,颜渊死于鲁哀公十四年,也即公元前481年,而此时孔子已经七十一岁(孔子七十三岁卒)。可由此推断,孔子及至古稀之年,所熟知的门人、弟子之数量不可不谓多。然而在与鲁哀公的对话中,孔子却直言自颜渊死后,弟子中已无人称得上“好学”.三千弟子,惟有一人可谓“好学”,且后无来者。这足以证明“好学”的标准、要求之高。
就孔子自己而言,他也把好学看作是十分重要、值得自足的品质。孔子对自己的评价向来十分严苛,如“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孔子还十分自谦地说:“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叶公询问子路孔子是怎样的人,子路没有回答。然而孔子却说:“汝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可见,孔子一方面以自己为例,勉励弟子们要好学;另一方面他也以好学为荣,把好学看成是比忠信更为难能可贵的一种品质。因此有学者指出:“好学,在孔子那里是建基性的德性,即其他德性都是以这种德性为基础。”[16]
这种建基性的德性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一说中,所包含的个体的主观意志和精神力量。所以就其根本而言,好学实际上意味着以学为志,而且是终身之志业。学能够成为终生之志业,也正在于学以成人、为仁为目的。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孔子对孝的论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显然这段话前后的基本关系就是,子之孝或不孝,在于其志、其行与父之道的关系。既然孔子是以道论父,这说明父之道必然对子之志、子之行具有导向、引领的作用。然而,“观”字表明在孔子看来,父道对子之志、子之行也仅仅只有借鉴、引导的价值。父并不能直接把“道”赋予子,这是因为对道的确立和追求,主要在于子自身,“古之学者在己”(《宪问》)。也只有这样,孔子才会把道作为志向追求,提出“志于道”.就父子关系而言,“志于道”即志于父之道,而这种志向的确立在根本上取决于子对父之道的认知和理解。这种理解和认同要获得成功,要使得子能够继父道而行,关键就在于子主观上的好学与否。也正是因为这样,孔子才始终只使用“观”一字,“观其志”、“观其行”.
综上所述,孔子孝思想包含了几个不同的层面,其中有具体行为的层面,如对孟懿子之回答,也有从内心层面而讲的以敬为孝,但其根本内容则是其文化传承意义,即从仁道理想而指明的好学、继父道之志。这是因为孔子所说的道,具有特定的文化指向和政治意义,“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所以以继父道为孝,其实质恰恰体现的是“好古”之孔子,主张复兴周代礼乐文明的理想。正是由于孔子坚信“天之未丧斯文也”,所以他把毕生精力致力于传承、复现夏、商、周三代以来灿烂的礼乐文明。这种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延续,自然离不开家庭、家族的参与,尤其是在家天下的政治背景下,正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周书·康诰》)。孔子所说的“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讲的也是家国同构,也是要说明“为政之道,不外明伦,故但能明孝弟之义,即有政道,与居位为政无异”[17].
在商代晚期至西周之时,孝已经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德行,而这实质上正与封建社会宗法世袭制,及其思想文化有着直接关系。陈来指出:“在商代和西周的封建社会,孝不仅是一种个人品质,而且是维护其所属的宗法共同体的品质,由是而成为和一个人的亲属关系、家族结构连接一体的荣誉。”[18]
因此从文明传承和文化发展的意义上来说,孔子孝论思想的本质,其实就是对先祖、家族的传统文化自觉地认知、汲取与发扬。这种继承和发展的成功与否,无疑有赖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志趣、学习和践行。可见,孝在形式上,虽然是一种仅仅与父母相关的家庭伦理,但其实质则是关系到宗族传承的文化品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