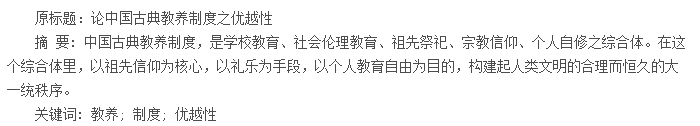
“人非生而知之者”,故人之发展必得教育而成。而国家、民族之发展乃个人发展之汇集,故国家、民族之扩大繁昌,必赖于教育之力。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必有一套自己之教育体系与制度。作为文明独立起源之中国,其教育体系与制度,必有特立卓异之处。科林伍德曰:一切历史皆是思想史。中国历史文教传统久远且深厚,其历史更具思想深度与内涵。全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思想教育史。“至少中国一切思想之主脑,或重心,或其出发点与归宿点,则必然在教育。”[1]234可见,教育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其地位及作用,十分重要。是以研究中国古典教育,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之最重要内容。然而,与现代教育制度之偏重知识技能不同,中国古典教育制度更注重“养子使作善”。孔子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故为研究方便,特示之与现代教育之区别,称中国古典教养制度而不称“教育”。
一、中国古典教养制度探源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其教育必随其文明发源而源远流长。柳诒徵撰写《中国教育史》,论中国教育自伏羲时代始。然而伏羲至黄帝,其历史皇古难考,渺不可征。司马迁写《史记》自黄帝开始,黄帝时代入中国正史。但司马迁对黄帝时代之事迹多存阙疑。《尚书》记载唐虞之政,其事甚详。《诗经》也有夏朝之风。但《尚书》与《诗经》之主体部分则是西周时代史迹,其中所载西周时代之教育,详备可考。是故,钱穆先生以为,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姑且从西周时代开始。
可以这样说,中国古典教养制度,溯源于伏羲时代。经黄帝、唐虞、夏商时代之发展,至西周时代,其制度逐渐趋于完善。故柳诒徵说:“三代学制,惟周大备”[2]49。
在西周时代,学校有辟雍、泮宫、庠序、瞽宗等。
辟雍是西周中央所设之大学,用来推行礼乐教育,以对外宣扬教化。《白虎通·德论》曰:“辟雍所以行礼乐,宣教化。”可见,辟雍是天子宣扬礼乐教化之教育场所。《说文》曰:“泮,诸侯饷射之宫。西南为水,东北为墙。”泮宫应是诸侯所设之地方大学,是诸侯宣扬礼乐教化之教育场所。古代以目盲者为乐官,乐师称瞽者。古代教育又以典乐为主,故学校又称为瞽宗。
古代学校也称庠序。孟子曰:“校者,教也。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夏商周三代教育一脉相承,其教育主旨皆在于发明人伦,修德宣化。又据孟子:“庠者养也,序者射也。”养就是养老,古代天子有养老之礼,在学校行之。《礼记·王制》篇曰:“养耆老以致孝。”《礼记正义》疏:“静养耆老,所以致恭孝之心。”可见,养老是施行孝道之教化,以上示下,使人人皆生行孝之心。古代有射礼,习射即是习礼。
又因“武事重于文事”,习射乃古代男子必学之艺。 后来,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教,盖西周时代已有。学校专言射,应代言六艺之教。
六艺之教,乃专门教育。人伦之教,乃全人教育。此两者,周代学校,兼而有之。然六艺之教虽为专门实用之教育,其中自有礼义精神在,所谓“习射亦所以培德”是也。人伦教育,在于教人如何做人做事,其“人伦”之明体现在专门实践中。
故六艺之教与人伦之教相通,而精神与行动并行。
西周教养制度趋于完备,实赖于周公之力。周公吸取三代,乃至于伏羲时代之教育经验,成功定制了一套教养制度,即后世所称之“礼法制度”。
但西周为封建制,其教养制度之重点在于家族。按照辜鸿铭先生之说法,西周之“礼治”属于“家族宗教”,学校教育乃“家族宗教”之附属物。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家族宗教”及其教养制度逐渐不适应历史发展之潮流。孔子出,提出儒家学说,变“家庭宗教”为“国家宗教”。所谓“国家宗教”,就是孔子将“家庭宗教”中对父母的爱———孝道,扩延至忠君爱国。中国古典教育制度开始以“国家宗教”为核心,而学校就是国家宗教的教会。
辜鸿铭说:“在中国,在儒家学说的国家宗教里,这种组织就是———学校。在中国,学校是孔子的国家宗教里的教会。”[3]40孔子虽然以“国家宗教”替代了周公的“家庭宗教”,但继承和保留了“家族宗教”的核心部分,即“家族祭祀”。可见,孔子与周公之教育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所以,钱穆先生说,“此项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精神和理想,创始于三千年前的周公,完成于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1]192中国古典教养制度之精神与理想,自孔子后,一直延伸到清末,而不曾发生过根本的变化。
无论是“家庭宗教”,还是“国家宗教”,都只是辜鸿铭先生类比东西方文化的一种说法。众所周知,“在中国的文化体系里,没有创造出宗教。”[1]192在现代社会里,宗教主情感与信仰,教育主知识与理智。宗教满足心灵之需求,教育满足大脑之需要。对于人类来说,两者皆不可或缺。中国古代没有创造出宗教,不意味着中国古人便无情感与信仰之寄托。没有宗教,教育便理应承担了这一职责。也就是说,中国古典教养制度既主情感与信仰,又主知识与理智。在中国古代,教育不仅承担传授知识的职责,更担负起了宗教所具有的责任。
中国古典教养制度,是学校教育、社会伦理教育、祖先祭祀、宗教信仰、个人自修之综合体。在这个综合体里,以祖先信仰为核心,以礼乐为手段,以个人教育自由为目的,构建起人类文明的合理而恒久的大一统秩序。
古代学校,有公立学校、私立学院,有书院、禅院、道院等。公立学院为中央和地方所设,如西周之辟雍、汉之太学。而书院、禅院、道院等皆私人讲学,历代不胜枚举。春秋时期,孔子居无定所,亦可随处设教。此外,个人自修也是古代教育的一大形式,读书人读圣贤书,自学成才,在历史中俯拾皆是。
按钱穆先生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官办教育亦终不为人重视。”[1]226中国古代官办教育主要是“行礼乐,宣教化”,辅助政治运营,其政治意味浓厚,代表的是官方意志形态,即政统。孔子后,中国古代教育,皆推尊于孔子,孔子代表的道统独立于政统之外。孔子开启私人讲学之端,古代读书人羡慕孔子,称孔子为“素王”,私人讲学之风由此而长盛不衰。是故,“中国教育史上,其真实影响力者,多在社会私家讲学之一途。”[1]231中国古代教育,入中央大学者及入私家书院者毕竟只在少数。孔子为所有读书人的“圣人”,读圣贤书犹如教徒之读“圣经”,有志于学而不得入于学校或书院者,便竭力追求儒家经典,亦可以自修成才。
中国古典教养制度,以祖先信仰解决宗教问题,并作为整个教养制度之核心。人之需要宗教,是对死后的一种妥善安排。西方之宗教,死后入天国是一种妥善安排。而中国先人,则认为其生命可以通过繁衍子嗣而得以延续。祖先得到子孙之追念和祭祀就是生命得以延续之圣神而庄严的仪式。
祭祀祖先解决了宗教问题。对祖先的崇拜和祭祀———孝道,是中国古典教养制度的核心问题。是以,后来之十三经以《孝经》为首。中国古典教养重在“养子使作善”,而“百善孝为先”,正是这一理念之准确而完满表达。
在现代人眼里,中国古代社会,教育根本得不到普及。但观古代社会之事实,虽不识字之愚夫愚妇,亦能熟知中国文化之精义。中国古典教养制度之伟大,正在于此,中国历史之恒久延续也在于此。
中国古典教养制度以孝道为核心,儒家精神可以通过祖先信仰一代代传承下去。儒家典籍可以毁坏,士大夫也可以有叛逆之时,但中国文化精神可以稳固地经愚夫愚妇而恒久不断地传扬下去。是故,“当世衰道微,士大夫成为文化罪人的时候,中国文化的真正的精神。反常常透出于愚夫愚妇之中,赖其‘死守善道’的一念至诚,以维族命于不绝,此种情形讫晚清而未改。”[4]22可以说,中国古典教养制度如此包罗广大,其奥秘在于中国人追求情感与理智之统一、追求大脑与心灵之统一、追求现实与永恒之统一。
二、中国古典教养制度之优越性
中国古典教养制度,以人文精神为其核心,其目的是构建以人文精神为根本的人类文明的大一统秩序。相比之西方文明,或其他文明,其教养制度的特点和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当然,金无足赤,其或许也有诸多缺点。但本文所关注的只是其优点。
其一,游走于科学与宗教之间。
对于现代教育来说,科学与宗教之分界是严格的。科学是科学,宗教是宗教。科学解决的是理智和实用问题,而宗教则是解决的信仰问题。现代之教育也主要集中于科学之上,而宗教则是教会的事情。科学与宗教并没有交集,两者也并无明显的相互影响。所以,现代人接受了完整的教育之后,其信仰往往也是缺失的,必须从教育体系之外寻找信仰。当然,主要是去宗教寻找。然而,要命的问题出现了,就是一直以来的科学教育与宗教信仰是相互排斥的。完全皈依宗教,则一直以来接受的科学教育是纯属徒劳,浪费时间;而不皈依宗教,则始终找不到信仰,人终归是一个无灵魂的躯壳而已。没有科学的应用知识与能力,现代人又很难生活。一般说来,人终归要向现实妥协,宗教信仰便彻底沦为形式和表面。人最终还是没有找到真实的内在的信仰,内心终将是一片荒芜。内心的荒芜,终将导致人性的缺失。而科学知识和技术在人性的缺失下,终不免误入歧途,严重者可以使人类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转基因技术的滥用,以及核武器的失控等都是这种歧途所在。但问题远没有结束,科学的去宗教化,使得宗教徒之信仰面目全非。极端宗教主义者,便以此作为清理叛逆的借口,煽动叛乱,引发宗教冲突,等等。
现代教育之不能建立合理的人类秩序,显而易见。在此,我并不想否定宗教的功能,或者不承认科学的好处。只是,现代教育体系将科学与宗教截然分开,似乎并不是人类文明大道之坦途。对此,中国古典教养制度显然有着不同的用力与方向。
在中国古典教养制度里,科学与宗教各得其所,并互相作用,相得益彰。在儒家学说中,孝是根本。对祖先的崇拜与祭祀就是宗教信仰及其仪式,也就是孝道。孝道作为一种信仰,是一代代合理的情感流动及伦理秩序,使得家庭、国家乃至人类无限繁衍昌盛下去。在这个信仰体系中,人不只是一个人,人人都是承前启后的,都是繁衍下去的关键一环。我们信仰祖先,同样信仰子孙对我们的信仰。让家族、国家、人类合理美好地繁衍下去就是孝道的信仰,是所有事情之前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一代中断了,便是不可饶恕的错误。相当于家族历史的终结。因此,人人守此信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丝毫不得怠慢。科学作为日常实用之技能,必得以此信仰为前提。不走极端的科学,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是孝道信仰下的必然发展。
人类之繁衍昌盛,社会之长生久安是孝道信仰下的自然理念。因此,我国先民之认识对象集中于现实人生上,诸如政治、社会、教育、文艺等。对神鬼敬而远之,因此也不会在彼岸多用心力,宗教自不会真正产生。科学研究也自会着眼于社会人事之上,而不至于为科学而科学,去深入地探索下去。
所以中国古典教养制度,只会在科学与宗教之间游走,既不会陷入宗教,也并不向科学作更深进入。因此中国古典教养制度“既无西方宗教性格,亦缺乏西方科学精神,而在人文本位上,则已渐渐到达一融通开明之境界。”[1]120此“开明之境界”,必能指引科学之合理发展方向,必能充实人生之内在信仰,使得人类文明恒久稳定地滚滚向前。
其二,学校造贤,与选贤相独立。自西周以来,教养制度与选举两者并重。西周之教育,权在贵族,乡学俊逸之才可以入于太学,并由此而参与政治。虽云贵族教育,平民亦可以以其才学而流通于上层。但毕竟学在官府,政府领导学术是毫无疑问的。春秋之后,官学流于民间,诸子百家开启民间私人讲学之风。特别是孔子,“以一平民,把以前相传的贵族教育开始转移到平民社会来,开出此下平民讲学之风。”[1]209如上所论,西周之教育核心在于“家族”,辜鸿铭称之为“家庭宗教”。孔子见春秋时,封建制土崩瓦解,天下非封建贵族之天下,一变而成天下人之天下。“家庭宗教”之局限性便凸显出来。孔子继承周公之志,在“家庭宗教”之上,发挥出一番大道理,变换出一个“国家宗教”来。“国家宗教”就是在“家庭宗教”的敬奉祖先基础上,推延至天下人皆“忠君爱国”上。非但要“忠君爱国”,还要把“治国平天下”作为一种信仰。人人皆可以通过自身修养,即“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此时政治已非贵族之特权,而成为每个读书人之平等权利。孔子开辟这一项,奠定了以后二千多年的“士人政治”格局。
而据钱穆考证,“中国教育史上,官办教育亦终不为人重视。”又“其真实具影响力者,多在私家讲学一途。”可见,中国古典教养制度中,贤士人才之培养多出于私学。孔子之儒家精神又是“自本自根”的,私学尊奉儒家之独立自由精神,往往不受政府权威约束。如徐复观所说,“儒家‘自本自根’之精神,既可不需要外在之上帝,则在政治上岂能承认由外来权威而来的强制作用。”[4]23故在中国古典教养制度中,私学严格按照儒家的标准培养人才,并不参考政府的标准和旨意。这就是所谓的“道统”独立于“政统”之外。
历代政府选拔取士,皆选取的是民间为学之士。虽各个朝代选拔考试标准并不相同,但正因选取的是具有独立精神的士阶层,政治之清流活水才源源不断,并依此增强政府乃至社会之生命力。
但考试本身作为选拔标准,代表了政府之用人标准和旨意。虽则儒家有“自本自根”之精神,但仍不免为世俗所趋鹜。然正是这独立精神,使得“公私教育,常成对立之势。”儒家精神的“自正自清”功能,由此可见其伟大。此种“自正自清”,还应得益于孔子之如宗教主一样的光耀千秋之精神光芒,这一身份与光芒,足以让世代读书人崇拜而信仰。
中国古典教养制度,其培养之人才是独立的,为构建光明合理的大一统文明秩序而培养的,不是为一朝一代而培养的。是故,贤士总能给腐朽的政治注入清流,增强政治之生命力。尤其重要的是,这一制度,使得中华文明并不因一个朝代的灭亡而中断,而是永久恒定地随时间走下去。
其三,有教无类,无分贵贱及种族。
中国古典教养制度,自孔子后,一直追求“有教无类”。“有教无类”内涵甚广。一者,民众资质有所不同,贤愚有别,但皆可受教。二者,无论社会身份等级如何,上至天子贵胄,下至贫寒之家,亦同等受教。三者,不分疆界,无论种族,皆在受教之列。《易》经曰:“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即是此三者之义。
“有教无类”,是教育思想的伟大创建,也是中国古代文明一直以来演化并自觉追求的必然结果。
帝舜出身侧微,得尧之教化,以孝道行于天下,并最终得禅让而为天子。教育不分贫贱,得而成之,便可“光宅天下”。西周确立封建制,以贵族主宰教育,但乡学与太学仍可流通,下民之俊逸之士仍可与贵胄同等受教。至孔子时期,封建制度瓦解,学问转向民间。孔子“以一平民,而把以前相传的贵族教育开始转移到平民社会来,开出此下平民讲学之风”。可见,自有明确历史记载之唐虞时代,一直到孔子,其教育平民化之趋势甚明。至孔子,则最终确立两千五百年以来的中国古典教养制度平民化时代。
孔子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马戎的《民族社会学》引申之曰:“中国有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
此两者,皆是明“有教无类”之道理也。中国古典教养制度,不区分种族的物理特性,只认可种族的文化教育标签。接受华夏文化之教育,便是华夏;接受夷狄风俗,便是夷狄。此理念之背后涵义是,教育没有种族之界限。这一点,显示了中国古典教养制度的包容性与博大性。中华民族能同化不同种族而最终融为一体,中国古典教养制度的这一理念功不可没。
其四,贵人尽性,以全人生。中国古典教养制度,其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成全人格的完善与完美。并以此人格之美善而达成功业之成就。人格之美善在于内,功业之成就在于外。养内而成外,是其一大特征。人格之美善,首先要从内心之诚修炼起。以内心之诚而不断关照自身,以促进自己人格的完善。
然后,才可以用此之已明之诚关照万物,乃至天下,并以所关照之天下万物反求于此内心之诚。这就是所谓的“反求诸己”。如此循环往复,人格得到不断的完善和充实,而外在的事功也自然顺成。
《大学》之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四条目专注于内心,而后四条目则是现实的外在人生。前四条目在前,而后四条目建立在前者之上而成。
尽人之性,必先内心能有“自得之地”。故中国古典教养制度,提倡“自得”之教。《孟子·滕文公上》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徒而震德之。”
教育之道,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和手段,劳、来、匡、直、辅、翼,皆所谓使人到达“自得之地”。自得者,内在学问生成也。知识、实践内化为人生内在之智慧。知识是外在的学问,智慧是内在的学问,知识通过实践内化为人生智慧,故称“自得”。人入“自得之地”,则其智慧内在生发,并外放与万物。因其内在智慧之一致性,作用于万事万物而不至于迷惑。若人不入“自得之地”,则不能以一理御万物,必致万物“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境地,而生迷茫惑乱之心。
《孟子·离娄下》曰:“君子深造以为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地,乃不借外物而能内在生发。内心若独立生发,则其人必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考。”则其心安定,故曰“居之安”。内心生发源源不断,故曰“资之深”。资深则予取予求,左右逢源。
中国古典教养制度,其教育理念可谓先进矣。
自得之教,以全人生,乃古典教养制度之精华。自得之教是从内在修养上培养人,而不单单是在能力上培养人。是对独立思考、独立精神之培养,是对完整人格之培养,让人能在万物之中自立自主,而非随波逐流。
其五,通德为本,专才为用。从上文可知,中国古典教养制度重在“全人”教育。“全人”教育培养的是人之宇宙观与人生观。在现代教育界看来,应该只是个“通识”课,虽然很基础,但却不受重视。其原因在于,现代教育为功利性教育,以成才教育为唯一目标。平心而论,分专业而分别教育,由于用力集中,人才之能力能快速显现。但诚如上文所论,技术和能力是把“双刃剑”,没有合理的文明理想作指导,这种技术和能力可能会迷失方向乃至入于“邪道”。
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以德行为第一,然后为其他。德行就是坚守合理的文明秩序,是大道。违反了这一大道,其他技能则会显现破坏性。孔子曰“毋为小人儒”。便是要求其弟子要坚守宇宙合理的大道,一切技能只在此之上才能发挥正面作用,或产生正能量。
即便如此重视“德行”,中国古典教养制度并不忽视专才之作用。“从来中国学校,亦重专业教育,如天文、历法、刑律、医药等”[1]198。中国之“专才”历代大家辈出,不胜枚举。
根据上文,中国之科学最终必转到现实人生上。专才之所掌之科学技术也必以此为出发点和归宿。是以,钱穆说,专才“也须懂得这一业在人生大道共同立场上的地位和意义,此谓之通识。”[1]198也就是说,科学技术之上还有通识,通识之上还有德行。科学技术之上有此两座大山,是中国科学技术近代未发展起来的一个原因。但正是这两座大山,才严实而稳定地控制了科学技术之用途与其发展方向,使其永远走不上“邪路”,中华文明才得以不因外物而受到本质的伤害。
但既然专才要为现实人生服务,其作用就是实在而重要的。因此,中国古典教养制度,在这一点上,追求的是通德为本,专才为用。
其六,教师为本,众生受教。孔子以一布衣之身,而成为“至圣先师”。孔子身上散发出来的如宗教主般的光芒,让后世所有读书人成为他的虔诚“信徒”。如上所言,中国文化虽不需要宗教,但教育担负了宗教所有的功能。
在宗教里,人们信教主要来自对教主之崇敬,也就是说,教主个人的魅力是吸引信徒的动力源泉。孔子开创之儒家教育既然承担了宗教的所有功能,这一点也必然相似。中国古代读书人把孔子作为“至圣先师”,孔子便如同教主。中国古典教养制度里,吸引读书人最大的动力来源于对孔子的崇敬,向下推衍开来,可以得出,教师之魅力和威望是古典教养制度中最为重要的因素。自孔子开启私门讲学以来,中国古代虽有官立学校,但毕竟学校之影响与作用有限,历代读书人皆以拜到名师门下为荣,而并不在意于学校或其开设之课程。孔子随处设教,而不择地点。在乡村中,一读书人有小成者,可以开设私塾,而乡村之人慕名前往受教。名山大川之中,有一名师,随便结一草庐,慕名者,不远千里,竭诚登门求教。历代各种书院讲学,皆有名师主持而得以兴盛。此皆教师为尊之例证也。
反之,若其名师不在,则其所教之所便渐渐零落。诚如钱穆先生所论:孔子死后,不闻有人在曲阜兴建一学校继续讲学。朱子死后,不闻有人在武夷、五曲,在建阳、考亭兴建一学校继续讲学。更如王阳明,只在他随处的衙门讲学,连书院也没有。中国传统教育之主要精神,尤重人与人之间传道。既没有如各大宗教之有教会组织,又不凭借固定的学校场所。只一名师平地拔起,四方云集,不拘形式地进行其教育事业,此却是中国传统教育之一大特色[1]200。
在中国古典教养制度中,教师如同教主,名声所到,向学之人辐辏云集。但毕竟与宗教不同,并没有所谓的固定教堂。中国之教堂只在家族宗庙。
天下之大,皆是受教之所。名师一至,便为庠序之地。形式之自由,必然一定程度上促成教养精神之自由。形式之自由,必然达成教师授教之自由,学者受教之自由。中国教育史,可谓是一部自由教育之光辉历史。
三、中国古典教养制度对当前教育之启示
中国古典教养制度之优越性众多,然时移事异,按今日之形势,复归古典教养制度是作天方夜谭之想。古典教养制度是一个整体而系统之工程,今天之教育事业同然。在时代背景发生极大而根本之变化时,建立在古典文明体系之上的古典教养制度显然不能直接移植到今天。但包括教育史在内的所有历史必然是一部精神之历史,其历史之精神仍然可以在今天重演。中国古典教养制度之形式虽已死去,然其教育之精神“不废江河万古流”,仍然可以为今世之教育提供极大的启示,乃至在“精神”上得以某种程度上的重演。
其一,重拾孝道精神,返中华教育之本。
教育本身就是知识传承的整个体系,知识传承之目的正在于文明得以不断积累而雄健地随时间延伸下去。文明之延续需要人来进行并完成。上一代的人把文明之接力棒传给下一代人,这样文明才得接力延续。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接力之下一棒,需要按照前一棒制定的规则和方向奔跑,不能停止,也不能随意改变规则与方向。如何保证这一点呢,在体育之接力赛跑中,依靠的是此团队之责任心与荣誉感。而在文明接力传承中,与此同理,需要的是,下一代对上一代的忠诚。这个忠诚,孔子称为“名分大义”,辜鸿铭称为“荣誉与责任的重大原则”。这个忠诚,作为一种精神,便是所谓的“孝道”精神。此“孝道”精神是中华文明得以恒久不衰之根本,是中国古典教养制度之核心内容。
今天,我们要传承知识,延续文明,应当理直气壮地借鉴和吸收古典教养制度之经验,应当重拾“孝道”精神,返教育之本。
重拾“孝道”精神,要从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四个层面一起做起,形成一股合力,构建整体的“孝道”体系。在家庭,首在重塑家长之权威与责任。在学校,首在让学生完整认知五千年华夏之历史文明,同情并热爱五千年华夏之文化传统。在社会,首在培育忠孝为“百善之先”的社会氛围。在政府,首在建立奖惩机制、礼义规范以及以身示范。
其二,解放教师,开放民间教育,促进教育平等均衡发展。
中国古典教养制度,通体闪耀着“师道”的伟大光辉。在其中,教师是自由的文化知识创造者与传播者。教师之宗旨在“谋道不谋食”,教师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文化的信仰与追求。是以,古典教养制度中,教师几乎是其全部。
而现代教育则不同,教师是份职业,是学校之职工。教师领学校之薪水,按照学校的要求与规定为其服务。教师不再是“谋道”之人,而是为薪水奋斗的“谋食者”。在其中,教师丢掉的是文化的信仰与追求。丢掉了这些,教师便丢掉了文化传承的独特担当。没有了这个担当,教育便丢掉了其根本意义与价值。
把教师从学校与薪水中解放出来,是现在教育的唯一出路。然而教师是精神文化与灵魂的工程师,不是培养出来的,是长期自觉而艰辛地修炼出来的。教师之能力、威望与魅力不是机构的任命,而应是民间的赞许与认可。教师从机构和薪水中解放出来,开放民间教育,也可以促进教育平等均衡发展。
其三,扎根通德教育,鼓励科学技术教育。发展科学技术教育,可以构筑文明自保的坚强物质盾牌,免受竞争者之野蛮强力攻击。然而文明始终是一部精神思想史。若人类仅存物质与强力,则与禽兽无异。故在物质与强力之上必有一伟大精神存在。这一伟大精神便是文明得以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原则,即“通德”。也就是在科学技术教育之上,必然加之于通德教育。而人类文明还有对现实人生的需求,每一种专门学问必须具有人生大道之意义。这一番意义,钱穆先生谓之“通识”。
通识教育位于通德教育之下,而科学教育位于通识教育之下。中国古典教养制度有重本轻末之倾向,故今世之教育需在通德通识之基础上,鼓励科学技术教育之发展,以弥补这一倾向。
参考文献:
[1]钱穆.国史新论[M].北京:三联书店,2011.
[2]黄绍箕,柳诒徵.中国教育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
[3]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
[4]徐复观.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