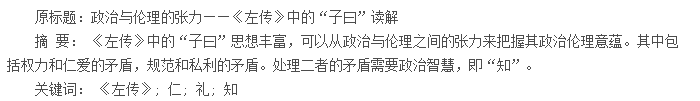
这里所谓的“子曰”中的“子”即孔子,“子曰”即“孔子曰”、“孔丘曰”或“仲尼曰”。《左传》中共载有“孔丘曰”3条,“孔子曰”7条,“仲尼曰”24条,总计孔子言语34条。《左传》中孔子的言行虽然散见于各处,但还是有一定的理论主题,有一定的理论线索可寻的。现有的成果对《左传》中“子曰”包含的哲学思想偏向于平列的叙述,理论主题的把握明显不足,这影响了对《左传》中“子曰”的性质认定。
可以把《左传》中“子曰”包含的思想纳入到政治伦理的范畴中来加以讨论。
在中国政治思想传统的语境下谈论政治伦理,有很多理论的难题,其中要回答的就是政治与伦理的关系问题,如何区分何为政治的,何为伦理的。梁启超说:“以目的言,则政治即道德,道德即政治。
以手段言,则政治即教育,教育即政治。”[1]梁漱溟也说:“不但整个政治构造,纳于伦理关系中,抑且其政治上之理想与途术,亦无不出于伦理归于伦理者。”[2]从政治和伦理的关系来把握中国政治思想,涉及到很复杂的关系。要么把政治归结为伦理,如梁漱溟所言,要么把伦理归结为政治,如萨孟武所言:“先秦思想可以说都是政治思想。”[3]要么从政治与伦理二者的张力中来理解。把伦理归结为政治则形成政治的一元论,把政治归结为伦理则形成伦理的一元论。如认为政治有特殊的伦理规范不同于一般修身的道德规范则形成一定的二元论,如认为政治规范完全不同于道德规范也会形成一种严格区分政治与伦理的二元论。就《左传》中的“子曰”而言,从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张力把握其政治伦理的意蕴是比较恰当的。
一 政治目的和手段
《左传》中的“子曰”最高的伦理范畴是“仁”。《左传·文公二年》中孔子列举了臧文仲不仁的三个表现,肯定了子产的仁。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郑国大夫然明提出“毁乡校”的建议,防止民众“论执政”,显然是想限制民众进行政治参与,其着眼点是巩固权威和稳定权力。从政治的角度来说,这个建议与政治的权力本性相适合。子产不毁乡校所依据的是一种伦理的理由。从手段的合理性来说,子产选择了道德为手段,即“忠善以损怨”,而非武力的手段,即“作威以防怨”。这里显示了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特征,政治手段的选择问题不全然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其中隐含了道德的判断,当道德的手段被纳入优先性的时候,技术性手段的选择本身就有了伦理道德的内涵。
就目的而言,子产的目的抉择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总的伦理原则是“不伤人”。从“不伤人”包括善恶而言,这个伦理准则是带有普遍性的,具有政治的元德的色彩。子产考虑到了伤人的多寡问题,从西方伦理学的视角来观察,显然具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在不能获得完全的仁爱之善的时候,当选择最大量的善。“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仁爱的原则显然凌驾于善恶之上。就政治来讲,子产为执政大臣,郑人为臣民,二者之间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但从道德上讲,民众及其贤者可以成为统治者的道德老师。在道德与政治之间出现了相反的关系,即“尊尊”和“贤贤”的矛盾。二者之间尊重的方向相反,构成了一定的张力,从而避免权力运作的失范。
仁是政治最高的伦理原则,其动机在于对所有人的爱,其目的在于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是公共的善。“好的治理寻求公共善的实现,坏的治理寻求个人的善的实现。”[4]36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左传·文公二年》)春秋时候鲁国大夫臧文仲不仁的表现有三。仁德表现为尊重贤能的人,贤能的人能够给民众带来更大的利益。臧文仲“下展禽”显然会损害公共利益。“废六关”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塞关、阳关等六关是禁绝末技游食之民的,臧文仲废除了六关;另一种解释是:本来自由通行不征税,现在设置六关收税。“废六关”为什么“不仁”呢?如果按照第一种理解,显然孔子认为禁绝末技游食之民更能保护大多数百姓的日常生活秩序,更能实现公共善。如果按照第二种理解,显然孔子认为设置六关征税是官员在与民争利。其三,以家中女奴为妾,或者让家奴织席出售则是在谋私利,而不是谋求公共利益。
这三个不仁的表现显然包含了追求个人善的实现和追求公共的善的实现的区别。
在保证爱更多人的前提下,可以采取合适的手段来实现。鲁昭公二十年,郑子产生病了,告诫子大叔有关治国方略,提到治国以“宽”或“猛”的问题。后来,由于子大叔“不忍猛而宽”,导致“郑国多盗”,最后不得不兴兵灭之。孔子对此事大为感慨。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
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谓猛,是指刑杀而言,《论语》中并无孔子强调用刑以治国的论述,当然也没有宽猛相结合的思想。”[5]119“宽”和伦理手段,“猛”和刑罚手段不完全等同,“宽”和“猛”更为抽象,刑罚则更具体一些。
另外,伦理手段也可以猛。这里的“宽”与“猛”基本上可以定位为政治中的手段的合适性问题。“手段的适合性问题是在我们希望就有效的治理进行考虑时出现的,它显然是一个技术性的而不是道德性的判断。”[4]46”“宽”还是“猛”最终要落脚在对大多数人的仁爱,能够实现多数人的仁爱的手段就是合理的。政治手段要和政治的伦理目的相适应,并受到伦理目的的约束。手段和目的之间有一定的张力,这个张力有的时候体现了政治和伦理的张力。从政治诉求来看,合适的手段可以达到有效的治理,但如果手段的运用脱离了伦理的目的,就不是好的治理。
政治的最终目的包含着仁爱和权力目标的冲突,包含着个人善和公共善的冲突。而从手段和目的的角度来看,围绕仁爱目的的论述包含着道德手段和刑罚手段的冲突,包含着手段和目的间的关系的处理。《左传》中的孔子坚持仁爱的至上性,具有伦理一元论的色彩。但这不意味着孔子忽略了政治与伦理之间矛盾冲突,恰好对仁爱的坚持是建立在对二者之间的冲突的认知基础上的。
二 政治规范
对于春秋时期的政治生活而言,各诸侯国力求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力求开疆拓土渐成风气。相应的,政治人物自身的政治行为也往往会脱离原有的礼仪规范的轨道,向着追求个人私利或者国家权力的领域倾斜。这样就造成了礼仪制度和国家权力和私人利益膨胀间的紧张关系,礼制遭遇了合法性的危机。伦理规范和变动了的社会现实的关联,其核心的内容是规范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这种调整往往是双向的。
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溪?”(《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公子围,楚共王之子。楚灵王伐吴,驻兵于今安徽亳县东南,因国都内叛乱自杀。在孔子看来,楚灵王伐吴的行为是和“克己复礼”相违背的。楚灵王的政治行为带来了恶的结果,这给孔子批评这种行为提供了机遇。政治行为要合礼,才是一种好的政治行为,政治行为要从属于道德的判断,或者说应该包含着道德的判断。
孔子在这里还把守礼的结果进行了推理和想象,也就是“岂其辱于乾溪”。按照礼制而行的政治行为获得的政治结果比违背礼制得到的结果更好。
《左传》中“子曰”赋予伦理道德行为以好的结果的思路曾经引起一些学者的质疑,认为这一思路更像是左丘明的想法,而不是孔子的想法。吴荣增认为,“《左传》贬低泄冶所起的作用,将是鼓励人们去明哲保身,这是左氏崇尚功利的一种表现,和儒家提倡的为义而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有点格格不入。”[5]116从《论语》来看,孔子曾对政治进行功利性的考量。“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这句话大约发生在孔子离开鲁国,初到卫的时候。“待贾者”虽然包含一定讽刺意义,不过也说明孔子对政治功利性的认知。
孔子对政治领域特殊的伦理逻辑有认识,关于这一点本杰明·史华兹有一定的说明。“人们确实在《论语》中发现了如下的紧张关系:一方面是‘纯粹伦理’;另一方面是政治生活的伦理学,后者常常涉及到在较大邪恶和较小邪恶之间进行权衡的那类政治选择。”[6]108对于个人自身道德修养来说,可以选择为义,而不为利。但对于政治过程来说,涉及到公共的利益,如果守护礼制不能给政治生活中的个人带来政治善和给众人带来公共善的话,礼制本身就会因为利益的冲击而逐渐丧失其合法性,从而带来合法性危机。规范要能保护和体现利益。规范带来的利益往往需要思想家去发现和说明。基于个人利益的冲动或者国家眼前利益的膨胀往往让统治者出现了智慧的短视,看不见违背规范带来的长远损失。《左传》中的孔子比较注重说明守护礼制才能获得更大量的善,包括私人善和公共善。
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桓子是以免。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县、繁缨以朝。许之。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
(《左传·成公二年》)仲叔于奚要求卫国大夫孙良夫赏给自己周代诸侯用的乐器和马的装饰。对孙桓子而言,对救过自己的人进行回报,是合乎一般的道德准则的,而且回报的是“邑”,应该说是很丰厚的。孔子显然觉得在物质利益上可以多付出一些,但是涉及到礼的部分要谨慎。“救”和“邑”对等,恰好停留在物质利益的层面。而把“救”和“曲县”与“繁缨”联系起来,就存在物质利益和礼制之间的交换关系,这种关系会逐渐瓦解礼制的合法性,从而带来制度的危机,进而发生社会危机。有了礼,人们才能恰当地认知自己的政治义务,从而带来公共善。
在“夹谷之会”的故事中,犁弥的观念把“礼”和“勇”对立起来,认为“孔丘知礼而无勇”,在政治与伦理的张力中偏向于政治的一面。结果孔子指出“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认为否则“于人为失礼”说服了齐侯。而后孔子由以私人善说服齐侯放弃“享”礼。指出“享”是为了起到“昭德”的效果。现有条件下举行“享”礼“用秕稗,君辱,弃礼,名恶”,无助于齐侯的私人善(《左传·定公十年》)。对守礼带来的利益的合理说明,收到了武力无法企及的效果,使得“夹谷之会”成为孔子政治生活中精彩的一笔,也成为学者争相讨论的话题。其中涉及的问题是:当时的孔子身份与可能发挥的作用问题。当时孔子为相,是否是卿呢?孔子为中都宰相。“相”只是国君的随从,还是起到卿的作用?不同认识会得到不同的结论。从文本来看,孔子是相礼的“相”。“相会仪也”[7]1577。关键就在于相礼的“相”能发挥多大的作用的问题。“春秋时,所重莫如相,凡相其君而行者,非卿不出。……而是时以阳虎诸人之乱,孔丘遂由庶姓俨然得充其使,是破格而用之者也。”[7]1577因礼本身的地位,相礼也自然成为重要的政治地位。否定这段文本的真实性的学者认为这段话给孔子注入了智勇的表现,“从《论语》等书中找不到孔子具备这样的性格”[5]119。这样的讨论应该说偏离了主题,孔子不过是自己亲身积极地去守护礼制,并且解释守护礼制的利益罢了!
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
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左传·哀公十一年》)这里面表现出了“贪冒”和“礼”的冲突,在孔子看来守护礼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根本,税负低,福利支出多,勤事创造财富,适当处理一些事务的耗费,才能“足”,用多征税的方法,在不约束贪欲的情况下,是不会达到“足”的结果的。“孔子两次根据人物的德行与乱礼行为对其未来的命运作出预言,这在《论语》中是找不到的,孔子是从不喜欢预言祸福休咎的。”[8]这里所说的两次其中一次是指《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晋国赵鞅铸刑鼎、着刑书的事情。孔子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孔子认为铸刑鼎、着刑书会扰乱君臣的秩序。“仲尼曰:‘赵氏其世有乱乎!’”(《左传·定公九年》)因为阳虎来到晋国,孔子就断定晋国有乱。把伦理道德和一定的功利结果联系起来,是《左传》中“子曰”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不过,孔子这种断定不单纯是一种预言,而是建立在礼的客观作用的认知基础上的。
孔子主张维护周礼,也主张对其进行适当的损益,从《左传》中的“子曰”来看,孔子维护周礼更为重视的是周礼本身的伦理诉求。从上面来看,“周公之典”在税负和福利方面的相关规定是合理的。
孔子说子产:于是行也,足以为国基矣。《诗》曰:“乐只君子,邦家之基。”子产,君子之求乐者也。且曰:“合诸侯,艺贡事,礼也。”(《左传·昭公十三年》)子产“艺贡事”强调“列尊贡重”,“合诸侯”强调“诸侯修盟,存小国也。”(《左传·昭公十三年》)在权力和私人或者国家的眼前利益和伦理诉求处于高度紧张关系的情况下,礼制被突破是常有的事情,从而发生“礼”和“仁”之间的矛盾关系。一个违背礼制的人,也可能做出好的政治行为并带来了符合仁爱要求的政治结果。这种情形见于《论语》之中,在此加以补充有助于思考《左传》中“子曰”和《论语》的关系。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作为一个大臣,管仲在他的门前建一照壁,这是诸侯国的统治者才能享受的仪式特权。从个人修身的角度来看,管仲的道德状况是有缺陷的。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子路的观点就是从一般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待政治人物管仲的。孔子肯定管仲的“仁”显然是从政治最终的伦理目的角度出发的。从功利原则来思考,桓公不用兵车之力九合诸侯取得的“善”的量显然高于牺牲个人道德操守这一“恶”的量。“对于依照普通人际关系的琐细道德标准来判断伟大政治家的做法,他颇不以为然。这里,我们又面临着两者之间的如下紧张:一种是个人道德观念,它以动机、意图的纯洁性为基础;另一种是关怀,它关怀的是良好的社会政治‘后果’,这种‘后果’要通过有杰出才能但很难说有什么德性的政治家才能取得。当然,孔子并非黑格尔,他的学说总体上似乎是给世界带来和平与和谐的社会目标只能通过由‘仁’人组成的政府来实现。但在这里,他似乎猛烈地朝‘国家理性’(raisond’état)倾斜。”[6]108管仲支持公子纠,但在公子纠被杀以后,他又支持桓公。从一般伦理学来看他不是一个仁者。但是从政治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从功利原则来看,他给民众带来了好处。从礼的原则退守到仁的原则,恰好是政治偏离孔子伦理诉求的情况下,导致的一个伦理结果。
三 政治理性
不能正确理解礼本身的价值内涵,并对守礼的结果进行评估,本身就是缺乏智慧的表现。鲁哀公哀悼孔子,子贡转述孔子的话说:“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左传·哀公十六年》)孔子在评价臧文仲的时候直接把“知”和“礼”联系在一起加以考虑。孔子说臧文仲“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左传·文公二年》)《论语·公治长》说:“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山节,刻成山形的斗拱;藻棁,画有藻文的梁上短柱。臧文仲使用的器物与自己的地位不符合。僖公为闵公之兄,也曾为臣,虽然继位,死后神位当在闵公之下,但夏父弗忌取悦新继位的文公,将僖公置于闵公之上,臧文仲并没有制止。海鸟爰居停在鲁国东门外,臧文仲以为神,让人祭祀这个海鸟。显然这些都是违背礼的行为。在孔子看来,只有顺礼并从充分考虑到他人的利益和立场才能更好地推行政务。
仲尼曰:“知之难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鲁国,抑有由也。作不顺而施不恕也。《夏书》曰:‘念兹在兹。’顺事、恕施也。”(《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知”的重要性就在于认识礼及其价值内涵,这增强了守礼的认识论基础,能够增强自我约束的自觉性,从而限制自己的欲望,从而构成调节政治与伦理张力的重要环节。
是否能“知”牵涉到是否能够限制欲望的膨胀,欲望的膨胀往往伴随着“知”的匮乏。但这不意味着“知”与对政治中的权力运作了然无知。齐国大夫庆克和齐灵公的母亲声孟子私通,鲍叔牙的曾孙鲍牵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齐国执政大夫国武子,希望国武子能够加以劝诫和制止。结果“秋七月壬寅,刖鲍牵而逐高无咎。”(《左传·成公十七年》)孔子对这件事的评价是:“鲍庄子之知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左传·成公十七年》)葵花会向阳光,并且转动保护自己的根部。当君子准备去向政治恶作斗争的时候,是要取得成功的,是要有伦理结果的。孤注一掷向恶作斗争适合于个人修身,却不适合政治伦理行为,因为政治伦理涉及到众人,涉及到公共利益。政治伦理要求有智慧,有“知”,政治伦理之“知”要考虑实现政治理想的可能性,要考虑自身生命的价值。
当政治生活中的人能够正确认识权力运作的现实的时候,这就增加了实现政治伦理诉求的现实性,君子就能够更好地结合伦理与现实的关系进行恰当的伦理判断,决定自己的进退取舍。能否正确认识权力运作的现实是是否具有政治理性的问题。认为《左传》中的“子曰”为来自左丘明的伪造的一个理由是左丘明喜欢以成败论人,结果往往颠倒是非。
以成败论人论事,是政治理性的表现。《左传》中的“子曰”表现出一定的政治理性。“政治理性产生于人类群体生活中的制度性焦虑,道德理性则产生于人类个体生命中的存在性焦虑;政治理性解决的是如何安顿人类群体生命的问题,道德理性解决的是如何安顿人类个体生命的问题;政治理性要求通过设计制度与建立教化来对治转化人的气质之性;道德理性则要求通过主观证悟与身心修为来对治转化人的气质之性。”
政治理性也有政治和伦理的张力,有不同的伦理取向。从政治取向和功利的角度来看,政治理性表现在对政治现实的认识,以及对成功的追求,对政治生活中自保的考量。而伦理的取向则表现在对礼制的认识和对其中包含的合理性的认知。《左传》中的“子曰”强调认识礼制的价值。形成合理的制度规范需要较好的理性能力的发展,遵守制度规范也需要理性能力来守护。仁爱和理性之“知”形成了守护政治伦理价值的双翼,这是《左传》中“子曰”思想的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3645.
[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83.
[3]萨孟武.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1.
[4][意]诺伯托·巴比奥.伦理与政治[J].廖申白,译.第欧根尼,2000(1).
[5]吴荣增.《左传》与孔子[M]∥国学研究:第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美]本杰明·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9.
[8]孟宪岭.《左传》中的孔子言语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34.
[9]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M].北京:三联书店,2003:10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