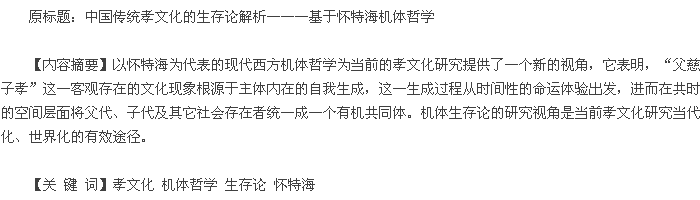
一旦我们提及中国传统孝道,多少会有一些尴尬与无奈:一方面,它遭遇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并迫使我们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判,而另一方面,“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的谓叹又顽固地回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并大有将其推而广之的“野心”,这便要求寻获一种普适性的研究视角来对之进行学理层面的剖析。而当前的研究现状是,要么过于强调中西文化差异,拒斥西方哲学的话语范畴,仿佛如此方能彰显其“纯正”;要么将之视为一种纯粹客观的文化现象,而未能深入到孝爱意识所生成的主观生存境遇之中,本文以为,恰恰是后者,为突破传统孝文化研究的文化藩篱提供了一个理论平台。
一、实体主义视野下的孝文化批判
孔子曾言:“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将一种致力于社会公共行为秩序的“政”还原为家庭内部伦理关系的“孝”,这充分印证了中国“政教合一”的社会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对准传统文化,正是要从根基上摧毁由此文化而衍生的封建政治制度。然后,或许正是目标导向上过于强烈的政治倾向,以至于这种文化批判未能在学理层面获得彻底性。自西学东渐以来,我们最早接触到的是催生西方民主政治的近代哲学,而这种“批判的武器”又只有在以后现代主义为表征的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机体哲学的反批判之映照下,方能对此获得一种自明性:即我们对传统孝文化的批判实则是采取了西方传统的实体主义的立场。
实体主义在西方哲学中源远流长,早期希腊自然哲学所关注的世界始基表现为某种具体、感性的“实物”,柏拉图的对话中首次出现了“实体”(ousia)这一概念。在希腊文中,ousia 来自动词 eimi(是,存在)的阴性分词 ousa 的一个名词,从字面意义理解,就是指“存在之物”。尽管柏拉图在 ousia的使用中存在一定的混乱,它有时用来指称流变的可感之物,但更多的却是用来表示原型、真实存在的东西。可以肯定地讲,柏拉图是第一个有意识地使用实体概念的哲学家。首先提出实体范畴并予以专门研究考查的是亚里士多德,他建立了一套以 ousia 为中心的哲学体系,其所谓的“第一实体”“之所以是最得当地被称为实体,乃是由于这个事实,即它们乃是其它一切东西的基础。”
这样,实体就成为其他属性与范畴的承载者,不管属性如何变化,属性背后的承载者,作为一种“硬核”是不变的。
近代哲学通过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启了实体主体化的趋势:“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它并不需要任何地点以便存在,也不依赖任何物质性的东西;因此这个‘我’,亦即我赖以成为我的那个心灵,是与身体完全不同的,甚至比身体更容易认识。”
如果说希腊哲学的实体范畴仍局限于宇宙论的话语范式之中,那么,笛卡尔的思维实体无疑具备了一种价值导向的潜在动力,它既回应了西方文艺复兴对人的价值与尊严的关注,又开启了近代哲学中人的主体性原则的先河。继笛卡尔之后,西方哲学继续推进了实体主体化的进程。斯宾诺莎彰显了实体存在的“自因”,并把实体规定为:“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
莱布尼茨更是将一种精神性存在的单子当作世界的本原,并特别强调单子是没有窗户的,以确保单子自身的独立性与自足性。如果说唯理论者对实体的肯定是为了保证知识本身的确定性并进而提供一种稳定的文化根基,那么具备怀疑论色彩的经验论者自然就要求否定实体的存在。洛克明确表明:“我们不能想象这些简单的观念怎样会自己存在,我们便习惯于假设一种基质(substratum),以为它们存在的归属,以为它们产生的源泉,这种东西,我们就叫做实体(substance)。”
休谟继承了贝克莱“存在就是被感知”的观点,首先就怀疑物质实体的存在,而所谓的精神实体,“都只是那些以不能想象的速度互相接续着、并处于永远流动和运动之中的知觉的集合体,或一束知觉。”
这“一束知觉”当然是不可知的,“至于我们所不知道的,那我们就只好听其自然了。”
至此,康德才对纯粹理性进行批判,藉以挽救以实体形式存在的理论世界,而将不可知的物自体让渡给道德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经验论者否定实体的存在,其思维模式则任然是不折不扣的实体主义,洛克所谓的实体明显就是对亚里士多德“第一实体”核心内涵的突出强调,而休谟的怀疑则暴露出在理解经验世界时实体主义所遭受到的自我否定,只可惜这种否定在休谟这里尚未完成,他固然可以否定物质性实体,但精神实体却要保留,至少也要将其作为“一束知觉”而加以肯定,因此,他注定了要承受“怀疑”的痛苦,而未能如黑格尔、怀特海一样,从机体主义的视角来予以重新建构。
从实体主义在西方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其精神内核可以归纳为三点,即个体性、主体性、静态性。个体性承认个体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所有个体都占据一个“位格”,在存在论上处于同一个层次,因而它们是平等的;主体性则是对个体在表现形式上的阐发,即个体的存在通过主体性才得以彰显,当其在一种文化发展进程中获得充分积淀之后,一种表征主体性的精神实体自然就成为近代哲学建构的基点;由于精神实体的封闭性与超验性,哲学体系的建构便只能基于实体之间静态结构的逻辑关联,从而丧失了流动性与鲜活性。
当我们立足西方实体主义的视角来审视中国传统孝文化之时,便不可避免地遭遇到深层次的文化冲突。按照有些学者的理解“,孝”乃是“老”与“子”的组合,意味着“父慈子孝”,因此,谈及孝道,就不仅仅意味着子代对父代的单向孝敬,同时也应包含父代对子代的慈爱,这种父子之间的双向关联又因各自的裙带关系而变得间接化与复杂化,以至于“居处不应,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礼记·祭义》)种种具体的伦理关系又在社会整体中被归结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网络结构,个体的存在便只能依托于“三纲”,其独立性与自足性自然是隐没不见了。一旦个体性得不到彰显,则以个体为基点的契约型民主政治便无从建构,因此,中国人实则是“有家无国”。在具体的家庭孝道伦理中,父子之间孝慈关系又往往并不具备对等关系,或许是因为父代对子代的慈爱更具有一种自然性,因而子代对父代的孝敬被予以突出强调,以至于成为一种情感性的“绝对律令”,孔子即云:“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为学》) 子代成就孝道的代价是自身话语权的丧失,他只能在自己的下辈当中获得一种补偿,这就形成一种次序格差、跨代流转的现象,个体的实现源于时间累积与经验沉淀,而非其自始相随的空间“位格”。“五四”之后,青年一代在现代化的感召下依靠自身力量逐渐成为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对于传统孝道所凸显的“老年权威”自然免不了一番口诛笔伐。
应该肯定的是,“五四”至今对孝文化的批判是与中国的现代化历程紧密相连的,而问题在于,依靠西方实体主义的批判立场,固然对准了传统孝道中个体性与主体性的丧失,并进而宣示了以孝道为核心的封建政治意识形态的崩溃,但孝爱意识自身所具备的自然性却是消解不了的,更何况,几千年以来“父慈子孝”的文化积淀已经成为中国人所归依的“生活世界”,因此,一种实体主义的现代性视角不可能彻底解构传统孝道,之所以它仍在顽强地生长且大有长国人民族文化“自豪感”的趋势,这种“既恨又爱”的尴尬心态的出现,正源于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理论视角来予以审视。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深入,以及对现代西方思潮理解的深化,从孝爱意识所生成的内在主观境遇入手,应该成为当前孝文化研究的新视角。
二、怀特海的机体生存论
黑格尔之后,以实体主义为表征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土崩瓦解,在这一进程中,黑格尔事实上充当了一个悲剧英雄的角色:一方面,他将理性与主体性提升到“绝对”的地位,从而堵塞了传统形而上学发展的空间,这注定了他要成为现代西方哲学实体主义批判的主要标靶;另一方面,他将“绝对精神”置于一个有机的辨证发展过程中予以描述,这本身就是一种机体主义的思维模式并对现代西方哲学影响深远,柏格森将真正的时间看作生命的“绵延”,海德格尔对系动词 being 的考察揭示出,存在者之存在维系于存在者如何“是起来”,这自然都是对传统实体主义的解构并具备了鲜明的机体主义的色彩,但真正提出“机体哲学”这一概念并建设性地实施体系建构的是怀特海。
怀特海明确声称机体哲学要回到前苏格拉底,即追问“宇宙的构成是什么”?这实际上是要从源头厘清传统形而上学的迷误之所在。他以科学家的敏锐视角洞察到近代科学所面临的深刻危机在于牛顿所谓的“简单位置观念”,这种简单位置关系意味着:“在时间中可以说‘在这一点’,在空间中也可以说‘在这一点’,在时-空中同样可以说‘在这一点’,其意义完全肯定,不需要参照时空中其他区域作解释。”
问题是,“在这一点”只是脱离纯粹感性知觉的一种概念抽象,它与人们的实际经验是格格不入的。科学唯物论者将这种无长短的瞬间自然状态一段一段加以连接,其结果不过是一副枯死的自然骨架,“活的自然”从中溜走了,休谟对因果关系的困惑同样源出于此。这种“简单位置观念”实则导致一种“误置具体性谬误”(the 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即将具体性放错了地方,如果从哲学上追溯源头,便直接指向了实体主义,因此,宇宙论的追问正是要从根源上纠正这一倾向,恢复宇宙的具体性与鲜活性。那么,宇宙的构成到底是什么?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中,怀特海称之为“事件”(event),这一术语在《过程与实在》中被“现实实有”(actual entity)正式取代。所谓现实实有,“是构成世界的终极实在事物。在现实实有背后不可能找到任何更实在的事物……这些现实实有都是点滴的经验,复杂而且互依的。”
这表明,现实实有首先是一桩经验事件(过程),它表现为经验的“脉动”(pulse),并具备自身的灵性(主体性、目的性);其次,这一个体性的事件所存在的根源在于,它乃是与其它现实实有的“共在”,因而它绝非封闭性的实体,而是“复杂而且互依”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怀特海将其称为“机体”,如果我们能够描述这一机体的生成过程,那么我们也就理解了整个宇宙。
“一个现实实有是如何生成的,这决定了该现实实有是什么;因此,对一个现实实有的两种描述并非是相互独立的。它的‘存在’(being)是由它的‘生成’(becoming)构成的。”
但生成绝非一种纯粹的流变,它有其生成的质料与生成的指向,前者由既往的现实实有组成,并对当下的生成过程形成了决定性的制约;后者则来自于非现实性的“永恒客体”,这实际上构成了生成过程的目的与价值理念,预示着现实实有有待于成其所是,换言之,一个现实实有“当下”的经验历程实际上综合了“过去”与“将来”,传统线性的、不可逆的时间概念在当下的经验活动中被有机地糅合起来。
将现实实有看作一个过程预示着静态的本质主义的研究视角对它来说是不适用的,它总是处于一种有待生成的状态,一旦它达到其目的,那也就宣判了它作为当下经验事件的死亡而沦为后续事件的客体(质料),因而,不能以一种单纯的主体或客体来标示一个现实实有。“一个现实实有既是进行经验的主体,又是它的诸经验的超体……‘主体’将总是被看成是‘主体—超体’(subject-superject)的缩写。”
作为客体,在于它能超越其个体的“私有性”,以一种公开的姿态弥漫于世;作为主体,体现了它的内在组织性与目的性,它永远渴望着终结这种未定性的状态,通过主体性的死亡来宣告其自我实现。
尽管怀特海的机体哲学以一种宇宙论的形式出现,但作为宇宙细胞之现实实有的微观生成过程表明,机体哲学更像一种生存论(生成论),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怀特海颠覆了传统宇宙论,即不再沉迷于对宇宙万物的抽象说明,而是深入宇宙自身的内在生成历程,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价值世界。方东美先生曾言,中国哲学“要把人的生命展开来去契合宇宙———表现‘天人合德’、‘天人合一’、‘天人不二’……去证明人与世界可以化为同体。”
在他看来,中国文化没有西方那种绝对的时空观,中国人的时间创化生生,中国人的空间萦情寄意,因此,中国人的宇宙功能无穷,这种宇宙本身就是一个生命流衍的境界,这也恰好印证了怀特海对机体哲学的评价:“机体哲学似乎更接近于印度或中国的思想,而不同于西亚或欧洲思想。前者把历程看做是终极的,后者把事实看做是终极的。”
作为一种价值理念,中国传统孝道与中国人所认同、所栖居的宏大宇宙背景密不可分,但这种机体文化尚需要现代西方机体哲学的明确昭示,否则它就是晦暗不明的。外在文化的刺激是推进孝文化研究当代化、世界化的必经路径。
三、孝爱意识中的自我实现
从机体哲学出发,我们不妨对孝爱意识的生成机理作一番剖析。一个首先要明确的前提是,孝爱意识的主体绝非被摆弄、被审视的外在客体,而是一桩具有时间跨度的生命历程,并非一个既成的主体产生了孝爱意识,而是,以一种孝爱意识为表征的生成过程如何促成了一个主体的自我实现。
孩童在幼年时代是一种完全被动的、自在的成长,他与外在世界是融为一体的,当其追问父母“我从哪里来?”之时,他便具备了一种根源意识,这种根源意识从外在世界逐渐精确化,一直到明白自己是父母“爱情的结晶”之时,从前与父母之间纯粹的“玩伴”关系便立即被一种敬畏的生养关系所冲淡,因此,最初孝意识的产生实则来自于对自身当下存在之根源的追问,在此追问中,根源与自我之间原初的同一性被打破,从而促进了自我反思以及自我意识的精确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最初的追问并非一种主动的追问,而是作为根源的“过去”经验对“当前”经验所形成的一种“促逼”,或者说,这种“过去”不可避免地在“当前”之生命存在中打下了烙印,并集中表现为父母的“十月怀胎”、以及“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阳货》) 对孝意识的发生学考察并不能极端化地理解成被动行孝,当自我人格形成之后,这种内在蒙昧的孝意识自然会以一种外在的文化形式呈现出来,并被加以自觉主动地遵循。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极端化地理解为“爱父母”其实是“爱自己”,即正是通过“爱父母”这种根源追问,才能不断获得自我确认与自我实现,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章》)孟子言:“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反过来讲,禽兽之所以沉溺于自然而无法形成自我意识,正在于其丧失了一种起码的根源意识。
在怀特海看来,“那些活机体懂得它们所出自的命运,也懂得它们所奔向的命运。”
如果说根源追问产生孝意识,那么对“将来”的期许便有可能理解为一种对子孙后代的爱意识。同样要注意的是,“将来”并非“我”的将来,而是,“将来”作为一种价值预设,始终参与到了“我”的生成过程之中,这与海德格尔“向死而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因此,我们不必等到娶妻生子之后方能宣称自己具备了爱意识,一个初步具备自我意识的小孩就已经在“布娃娃”身上展现出了这一意识倾向,而自己的孩子,作为“身上掉下的一块肉”,以一种具体感性的方式将“将来”突出地呈现于“当前”,从而使一种“将来”的内在意识集中表现在对子孙后代的慈爱行为之中。我们习惯于从人的自然性来考察爱意识,因为动物似乎也具备这种能力,这实际上没有从爱意识中揭示人之生存的超越性。
从机体哲学内在时间意识入手,可以将孝爱意识归结为人的一种命运体验,“所出自的命运”与“所奔向的命运”共同建构起当下的命运,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其深层意蕴即在于,作为家族繁衍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个体存在的意义维系于勇于担当这一环节的使命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孝爱意识以及由此衍生的孝爱行为都指向了个体的自我实现,诚如费尔巴哈所言:“只有有所爱的人,才是存在的,什么都不是和什么都不爱,意思上是相同的。一个人爱得愈多,则愈是存在,愈是存在,则爱的愈多。”
这种“存在”,我们当然不能将其等同于一种实体意义上的存在,而要从生存的内在价值上予以衡量,一个人的孝爱意识越强烈,便越能体悟到自身的存在意义,从而越能获得其自我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主观内在的自我生成在客观的现实意义上,又促成了社会整体的有机建构。在个体的命运体验中涌现出来的先辈与后辈,在当前共在的社会空间中能够勾连起来,以父子两代之间的血缘关系为基点加以泛化,便形成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的横向一体化状态。怀特海曾用“合生”(concrescence)来表述这种有机结构的形成:“‘合生’是这样一个过程的名称,在这个过程中,由众多事物组成的世界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是伴随着‘多’中的每一项被明确地下降为新颖的‘一’结构中的从属物而形成的。”
意味着,从每一个体内在生成的主观视角去考察社会个体的“多”,则所有“多”都在自身的自我生成中有机地关联起来。而西方实体主义将一个大写的、先天自足的“我”当作不证自明的出发点,而忽略了“我”之所以存在的发生学考察,或者说,丧失了对自我的命运体验,因而,外在的对象只能作为一种异己的“他者”而出现,由此就不难导致家庭以及社会公共领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契约化。
现代西方文化转向机体主义,尤其是对人的生存论研究开显了西方人一直遭到遮蔽的命运体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从此就可以走向“孝道”,事实上,“父慈子孝”仅只是命运体验的一种显性的心理现象,通过文化建构,它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独特的“宗教”,西方人则有可能诉诸另一种宗教式的文化样态来加以体验。当我们当前的孝文化建构中,既要站在民主自由的立场上批判其封建意识,又要张扬国人骨子里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孝爱意识,因此,一种惯常的做法是采取“一分为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式的所谓辨证研究,其本质不过是一种“合稀泥”式的折衷主义。将孝文化尤其是具体的孝爱行为当作一种“在场”的客观文化现象加以摆弄式的建构,并无助于问题的深入理解。真正要解决的是廓清主观的孝爱意识与客观的孝爱行为之间的分际,剖析孝爱意识的内在生成机制,如此方能保持一种坦然面对的心态,也恰恰是这种研究路径,使得中国传统孝道与现代西方机体生存论获得了比较研究的可能性,这本身就是孝文化研究的当代化、世界化。
参考文献:
[1]古希腊罗马哲学[M].上海:三联书店,1957.
[2]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3][荷兰]斯宾诺莎.贺麟译.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4][英]洛克.关文运译.人类理解论(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5][英]休谟.人性论(上)[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