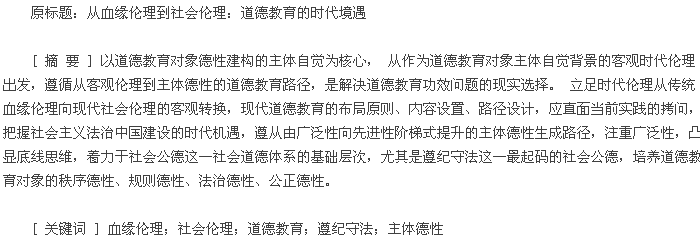
自殷周变革之际, 周人将以道德为内容的人文精神注入殷商的宗教生活,从而推动中华文化由“敬天”转向“敬德”、由“天道”转向“人伦”以来,历朝历代,无不如孔子所言:“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论语·学而》)。 因此,3000 多年来,整体而言,道德教育不仅一直位居我国教育的中心,成为我国教育的主题,而且在大多数时候都有效地发挥着传承中华文化、传播中华文明、传递时代主流价值观念的正向作用。 然而,直面当下,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以传递社会主流价值观、塑造社会理想道德人格为根本目标的道德教育,其功效时时面临实践的拷问。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新中国成立 66 年来,我们一直在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道德教育,但近三十年来,我国的信教人数却在不断增长,而且知识分子、高收入者、城市居民和中青年的信教比例不断增加。[1]
相反,英国广播公司(BBC)2011 年 3 月 22 日报道:宗教在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捷克、芬兰、爱尔兰、荷兰、新西兰、瑞士 9 个国家可能走向消亡。[2]不难看出,在我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道德教育没能为人们提供足够的精神支撑, 没能为人们提供足够的安身立命之本。面向这一时代课题,本文拟从时代伦理由传统向现代的客观转换角度,谈谈自己的理解,以期为我国道德教育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点浅薄建议。
1 血缘伦理:传统道德教育的立足点
道德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明确的,就是建构道德教育对象的主体德性。 而要建构道德教育对象的主体德性,离开道德教育对象的主体自觉,是不可能完成的。
在道德教育过程中, 教育者仅仅起到一个给予教育对象以道德认知的作用, 仅仅起到一个唤醒教育对象情感共鸣的作用。 在其中,至关重要的环节是,道德教育对象的情感认同,道德教育对象的自觉内化和外化,即在情感认同的基础上将认知的外在的伦理准则、 道德规范自觉转化为自身内在的道德意识、 道德信念和道德意志,进而将自身内在的道德意识、道德信念和道德意志自觉转化为外在的道德行为,累积为道德习惯。而要获得道德教育对象的情感认同及其自觉的道德内化和道德外化, 关键取决于我们的道德教育内容对道德教育对象的经历、体验和生活是否具有解释力,亦即是否贴近道德教育对象成长和生活的伦理背景、 伦理困惑和伦理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当前道德教育功效的式微,在学理上,根本性的问题在于,没有界划清楚作为道德教育背景的“伦理”和作为道德教育目标的“德性”;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我们总是基于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科学”的界定而把“伦理”和“道德”相混淆了。
在日常生活、日常交往和日常表达中,把“伦理”和“道德”这两个概念不加区分地使用,是没有大碍的,也是能够明白所要表达的意思的。 但在道德教育这一专业领域,如果不加以严格区分,就会导致问题无着落,内容无实指。于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指向的实实在在的道德教育, 虚化为一种空对空的理论传授和道德说教。结果,教者稀里糊涂地教,学者稀里糊涂地学,教了等了白教,学了等于白学。甚至更极端的,不教不学,倒还明白;教了学了,反倒糊涂了。
关于“伦理”与“道德”的区别,我们首先从一般用语层面来感知, 然后从学理层面来分析。 在一般用语中,形容人,用的是“有(没)道德的”,而不用“有(没)伦理的”;形容人的代际关系的错乱,用的是“乱伦”,而不用“乱德”;学科名称,用的是“伦理学”,而不用“道德学”;对伦理学内部结构的细分,用的是“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德性伦理学”,而不用“元道德学、规范道德学、德性道德学”. 学理层面,《礼记·乐记》:“凡音者,生于人心也;乐者,通伦理者也。 ”郑玄注:“伦,犹类也,理,分也。 ”将“生于人心”与“通伦理”综合起来看,“伦理”即人伦之理。因此,朱熹说:“正家之道在于正伦理,笃恩义”(《朱子语类·卷七二》)。道德呢?《礼记·曲礼》:“道德仁义,非礼不成。 ”“道德”与“仁义”并列,亦即一种基于内心信念的良好社会意识。因此,韩非子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在西方,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明确区分“伦理”与“道德”,并认为“伦理”比“道德”层级更高,“道德”是主观的,“伦理”是抽象客观意志和个人主观意志的统一。由此可知,“伦理”和“道德”至少存在这样三个方面的区别和联系:(1)“伦理” 更多强调客观的、外在的、社会的,“道德”更多注重主观的、内在的、个体的;(2)“伦理”更多表达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公共规则;“道德”更多表达一种内心信念和个人修养;(3)在伦理学学科体系中,“伦理”可以包含“道德”,但“道德”不能包含“伦理”,如果说“伦理”是一级概念,“道德”则是二级概念。
明确了“伦理”与“道德”的区别和联系,在道德教育实践中, 我们就能从道德教育对象的客观伦理关系出发,做到主观和客观相统一,而不是在“道德”这一主观论域兜圈子, 用一种指向未来的想象中的主观去面对另一种意指教育对象的想象中的主观。同样,明确了“伦理”与“道德”的区别和联系,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传统道德教育两千多年中传承中华文化、 传播中华文明、传递传统中国主流价值观的显着功效之所在。相应地, 也就能更清晰把握我国现代道德教育的出发点和着力点。
传统中国道德教育的体系设置,整体而言,以仁爱为原则,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君子人格为目标,以自我修身为方法。 考察自西周至晚清两千多年间的中国传统伦理结构,这样一套道德教育体系,恰恰是与形成于西周、延续至晚清的传统血缘伦理特质完全同构的。
自西周至晚清两千多年间, 传统中国尽管经历了数次朝代更替和社会变迁, 实质上这些更替和变迁只是停留于政治表层,只是一个“农民王朝”代替另一个“农民王朝”,其深层的宗法制社会组织形式、“家国”结构,以及作为宗法制社会组织形式和“家国”结构心理基础和文化支撑的血缘伦理和纲常名教, 基本上没有发生改变。 西周至晚清两千多年间的伦理文化,其核心基质,1别亲疏,并以此为基础在家族内部区分尊卑长幼,规定伦理关系,界划道德义务。因而,传统中国的伦理表述,诸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仁、臣忠等,无不基于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等自然联系和血缘关系及其放大的血缘关系---君臣关系。 正是因为传统中国的道德教育与作为其立足点的血缘伦理完全同质同构,因而其功效,整体而言,不折不扣。 传统道德教育,不仅历两千余年基本不变,而且深入人心。
2 社会伦理:现代道德教育的出发点
无论是从逻辑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都不难确认,道德教育的出发点,不是某个面向抽象未来的主观设定, 而是作为道德教育对象生活和成长背景的客观伦理关系、伦理困惑和伦理问题。针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形态家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词句”的脱离现实的自以为是,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 ”[3]
论及未来理想社会时, 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 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 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3]
作为现代道德教育出发点的客观伦理关系、 伦理困惑和伦理问题,其时代特质,表现为什么呢?显然,表现为“社会伦理”.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社会伦理”,不仅仅指社会的伦理,而是意指一种既不同于传统“血缘伦理”,也不同于主观“个体道德”的当今时代客观伦理关系和伦理特质。
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论语·学而》)传统“血缘伦理”建基于自然联系和血缘关系基础上, 因而呈现为一种由近及远的“差序格局”和等级序列。 尽管孔子主张,“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的“一言”,是“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其积极的表达方式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孔子这里所讲的“己”和“人”,如果不是对其进行了现代转换的话,在传统“血缘伦理”体系中,不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个体意义上的己和人,不是人与人的社会联系意义上的己和人, 而是家族意义上的己和人,是血缘关系意义上的己和人,亦即受制于因血缘关系而形成的远近亲疏关系中的己和人。 这一点,从孔子关于父亲偷了别人的羊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的主张就看得明白。 当然,从“上智”与“下愚”、“君子”与“小人”、“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妻”的伦理对立,更看得明白。 也就是说,传统“血缘伦理”中的“己”和“人”是不可通约的。 和作为其基础的血缘关系一样,传统“血缘伦理”“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也愈推愈薄”.[4]与传统“血缘伦理”完全不同,“社会伦理”超越血缘关系而建基于人与人的社会联系上, 表达的是可以通约的人与人的伦理关系, 是一种基于个体独立的人与人平等的伦理关系。 这是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