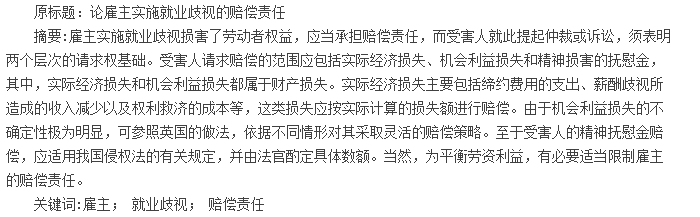
一、两个层面的请求权基础
对于雇主的就业歧视行为,除由公权力部门追究公法责任外,受害人可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财产损失或非财产损失的民事责任,而受害人为此提起民事诉讼,必须表明其请求权基础何在。就业歧视的受害人提起民事诉讼,应分别在两个层面上表明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
第一个层面的请求权基础为平等就业权保护规定( 或反就业歧视规定) 。这类规定为劳动法的组成部分,却并非仅存在于专门的劳动法文件中,比如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雇佣平等的规定。在我国,该问题的主要争议是,宪法规定能否作为就业歧视的定性依据,也即能够作为第一个层面的请求权基础。平等权和就业权属于宪法基本权,加之宪法的高位阶效力,援引宪法规定追究就业歧视的法律责任,自然成为一部分人的想法。有学者提出,“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反就业歧视的宪法诉讼机制,允许个人在其基本权利受到侵犯时提起宪法诉讼,实现宪法基本权利的司法化。”
周伟教授也指出: “禁止歧视规定位居宪法基本权利之首,在其他权利都可以直接约束私人的情况下,认为禁止歧视对私人行为没有直接效力的观点显然与宪法条款的规定不一致。”而张千帆教授却认为,“宪法可以禁止政府部门的就业歧视,而对普遍存在的私人部门的就业歧视却无能为力。”
在实践上,被称作“中国宪法平等权第一案”的蒋韬诉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就业歧视案中,原告的起诉理由是,该行对于应聘者身高的限制,违反了我国《宪法》第 33 条的平等权规定。不过,法院最终以该案不属于法定的受案范围和起诉条件为由驳回起诉,并未进行实体上的审理。
笔者认为,我国宪法规定极为抽象,无法作为法院的裁判依据,即便被法院援用于案件处理,具体裁判结论仍须通过适用其他法律得出,宪法规定仅起到增强裁判权威的形式意义。梁慧星教授针对“齐玉苓受教育权侵害案”就指出,山东省高院的判决并没有适用《宪法》第 46条的规定,实际适用的是《民法通则》关于侵权责任的第 106 条第 2 款的规定。
不仅如此,由于我国当前缺乏适当司法体制和机制的配合,宪法规定用于处理民事案件反而容易带来法院对于私权过度干涉等负面效应。最高法院也正是意识到对于齐玉苓案适用宪法解释的不妥当,于 2008 年以“已停止适用”为由将它废止。
其实,从我国的立法现状看,平等就业权保护的直接规定虽尚须完善,却已成体系。我国《劳动法》第 12 条规定: “我国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而2007 年颁布的《就业促进法》专章规定了公平就业,并明确规定受到就业歧视的劳动者可向法院提起诉讼。除此之外,在我国的《妇女权益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以及《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中也有相关的规定。这些规定可以认为是宪法规定的具体化,这样,对于就业歧视所造成的损失,无论受害人提起民事诉讼还是法院审理案件,实无必要援引宪法规定。
第二层面的请求权基础主要为侵权法或合同法的规定。考察一些国家的平等就业权保护立法就会发现,这些立法都将反就业歧视的积极行动措施、行政监督以及歧视界定等事项作为规范重点,而涉及赔偿责任的规定普遍相对简略,有的如我国《就业促进法》的规定仅授予当事人诉权。此意味一旦就业歧视被界定后,要适用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雇主的赔偿责任,如果该行为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就依据侵权法的规定提起侵权之诉,而如果构成违约行为或者缔约过失行为,则依据合同法规定提起违约之诉或者缔约过失之诉。
在英国制定的《1995 年残疾歧视法》第 8 条规定,判令被告对控诉人进行损害赔偿赔偿的数额应该根据侵权之诉中计算损害所运用的原则来计算,或根据( 在苏格兰) 违反法定义务的赔偿之诉中计算损害的原则来计算。我国立法中没有这样的规定,加之部门法划分对于法律思维的影响,致使歧视受害人提起赔偿诉讼不敢于援用民法的规定。在林某诉徐州徐工铁路装备有限公司案中,原告在起诉状中,直接以平等就业权受到侵害为由,要求雇主支付的赔偿金包括交通费、误工费以及房租费等共计 9470 元的经济损失和4 万元精神损害赔偿金。
本案受害人起诉的缺陷在于: 没有表明就业歧视的民事违法何在,致使请求权基础不够完整。就此而言,法院如不支持受害人的赔偿请求似乎也无可指责。
二 、财产性损失的赔偿
( 一) 实际经济损失的赔偿
实际经济损失主要包括缔约费用的支出、薪酬歧视所造成的收入减少以及权利救济的成本等方面的损失。缔约费用的损失发生的情形为: 劳动者已参与到雇主的应聘过程,除支付了简历制作费、交通费、住宿费等费用外,还投入了一定的本可用于工作的时间,而雇主以歧视性理由剥夺了劳动者的竞聘资格或者录用资格,使其落得前功尽弃的结局。由于缔约费用损失可以解释为信赖利益的损失,上述雇主歧视行为符合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学者主张的“引入合同法上的缔约过失责任”具有合理性。
在现实中,我国的一些法院基本上循着这样的思路审理案件,比如前面提到的林某诉徐州徐工铁路装备有限公司案。而在高某诉比德创展公司案中,法院判决清楚指出,比德创展公司违反平等就业原则,拒绝录用高某的情况下,应该赔偿高某的信赖利益损失,包括高某离职前 6 个月的工资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 1.9 万元。
当然,合同法上的缔约过失责任规定在此可以被直接适用,无需通过特别规定或者法律解释的“引入”方式。在我国,薪酬歧视所造成的收入损失是指劳动者因雇主歧视而不能享受同工同酬待遇的经济损失。我国《劳动法》第 46 条规定: “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
因此,同工同酬是雇主对于劳动者负有的一项法定义务,不能通过当事人的约定排除,也不能由雇主制定的规章制度排除。显而易见,在存在薪酬歧视的情况下,雇主应赔偿歧视受害人应得而未得的收入损失。2013 年 6 月,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法院就判决了一起薪酬歧视案,由原告朱某所在单位向其赔偿 10 年的工资差额 38 万余元。不可否认,在我国现实条件下,同工同酬原则的全面贯彻还面临不少难题,因此,不能将同工同酬泛化,薪酬歧视赔偿额的计算应限定在“同一用人单位的同一工作岗位上”的薪酬差额。
?至于“薪酬”的范围,不能狭隘地理解成定期支付的工资和津贴。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同酬公约》( ILO 第 100 号公约)的定义,它应包括因工人就业而由雇主直接或间接以现金或实物向其支付的常规的、基本或最低的工资或薪金,以及任何附加报酬。同时,由于劳动待遇为劳动合同的必备内容,同工同酬也是雇主对于劳动者负有的一项合同义务,相应地,薪酬歧视可作为违约行为对待。德国的《一般平等待遇法》第 7 条第 2 款就规定:
“雇主对雇员若有歧视行为,视为对合同义务的损害”。基于此,按照合同法原理,劳资双方可以通过集体合同或劳动合同约定就业歧视应承担的违约金数额或规定违约金的计算办法,以免除赔偿额计算的麻烦。美国已有这方面的立法例,依据美国的《1963 年同酬法》第 216 条( b) 规定,受到薪酬歧视的受雇者可获得“约定损害赔偿( liquidated damages) ”的救济。
至于权利救济的成本,如果属于法定之外的( 主要是诉讼私人成本) ,按照我国现有法律规定,须由就业歧视的受害人负担,这部分费用主要包括律师费用、交通费、复印费、咨询费、通讯费等。这些权利救济成本与就业歧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却并不是直接明确的因果关系,要求雇主进行补偿似乎在情理上有所勉强。然而,“为权利而斗争的问题,成了纯粹的计算问题。进行决断时,就必须衡量其利益和损失。”
如受害人付出的救济成本不能获得补偿,在涉及金额不大的情况下,会倾向于选择忍耐。这种状况既对受害人不公平,又会纵容了雇主的歧视行为,而再考虑到劳资关系的不平衡特性,让雇主承担受害人权利救济的必要成本有其必要性。2012 年,广州的温某因在求职过程中基于其性别而被拒录,通过当地劳动行政部门的调解,广州宝勒商贸有限公司赔偿了温某电话费、快递费、交通费等投诉产生的费用共 600 元。
就业歧视的受害人获赔法定之外的救济成本,在我国确实难得一见,因此,即使该赔偿是行政调解的结果,也具一定的示范意义。另外,美国这方面的做法可供借鉴,美国的《1964 年民权法》规定了胜诉方可请求支付律师费,而《1991 年民权法》进一步规定,胜诉的被歧视者除请求支付律师费外,还可请求专家劳务费以及其他诉讼费用。
( 二) 机会利益损失的赔偿
这里的机会利益损失指由于雇主实施的歧视行为,劳动者失去特定的工作机会或者职业发展的机会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劳动力蕴藏于人的体内,是人体力与脑力的总和,其价值在与生产资料结合的动态过程中实现,为此,劳动者必须和雇主建立起劳动关系,否则,劳动力价值也不能被劳动者自己保留,会被闲置而形成浪费。再者,劳动力供求失衡为我国面临一项重要难题,严峻的就业形势将长期持续,劳动岗位成为一类稀缺资源,特定劳动关系的利益化严重。
如此以来,“失去了工作机会,意味着失去了获得工作报酬、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劳动权利的机会。”
对于在职劳动者而言,劳动力的使用效果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工作经验、资历以及他人认可度的提升而持续增加,而如劳动者不能公平享有职业发展机会,虽然通常不会影响其生存,却无疑会影响到其收入水平。因此,“赔偿应依据就业歧视发生于求职、工作、以及解雇等不同阶段而有所变化,其范围应涵盖机会损失( loss of opportuni-ty) 、报酬及其增加额损失( likely increments) 以及就业市场上一般性机会损失。
?机会利益损失的不确定性较为明显。失去机会意味着应然情形已无法验证,那么,机会利益损失只能建立在可能的假设之上,无法依据现实信息予以准确判断。应当认为,权益保护不应以难度的大小为选择标准。“如果机会的实现具有现实可能性,则机会的损失也构成确定的损害,应予赔偿。”
?当然,需要灵活对待上述的“最高指导原则”。在美国,歧视受害者可获得的救济措施之一为: “当恢复原状不可行时( 如只有一个岗位,除非解雇现有职工否则无法恢复原状) ,则可以未来工资替代。当然未来工资的标准存在极大的任意性。原告的减少损失义务也同样适用于未来工资。”
传统上,英国法庭通过“各项可能平衡( the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 ”方法计算预期利益损失,就是评估歧视受害人职业发展的各种可能路径,得出单一的最可能的结果,相关的收入损失( associated loss of earnings) 就是应赔偿额。后来,劳工上诉法庭( the Employ-ment Appeal Tribunal) 认为这种计算方法存在缺陷,又倡导采用“预期损失( expected loss) ”的计算方法,就是首先预测各种可能的职业发展路径,对于每条路径以及未来盈利的相关损失进行评估。不同的可能性被结合在一起进行“预期损失”的计算,再乘以每项损失的概率,然后得出预期损失或平均损失。
我国有学者提出,可以从实际损失的角度转换到预防侵害行为的角度来解决机会利益损失的赔偿问题。
该主张所提供的技术思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过,如缺少可能损失的估算结果,那么预防侵害行为所需赔偿额岂不仍为未解难题。笔者认为,就我国现实而言,可参照英国劳工上诉法庭倡导的赔偿办法,并根据就业歧视的不同情况对于受害人的机会利益损失采取相应的赔偿策略。一是对于求职者因歧视而被拒绝录用的情况,可将机会利益损失作为缔约过失的赔偿内容之一,而具体赔偿额则依据下列个案因素酌定: 求职者的文化水平、专业技术资格、工作资历; 竞聘获胜的机率; 所参聘工作岗位的受欢迎程度和重新获得类似应聘机会的可能性; 可领取的失业救济金,等等。二是对于职业发展机会损失的情况,如果劳动合同有约定的,则依据约定赔偿,否则,由法院考虑受害者的职业竞争力、收入水平受影响状况、歧视行为对于未来求职的不利影响以及换回损失的可能性大小等因素综合确定赔偿额。三是对于歧视性解雇的情况,受害者可以雇主实施违法解雇为由,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请求雇主支付两倍的经济补偿金。按笔者的理解,这里的两倍经济补偿金除体现对于雇主违法行为的惩罚外,还包含补偿机会利益损失的成分。还需要说明的是,如果雇主的招聘简章或者广告包含有歧视性内容,对于受影响的具体个人而言,也不能否认其机会利益损失的存在,然而,依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受害人可就此向行政机关投诉,却不能提起民事赔偿诉讼。
三、精神损害的抚慰金
王泽鉴教授认为: “劳动关系不仅是以‘劳力’与‘报酬’之交换为核心而建立之财产关系,同时也具有人格上之特性; 劳力不是商品,劳动者人格之尊严及合理之生存条件,应受尊重与保护。”基于此,雇主虽然享有用工自主权,但将与工作无直接关联的因素作为人事决策依据,就会伤害到受歧视者的平等感,进而使其产生卑微感和羞辱感,亦即“产生一种他们的人格与共同的人性遭到侵损的感觉。”
不仅如此,就业既是劳动者谋取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手段,也是赢得社会认同和尊重的重要途径,而就业歧视严重阻碍了这两个目标的实现,导致劳动者产生悲观和失落等不良情绪,甚至对于未来生活完全失去信心。
可见,就业歧视不仅损害了受害人的财产利益,还损害了受害人的精神利益。精神利益固然是抽象的、无形的,适当的金钱赔偿能够补偿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在这一点上,财产损害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虽然有所不同,但就填补损害的基本功能而言却是一致的。”
从一些国家(地区)的反就业歧视立法看,普遍对于精神损害赔偿有直接的规定。德国的《一般同等对待法》第 15 条规定: “男性或女性雇员可以就一项非财产损失要求以金钱的方式得到适当赔偿。”英国的《1995 年残疾歧视法》第 18 条规定: “为避免疑问,就此宣布: 如果歧视属于本部分规定的违法方式进行的,那么不论是否包括其他项目的赔偿,损害赔偿均可包括对感情损害的赔偿。”依据美国的《1991 年民权法》第102( b) ( 3) 的规定,在雇主实施蓄意歧视情况下的,起诉人可从雇主那里获得包括未来金钱损失、情感痛苦、精神或者肉体上的痛苦、搅扰、精神上的极度痛苦、丧失生活的乐趣以及其他非金钱损失判决给付的补偿性损害赔偿金。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相关立法也有这方面的规定。香港的《性别歧视条例》第 76 条规定: “为免生疑问,现声明: 就违法歧视作为或性骚扰而判给的损害赔偿﹐不论是否包括其它项目的补偿﹐均可包括对感情损害的补偿。”而我国台湾地区的《性别工作平等法》第 29 条也规定:“受雇者或求职者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由于我国的相关立法没有这方面的直接规定,在具体个案中受害人应否获得精神损害赔偿以及如何确定赔偿数额等两个基本问题,则需要完全依照我国侵权法的规定进行确定。林嘉教授指出: “一般劳动者在就业中受到歧视的,可以认定用人单位侵犯劳动者作为民法上的人所享有的一般人格权,受侵害的劳动者可以提起侵权行为诉讼,要求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称《精神损失赔偿解释》) 第 8 条以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22 条的规定,精神损害达到“严重”程度应为受害人获得赔偿的基本条件。“严重”是较为抽象的表述,在实践中不容易把握,不过,笔者并不赞同去除该限制,曾世雄教授就此已作出清晰的解释,他认为: “非财产上不利益仅痛苦方有获得救济可能,不方便、不愉快、不适宜不能获得救济。……至不方便、不愉快、不适宜不能获得救济,原因无他,盖不方便、不愉快、不适宜,发生频繁,情节轻微,本诸繁微不规范之原则,其不能获得救济,自属当然。”
然而,应基于就业歧视的精神损害特性及其表现,确定与之相应的“严重”与否的判断标准。笔者认为,这些判断标准应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受害人基于相同的歧视因素已受社会偏见的困扰。由于相同歧视因素的存在,受害人之前已承受了一定的来自社会的精神压力,受害人心理通常非常敏感和脆弱,易于受到伤害。据此判断,我国现实中出现的属相歧视以及姓氏歧视,一般不能认为被歧视者受到的精神伤害达到严重程度。第二,歧视对象为特定化的个体或人数较少的群体。现实中,雇主设置的招聘条件中含有歧视性内容,歧视对象为某一类别的抽象人群,具体个人所受到的精神伤害一般不会达到严重的程度。第三,雇主具有恶意的主观状态。雇主恶意的主观状态不仅本身具有明显的可责性,还表现出对他人的极其不尊重,对他人情感的造成剧烈冲击。
精神损害的赔偿额应由法官酌定。“精神损害不能直接以金钱来准确计算,精神损害赔偿不可能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害给予客观、全面、精确的赔偿,而只能综合各方面的情况,确定一个大致合理、可行的数额。”同时,也应对于精神损害赔偿设置一定的标准,以制约法院的自由裁量权。王泽鉴教授指出: “慰抚金之表格化或定额化,除具有使慰抚金客观化之作用外,尚可减少争论,对于诉讼外和解,甚有助益,自不待言。”
比如德国的《一般平等待遇法》第 15条规定: “对于非财产性赔偿,如果男性或者女性雇员在无歧视的情况下不会被调职,那么赔偿数额在不调动职位的条件下不得超过 3 个月的工资总额。”这里的赔偿限额不仅限定了雇主的赔偿责任,还能够为法院确定具体赔偿额时提供参考。就我国而言,法院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额时,应将《精神损失赔偿解释》第 10 条的规定作为基本依据,同时还要考虑到受害人精神痛苦的内隐性和长期性、受害人的弱势地位以及我国就业歧视的严峻性等一系列特殊因素。
四、赔偿责任的限制
法律在对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同时,还应避免让雇主承担不适当的赔偿责任,从而造成新的不公正,并影响到雇主的生产经营活动,而这反过来又会对劳动者产生不利影响。在各国的侵权法和合同法中,会有赔偿责任的限制性规定,这些规定同样适用于就业歧视纠纷。除此之外,一些国家( 或地区) 的反就业歧视法在赔偿数额以及诉讼时效等方面也有限制雇主赔偿责任的内容。
赔偿数额的限制一般是规定就业歧视的受害人可以获得的最高赔偿额,不管实际损失情况如何,法院裁决的赔偿数额均不得超过规定的标准。数额限制可能针对精神损害赔偿、机会利益损失以及惩罚性赔偿等特定的赔偿项目。比如依据美国《1991 民权法》第102 条( b)的规定: 对于判决给付的未来金钱损失和非金钱损失的经济补偿金以及惩罚性损害赔偿金的金额,对于每个起诉人,不应超过依照雇佣规模所设定的 5 万美元至 30 万美元的数额。也可能针对赔偿总额。比如香港的《性别歧视条例》第 76 条( 7) 规定: 在雇佣范畴的歧视及性骚扰歧视的,申索人的损害赔偿额不得超逾 15万港元。瑞典的规定较为特殊,该国主要的几部反歧视立法都规定,雇主违反禁止性规定歧视雇员,应当给雇员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而同时又规定依据“合理原则”,可以减轻或免除雇主损害赔偿责任。
诉讼时效是对就业歧视的受害人行使赔偿请求权的期限要求,雇主可以此免受“历史债”的困扰。大陆法系国家(地区)的民法典基本上都有诉讼时效的规定,歧视受害人的赔偿请求权应受该规定的约束,不过,基于就业歧视的行为特性,仍需对于受害人行使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作出专门规定。我国台湾地区的《两性平等法》第 30 条规定: “损害赔偿请求权自请求权人知有损害及赔偿义务人时起,2年间不行使而消灭。自有性骚扰行为或违反各该规定之行为时起,逾 10 年者,亦同。”德国的《一般平等待遇法》第 15 条则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根据歧视受害者提出的索赔要求必须在 2 个月的期限内以书面形式提出,除非劳资双方另有协议。这一期限始于申请之时或者职场晋升被拒绝之时,或在特殊的歧视情况下始于男性或女性雇员获悉歧视之时。
此外针对雇主的援引其他法律法规的索赔要求仍然成立。”
以上赔偿限制反过来被认为可能将就业歧视的受害人置于不利境地,使其所遭受的损失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赔偿。欧盟法院在 Mar-shall 案中就指出: 设立获得赔偿额的最高限额和拒绝支付利息都没有正确实施第 6 条的规定( 即同工同酬的规定) ,因为这种限额限制了通过适当补偿损失和伤害作为歧视性解雇结果来保证真正的平等机遇要求,并与赔偿数额保持一致。
正是该案的判决结束了英国对于不公平解雇和歧视的赔偿不超过 1. 1 万英磅的限制。另外的例子,奥巴马总统 2009年签署的《莉莉·丽贝特公平报酬法案》修正了美国《1964 年民权法》第 7 条的规定,即受害者的权利救济请求需要在 6 个月内提出,以使雇员可在因性别、年龄、种族而遭受不公正待遇后任何时间内对于雇主提出索赔请求。
当然,上述全盘否定的做法并非较妥当的处理方式。其实,欧盟法院否决一些成员国对于数额的限制,主要针对的是成员国赔偿限额过低的状况,比如在 Von Colson 案和 Harz 案中欧盟法院认为,赔偿被单纯限制在偿还旅行费用的象征性数额内,这不符合第 6 条的规定。并且,欧盟法院后来也考虑到了赔偿的适当问题,认可了在特殊情况下限定赔偿额的合理性。
从美国对于莉莉·丽贝塔案的争论看,批评者的主流观点并未否定时效存在的必要性,只是认为“较短的时效限制与普遍接受的‘社会标准’相冲突,加之雇主规定禁止雇员谈论薪水或者相互比较薪水,使得雇员在《1964 年民权法》第7 条的限制下,会失去维护他们权利的机会。”
而奥巴马之所以签署《莉莉·丽贝特公平报酬法案》,很大程度上是要兑现当初为讨好妇女阶层所作出的竞选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