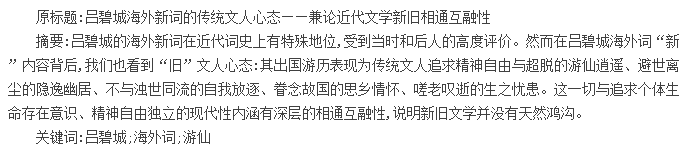
吕碧城海外新词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面世后受到高度赞誉,孤云(潘伯鹰)在《评吕碧城女士〈信芳集〉》中说:“其在诸外邦纪游之作,尤为惊才绝艳,处处以国文风味出之,而其词境之新,为前所未有”,吴宓也大力赞同孤云的评价。朱庸斋《分春馆词话》赞叹说:“缕述异国事物,开拓前人未有之词境,雄奇瑰丽,美不胜收,使人耳目为之一新。”钱仲联在《近百年词坛点将录》中称吕碧城“中年去国,卜居瑞士”后所作词是“前无古人之奇作”。这些评价很精当,可惜都没有充分展开。
21世纪以来学界对吕碧城海外新词研究更为深入细致,一方面认为吕碧城海外词“既拓宽了词的表现范围、又符合梁启超‘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界革命’”,“具有超越传统的新气象”。另一方面,在高度赞赏同时,也敏锐的捕捉到一些值得深思问题:吕碧城海外词有着“飞扬超拔的恢弘气势”,但又“终究无法消弭羁旅生涯所带来的寂寞与倦怠”,“任何异国现象都可以用无所不包的中国传统文化来加以吸收和处理”;或认为“其作品总体上新思想新意境不强”,“以新旧来评价吕碧城海外词,无论新瓶装旧酒,还是旧瓶装新酒都不合适”,更有一些学者为吕碧城词未能进入现代文学领域而遗憾。
赞誉或批评的背后其实都有潜在观念,即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对立、割裂和绝对化,赞誉者强调其“新”,而未充分认识传统文人心态对吕碧城海外新词创作所产生的本质性影响;批评者则从五四新文学反传统主义立场出发,认为吕碧城是“旧”文人,因而有所谓“遗憾”之叹。本文侧重探讨吕碧城海外新词的传统文人心态,以及这种心态与现代性内涵相通互融。
吕碧城生于1883年,她28岁以前的人生是在前清度过的,接受的是传统文化教育。此后,近代西学的影响使她具有鲜明的新国民、新女性的自由独立意识,并积极参与了近代女性教育、改变女性命运的社会实践,她热烈向往西方文明、追求突破旧有的生活模式,因而才有欧美旅居之举。然而,她深层的文化习性、价值理念以及文学审美趣味已经深植于传统文化之中,传统文人人格、文化心态已经形成,很难因为外部社会生活的变化而改变,这一点或许连吕碧城本人也未必自觉意识到。正因如此,她的海外新词最能体现近代文学的典型特征:既接受和拥抱西方新事物新生活,但又以传统文化习性、文化心态去吸纳、投射这一切。
仙游:以异乡为仙境游,在中国古代有悠久的历史,最早表现对现实不满而出游的反而是女性,《诗经·邶风·泉水》表现一女子出嫁后生活不幸福欲归娘家却不能,因而产生了“我心悠悠,驾言出游,以泻我忧”的出游心理,这里的出游表现为对个人感情的宣泄。而后,“游”又表现为君子应有高远的志向、宽广的视野,孔子云“士而怀居,不足为士矣”、《楚辞·远游》有“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形穆穆以浸远兮,离人群而遁逸”。“远游”被赋予对精神与道的追求意味,成为摆脱世俗沉浊污秽的精神行为。
中国古代的“游”与“仙人”“仙境”总是密切关联,如《穆天子传》卷三较早记载远游故事的是周穆王西征遇西王母,并与西王母在瑶池把酒言欢,为后世津津乐道。远游遇仙为历代文人所向往,并成为传统诗歌的重要内容之一,汉代有“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导我上太华,揽芝获赤幢”(《长歌行》),唐朝李白有“仙人浩歌望我来,应攀玉树长相待”(《怀仙歌》)、卢照龄也有“若有人兮山之曲,驾青虬兮乘白鹿,往从之游愿心足”(《怀仙引》),远游遇仙是中国古代文人对精神自由的向往。
吕碧城海外词常常直接称海外游历为“仙游”:“且休管、花开落。仙游一枕,世外斜阳西匿,柳边风铃未制。”
“仙游如梦初遽”“雪山长往,看瑶光多霁,此是仙源避秦地”。她有八首联章体《望江南》组词写海外生活和海外新事物,每首词以“瀛洲好”开头,“瀛洲”是汉代东方朔《十洲记》所记载仙人居住之地,是中国古人构想的海外仙境。吕碧城对异国他邦的山水自然、人文事物无不感到无比新奇喜悦、心旷神怡,在瑞士,她所居之楼正对欧洲第二大雪山———白琅克冰山,每日可欣赏雪山日出,《齐天乐》词即写此情景:“光满遥峰,春溶碧海,慵顾姮娥梳洗”,仿佛身在仙界,与姮娥为伴,有飞离尘世之感。她常常运用一连串古代神话典故,创造出光明澄澈的神仙境界:“平澜叠翠,惊泷泼雪,广寒飞下冰夷。
娥驭俊征,晶轮艳转,众流澎湃相随。云叶想旌旗,似群真跄济,羽葆轻移。旧侣难招,佩环何处怨来迟。”“尘寰小住为宜,望神山缥缈,白奈花零,紫兰人杳,蕊宫无限凄迷。”
这首《望海潮》词作于1928年至1929年初,吕碧城时居瑞士,在她眼里日内瓦碧湖雪山就是人间的月宫仙境,使人心清意远。在吕碧城笔下,西方现代建筑也是仙境中事物,日内瓦铁网桥是仙界的鹊桥“步虚仙屧传清响,度星娥、鹊群休傍”,仿佛有仙女在桥上走过;巴黎铁塔也是“云烟飘渺、远共海风、吹入虚步”“借云斤月斧,幻起仙宇”“问谁将、绕指柔钢,做一柱擎天,近衔羲驭”。海外游历使她心境无比欢畅、自由自在、精神飞扬,如同在仙界一般。
以旅居海外为仙游,固然由于异域新奇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象的强烈激发,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吕碧城在海外摆脱种种现实的困扰与束缚,在完全陌生的时空里,以“游客”或“旁观者”身份,观照生活,达到对现实世界的暂时出离。这种“出离”使她获得极大的自由,充满飘飘欲仙之感:“似壶公幻就,蓬瀛缥缈,迷蜃市,通仙境。”
异国的人情交往单纯随兴、闲散自由,超越现实功利,没有旧的人情瓜葛牵绊,她有一首《绛都春·日内瓦湖习桨》词记载一次与日内瓦陌生少年游湖情景:“烟霞无价,供欣赏、说甚他乡吾土。几许梦痕,濯入沧浪慵回顾。仙踪况许壶天住。”湖光山色与异国人情交往的洒脱,使词人怡情尽兴,如入仙境,“何处飞仙,指风送、东溟三万。尽相逢一笑,莫论主宾,休问胡汉”,心中完全消弭了国界,身在异乡如仙乡。
这种以异乡为仙乡的逍遥的境界,其实也是中国古代游仙文学的折射。游仙文学是中国古代文人试图超越时空局限的而追求生命升华的祈望,是对人间俗务不满而试图摆脱束缚的心理,借“游仙”的文学想象而远离尘世,追求理想的生活乐园,表现任化自然、回归自然、超越个体生命的终极目标,借此展现精神的自适与舒展,是古代文人精神栖居的场所、自由理想寄托的载体。“游仙”也意味着宣布自己是自由的、是摆脱了种种羁绊的独立的精神主体,是积极追求自我价值的实践。吕碧城海外词“仙游”的文化内涵恰恰是这种传统文人心态的表现,呈现为精神的自由舒展,超迈逍遥,气宇轩昂,而这与追求精神自由的现代性内涵不是恰恰相通的吗?
悠游:以海外为隐逸隐逸的文化传统,使古代文人或多或少地摆脱了“政统”的限制,从而获得人格独立与自由。“逸”是一种超凡脱俗、不拘法度常规、自由自在的状态。隐逸人格精神,实际上成为了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始终对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吕碧城传统文化浸润深厚,其父吕凤歧有着极为浓厚的隐逸倾向,他自号为“石柱山农”,50岁就在安徽六安购置田庄,拟辞官归隐。吕碧城也有着隐逸文化趣向,早在1913年《游钟山和省庵》诗中就写道:“烟霞暧暧渺仙踪,招隐人间有桂丛。”她1917年七月登庐山时曾写《沁园春》词,词前小序云:“丁巳七月游匡庐,寓FairyGlen旅馆,译曰‘仙谷’高踞山坳,风景奇丽,名颇称也。纵览之余,慨然有出尘之想,率成此阕。”
“慨然有出尘之想”是中国文人心灵深处的集体无意识,同样根植于吕碧城心灵中。她在海外旅居,内心深处其实是追求避世离尘。她在《鹧鸪天·戊寅二月重返阿尔伯士雪山》词中写道:“寥落天涯劫后身,一廛重返旧时村。犹存野菊招彭泽”,显然要像陶渊明归隐田园一样,以海外寓居为“归隐”;《祝英台近》是一首题画词,可能是她自己的一幅画作,词前序云“自题寒山独往图,为归隐欧西阿尔伯士雪山之作”,明确表示了自己寓居瑞士是“归隐”,词中有“一往心期,长于此终古”之句,可见她是打算长期隐居于此的。
吕碧城海外词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写海外隐居的怡然逍遥、离尘忘俗、悠然自得。寓居瑞士时,她曾写过一首《浣溪沙》词:“珍侣嘤嘤不避人,三年山馆伴芳邻。丽湖残梦付行云。信手花间招翠羽,微吟波面引文鳞。机心消处尽天亲。”词后自注:“予居瑞士数年,鱼鸟皆识,每观予则追随求饷。日内瓦湖原名丽曼湖。”
她以隐者恬然自适的心态,与鸟鱼为友,消尽机心,她的海外词反复描写鱼鸟之乐:“尽狎江湖凫雁,遍瞻万国衣冠”“闲中消岁月,有升平花鸟,与人同乐。锦羽忘机,琼枝索笑”“双占水天光上下,一凫对影成图画”……这些均与中国古代与鸥鹭结盟、忘却机心的隐逸文化精神意趣相同。
隐逸者的悠游闲适心态对自然界万物有着更为细致的品味欣赏,尽情享受大自然之美,作为女性词人,吕碧城最关注的是花,她的海外词中写了大量的赏花词:《江城梅花引》写日内瓦湖畔樱花如海的盛况;《翠楼吟》写瑞士水仙花长在陆地情景:“艳骨冰清,仙心雪亮,羞看等闲罗绮,柔乡羁素袜,指洛浦、芝田双寄”;《琐窗寒》词瑞士日内瓦芒特儒湖畔高大玉兰树“湖畔玉兰高树,婆娑巨朵,千百掩映,遥峰玉宇,饶华贵气象。予每春来此看花,已三度”;《风流子·芍药》词“长安看遍后,瀛洲外、重见靓妆浓”“不道万里重蓬远,一笑相逢”。在隐居者笔下异乡山水呈现出宁静安详、世外桃源的境界这类海外词内在文化品格完全是中国古代文人的隐逸心态。
隐逸文化的人格精神特征表现为对现实抱有一种疏离、怀疑、厌恶、批判甚至否定的态度,总是力求与人伦群体保持距离,极为看重自己的人格尊严,心气高远。吕碧城归隐海外,是有其复杂原因的。首先,是对当时国内政治混乱、社会浊暗现实的极其不满。她曾对老友费树蔚纵谈时事,表示要漫游欧美不再回国,她在《遣兴》诗中云:“客星穹瀚自徘徊,散发居夷未可哀。”
“散发夷居”是“子欲居九夷”(《论语·子罕》)、“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表达,居夷浮海只是孔子对当时现实感到失望而表现出愤世避世态度而已,都是远离浊世、心志高远的精神追求,此点儒道皆同。史料虽然没有记载吕碧城当时与费树蔚“纵谈时事”的具体内容,但显然是对当时中国内忧外患政治局面的忧心忡忡,才决心归隐海外、避世离尘。其次,在中国落后黯昧的社会世情、人际关系网络中,吕碧城感到困扰、郁闷、压抑、愤懑不平。她曾在《浪淘沙·拟李后主》中说:“人间无处可埋忧,好逐仙源天外去,切莫回头。”
对吕碧城出国前的处境,严复最为同情与理解,他在《与甥女何纫兰书》中写道:“此人(指吕碧城)年纪虽小,见解却高,一切陈腐之论不啻唾之,又多裂纲毁常之说,因而受谤不少。初出山,阅历甚浅,时露头角,以此为时所推,然礼法之士疾恨如仇。自秋瑾被害之后,亦为惊弓之鸟矣。现在极有怀谗畏讥之心,而敛之又往往加以评骘,此其交所不终也。即于女界,每初为好友,后为仇敌,此缘其得名大盛,占人面子故。往往起先议论,听者大以为然,后来反目,则碧城常作如此不经意论,以诟病之。此处世之苦如此。”
年,吕碧城与师友兼恩人英敛之、傅增湘关系破裂,她的情感受到伤害,人与人之间沟通之难,使她感到困扰失望。
吕碧城个性极为率真,她极不愿意屈从自己的意志来维持友谊,为了真诚地活着,她需要逃世,远离世俗喧嚣,在遥远的的异国他乡寻找内心的清净安宁。第三,“家”对于吕碧城来说是深深的创伤。吕碧城12岁时父亲突然病故,恶戚之所以理所当然抢占家产也是宗法制国情所致,母亲及姐妹差点送命。后来母女们不得不投奔外家,寄人篱下,这在她的心灵上烙下深深创伤。
母亲去世后,她哀伤地写道:“荆枝椿树两凋伤,回首家园总断肠”“登临试望乡关道,一片斜阳惨不开。”尤其是小妹妹贤满夭折于厦门、大姐惠茹病故、与二姐吕美荪失和,她的心中已经彻底失去了“家”的温暖,《沁园春》即云:“家山梦影微茫,记摘蔓燃萁旧恨长。”
“家”的破碎使她内心深处有难言隐痛,她有着“孤零身世净于僧”的痛切之感。
家国如此,更促成吕碧城隐居海外、避世逃俗了,“异邦消得凭栏,身闲便觉天宽”。吕碧城极为崇尚个体心灵真诚不欺,不愿媚俗,因此往往曲高和寡、难以致世,而这恰恰是隐逸文化人格的特征。隐逸的离世色彩具有非功利的精神向度,最富于诗性特征。隐居海外使吕碧城暂时摆脱了国内世情的喧啸嘈杂、日常琐碎的困扰,走向宁静、冲淡直至孤寂,心灵恢复本然状态,审美焦点集中在大自然的自由生命情态,她海外词中这类作品在文化品格和艺术趣味上都与中国传统文人的隐逸诗词趣味和风格极为相似,表现出空灵玄远、冲淡幽静的审美特征。这种疏离群体、追求独立尊严、享受自由生命的意识与现代性的人文精神亦有着内在相通之处。
远游:放逐与思乡吕碧城在海外游历、旅居,一方面感到精神自由、如历仙境,远离尘嚣、隐居悠游,但另一方面,也伴随去国远游者的孤独与漂泊感:“寒鸟绕树,哀蝉啼叶,飘零身世同我汝”“仙居占断湖角。未信俊游堪恋,风怀倦羁客”。这种羁旅行役之情甚至让词人后悔出国:“苍云换世,去国疑非计。”
吕碧城在很多海外词中称自己寓居海外是屈原远谪,有“悲乡远”意味。她在《木兰花慢》词小序中称自己客居海外是“远谪异国”,并伴随人生寥落、聚散无常的沧桑感;《减字木兰花》词前小序中说“友人来书谓予客海外,有屈子行吟之感”;《洞仙歌》词也以寓居海外自比屈原。她的海外词反复以“屈子行吟”自喻:“千秋悲屈贾,数到婵娟,我亦年来尽堪拟”,“何处避秦人,行吟独苦辛”“倦旅天涯,依然憔悴行吟”。可见,吕碧城旅居海外充满古代文人自我放逐的心态。
自我放逐的远谪心态,即含有远离浊世的孤高自诩,也伴随着对故土强烈的思念,正如屈原的大部分楚辞,都融铸了浓重的思乡念国、故土难忘之情:“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吕碧城在海外旅居期间,对故国梦魂萦绕,她会无端在梦中听到故国音乐,在《还京乐》词前小序中说:“梦闻故国歌声,极顿挫苍凉之致,感而赋此。”旅居海外虽然衣食无忧,但对祖国陷于战乱危难之中,忧心忡忡,茫然不知何以改变这一处境:“浪迹遐荒,万方多难此凭栏。孤吟去国,杜陵烽火,庾信江关”“梅枝难寄,乡心凄黯,笛语哀顽。”
“故国愁云横远碧,莫问梅枝消息”。她有一首《高阳台》词,写她接故国友人书,诉国内兵燹之苦,心情十分沉重:“几番海燕传书到,道烽烟、故国冥冥”“奈万家春闺,悽入荒砧,血涴平芜,可堪废垒重寻。”内心涌动着对故国战乱纷扰的深深忧虑,然而救国无方,只能行吟憔悴。长年漂泊在外、孤独无依,吕碧城尤其在中国人重要的节日之际,思乡之情更为深切。
1929年除夕,是吕碧城重返欧洲旅居瑞士第三年,她遥想国内千家万户此时正老少团圆、围炉守岁,内心莫名惆怅,写下《凄凉犯》词:断霞吹霰胡天晚,残年尚弄凄丽。山横玉垒,塔明金籀,感怀殊异。长街裙屐,望来去、仙仙魅魅。问何心、飘零萍梗,艳说避秦地。除夕三番矣,习与时迁,语随乡易。锦囊诗料,更兼收、十洲澜翠。故国今宵,定桦烛、千家无睡。对蛮花、自剪红绡罥蒨蕊。
在国人的除夕之夜,她“感怀殊异”,尖锐的异国飘零感格外深深刺痛吕碧城,尽管已经习惯异国生活方式和语言,但远离故土,仍然使她莫名惆怅,因此,满街上异国女子曳地长裙来来往往,是仙?是魅?她感到恍惚,身在异乡有生命被悬浮于空中的虚幻感,她遥想“故国今宵,定桦烛、千家无睡”,而自己在异国他乡只能孤独地“对蛮花、自剪红绡罥蒨蕊”!中国文人对故乡的情感,往往在某些特定的时间被激发,比如秋夜、日暮、重阳、中秋、除夕,而除夕是其中最易诱发思乡伤感的,“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愁鬓明朝又一年”(高适《除夜作》),念土思乡的情怀在中国古代几乎萦绕着每一位文人墨客心头,成为中国传统文人心态的特征,也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母题。然而,思乡念土之情是文人精神的最高体现,无论新旧文学、新旧文人都无不如此,台湾现代诗人余光中即是典型代表。
倦游:忧生与叹老吕碧城海外词的思乡之情又是极为复杂矛盾的,她知道自己是无“家”可归的,“孔雀徘徊,杜鹃归去,我已无家”“家何在?苏武不须归”。她渴望回归故土,然而当她真的回国时又充满陌生与失望:“仙心已倦沧溟梦,愁山怨水飘零凤,何处是檀栾,琼楼玉宇寒。劫灰金塔下,白首胡僧话。一样感沧桑,还乡更断肠。”
透过这些词,我们触摸到吕碧城心无所安的幽微思绪,在异域,她感到“愁山怨水飘零凤”,心境凄惶黮黯,回国则“还乡更断肠”;海外旅居她心系故土,回乡却又很失望:“归来临旧圃,荆棘仍如故”;故乡使她感到恍若隔世的陌生:“十载重来,黯前游如梦,愰然辽鹤。”
由此可见,吕碧城的“思乡”其实还隐含着对精神家园的寻求和皈依,并且融入了对人生无常、生命与时间流逝的无奈、对天地宇宙浩渺不可知的伤怀:“叹浮生,万缘波逝,更无一事可还珠。”这种心态其实是中国古代传统文人“生之忧患”心态的表现。这种“生之忧患”在吕碧城海外词中表现为对“时间”的焦虑,对老之将至、生命无常的隐忧。漂泊、忧生与叹老几乎成为吕碧城海外词后期作品的重要内容,“飘零休诉,人远天涯,树老江潭。”“南冠客,慵理鬓边丝。”
《破阵乐》词描写词人登上欧洲阿尔卑斯山雪山所见壮阔情景,是吕碧城海外词中最豪迈劲健、慷慨激越的作品,然而却充满感伤意味,词的上阕可谓气势恢弘、雄奇壮丽:“混沌乍启,风雷暗坼,横插天柱。骇翠排空窥碧海,直与狂澜争怒。光闪阴阳,云为潮汐,自成朝暮。”下阕更是无比骄傲豪迈:“问华夏,衡今古,十万年来空谷里,可有粉妆题赋?写蛮笺,传心契,惟吾与汝。”
正如她在词前小序中所言“东亚女子倚声为山灵寿者,予殆第一人乎?”这种豪纵的确是千年词史也不多见!但是,词的结尾却写道:“省识浮生弹指,此日青峰,前番白雪,他时黄土。且证世外因缘,山灵感遇。”表现的是人生短暂、一切变幻无常,人生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的“生之忧患”。
这种面对宏伟、永恒大自然景象而生起生命短暂渺小的沉郁感叹,对生命在时间中展开的短暂过程所感受的悲哀,几乎贯穿中国历代文人的心灵;这种悲情传达着对人生本质的智慧察觉,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特有的文化心态;这种带着哲思的“生之忧患”在中国古代诗词中置换为伤春悲秋的主题,它也同样成为吕碧城的海外词的情感底色,在吕碧城海外词中有大量惜春伤逝之作。
1928年她第三次到意大利罗马,一连写了两首《摸鱼儿》词,第一首词小序言:“暮春重到瑞士,花事阑珊,余寒犹厉,旅居萧索,赋此遣怀。”词云:“孤馆静,任小影眠云,梦抱梨花冷。吹阴弄暝,叹婪尾春光,赏心人事,颠倒总难准。”“空惆怅,谁见蕊秾妆靓,瑶台偷坠珠粉。闲愁暗逐仙源杳,更比人间无尽。还自省,料万里乡园,一样芳菲褪。”惜春伤逝与离土思乡之情交织缠绵,难以驱遣。第二首词序云:“客里送春,率成此阕,感时伤事,不禁词意之凄断也。”词极细致真切地表现她伤感忧郁的心绪:“悄凝眸,绿阴连苑,啼莺催换芳序。春归春到原如梦,莫问桃花前度。”“天涯远,著遍飘英飞絮。粉痕吹泪凝雨。”“今试数,只一霎韶华,幻尽闲朝暮。人间最苦。”
在吕碧城内心深处充满对岁月流逝、生命老去的无奈和悲哀,这类内容在吕碧城海外词中占很大比例。例如在《玲珑四犯·日内瓦之铁网桥》中,吕碧城将这座20世纪欧洲现代铁网桥联想为惜春少女的巨型“秋千”:“还似索挽秋千,逐飞絮、落花飘荡。”因而“锁镜澜凄暗,回肠同结,万丝珊网”,充满伤春惜时的生之忧郁;即使雄伟高俊的埃菲尔铁塔在吕碧城词中也被想象成是为了留住春天才建造的:“万红深坞,怕香魂易散,九洲先铸”“把花气轻兜,珠光团聚”(《解连环·巴黎铁塔》),当她登上高耸入云的塔顶俯瞰桥下时,看到“绣市低环,瞰如蚁,钿车来去”,深深体悟的是人之渺小、时间之匆遽,所以结尾写道:“更凄迷。斜阳写影,半捎蒨雾”,完全是伤春惜时的话语与心态。
在吕碧城海外词中这种对岁月匆遽的迟暮之叹处处皆是:“归辽待寻鹤梦。料沧桑故国,几度摧换。且蹉跎、老我浮生。”“十年迁客沧波外,孤云心事谁省?兰城辞赋已无多,觉首丘期近。”“雪山一卧朱颜改,红海十年归,相看身世非”、“问谁证,悠悠百年心,黯佇尽斜阳,逝川无际。”
岁月无情、生命衰老的无奈感使这一部分海外词意境清冷而苍凉。惜时嗟老是对时间流逝的忧惧,其实是对生命的无比珍惜,是中国传统文人心态的重要表现,因此也成为中国古代诗词的重要主题,屈原“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离骚》)、谢灵运“览镜睨颓容,华颜岂久期?苟无回戈术,坐观落崦嵫”(《豫章行》),从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魏晋南北朝诗人、直到李白、杜甫、晏殊、欧阳修、苏轼等历代文人都有大量嗟老伤逝之作。
吕碧城海外远游之词的思乡念土之情融入自我放逐之痛、远谪之悲,海外倦游的孤独飘零之感融入叹老惜时、对生命终极价值的思虑、对精神家园的企望与寻求,这是吕碧城海外新词最为深刻、最为动人之处,是最值得人们深入研究品味之处,这一切难道不也正是今天的文学现代性仍然在探索的问题吗?
综上所述,吕碧城海外新词虽然描述了海外新事物新生活,然而这一切无不被纳入中国传统文人心态的结构中,并且成功而优美地表现了吕碧城这位近代女性文人真实的生命情态,同时,她的海外词中所表现的生存自由、独立精神、生命意识又无不与现代性内涵相通共融。由此可见,最深刻、最地道的传统文化也是最具现代性的,因为都是人性最深刻的表现。吕碧城海外新词客观地表现了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并非对立、并没有天然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相通互融的。
参考文献:
[1]李保民.吕碧城词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王慧敏.彩笔调和两半球———试论吕碧城的海外新词对传统词体的突破[J].长江论坛,2010,(6).
[3]吕菲.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游走[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5).
[4]刘纳.风华与遗憾———吕碧城的词[J]中国文学研究,1998,(2).
[5]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2.
[6]聂石樵.楚辞新解[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7]李保民.吕碧城诗文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8]王栻.严复集: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