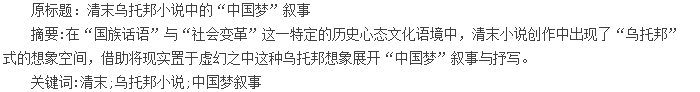
虽然“乌托邦”(utopia)一词最早出现于严复翻译的《原富》(原作者为亚丹·斯密:《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但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具有“乌托邦”想象的作品早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如《诗经·硕鼠》,再如流传千古的《桃花源记》,就反映了古代中国社会在农耕文化中形成的社会思潮:无需国家机器去统治的“无为”世界,共建一个没有战争、剥削、压迫的王道乐土。这种“乌托邦”想象超越了社会发展、国家运转的历史时空,所以它只能是海市蜃楼般的空想。这种空想发展到20世纪初,在西方政治、科学和社会思潮的撞击下,发生了质的改变,即它不再是一种天马行空式的空想,而是在国族话语权下依据现实社会而描绘出未来的具有现代性的社会与理想生活的心灵图景。在家贫国弱的社会现实刺激下,小说创作者在“小说界革命”的号召下,将社会之真相建构于理想中的“中国梦”叙事之中,于是产生了一批具有“乌托邦”色彩的寓现实于想象、借梦想追逐现实视野的新小说。首开其篇的当属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1902年连载于《新小说》),随后有蔡元培的《新年梦》(1904年载《俄事警闻》65、66、67、68、72期)、陆士谔的《新中国》(1909年改良小说社印行)等。这些小说被标为“政治小说”,“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其论皆从中国为主,事实全由于幻想”。此时的幻想,不再局限于国家政治体制的变革与改良上,不再单纯寄希望于科学利器的构想上,也脱离了明清小说中神仙武侠式的虚幻,而是通过个体想象来设计国家未来的政体。这种设想如发育不足的早产儿,只顾及汲取西方先进思潮之养料,而忽略了对现实社会的真实了解和足够认识,就匆忙而来,给人一种乌托邦式的虚幻;但这种虚化的国族话语却给人以希望,尤其在“中国梦”叙事上,它展开了除新的国家想象外的对民族前进之路的科学断想。
一
清末小说家将创作的视野锁定在国族叙事的维度,将小说作为革新社会与重构国家的”药石”,以此来宣传“国族”、“国民”、“宪法”等具有鲜明西方意蕴的新思想。这类作品深受“文以载道”传统精神影响,导致在小说中出现“寄论著于说部”、“寓说部于论著”二元交叉的文体形式。这种形式又多借助于“乌托邦想象”来进行文学叙事,规避政治、预警政治、言说政治、虚构未来、执著于现实等来搭建一个虚拟或幻想的“桃花源”。这种真实与想象、现实与未来的多重变奏,成为清末小说家的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在这些具有“乌托邦想象”的清末小说中,创作者们始终在围绕“国族话语”展开叙事,尽管他们虚构了时间、人物、地点,但始终没有离开现实中的清末社会。在现实社会中,亟待解决的“抵御外辱”、“富国强种”、“重构国家”等国家政事成为整个社会关注、谈论的焦点,可当一次次政治变革遭遇强大阻力而无法继续,一次次图强被列强的坚船利炮击毁的烟飞灰灭,他们心灵遭遇的创伤远远大于肉体的戕害,于是寄予未来与空想的民族富强之梦通过文学叙事展开。
在清末小说家的笔下,他们梦想着未来的中国是一个繁荣昌盛、独立统领世界的强大国家。“不到两三年的时候,竟是上下一心,居民一体……登时变了个地球上惟一无二的强国。”
他们忽略了中国如何从一个弱国走向强国的过程,将更多的笔墨集中于对强大起来的中国盛世局面的涂画上,用传统文化所凝聚起来的散发着强烈的民族自信之气息,来编织恢复天朝上国之地位、成为世界之领袖的中国梦。在这些有关“中国梦”叙事的小说中,他们幻想一个以中国为轴心的国度,如《新中国未来记》。百日维新断送了梁启超的政治前途,却开启了他文学变革国家之梦境。虽然《新中国未来记》属于一部未完成之作,如作者在《绪言》中说:“顾确信此类之书,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
借助小说来言说国家民族之前途,可以说是梁启超“维新思想”的延续。《新中国未来记》的发表,标志着现代国家政治建构与国族话语的乌托邦想象介入文学创作活动的开始,其所建构的国家也完成了梁启超在现实世界没有实现的国度,引领了清末缔造民族国家与国族叙事之风潮。再如蔡元培的《新年梦》说,称雄世界的目的不是为了弱肉强食,而是为建立一个和平、到处飘荡着“大炮打成黄世界,短刀砍出汉乾坤”的大一统世界,民族的自尊、自大、自傲之心让饱受屈辱的国人在脱离现实之后进行精神上的“意淫”,以此满足空旷的精神需求。现实中处在挨打境地,可在精神想象的空间却处处在幻想满足复仇心理的乌托邦世界。中国倚仗发达的军事与民族凝聚力挫败西方强敌的侵略,用武力征服世界,但征服的对象却是那些来自现实社会正在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国家:“电王黄震球单枪匹马把‘西威国’化为焦土。”
同样的场景和战争出现在《新中国未来记》、《新年梦》、《电世界》、《新纪元》中,战争的结局是签订城下之盟、赔偿军费、享有治外法权、开设租界、驻扎军队等那些列强与清政府签订的种种霸王条款被颠覆过来。但是,儒家“和为贵”的仁者之心却让这些小说家一改强烈的复仇心理,他们的武力侵略弘扬的却是追求和平共处的精神。当清末遭遇历史上未尝有过的民族灾难与危机之时,先知的政治家们承认在中国政治制度和国家实力上落后于西方,但在思想文化、道德伦理领域上却认为超越了西方。所以,当他们不能从历史中寻找到自我强大的历史经验与答案时,将西方成功者的经验拿到中国本土贩卖,但现实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如此艰难,在无力回转之际他们借助民族想象来满足精神上的“自慰”。这也是这些小说忽略中国打败侵略者走上富强的过程而直接去描绘太平盛世的图景根源所在。
清末小说中所呈现的众声喧哗的“中国梦”叙事,虽然将其寄予于乌托邦想象之中,但现实社会的变革之路对其影响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国体如何变革成为社会各界期待、憧憬、关注的重点,同样影响到小说的创作,很多作品中通过乌托邦想象描绘了立宪后中国的繁荣富强。《新中国》可为其代表。
《新中国》叙事地点设在上海,在陆士谔的笔下,作为新中国一隅的上海,外国巡捕不见踪迹,华捕穿上中国警察号衣,治外法权已经收回,国会开后,“第一桩议案就是收回租界、裁革领事裁判权的事……国会开了,吾国已成了立宪国了。全国的人,上自君主,下至小民,无男无女,无老无少,无贵无贱,没一个不在宪法范围之内。外务部官员,独敢违背宪法,像从前般独断独行么?……吾国闽、粤两帮人,侨寓在南洋群岛、新旧金山各处的,也与欧洲各国人一般的享着权利了”。
要改造一个民族国家,必须从民族魂的改造做起,在“中国一民”的梦想中,中国与世界应该是如此的样子:“请设一万国公法裁判所,练世界军若干队。裁判员与军人皆按各国户口派定。国中除警察兵外,不得别设军备,两国有龃龉的事,悉由裁判所公断。有不从的,就用世界军打他,国中民人有与政府不合的事,亦可到裁判所控诉。那时候各国听中国的话,同天语一样。又添着俄、美两国的势力,没有敢不从的”。中国经过改造成功后,中国国内的民众从“三纲五常”的传统中走出来,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机器,一切都回归到“无为”世界。在这个“无为”世界,中华民族强于世界的梦想却没有改变,这也是清末政治乌托邦小说一个共同的国族话语叙事主题。如颐琐的《黄绣球》虚构的是一个地处亚细亚洲东半部温带之中聚族而居的“自由村”,村中黄姓族分、人口都占居最大,物产丰盈,田地广阔,温儒安居,同时与外村隔绝未来。“自由村”与“黄氏子孙”俨然为清末社会与国民的缩影。受西方政体和社会思潮的影响,国人在对国族话语的叙事上追求的是建构一个繁荣昌盛,并走上大同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些乌托邦小说在结尾都带上了一个大同尾巴:中国强大,中国走向世界主宰之地位的目的是为了世界和平、维护世界健康发展,这一远景想象融合了清末知识分子对国家未来之路的探索,即以西方现代国家和中国古代“桃花源”式“无为”社会为蓝本进行“中国梦”的构想。
二
在“中国梦”叙事中,除了对民族国家主权的重新构置外,还有对社会科技发展的远景宏图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如《新中国》中提到:“自行设厂,仿制各种呢绒布匹。”而金冠欧先生的学成回国,为祖国的发展提供先进的科学技术,实现了“不到二年,金、银、铜、铁都有了。于是,鼓铸金、银、铜各币,开办国家银行,把民间国债票全数收回,国用顿时宽裕了。……吾国兵舰,都靠着电机行驶的呢!”
再如《痴人说梦记》第三十回写到:“中国十八省统通把铁路造成了,各处可以去得。……各处设了专门学堂,造就出无数人材。轮船驾驶,铁路工程,都是中国人管理。……那街道一层还不够走车,上面还有一层路,车马喧阗,人声嘈杂。原来是两层马路。”
在现实的清末中国地理范围之外,小说家通过想象的乌托邦开辟了一个未来中国、理想中国的“中国梦”叙事空间。在这个空间内,合资创办民族企业、独立修筑铁路、开办矿藏、传播科技文化、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等在“中国梦”叙事中频繁再现,表面上具有荒诞性,但都是清末中国现实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乌托邦小说通过“物”或“科学技术”从不同的角度延续了民族国家构建的社会层面上的想像,与政治思想层面上的民族国家想像共同组成现代性的一种主题多重层面的体现。清末国家遭遇的历次民族屠难促醒了中国人对“世界”的新认识,他们意识到我们的国家处在一个划定的世界秩序中,中国人不得不重新在源于全球的民族国家体系的世界秩序中寻找自身的位置,所以在乌托邦想象中他们叙述的“未来中国”不再是一个与世隔绝、独立存在的孤立的农耕为主流的自然经济国家。在小说的叙事话语中出现“万国和平会议”、“万国博览会”等,是小说叙事者通过想象的世界共体空间营造出被解殖(decolonization)成功后的中国在世界体系中重新获得中心的位置。
在追求科技进步的同时,小说家还肩负着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政治上的失败并不等同于文化的落后,在中国文化史上,每一个朝代的更迭都促进了文化的重新选择,但这种选择始终处在儒释道三教合流以儒为主的文化主流中;同时,任何一种外来文化经过诠释、融汇、消解,最终汇入中华传统文化长河。时至清末,当传统文化遭遇西方文化的侵袭,人们虽然从家天下的窠臼中走出来,而且意识到世界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共同存在的一个共体,但文化一统天下的心理始终令清末知识分子群体难以舍弃。
最重要的是,民族复仇心理在他们心中的影响,如《痴人说梦记》中的“仙人岛”、《狮子吼》中的“民权村”、《瓜分惨祸预言记》虚构的“兴华邦独立国”、《自由结婚》中虚构的一个叫做“爱国”的大国等,他们在强国梦的叙事过程中没忘记民族复仇。与列强不同的是,他们的民族复仇不是靠强兵利器,而是靠儒家仁政去统治世界,以语言变成世界通用的公共语言为基础,进而将儒家文化中的大同世界观推广全球。这些具有民族复仇的帝国幻想之梦暴露了清末知识分子的民族观,在批判西方列强殖民主义的同时,不自觉地重蹈着民族强权的逻辑,进而启蒙愚昧,疗治民族创伤,实现小说叙事之目的:“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
三
在清末国家社会体制的革新过程中,虽然自由平等、民主自治等是西方民主国家得以建立的基础,而且这些因素促使西方人完成了富国强种的历史使命,然这些“舶来品”移植到清末的中国,却无法在中国本土实现在场的转换。虽然急骤的国家变革在分解、取代旧的体制过程中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在民族国家的断链式不同时间、空间的乌托邦想象中为不同的阅读者提供了同一个民族国家想象之源,而且其所营造的“中国梦”之图景在小说创作者的思维意识中一再展现,但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小说创作者们并不能直接言说,只能在规避中进行自己的政治表达。
首先,寓现在之事于未来之“乌托邦想象”中。“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从“天下”到“国家”渐进过程中,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固有文化体系的解构与新的时空观的诞生,一种新的民族国家意识植入中国人的思维世界。“甲午战争之前,吾国之士夫,忧国难,谈国事者,几绝焉。自中东一役,我师败绩,割地赔款,创巨痛深,于是慷慨爱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非今优于昔者,昔者不自知其为国。今见败于他国,乃始自知其为国也。”
国族话语在清末知识分子群体营造中国再生的心理构想中,通过小说这种虚构叙事来重铸强国之梦。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在梁启超的倡导下,清末小说界革命由此而生。清末报刊业的发展,小说逐渐取得合法席位,儒释道精神在西方宗教文化的侵蚀下开始瓦解,中华民族赖以维系的民族心理遭到冲击,外来文化与特殊的文化语境为梁启超等小说家建构民族国家想象提供了历史契机。在小说中,关于国族话语这一政治敏感问题常常隐喻到未来之事当中,将小说发生的时间进行位移后置,如《新中国未来记》将时间的起点设定在1902年,而小说叙事则发生于一个甲子之后的1962年壬寅正月初一;《新年梦》的叙事时间为60年后的正月初一(《新年梦》开始于甲辰年(1904年)正月初一),即一个甲子后的时间倒置;1908年上海小说林社初版的《新纪元》(碧荷馆主人)同样将时间设定在将来,其所描绘的事情在处于将来进行时状态;1909年发表的《电世界》(高阳氏不才子)将画面定格在宣统一百零一年(公元2009年)正月初一;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初一,陆士谔一觉睡醒,在四处是“恭喜”、“发财”之类的祝福语下,时间已经跨越到了宣统四十三年的正月十五了。这些小说家一改以往小说创作者于过去之事(历史上的某段时间发生的事件)中展开思维想象与语言描述,也不同于在现在之事(创作者所生活的环境中即时发生之事)中进行勾画,而是热衷于在未来之事中将中国虚幻成具有辉煌前程的政治图景。可是,这种虚构的未来之事却彰显着太多的现在之事的幻影,不管是未来的中国与世界之事,还是现实中的中西世界,都源自作者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对国族前景走向的焦虑。
其次,将未来之“乌托邦想象”回归于现在之事。在清末乌托邦小说的“中国梦”叙事主题中,不管创作者怎样幻想未来中国社会,实际上都没有脱离现实社会这一创作背景和文学创作的历史使命。
清末中国在走向现代性的历程中,需要进行多重社会变革,而变革的主导因素是科技。这是清末先觉人士所一直倡导的主体。在小说家创作的作品中,他们忽略国家政体变革的历程,却将社会科技文化变革作为主要描绘对象进行重笔勾画。经历若干年的历史,中国的强大主要来自科技与文化的强大,如《新中国》、《新年梦》、《新纪元》等小说中都写到中国强大于世界是靠科技进步所取得的,而非对外族的侵略。除了对科技的进步想象外,更重要的是对儒家经典的重新发掘与充实。面对帝国主义的弱肉强食的侵略行径,先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致认为是“礼”的破坏与颠覆,必须以儒家的“仁”、“礼”操守为外在的道德秩序作为维持大同世界的前提。用文化来控制世界和平这种心理需求一直是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对外交往的传统,中国的世界中心论不是靠侵略、扩张来完善、补给国家版图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而是通过发展文化的向心力来维系那种“天朝上国”之尊位。所以,清末小说家在“中国梦”叙事过程中,常常舍弃对中国由羸弱走向富强的过程描写,而是将想象的细胞用在恢复、完善、重建“文化霸权地位”的构思与发挥上。中国发明的新式语言文字风行全球(《新年梦》);汉语差不多竟成了世界的公文公语(《新中国》);实现世界大同,靠的是自身“真文明国”的示范(《新石头记》)。在清末乌托邦小说中,“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的儒家理念被置于世界大同思想中重新诠释,而用“王道仁政”的本土文化来抵制西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淘汰理念,只能在空想中满足自我虚构的王道乐土之心理。
再次,在隐讳与反叛之间言说创作者的政治理想。在清末乌托邦小说的“中国梦”叙事中,表面上是在幻想中国未来之繁华,实际上不同的作品却隐喻着作者的政治欲求,文学成为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各种政治思想汇聚的试验场。“在第三世界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
他们都在恣肆想象未来中国是按自己的政治诉求建构的,虽然他们都是通过梦来绘景中国的未来,可有的是通过立宪达到独领世界(如《新中国未来记》、《光绪万年》、《新中国》、《新年梦》等),有的通过革命的手段来实现中国独立(如《狮子吼》、《卢梭魂》、《黄绣球》等),有的则追求一种没有任何约束的自由空间,人人平等、各取所需的桃源世界(如《新石头记》、《月球殖民地小说》等)。从文学创作回归现实社会,清末主张“立宪”、“革命”、“复古”等多种思潮纠结于国家政体的变革过程中,而这种政治纠结主要来自那些徘徊在国体边缘而无法参与到国家变革过程中去的文人群体,他们满怀政治热情却无法寻找到释放领域,清政府“缉捕、屠杀”的高压政策让他们只能趋于地下活动,只好借助文学作品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和宣泄自己的政治怨气。在寻找治国良方的道路上,吸纳成功者之经验、翻阅历史往事成为置换国体的良剂。不管是以资本主义为蓝本构想的立宪万年之盛世,还是通过历史反思进行革命重获新生的中华帝国,都映射了他们在国家叙事中的政治立场。
清末乌托邦小说中的“中国梦”叙事,反映了清末内心焦虑的文人与政治改革家共同抵御民族国家重构与独立过程中呈现的困境,实现了文学家与政治家的同声共振。虽然清末乌托邦小说都是在虚构的空间环境展开“中国梦”叙事,但又都将清末社会的现实状况介入小说中,梦境中其改革方案源自西方社会文化、自然科学知识与本土文化的重新整合。
现实世界和未来世界之间的真假幻想,直接刺激着中国人的超前想象思维,用陌生化的空想世界来启蒙、变革现实世界中的民族国家与社会革命,最终引领其走上现代性的轨道,这也是清末乌托邦小说流行的叙事方式。在小说家的努力下,小说成为创作者建立民族国家的现代乌托邦的试验场,他们借“中国梦”叙事之笔给社会进步规划出了基本路向和文化发展远景图标,社会图景通过隐喻、明化等“总体性”的写实主义手法表现于小说的空间图景之中,中外矛盾、殖民与被殖民、革命与改良、维新与保守、政治危机与文化危机等诸多矛盾的写实与虚构之间无距离的切近,高度的重复,充分表征出一个危机四伏与乱象重生的“中国”,国族想象已脱离封建王朝独立性与隔绝性,完全参与到全球体系中无民族殖民的国家体系空间。
参考文献:
[1]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J].新民丛报,1902,14.
[2]春颿.未来世界:二十四回[N].月月小说,10-20、22-24.
[3]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M]//中国近代珍惜本小说·伍.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459.
[4]黄人世界八回[N].游学译编,11、12载.
[5]高阳氏不才子.电世界:十六回[N].小说时报,1年1号.
[6]陆士谔.新中国[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
[7]蔡元培.新年梦[M]//蔡元培全集:第1卷(1983-1909).北京:中华书局,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