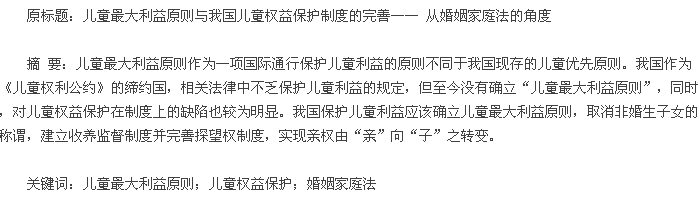
当下我国损害儿童权益的事件较为常见,如“麻江儿童窒息死亡案”、“兰考弃婴火灾案”、“贵州毕节流浪儿童垃圾桶死亡案”等,不一而足,而且农村留守儿童和城乡流动儿童人数不断扩大,2013 年已达到 9683 万①。从侵犯儿童权益的事件发生频率和留守、流动儿童的规模来看,儿童权益保护问题日趋严峻。中国作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应遵循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从儿童最大利益出发完善立法不足,切实保护好儿童的合法权益。
一、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确立及其意义
从自然因素来看,儿童因父母所生,作为一家之长的父母就自然享有管辖和支配处置之权。
儿童一出生就处于一种私有财产的地位,家长有权决定留养或抛弃,且属于“一家”之内部事务,国家难以干预。所以,起初,儿童是作为有一定价值的价值体而存在的,因为对家庭有一定的经济价值而得以保护,犹如保护一件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一样,本身并不是一个权利主体。
但人类也天然具有悲悯弱小和恤幼的社会属性,对儿童的特别保护也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步。尤其是从 14 世纪到 16 世纪,受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儿童开始从被怜悯和被保护的客体转变为具有主动诉求的权利主体,并且这种人性的提升得到了法律的认可。英国分别于 1808 年、1874 年、1886 年通过了《少年法》、《未成年人援助法》、《未成年人监护法》等法律,成为较早通过体系性立法来保障儿童权利的国家。1899 年美国通过的《少年法庭法》,被认为是“世界儿童立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1]。联合国于 1924 年通过了《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1959 年通过了《儿童权利宣言》,在国际层面上宣示了儿童的权利,并提出了相关立法要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立足点。1989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实现了从宣言到具有实际约束力的国际公约的转变,其中,“儿童利益最大化”被确立为基本原则之一,目前已获得 193 个国家的批准。这成为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保护儿童权利的国际性条约,是儿童权利保护的“大宪章”[2]。确立了儿童作为独立个体权利主体的地位,体现了儿童权利保护的相关立法的价值取向,也为实践中解决儿童权益问题提供了法律准则。“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体现的是儿童个体权利的最大化,是儿童作为权利个体所享有的‘最大利益’的权利。”[3]
二、我国儿童利益保护不足的主要表现
第一,父母本位倾向明显。在我国封建思想“父为子纲”的影响下,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度也打上了父母本位的深深烙印,主要表现在:一是监护权制度设计上侧重权利。父母对儿童的监护是围绕着监护权利来进行的制度设计,而义务往往被忽视,因此,父母往往为监护权而争夺,而常常忽视了监护义务。这种权利优位的制度设计进一步强化了父母本位。二是母子利益捆绑。我国婚姻法有一个特点就是将儿童利益与母亲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不论母亲抚养能力如何。这样,儿童利益不仅没有满足最大利益的要求,甚至儿童利益优先的原则也没有体现,结果往往在抚慰和帮助一个弱者的同时又制造了另一个弱者。三是父母单方决定收养。我国收养制度规定了收养人与送养人可以双方协议解除 10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收养关系,单方面体现了父母愿望及利益,忽视了儿童的利益。四是非婚生子女受到歧视。从自然因素来看,无论是婚生还是非婚生,都属于“生子女”,而“婚生”与“非婚生”这种社会行为的选择在于父母,不能将父母的违法行为烙记在子女身上,让子女永远背上违反婚姻法之名。这种“非婚生子女”的称谓将儿童一出生就置于“被违法”的地位,是父母本位的另一种表现,显然违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第二,儿童的权利被忽视。儿童的权利是儿童利益的重要载体,儿童权利被忽视或得不到有效保障,儿童的利益就无法实现。应该说,我国儿童的法定权利并不缺乏,但实际享有的现实层面并不理想,权利“纸面化”的现象比较严重。主要原因有:一是由于儿童处在心理和身体的发展阶段,心智尚不成熟,经常被当成监护人的附属物,儿童的权利往往被忽视。二是在监护抚养过程中缺乏监督机制。在我国现实中,儿童往往会被看作是父母的私有财产,所以无论是完整的家庭还是离婚后的家庭,家长虐待孩子、对孩子不尽义务、侵占孩子利益等行为只要不是严重到触犯刑律,都被看作是“家事”,外人无权干涉或没有专门机构进行干预,从而使儿童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三是离婚过程中没有保障儿童权利的制度机制。父母在离婚过程中,涉及儿童利益的事项往往处于从属地位。所以,只要离婚夫妻双方就未成年子女的事项达成协议即可,而协议是否有利于儿童的利益则不在审查范围之内,现实中还有一些个案存在着父母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去牺牲儿童利益的情况。
第三,探望权制度不完善。根据我国 2001 年修订后的《婚姻法》,探望权仅是指夫妻离婚后,不与儿童共同生活的一方依法享有的与其子女相聚、交往的权利,性质上属于亲权。但仅仅规定父母的探望权,以父母的愿望为优先考虑因素,儿童不知不觉“被探望”,只是单方面满足了父母的精神抚慰要求,儿童的利益被忽视。以儿童最大利益为考量,目前探望权制度还存在如下问题:一是探望权主体范围太过狭窄。从我国《婚姻法》第 38 条的规定可以看出离婚是探望权行使的必要条件,而探望权的主体是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离婚的父或母,这就排除了因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同居、通奸、强奸、卖淫、嫖娼情况下生有孩子且分居的父或母及离婚前分居的父或母。同时也排除了非直接抚养方的近亲属(如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及其他关系亲密的人)作为探望权的主体,这就使未成年子女失去了与不跟其生活在一起的父或母方的近亲属情感交流的机会,这不利于儿童的亲情培养。二是我国探望权没有规定子女作为探望权主体的法律地位,忽视了子女有权探望父母或要求父母探望自己,希望得到他们关爱的权利,是对未成年子女意愿的不尊重。三是我国婚姻法只规定了探望权是一种享受亲情权利,而没有规定探望未成年子女也是负有关心、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义务的父或母应尽的法定义务。四是探望权中止的法定事由是“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这种法定事由太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在实践中容易产生分歧,引起离婚当事人双方对中止探望权的争议,更不利于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对探望权纠纷的裁定。
第四,收养制度有待改进。我国收养法中没有明确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且在保护被收养儿童的最大利益方面存在如下不足:一是没有规定试收养期。收养人与被收养儿童如果没有一定时期的熟悉与双方情感上的交流认同,在收养关系成立后会产生一些情感及心理的不相容,使被收养人不能接纳收养人或被收养人很难融入到收养家庭中去,对儿童的成长造成不利影响。二是收养协议解除制度有待完善。根据我国收养法,收养人、送养人双方协商就可以解除十周岁以下的养子女的收养关系,儿童的意愿或儿童的利益没有一个独立的制度机制来予以保障,仅从收养人、送养人的利益出发,不利于保证儿童利益的最大实现。三是收养监督机制的缺乏。我国收养法只规定了对收养人与被收养人资格和条件上的形式审查,没有设定收养关系成立后的跟踪监督制度,这不利于监督收养人是否尽到父母的抚养、教育、保护等义务,是否对被收养人有虐待、遗弃等行为,或者是否利用被收养儿童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从而不利于被收养儿童利益的保护。
三、我国儿童利益保护的制度完善
(一)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国外立法例
1.英美法系国家有关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立法
英美法系国家大都通过单独的专门立法来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英国 1989 年的《儿童法》提出了保护儿童利益的三个原则,即“儿童福利原则”、“无法令原则”和“不得延迟原则”,并且规定了该原则适用时不仅应考虑到儿童的年龄、性别、环境等客观因素,而且还要考虑到儿童的精神需要、教育、自身意愿及情感等主观因素,以实现儿童的最大利益。美国的《统一结婚离婚法》、《收养和家庭保障条例》都确立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离婚后监护权归属、探视权的行使和收养都要考虑儿童的身心状况、适应能力和父母抚养能力[4]。澳大利亚 1995 年修订后的《家庭法》正式确立了儿童诉讼利益最大原则,法院应该从子女的愿望、生活环境、父母的责任心,尤其是有利于儿童的身心健康方面去实现儿童的最大利益,杜绝儿童遭受变态对待、虐待和家庭暴力等行为所造成的生理和心理上的伤害。加拿大在婚姻家庭立法也十分注重对未成年子女利益的保护,特别规定了“儿童与父母最大限度的交往”,这体现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5]。总体来看,英美法系多数国家在确立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同时,还具体细化了法官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子女最大利益时应考虑的主客观因素,尤其是心理、情感等主观因素,从而增强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可操作性和人性化设计。
2.大陆法系国家有关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立法
在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中,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并没有采取单独立法的立法体例,而是通过民法典中相关制度的改造来体现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德国和法国是大陆法系的典型国家,通过民法典的改造来建立儿童最大利益保护制度也较为突出。1900 年的《德国民法典》第 1626 条规定:父母有照顾儿童的义务和权利。这种照顾包括了人身和财产上的照顾,是义务和权利的综合。关于父母照顾权的行使、对子女幸福危害、父母照顾权的剥夺、子女交往权以及日常事务决定权的限制等规定,都体现了优先考虑子女最大利益原则。《德国民法典》的修改还将“亲权”这一法律用语改为“父母照顾”,这一转变体现的不仅是一个词的变化,还涉及到该制度理念的转变,强调了父母对子女生存发展的照顾义务,实现了亲权的由“亲”向“子”的转变,遵循了儿童利益优先保护的原则。1997 年《德国民法典》增加的第 1697a 条还对法官涉及子女利益裁判作出了明确的要求,法院应当考虑实际情况和各种可能性以及利害关系人的正当利益,做出最有利于子女的利益的裁判。《法国民法典》中关于亲权的行使、撤销和监护的规定,都已成功将“亲”之亲权过渡到“子”之亲权,体现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亲权在罗马法中反应了父母尤其是父亲对儿童的支配、控制及其管教的权利,其强调的是“亲”权,并非“子”权。《法国民法典》第 287 条第 1 款规定,亲权由父、母双方共同行使。在双方不能协商一致时,或者法官认为所达成的协议违背子女利益时,法官得指定由子女在其处惯常居住的父或者母单方行使亲权。第 371条规定,保护儿童的健康、安全和规范道德行为的权利属于父母,父母对儿童有照料、教育和监督的权利和义务。随着儿童最大权利观念的提出,儿童成为权利的主体,亲权不再强调父母的利益而是儿童的利益。亲权由父母双方共同行使替代父权的单独行使,而且亲权更常作为一种义务的形式出现。日本关于亲权的行使和亲权人变更的规定也都体现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比如《日本民法典》第 819 条第 6 款规定,认定为子女利益所需要时,家庭法院因子女亲属的请求,可以变更他方为亲权人。该法典第 826 条也规定,如果亲权人为子女利益相反的行为时,其他亲权人可以请求法官为子女选任特别代理人。亲属对亲权人权力行使进行监督,有益于多方面保障儿童最大利益。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往往通过亲权的行使来体现。所以大陆法系国家通过民法典相关亲权制度的改造,将“母”之亲权过渡到“子”之亲权,将父母的义务置于突出地位,以此来体现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二)我国儿童利益保护的制度完善
我国婚姻法等相关法律中不乏保护儿童利益的规定,但都没有对“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作明确具体的规定。为了更好地保护儿童利益,为了更好地体现婚姻家庭法的发展趋势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精神,以下方面的制度及其机制应重点加以完善。
1.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我国虽然在规范层面上确立了儿童优先原则,如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但毕竟不能代替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也不能视为最大利益原则在我国的变换适用,二者的适用范围和境界都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二者的内涵不同。优先原则强调的是次序,是先与后的问题,最大利益原则强调的是量值,是大与小的问题。
其次是二者体现的法律理念也不尽相同。最大利益原则以维护儿童权利为己任,涉及儿童利益的方方面面,真正体现了儿童权利本位。而儿童优先原则是将父母作为参考对象所建立的原则,至多体现儿童利益优位而不能完全体现儿童权利本位的理念。三是效力范围不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是现代意义上的一项具有普适性的国际原则,现已获得 190 多个国家的认同,而儿童优先原则只是中国特定背景下的一项保护儿童权利的准则。当前,首先要克服未成年子女监护中的“父母本位”倾向,修改相关将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与母或父母利益绑在一起的法律规定,以确保儿童的最大利益。其次,宪法应体现出保护儿童最大利益之精神,确认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宪法地位,为部门法提供立法依据和指导。19 世纪,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发达国家部门法的改造提供依据,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6]。这一改造效果,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如在我国《婚姻法》、《收养法》、《未成年保护法》等部门法修订中确认最大利益原则,以更切实地保护儿童权利。
2.建立儿童最大利益保护的监督制度
借鉴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的立法经验,设立未成年子女“子女代理人”或“诉讼监护人”、“儿童委员会”等儿童利益的监督、保障机构,以确保儿童最大利益的实现,尤其要设立离婚程序中儿童最大利益的监督保障机制。我国夫妻离婚过程中涉及到的儿童事项往往是从属性的,这就容易导致法官对儿童利益的忽略。对此,我国可借鉴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具体实际,设立保护儿童利益的“诉讼代表人”制度,从儿童的立场上为其争取应当享有的权利。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离婚时,应就离婚夫妻对儿童相关事项的协议进行实质性审查,如果夫妻就未成年子女相关事项达成的协议违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婚姻登记机关就不予登记。
3.建立收养过程及收养关系成立后的监督机制
收养登记机关不仅要对当事人所提交材料进行形式和真实性的审查,而且登记机关有权利也有义务对收养人、被收养人、送养人的情况,尤其是收养人的健康、品德、家庭经济状况、收养动机等进行实地考察,以保证被收养儿童收养关系成立后有良好的生活环境。建立儿童收养跟踪、调查制度,定期了解被收养人的生活健康情况,同时监督收养人履行父母义务。若收养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甚至有虐待、残害被收养儿童等违法行为的,可向法院提请解除收养关系,触犯刑法的,应承担刑事责任。
4.取消非婚生子女的称谓,完善探望权制度
受我国传统道德的影响,“非婚生子女”这一群体本身就受到歧视。所以为了更好地保护“非婚生子女”这一弱势群体,我国应汲取美国、德国等其他国家先进的立法经验,取消“非婚生子女”的歧视性称谓,将“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统称为“生子女”,以区别于养子女、继子女。如果在现实生活和司法实践中确实需要有区分的,可借鉴德国的立法模式,从父母的角度区分:“有婚姻关系的父母所生子女”和“无婚姻关系的父母所生的子女”[7]。在完善探望权制度方面,首先,在立法上应适当扩大探望权权利主体的范围。可向美国华盛顿州立法进行借鉴,华盛顿修正案扩大了探望权的范围,即在任何时间,任何人可向法院申请探望权,此不限于抚养权诉讼。当为儿童最大利益考虑时,法院可命令任何人行使探望权。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罗克塞尔诉格兰维尔一案中确立了亲权在保护儿童和重要第三人的关系的情况下,儿童利益至上,即探望权的主体不仅仅局限于父母[8]。我国应借鉴美国的经验,把探望权放宽至与儿童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如将享有探望权的主体扩大到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等近亲属及因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同居、通奸、强奸、卖淫、嫖娼情况下生有孩子或分居的父或母,离婚前分居的父或母也应适用。其次,赋予未成年人受探望权主体的法律地位,赋予其要求父或母探望的请求权。再次,我国相关法律明确规定探望权既是一种权利,同时也是一种法定的义务,如果义务人不履行义务,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此外,借鉴美国的“监督探望权计划”,在社区投入资金来发展监督探望权计划,主要对家庭暴力、性侵犯和虐待儿童的行为进行监督[9]。
参考文献
[1] 王勇民. 儿童权利保护的国际法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0: 29.
[2] 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 法治视野下的人权问题[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30.
[3] Alston W P. The Best Interests Principle: Towards a Reconciliation of Culture and Human Rights [C] // Alston W P.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hil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10.
[4] Parkinson P. Child Protection, Permanency Planning and Children's Right to Family Life [M]. Oxford: 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03: 5.
[5] 任学强. 论探望权中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保障[J]. 天中学刊, 2010, (1): 58-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