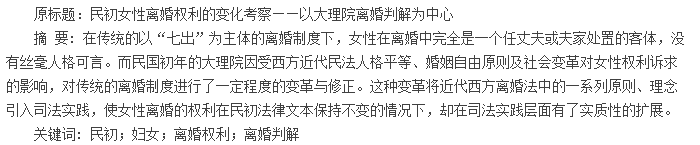
传统的离婚制度主要是以丈夫专擅离婚的“七出”制度为核心构建起来的,在这样的制度下,妇女并无真正的离婚权。妻子完全是一个任丈夫或夫家处置的客体,无丝毫人格可言。法律虽然也规定妻子在丈夫“逃亡三年”、“夫殴妻至折伤以上”、“夫典雇妻妾”及“抑勒或纵容妻妾与人通奸”的情况下,可以提起离婚,但传统礼俗对妇女再嫁存在偏见,所以“官方所赋予已婚妇女的离婚权利很少为妇女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她们即使在利益受到侵害时,如被嫁卖等,多数妇女表现出对丈夫安排的屈从 。即使有不满,也多借助于民间手段来解决,妇女社会地位之低在这些方面充分显现出来”。
民国初年适用的民事基本法《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仍然是传统法律的延续,但社会已非传统社会的简单延续。由于西方价值观及女性运动的影响,婚姻中的两性平等观念在萌发并不断扩展。如此,作为当时最高司法审判机关的大理院,就必然得在裁判活动中协调法律文本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以达致二者的平衡。笔者拟从女性离婚权角度对此进行全面的考察。
一、大理院判解对女性离婚理由的扩展
按照民初《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相关规定,女性可以提请离婚的理由主要有: “典雇妻妾”、“抑勒或纵容妻妾与人通奸”、“夫逃亡三年不还”、“夫殴妻至折伤以上”等。这些规定与当时正在勃兴的夫妻平等观念有天壤之别。为了使妻子在离婚时处于与丈夫更“平等”的地位,大理院在司法实践中,对这些理由作了无一例外的扩大解释,典型情形如下:
(一) 受夫不堪同居之虐待者,妻得请求离婚。在传统法律中,丈夫殴打妻子只有达到折伤以上的程度时,妻子才被允许提出离婚。明清律·斗殴门(妻妾殴夫条) 规定: “其夫殴妻,非折伤勿论; 至折伤以上,减凡人二等(须妻自告乃坐) ,现行审问夫妇如愿离异者,断罪离异; 不愿离异者……”从这一规定可见,明清两代,“夫殴妻至折伤以上”虽可构成妻请求离婚的原因,但也并非妻单方请求离异的理由,因为夫仍然有选择离与不离的权利。这无异于法律赋予了丈夫殴打妻子、侵犯妻子人身的合法权利,而妇女只能被动接受来自丈夫及夫家的虐待,而无去“天”之理。
《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从清律之规定,仍然完全保留了男女离婚权利的这种不平等性。但大理院在司法实践中明确规定: “夫妇之一造经彼造常加虐待至不堪同居之程度者许其离异”(五年上字第 1457 号判例) 。与传统法律“夫殴妻,非折伤勿论”的规定相比,大理院所提出的“不堪同居之虐待”这一离婚理由,极大地扩展了解释空间,也更有利于妻子的离婚请求。关于此点,笔者在后文专门分析,在此不赘。
(二) 受夫重大侮辱者,妻可据此请求离婚。在“夫为妻纲”的传统伦理下,妻子没有独立人格,不可能因为受到丈夫的侮辱而离婚。但是,民初大理院通过判解,将“重大侮辱”这一法律概念导入司法实践,明确“夫妇之一造,因受他造重大侮辱而提起离婚之诉者,一经查明实有重大侮辱之情形,自应准其离异”(五年上字第 1073 号判例) 。关于什么是“重大侮辱”,大理院的解释是: “所谓重大侮辱,当然不包括轻微口角及无关重要之詈责而言。惟如果夫言语行动足以使其妻丧失社会上之人格者,其所受侮辱之程度至不能忍受者,自当以受重大侮辱论: 如对人诬称其妻与人私通,而其妻本为良家妇女者,即其适例。”(五年上字第 717 号判例)基于这样的理由,民国 14 年上字第 44 号判例中,张陈氏因夫诬陷其通奸,诉请与其夫张金生离婚,就得到了大理院的支持。大理院在判决理由中明确宣示: “查夫妇一造受他造重大之侮辱者,得以请求离异。如夫之于妻有诬奸告官之事实,即属行同义绝,应认为有重大之侮辱。此在本院迭经著为先例。”
(三) 男子通奸,女方可请求离婚。传统法律以男权为中心,重在保护男性的利益,所以,法律上明确规定妻犯奸夫得请求离异,而夫犯奸则妻不能提起离婚之诉。其理由是“妻与人通奸既对夫的名誉有害,且有混乱血统之虞”。
《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关于通奸离婚仍然沿袭了清律之旧有规定,而且在民国初年的司法判解中,一直得到严格遵守,明确“男子犯奸盗依律虽为解除婚约之原因,惟律文既明载未成婚字样,则已成婚者自不能拒此请求离异”(八年上字第 753 号判例)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民国十五年才有了突破。民国十五年上字第 1484 号判例中,生李氏因丈夫生贤华通奸被处刑,请求与之离婚,得到了大理院的支持而胜诉。在判决理由中,大理院认为: “夫犯奸通常固不可与妻犯奸并论而迳许离异,但若已因犯奸处刑则情形又有不同,为保护妻之人格与名誉计,自应援用现行律未婚男犯奸听女别嫁之规定,许其离异。”
这一判解打破了双重性道德标准的法律传统,虽然判解还以偏护男性为特点,但与原来女性根本没有以夫犯奸提起离婚的情形相比不能不说是一种突破。“本例依然打破重男轻女之陋习,而开成夫妻齐一之蹊径,其正义、勇敢,诚属可钦”。
(四) 夫恶意遗弃其妻达三年,妻可不经“告官”程序自行改嫁。关于遗弃离婚,《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只规定了男方在“妻背夫在逃”的情况下可以请求离婚,及女方在“夫逃亡三年以上不还”的情况下,可以“经官告给执照别行改嫁”。按照相关规定,妻子只要有背夫在逃的情形,既不问原因也不问期限长短,男方均可请求离婚。但是,夫逃亡必须达三年以上,女方才能请求离婚,而且还必须经“告官”之严格程序,才能改嫁,体现了夫妻之离婚权利的不平等。
大理院在维护《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规定的基础上,通过判解对女方因男方“逃亡三年以上不还”别行改嫁的程序有了放松。大理院明确: “女子如实因夫逃亡三年以上不还而始改嫁,虽当时未经告官领有执照而事后因此争执,经审判衙门认其逃亡属实而年限又属合法者,其改嫁仍属有效,不容利害关系人更有异议。”(三年上字第 1167 号判例)按照大理院的解释,若夫逃亡确达三年以上,且没有音讯者,即使妻没有经告官程序而另行改嫁者也属有效。如民国九年统字第 1362 号解释例中的情形,妻在因丈夫外出多年没有音讯而改嫁的诉讼中,得到了大理院的支持。大理院在本案回函中称: “现行律婚姻门出妻条,夫逃亡三年不还者,并听经官告给执照别行改嫁。至经官告给执照本为防止日后争执起见。故如当时虽未告官而事后争执,审判衙门认其确系逃亡有据,即出走后始终毫无踪迹音信,其年限又属合法者,改嫁即属有效。”
可见,大理院虽然继续维护《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夫逃亡必须达三年以上”妻才可以请求离婚的规定,但在程序上有了明显放松,使妻子在这种情况下的改嫁自由权有所扩展。
(五) 夫纵容其妻与人通奸或典卖其妻者,女方可以请求离婚。即使传统社会,也绝不允许丈夫某些侵害妻子的行为存在。比如,夫纵容其妻与人通奸或用财买休卖休、典雇妻女等行为即属其内。清律对于这类行为不仅处以严厉的惩罚,而且允许妻子据此请求离异。《大清律》规定: “凡将妻妾受财典雇与人为妻妾者,本夫处八等罚。典雇女者,父处六等罚,妇女不坐。若将妻妾妄作姊妹,嫁人者,处十等罚,妻妾处八等罚。知而典娶者,各与同罪,并离异。”
《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从清律之规定。而大理院在继续认可这些规定的同时,对这些行为的认定标准明显放宽。
大理院在判解中明确,只要“夫对于妻有嫁卖显著之事实,仅以他种原因未遂所为者,得予离异”(民国七年上字第787 号判例) 。这与《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以“嫁卖已成”为认定标准相比,显然条件放宽。三年上字第 433 号判例中的吕李氏,因丈夫图卖自己未成,请求与丈夫离婚,得到了大理院的支持。大理院在判决中按照前清现行律之规定解释道: “本夫抑勒其妻嫁卖为娼者较之抑勒通奸典雇为妻妾及卖休之情形尤不可恕,依当然之条例类推之解释自在应离之列,即使图卖未成确有证据者亦为义绝,自可据以离异。”
此外,大理院进一步强调: “妻之改嫁无论是否由于其夫之诈欺胁迫抑或出于合意,但如果系用财买休卖休者,依律自应令与其夫离异。”(六年上字第 1068 号判例)(六) 男子婚后有残疾,女方可以请求离婚。传统社会中,丈夫可以因妻“有恶疾”而出妻或休妻,妻子却不能因为丈夫有恶疾而请求离婚。历代法律均无成婚后男方有残疾、女方可以据此请求离婚的规定。对此,《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也只规定在定婚之初,务要双方明白通知,各从所愿,否则可以解除婚约。至于成婚后之残疾可否为离婚之理由,并未规定。
大理院打破了这种惯性,明确规定即使定婚后男方有残疾,女方也可以据此请求离婚。大理院所谓残疾是指“凡人身五官四肢阴阳之机能有一失其作用者而言”(七年上字第910 号判例) 。按照大理院的解释,这种情况主要是指婚前已经有残疾,但在定婚之初未明白通知对方,在成婚后,对方发现其有残疾的,可以请求离异。因为有些残疾在婚前无法知晓,只有在婚后才能发现(如天阉、石女等) ,若不允许当事人请求离异,与近代民法婚姻自由的理念不符。故大理院明确宣示: “结婚后男女之一造,发现对造身有残疾者,自可为请求离异之原因。”(民国九年上字第 291 号判例)(七) 男方重婚 ,先娶后娶之妻均可以请求离婚。传统社会中,男性虽然可以一妻多妾,但在嫡庶有别的观念下,非常强调一夫一妻制,故禁止重婚是当然之事。唐律户婚律规定: “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 若欺罔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
明清之法律也规定:“若有妻更娶妻者,杖九十,离异。”在这些规定中,允许后娶之妻因男方重婚请求离异,但关于先娶之妻是否可以据此请求离异,没有明确规定。《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仍然遵从了这些规定。大理院对这一规定进行了扩大解释,不仅明确“已有妻室之人,如果欺饰另娶,其后娶之妻,自在应行离异之列”(五年上字第 1167 号判例) ,而且明确先娶之妻也可以据此请求离异。民国九年上字第 1124 号判例中的李黄氏就因为丈夫重婚而请求与之离婚的主张得到了大理院的支持。大理院在本案的判决理由中明确: “按现行律载,有妻更娶,后娶之妻离异归宗。至于先娶之妻能否以其夫有重婚事实主张离异,在现行法上并无明文规定,惟依一般法理,夫妇之一造苟有重婚情事,为保护他一造之利益,应许其提起离异之诉以资救济。故先娶之妻如以其夫重婚为理由主张离异自不得认为不当。”
至此,先娶之妻也可因丈夫重婚而主张离异了。
二、以“不堪同居之虐待”为例
看女性离婚权的进一步扩展前面分析表明,在民初司法实践中,大理院突破了《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规定,对女性提出离婚的理由有诸多扩展。这种扩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渐进的。为了清晰展现大理院的司法脉络,我们以“不堪同居之虐待”这一离婚理由为例进行考察。
“不堪同居之虐待”最早出现在《大清民律草案》中,该草案第 1362 条规定的九大离婚理由之一即为: 夫妇之一造受彼造不堪同居之虐待或重大侮辱者,对方可以请求离婚。民初大理院导入这一概念,显然是受了《大清民律草案》的影响。大理院虽然没有明确界定“不堪同居之虐待”的含义,但通过判解,对“不堪同居之虐待”的认定标准及内容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些解释不仅使这一概念的认定标准逐渐放宽,而且使其内容也有了扩展,使“虐待”的行为从普通的暴力殴打延伸至夫妻婚姻生活的其他方面。
(一) 对“夫殴妻”离婚的认定标准放宽
1. 民国前三年固守旧法。大理院在民国头三年,对以“夫殴妻”为由请求离婚的案件,严格坚持必须达“折伤以上”妻才可据此请求离异。而且即便已经达到折伤以上,也要先行审问丈夫是否愿意离异,如果丈夫不同意离异,妻子仍然很难被允许离婚,诸多判例均如此。大理院这种固守旧法的态度,在三年上字第 38 号判例中可见。该案中,妻张李氏以夫张瑞江虐待殴打自己为由,请求与之离异。结果大理院以“律载夫殴妻至折伤以上,先行审问夫妇各愿离异者断罪离异”为理由,认为本案中张瑞江殴打张李氏并未至折伤以上,不合离异条件,所以驳回了张李氏的诉讼请求。
同样的情形还有民国三年上字第 518 号判例中的吴王氏。本案中吴王氏的上告理由是: 被上告人(其夫) 经常殴打上告人并不给养赡,所以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云云。大理院对于此案的意见是: “本院查离婚之制本为现行法例所认。被上告人打骂上告人诚有不合,非未至折伤程度即与律载离婚条件有所不合,自难予以准许。”故驳回了吴王氏的诉讼请求。
从以上判解及案件看,大理院在民国前三年一直严格坚持夫殴妻必须至折伤以上,妻才可以请求离异,但这种严格遵从《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态度在民国五年开始有了明显变化。
2. 对旧法的突破。民国五年开始,大理院在以“夫殴妻”为离异理由的案件中,对女方受伤程度的认定开始变为“夫虐待其妻,致令受稍重之伤害者”即可判离,“如其殴打行为实系出于惯行”或“常加虐待”,则所受伤害不必已达到较重之程度,既足证明实有不堪同居之虐待情形(五年上字第 1073 号判例) 。按照大理院的这一解释,夫殴妻不必达折伤以上,只要使妻受稍重之伤害,妻即可请求离婚。如果夫殴打妻未达较重之程度,只要妻子能够证明夫的殴打行为是经常性的,妻也一样可以请求离异,法院也可以判离。至此,大理院明确将《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夫殴妻必至折伤以上方可离异”的标准推翻,女性只要证明经常遭受丈夫的暴力殴打,达至“不堪同居之虐待”,即可请求离婚。
不仅如此,民国六年时,大理院还进一步宣示: “夫殴妻至折伤以上之程度,其妻请求离异,应即准其离异,无须再得夫同意之理。”(六年上字第 634 号判例) 从此,“夫殴妻至折伤以上”完全变成了女性单方面请求离婚的理由。
(二) 对“不堪同居之虐待”内容的扩展
大理院不仅在“夫殴妻”伤害程度的认定标准上突破了《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规定,而且明确妻子可以以“不堪同居之虐待”为理由请求离婚。关于什么是“不堪同居之虐待”,大理院并没有明确解释。民国时期的学者蔚乾先生认为,大理院判解中的“虐待”主要是指“非道残酷或加以种种恐吓之待遇也”,而且此种虐待必须达“不堪同居”之程度,方许离婚。怎样才算“不堪同居”? 他概括为如下三种: 殴打至折伤以上; 惯性殴打; 故意不予日常生活费用使之冻馁者。
但笔者发现,在大理院判解中,“不堪同居之虐待”所涉内容,并不限于上述三种情况。
1. 将丈夫拒绝与妻子过性生活也归属为“不堪同居之虐待”。在民国七年统字第 828 号解释例中,妻子因丈夫拒绝与其过性生活请求离婚,得到了法庭的支持。在这个案件中,夫妻双方并无其他矛盾,妻子请求离婚的唯一理由就是丈夫拒绝与其过性生活。大理院对下级法院的答复是: “妻受夫不堪同居之虐待,应认义绝,准予离异。”从这一解释可见,大理院将“不堪同居之虐待”的内容由夫妻间表面的“殴打”延伸到夫妻生活的实质———性生活方面。
2. 将丈夫限制妻子人身自由的行为也归于“不堪同居之虐待”之下。在民国九年统字第 1408 号解释例中,妻子因丈夫殴打,并私制木狗将其钉锁,请求与丈夫离婚,得到了法庭的支持。本案中,某甲娶妻某乙已经数年,甲因外出谋事回家时,恰逢其妻乙不在家中。甲即呈状起诉到案,称其妻背夫在逃。县讯,某乙供称,因为糊口无资,那天恰在邻县亲戚家中就养。并称其夫甲时常虐待自己,婚姻不能复合。但经县判仍令其回夫家完聚在案。不料乙回家后,甲遂对乙实行虐待,并自制木狗私刑,将妻乙钉锁十数日之久,不令动转。
乙受虐不过,乘间脱逃,结果被甲追至丙村,又用铁狗将妻乙痛打不堪,随即逃避。为此乙坚决请求断离。直隶高等审判厅认为大理院上字第 1457 号判例载,“夫妇之一造经彼造常加虐待,至不堪同居之程度者许其离异等语”。认为甲虐待其妻讯证明确,函请大理院可否准妻离异。大理院在回复时说,“甲于胜诉后自制木狗私刑将乙钉锁,自可认为不堪同居之虐待,许乙再行诉请离异。”
本案是丈夫暴力限制妻子人身自由并殴打妻子的实例。案件中,丈夫殴打妻子并未至折伤以上,而且直隶高等审判厅函请解释的主要事实专指“丈夫自制木狗,私刑钉锁妻子”可否为离婚理由。大理院在回函中也一样将“甲自制木狗私刑将乙钉锁”之行为认为属于“不堪同居之虐待”。按照大理院的解释,丈夫私刑限制妻子人身自由的行为属于“不堪同居之虐待”,允许妻子主张离婚。
以上两个案件表明,“不堪同居之虐待”的内容从单纯对女性身体的侵害,已经延伸到对女性人身自由的限制,以及对妻子性生活权利的拒绝这些方面。因为缺乏更多的典型案件,无法判断这些情形是否可以独立成立“不堪同居之虐待”,但也足可看出大理院在“不堪同居之虐待”的概念下,对其中体现夫妻不平等的“夫殴妻”之规定进行了突破性的变革,并赋予了一些新的内涵。
三、大理院判解对丈夫专擅离婚权的限制
从妻子的角度来看,大理院对女性提起离婚的理由进行了扩张性解释; 从丈夫的角度来看,大理院对男性的专擅离婚权也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与修正。
(一) 对丈夫专擅离婚权的“七出”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正。《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仍然将“七出”作为丈夫专擅离婚的理由。但大理院对与社会趋势明显不合的“七出”进行了限制性解释,使女性被随意休弃的情况有所改善。
1. 丈夫不能以妻有“不治之恶疾”为理由主张离婚。传统法律规定,妻有恶疾,夫得据以为出妻之原因,但夫有恶疾则否。而且唐宋律还把“恶疾”作为妻之“三不去”的例外情形,即妻犯七出虽有三不去,但若有恶疾仍在必出之列。到了明清,法律才只将“妻犯奸”作为“三不去”的例外,而将恶疾作为出妻之正常理由。显然恶疾之规定只针对妻方而言,如果丈夫有恶疾,妻不能据此请求离婚。大理院为了救济此种不平等起见,对于恶疾离婚设了限制。
在民国三年上字第177 号判例中,男方隋用才请求与胳膊受伤并生疮的妻子离婚,就没有得到支持。大理院在审理中明确: “现行法例关于男女之残疾解约,以定婚之初并未预告或系出于妄冒等情为限。……而该女胳膊受伤并生疮既在成婚之后,自难遽予离异。”
随后,大理院在九年统字第 1424 号解释中,进一步明确宣示: “已成婚后发生之恶疾,不能为离异原因。”
2. 将“不事舅姑”的认定标准客观化。传统的“七出”将“不顺父母”列为出妻之首要原因。何谓“不顺父母”或“不事舅姑”并无一定的标准,通常只是以舅姑之主观好恶为原则。陆游因母亲不喜欢唐婉而休妻,《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因母亲厌恶刘兰芝而休妻的例子就是极好的说明。
而民初大理院却对丈夫这一离婚理由的认定标准进行了严格解释。如民国六年上字第 947 号判例谓: “按现行律七出之条,虽列有不事舅姑一项,然细释律意,所谓不事舅姑,系指对于舅姑确有不孝之事实并经训诫,怙恶不悛者而言。若因家庭细故有所争执,尚不能遽认为离婚原因。”另外,八年统字第 1134 号解释例也谓: “现行律所谓不事舅姑系不孝之义。即指虐待及重大侮辱而言。”由此可见,“不事舅姑”必须以“确有不孝事实”且达虐待及重大侮辱之程度为标准,丈夫方能以此为理由请求离异。而因家庭细故与翁姑的争执不能认定为“不事舅姑”。显然院判将“不事舅姑”之认定标准的任意性解释成必须有客观的“不孝事实”为凭,否则不允许任由丈夫随意离婚。这一判解态度,既对丈夫专擅离婚权有了限制,也对女性的苛责有所减轻。
(二) 严格解释“妻背夫在逃”的认定条件。传统法律强调妻对夫的同居义务,所以历代法律均严格禁止妻“背夫在逃”行为,否则夫可以据此请求离婚。如《唐律》义绝离婚条载: “妻妾擅去者徒二年。因而改嫁者加一等。”明清律也明确规定: “若夫无愿离之情,妻辄背夫在逃者,杖一百,从夫嫁卖。其妻因逃而自改嫁者,绞监侯。其因夫弃妻逃亡,三年之内,不告官而逃去者,杖八十,擅改嫁者杖一百。”该条规定到前清末年,开始将“从夫嫁卖”改为“听夫离异”。《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从清末之条文规定: “若夫无愿离之情,妻辄背夫在逃者,徒二年,听其离异。”
其实,“背夫在逃”一词本身就清楚地说明了法律的立场,即妻子应该与丈夫在一起,从他身边逃开就是犯罪。相反,丈夫从来不会被认为是在遗弃老婆。如果他离开她几年没有回家,法典只假设他是正在逃避法律的罪犯,被这样的丈夫遗弃三年以上,妇女方可请求解除婚姻。所谓“背夫在逃”,其实是许多妻子回了娘家,这是传统法律下受尽虐待的妻子寻求解脱的主要方法。即便如此,男方也一样仍可以妻“背夫在逃”的名义逼迫妻子回去或主张离婚。
民初大理院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背夫在逃”进行了严格的解释。如五年上字第 598 号判例谓: “背夫在逃,在现行律虽为离婚原因之一,然律条所谓在逃云者,必其出于一去不返之意思,非谓其妻偶有所适,未经预先告知其夫,即谓为背夫在逃。”此外大理院于十一年上字第 810 号判例又谓: “现行律载,若妻背夫在逃者,听其离异等语,背夫云者,系指立意背弃其夫而言,如在逃系因别事,即非立意背弃其夫,尚不能为离异之原因。”
按照大理院的这两个解释,“背夫在逃”必须具备一个主观条件,即从主观上妻子确实有背弃其夫、一去不返之故意。如果妻子仅是偶尔因为他事外出而未预先告知丈夫者,不为背夫在逃。在这种情况下,丈夫不能提起离婚请求。这一解释显然对于女性人身自由的限制略有放松,对于丈夫以“背夫在逃”为由请求离婚的权利有了明显限制。
(三) 明确夫妇离婚,无论男女,必须符合法定条件,不允许任何一方任意离婚。民初大理院不仅对丈夫专擅离婚的“七出”做了一定的修正,还明确规定“除夫妻不相和谐而两愿离异者外,必须具备一定条件方准离异”(大理院三年上字第 223 号判例) 。这一规定虽然是限制夫妇双方之任意离婚权的,但事实上更多是对男性以“七出”为名,任意离异妻子权利的一种限制。按照这一解释,即使是丈夫请求离婚也必须符合法定条件,否则不能允许其随意离婚。
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民国三年北京的于俊德请求与妻子离婚的主张遭到了大理院的驳斥。本案中,于俊德以夫妇“两情不洽,积怨已深”,及妻子于张氏“患病甚重”、“居住母家常年不归”、“不尊崇尊亲并对翁父有强横之行为”为理由,请求与于张氏离婚。结果大理院在审理中以“上告人之主张与律载离异条件无一符合,且被上告人供称不愿离异”为由驳斥了上告人的诉讼请求。
(四) 限制有责配偶的离婚请求权。大理院在民国九年上字第 809 号判例中明确: “夫妻一造受他造不堪同居之虐待者,为保护受虐待一造之利益,固应准其请求离婚,然于虐待之一造,不得准其自行请离。”大理院的这一解释其实就是今天所谓的“限制有责配偶的离婚请求权”。这种做法,在西方近代的婚姻立法中被普遍采纳,明确过错方不得提出离婚,这是近代民法的一项重要法律原则。该原则之目的是为了惩罚过错方,对其提出的离婚诉讼请求予以驳斥,从而达到抑强扶弱、弘扬正气、抵制婚姻家庭中配偶的不良行为。
大理院首次导入这一原则,虽然针对的是实施“不堪同居之虐待”行为的男女双方,但显然在婚姻中对配偶实施侵害行为的主要是男性。所以大理院的这一判例无疑是在限制丈夫的离婚请求权,目的在于避免丈夫为了达到和妻子离婚的目的而加大对妻子的侵害。
四、大理院判解赋予女性专门的赔偿请求权
在清末的法律转型中,《大清民律草案》率先规定了离婚过错赔偿制度。该草案第1369 条规定: “呈诉离婚者,‘依1362 条应归责于夫者’,夫应暂给妻以生计程度相当之赔偿。”虽然《大清民律草案》在民国初年被搁置了,但大理院以条例形式复活了该制度。
三年上字第 420 号判例即是一个典型案例。本案中,暴左氏在与丈夫的离婚诉讼中获得了丈夫的赔偿。暴左氏与暴振风结婚多年,并生有二子。因暴振风经常骂詈殴打暴左氏,而且还时将暴左氏逐回母家不管不顾。为此,暴左氏以其夫虐待遗弃为由诉请离婚及请求给予损害赔偿。此案先经奉天高等审判厅判决: 准予离婚,并判令暴振风给与暴左氏生计费1500 元。判决下达后,暴振风的反应很激烈,认为我国法律从来没有妻子与丈夫离婚后,还要由丈夫来出养赡费一说,觉得法院的判决既不符合现行律之规定,也不符合几千年的传统习俗,这样的判决只能是鼓励女性不守妇道,争相弃其夫,所以向大理院提起上诉。大理院驳回了暴振风的上告请求。理由是: “查现行法例,关于离婚后损害赔偿之请求虽无明文之规定,而按照一般法理,凡妻因其夫虐待离异而请求损害赔偿者,审判衙门依当事人之请求准予离异外,判令其夫给与养生之费。其费额之多寡,恒以当事人之财力地位及生活程度为标准。本案据原审认定事实,被上告人请求离异实出于上告人之虐待,则原审体察上告人财力地位及被上告人之生活程度,判令酌给养生费一千五百元,使无冻馁之虞,洵属允当。
故上告人关于此点之论旨,亦不得谓为正当,据以上结论,本案上告认为无理由,应予驳回。”
大理院判解中关于离婚损害赔偿之规定,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的是男人或丈夫应负的责任,并非是夫过错行为所承担的责任。因为大理院同时明确规定,如果离婚原因出自妻子,夫只能请求离婚,而不能主张妻给予相当之赔偿(四年上字第 1407 号判例) 。大理院将赔偿的情形限定于离婚原因由“夫”而引起,这体现了有责主义原则。同时,大理院将赔偿请求权只赋予妻子,又体现了对女性的特殊保护。
综上,围绕大理院关于离婚的诸多判解,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 民初婚姻中的女性开始逐渐摆脱男性的绝对控制,在某种程度上,正由纯粹客体而演变成主体。除了社会力量之外,大理院无疑是当时这个过程在法律上的主导者。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总结大理院对此的贡献:
其一,在法律理念层面,民初大理院的推事们已然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男女平等的价值观,他们在离婚判解中的法律表达,基本立足点与传统制度判然有别。相对于《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大理院在判解中补充了很多离婚理由,比如,“重大侮辱”、“不堪同居之虐待”、“重婚”、“恶意遗弃”、“通奸”等,这些概念至少在法律形式上抛弃、淡化了传统离婚问题上,公然欺凌女性的性别色彩,近代法律理念藉此而得以推行。
其二,在现实层面,大理院的推事们并非只是学术理念的奉行者,所以,在涉及通奸、遗弃等离婚理由时,大理院判解中的内容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固守着传统。这很容易被解释为大理院作为司法机关的保守性。不过,这种评价不尽准确、全面。因为有时候,大理院放弃了所谓男女平等的一般理念后,恰恰能够维护离婚女性的实际生存困难。大理院赋予离婚女性的赔偿请求权即体现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 王跃生. 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 田涛,郑秦. 大清律例[M]. 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8.
[3] 大理院公报[Z]. 民国十五年三月三十日第一期,现藏于社科院法学所图书馆.
[4] 蔚乾. 离婚法[M]. 上海: 益世报馆,民国 21 年 8 月版.
[5] 大理院公报[Z]. 民国十五年九月三十日第三册,现藏于社科院法学所图书馆.
[6] 傅圣严. 判例商榷[J]. 法律评论,1924,(197) .
[7] 郭卫大. 理院解释例全文[M]. 台湾: 成文出版社,民国六十一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