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民事案件主要是民间借贷案件。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 超出了民法的阈限, 触及到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的关系这一根本, 成了困扰民事审判的一大难题。对此, 理论上与实践中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方法论立场, 即刑主民附论与刑民分离论。然而, 这两种立场都有失偏颇。只有消除立场上的偏颇, 才能将合同效力认定纳入正确的轨道。吸收资金不应被认定为违法所得, 不应适用追缴或责令退赔。如此, 由于追缴与责令退赔的适用所引发的刑民间评价矛盾及其对效力认定造成的干扰, 才能被彻底消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是行政犯, 合同违法性评价, 应以《商业银行法》第11条第二款规定为根据。从规制对象来看, 作为准入规制的《商业银行法》第11条, 并不意在规制合同行为;依法益权衡而言, 认定合同有效也并不阻碍该条规制目的之实现。因此, 《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非《合同法》第52条第 (五) 项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定。对该条的违反, 不应成为认定合同无效的理由。
关键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刑民交叉; 合同效力; 违法所得; 强制性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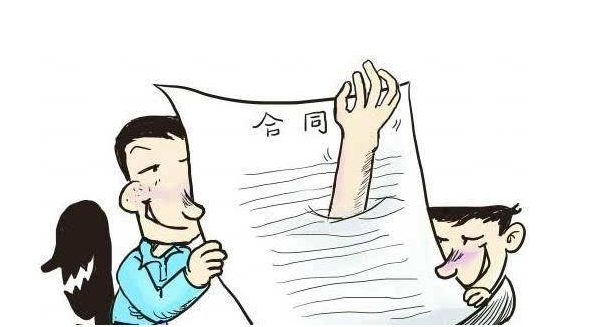
On the Validity of Contracts in Cases Involving Illegal Collection of Deposits from the Public
XIAO Weizhi GONG Hengyu
College of Credit Risk Management, Xiangtan University College of Law, Xiangtan University
Abstract:
Civil cases involving the illegal collection of public deposits are mainly those involving private lending.It has become a difficult problem in civil trial that the validity determination of loan contract and guarantee contract goes beyond the threshold of civil law and touches up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inal law evaluation and civil law evaluation.In this regard, there are two opposing methodological standpoint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one holding criminal law first and civil law incidental, another thinking the separation of the two.However, both standpoints are biased.Only by eliminating the bias on the standpoints can the validity of the contracts be put on the correct track.The money that has been collected is not illegal acquisition so that the criminal measures for recovering or restituting should not be applied to the cases of illegal collection of public deposits.The crime of illegal collection of public deposits is not a " malum in se", but a " malum prohibitum".The validity of contracts involved should be judged on the base of the regulations in the Law of Commercial Bank (LCB) .The Article 11 of the LCB is not intended to regulate the conduct of contract and approving the validity of related contract will not impede its progress.The Article 11 of the LCB is not a mandatory regulation in the sense of the Section 5 of the Article 52 of Contract Law, and the violation of it should not make the contracts void.
Keyword:
illegal collection of public deposit; criminal-civil crossed cases; validity of contracts; illegal acquisition; mandatory regulations;
一、问题的提出与本文的思路
根据《刑法》第176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依法批准或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 通过向社会公开宣传并承诺还本付息或给付回报, 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民事案件, 主要是民间借贷案件。近年来, 法院受理的这类案件明显增加。2003年至2013年, 全国法院年均一审审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案件762件;2014年1 907件;2015年达3 173件。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 2015年, 各级法院“新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536 681件, 同比上升41.48%”;2016年, “审结民间借贷案件142万件, 标的额8 207.5亿元。”1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中, 法院遭遇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情形, 呈增长的趋势。
依《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非法集资意见》) 的表述, 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人包括吸收人和帮助吸收人;出借资金的人是集资参与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2015》) ,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民间借贷案件, 主要涉及三类主体、两种合同, 即: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出借人与保证人之间的保证合同。此类案件, 一般以出借人为原告, 以借款人和/或保证人为被告。刑事程序中的犯罪嫌疑人, 可能是借款人, 也可能是保证人, 还可能既不是借款人也不是保证人, 而是以他人名义吸收资金并实际支配资金的人, 这类人在民事案件中通常被称为“案外人”。借款合同和/或保证合同的效力认定, 是民事审判经常面对的难题。此外, 犯罪嫌疑人或其家属与受害人 (即债权人) 签署的“代偿协议” (1) 2, 以房抵债为目的的房屋买卖合同 (2) 3, 吸收人以出借人身份向他人提供借款所签的借款合同等的效力问题, 也困扰着民事审判。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发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刑民交叉规定》”) 和《非法集资意见》均未就合同效力认定作出规定。《民间借贷司法解释2015》第13条规定“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 第14条列举了应认定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有人认为, 这些规定“具有重大意义”[1]。然而, 笔者并不这么认为。《民间借贷司法解释2015》的出台, 不仅没有减少分歧, 反而制造了新的分歧点。
(一) 立场分歧:合同效力认定的现行理论与实践
合同效力认定是一种依据特定价值标准进行的评价活动。若该评价活动限于民法体系之内, 所遭遇的价值标准之间的冲突, 就应该限于民法体系之内, 依民法方法论予以解决。然而,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民间借贷案件中的合同效力认定, 超出了民法的阈限, 触及到了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本质上, 这是一个方法论问题, 是一个协调不同价值标准之间的冲突与矛盾的问题。正是在这一根本问题上, 现行理论与实践存在着立场上的分歧。
一方认为, 民法评价必须服从刑法评价, 笔者称之为“刑主民附论”。该论有两种表达。其一, 刑法评价排除民法评价。《刑民交叉规定》第11、12条区分了“经济纠纷案件”与“有经济犯罪嫌疑”的案件。若属于后者, 即不属于前者, 若已作为经济纠纷案件受理, 法院应驳回起诉。《非法集资意见》使用“确属涉嫌犯罪”的表达, 《民间借贷司法解释2015》则区分了“本身涉嫌”与“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 也都体现了这种“非此即彼”的思路。虽然上述规定未明确驳回起诉的根据, 但多数法院认为, 案件若涉嫌刑事犯罪, 即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 (3) 4。其二, 犯罪即无效。依《非法集资意见》, 吸收资金属于“违法所得”, 应予追缴, 出借人所得利息或分红也应依法追缴。这种定性折射出借款合同无效这个前提。在一裁定书中,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所涉借款, 为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事实的一部分, 不能从整体犯罪行为中独立、分离出来。抵押担保系进行非法集资的手段。借款行为违反了《刑法》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定, 该规定是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因此, 案涉借款合同、抵押担保合同均无效 (1) 5。理论上, 也有学者主张以放贷为目的、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借贷合同应为无效, 因为, “虽然单个的借贷合同不构成犯罪, 但该行为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成立提供了土壤, 为损害社会整体利益创造了条件”, “破坏了国家对存款的监督管理制度”, “无法保证存款人的利益, 使公众财产处于受损的危险之中甚至最终导致公众财产受损”[2]。
另一方, 以吴国军诉陈晓富、王克祥及德清县中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案一审判决所表达的观点为代表, 强调两个“分离”。一是评价对象上的分离, 即构成犯罪的行为是“数个向不特定人借款行为的总和”, 而每一个“单独”的借款行为都不是“刑事法律事实”, 不是刑法评价的对象。二是评价根据上的分离, 即“对合同效力进行判断和认定属于民商事审判的范围, 判断和认定的标准也应当是民事法律规范。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合同的效力问题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问题” (2) 6。这种立场可称之为“刑民分离论”。不少法院据此判决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有效。最高人民法院曾援引《民间借贷司法解释2015》第8条“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 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规定, 认为:“合同一方当事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并不当然影响民间借贷合同以及相对应的担保合同的效力” (3) 7。理论上, 支持刑民分离论的, 略为多见[1][3-5]。
(二) 问题聚焦:合同效力认定面临的两大难题
对于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合同效力认定, 现行理论与实践对于合同效力认定的焦点所在仍未有清晰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 这是现有研究和实践难以达成共识的重要原因。通过梳理相关裁判文书和理论文献, 笔者认为, 下述两个难题是问题焦点所在, 也应是理论反思与实践用功的重心所在。
1. 如何走出追缴与责令退赔的适用引发的司法困境?
在我国, 一份有罪判决, 除就犯罪与刑罚作出裁判外, 还可能涉及经济损失赔偿、财产合法性认定、财产权利变动、财产返还责任等与民事权利处分、义务负担、责任承担紧密相关的事项上的判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案件中, 有些法院根据《刑法》第64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 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规定, 将追缴或责令退赔的内容写入判决主文。然而, 对于生效刑事判决中的“追缴与责令退赔”, 民事审判机构的态度却迥然不同。首先, 在刑事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且判决追缴或责令退赔的情形下, 有的法院认为:案渉借款已经由生效刑事判决认定构成犯罪, 故借款合同应认定无效, 保证合同亦无效 (4) 8;有的则以生效刑事判决已作出追赃处理为由, 认为应当驳回民事案件的起诉 (5) 9。然而, 即使原告已被刑事判决载明为退赔对象, 有的法院仍然认定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有效 (6) 10。其次, 若刑事判决仅认定借贷行为构成犯罪, 但未判决追缴或责令退赔, 多数法院不会驳回起诉, 而是继续审理并判决合同有效 (7) 11;但仍有法院根据《刑法》第6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若干问题的批复》和《民间借贷司法解释2015》第5条的规定, 认为:既然借贷行为本身涉嫌犯罪, 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集资犯罪行为占有、处置的财产”的, 应不予受理 (1) 12。最后, 虽然所受理民事案件中的借贷事实未被纳入判决认定的刑事犯罪事实, 有的法院仍然以两者“极为相似”为由, 裁定驳回起诉并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材料 (2) 13;有的则直接基于这种相似性, 认定合同无效 (3) 14。
对于生效刑事判决, 有的民事审判机构把它当成必须服从的权威, 有的则置之度外、不予理会。民事案件的原告, 到底能够获得怎样的救济, 不仅取决于刑事判决的主文内容, 还取决于民事审判机构对待刑事判决的态度。有研究指出, 将追缴或责令退赔作为刑事判决的内容, “会形成一种司法困境”, 即如果民事法官以“生效的刑事判决已经对民事实体问题作出处理”为由驳回起诉, “会侵犯公民的民事救济权”;但“如果民事法官大胆地避开这一判项”, 该条款“又不免落入‘稻草人条款’, 最终损害司法公信力”。司法者应“能动的探求法条背后的立法旨意与精神内涵, 寻求衔接之道。”[5]但是, 这一“衔接之道”, 到底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呢?该研究并未深究。如果不找到走出此种困境的道路, 刑事判决主文内容的不确定性, 民事审判机构态度上的不确定性, 将使得在合同效力问题上寻求确定的答案, 几乎变得不可能。
2.《刑法》第176条是《合同法》第52条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定”吗?
否定合同的效力, 必须基于法律明确规定的根据。民法体系外的规定, 也可能成为否定合同效力的根据, 但须经由《合同法》第52条第 (五) 项———这根“让管制法规的政策考虑‘流入’私法关系的管道”[6]。该规定属于“为了在私法领域实现公法管制的效力”的引致规范[7]。
刑主民附论, 将“犯罪”与“无效”划等号, 意图从放贷目的的恶意性质、客观上对社会整体利益与存款人利益的损害后果, 来论证借贷行为对国家金融管理制度的破坏, 从而将《刑法》第176条涵摄至《合同法》第52条第 (五) 项之下。但是, 语义上,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既未要求主观上有恶意, 也未要求客观上有损害后果。其中的“强制”是“效力性强制”, “违反”是“目的性违反”, 两者结合即:合同有效会阻碍强制性规定的目的之实现, 只有否定合同效力才能消除此种阻碍。所以, 仅论证借贷行为对金融管理制度的破坏性, 而未论证否定合同效力是防止或消除此破坏性所必然要求的, 就不能认为达到了论证的目的。
刑民分离论通过区分“单个的借款行为”与“借贷行为的总和”, 运用量变质变原理, 认为犯罪行为与合同行为不重合, 或者说两个行为不是“同一事实”, 所以, 其中的民事行为 (不是犯罪行为的那个民事行为) 应该有效。事实上, 这种推理与“不犯罪即有效”几无二致。既然如此, “犯罪即无效”又错在哪里呢?为解决这个问题, 刑民分离论也援引《合同法》第52条第 (五) 项, 但目的在于打断《刑法》第176条与《合同法》第52条之间的联系。该论阐述了两个观点。第一, 当事人在订立借贷合同时, 主观上具有借贷的真实意思表示, 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然而, 意思表示真实性只是影响合同效力的因素之一, 真实的意思表示不一定就是有效的意思表示。此处着重强调“借贷的真实意思”, 其实是强调当事人没有“犯罪的意思”。第二, 民间借贷合同的当事人“既没有主观上要去损害其他合法利益的故意和过错, 客观上也没有对其他合法利益造成侵害的现实性和可能性”[3]。综合这两点, 该分析的真实意图是为了建立这样一个链条:单个借款行为主观上没有损害的故意, 客观上也没有损害的现实与可能, 单个借款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 单个借款行为没有触犯《刑法》, 不是犯罪行为, 因此, 单个借款行为没有违反强制性规定。这仍然没有逃出“不犯罪即有效”的思维定式。
刑主民附论与刑民分离论, 均未就《刑法》第176条与《合同法》第52条第 (五) 项的关系给出一个清晰、合理的说明与论证。两者纠结于相同的难题, 即:《刑法》第176条属于《合同法》第52条第 (五) 项的强制性规定吗?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合同效力问题而言, 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吗?如果是, 如何回答才能提供一个满意的答案?如果不是, 我们面对并必须解决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三) 合同效力评价的立场转变与本文思路
无论主张刑法评价排除民法评价、犯罪即无效的刑主民附论, 还是将两者刻意分离、割裂的刑民分离论, 对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的关系的认识都存在根本性错误。前者过于强调刑法打击犯罪的立场, 忽视甚至抹杀了约定必须信守、信赖利益保护在民法体系中的价值。后者则过于迷恋私法自治的立场, 没有看到打击犯罪对于保护财产安全、维护交易秩序所具有的意义。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民间借贷案件是典型的刑民交叉案件。刑民交叉案件的根本特征, 是这种案件在处理上存在着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发生冲突、矛盾的可能性。刑主民附论与刑民分离论, 不仅忽视了这种可能性, 而且对实际发生的冲突与矛盾也视而不见。笔者认为, 只有正视这种可能性, 并保持评价立场上的整体性与开放性, 让评价者眼光在刑法与民法之间进行体系间往返流转, 努力寻找、反复比较协调冲突与消除矛盾的各种方案, 才能避免刑主民附论与刑民分离论未予正视、未能克服的体系间评价矛盾。这种评价立场的转变, 并非价值标准本身的变化, 而是方法论立场上的变化。
追缴与责令退赔的适用引发的司法困境, 源自这种适用可能导致的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在裁判内容上的矛盾。裁判内容上的矛盾包括两种, 其一, 在判断某一事实是否符合构成要件上的矛盾, 比如, 刑事裁判中认为A行为构成诈骗罪, 而民事裁判认为A行为不构成欺诈。其二, 在实体权利、义务、责任的性质和内容裁判上的矛盾。比如, 如果刑事裁判认为甲基于A合同占有的财产是违法所得, 甲必须返还;而民事裁判则认为A合同有效, 甲必须继续履行合同, 即发生了矛盾。因为, 刑事裁判确定为违法所得, 实际上就宣布A合同是违法的、无效的, 不能成为甲合法占有其财产的根据, 民事裁判宣称A合同有效、甲应继续履行, 就与刑事裁判在甲之占有的法律性质、甲之民事责任的性质上发生了矛盾。若不消除这种“隐藏”的矛盾, 合同效力认定将无法建立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之上。正视“前见干扰”的可能性并设法予以消除, 才能走出困境。这是本文第二部分论证的目的。
刑主民附论企图通过“压制”的方式确保评价结论上的一致性, 完全没有看到这种方式对民法价值体系带来的“冲击”。过于简单地在“犯罪”与“无效”之间划等号, 未对评价对象进行更细致的区分, 导致合同效力认定变得极为不确定、不稳定, 交易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按照该论的逻辑, 在操纵证券交易罪的情形下, 以操纵者为一方成立的所有证券买卖合同都应该是无效的;在内幕交易罪的情形下, 内幕交易人所签订的所有证券买卖合同也应该是无效的。如此, 证券市场将陷入极为混乱的状态, 证券市场的功能将不能正常发挥。刑主民附论错误地绝对化刑法评价, 而刑民分离论则错误地将私法自治的价值绝对化了。刑民分离论强调合同效力问题是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截然不同的问题, 是民事规范、民事审判的范畴。此种表达, 容易让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合同效力认定与刑事规范、刑事审判无关。但这显然不仅在理论上不成立, 也与现实不符。我们无法想象, 如果将毒品交易中的犯罪行为与合同行为做这种区分处理, 会发生怎样的后果。哲学上, 事物的无限可分性, 与普遍联系性一样, 都是可接受的认识论立场。但是, 如果法律上的认识也无条件恪守这样的立场, 那么, 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规则, 法律上的拟制规则、类推方法, 都将失去存在的根基。法律上的区分, 并非仅仅基于对象自身的特征, 而必然要考虑区分的目的。而且, “目的”才是决定性的。“对象”的特征, 也是因为“目的”所需被拉进法律的思维。因此, 规整对象事实上的可区分性, 只是法律上应为区别对待的一个契机, 只有通过价值判断层面的充分检验, 才能为法律上的区别对待提供最终且最根本的理由。出于保护私法自治与交易安全的需要, 完全忽视刑法在规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上的价值考量, 刑民分离论只是基于单一价值追求的单向推演, 而非相冲突利益与价值之间的比较与权衡。刑民分离论的理论根基十分脆弱。只有理清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在合同效力认定问题上可能发生的冲突与矛盾, 经由客观、全面的利益衡量与价值考量, 以解决“强制性规定”的引致适用难题, 才是消除分歧、达成共识的根本出路。这是本文第三部分的思路。
二、追缴与责令退赔的限缩适用:基于两种救济模式的比较
在刑事判决中写明追缴与责令退赔, 既是刑民体系间在裁判内容上发生矛盾的触发点, 也是体系间价值冲突的导火索。“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 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规定, 既可作为采取刑事措施的根据, 也可作为变动民事法律关系的根据。违法所得的认定, 一方面, 宣告了对一切财物事实上的支配状态的非法性;另一方面, 产生了一种追及一切财物的效力, 直到遭遇善意第三人保护的价值屏障。按照民法原理, 取得财产的民事法律事实主要是事实行为和民事法律行为。违法所得的认定, 实际上宣布了作为财产取得原因的事实行为的违法性与民事法律行为的无效性。因此, “基于违法所得认定的追缴与责令退赔”与“基于合同有效的民事救济”实际上是两种非此即彼的救济模式。前者体现“刑民一体”的思路, 打击犯罪的同时实现民事救济;后者属于“刑民分治”, 刑罚措施实现打击犯罪的目的, 民事救济实现受害人保护的目的。有研究认为, “公安、检察机关通过刑事程序救济受害人显然远不及民事诉讼更周延、更全面和更长远”[1]。笔者赞同这一研究结论, 但并不认为这个结论是如此“显然”, 也不认为两种模式的差距达到了“远不及”的程度。这个比较与权衡的过程, 涉及众多因素的复杂考量, 两者的利弊优劣, 并非那么容易作出判断的。
(一) 刑民一体模式与刑民分治模式的适用效果比较
笔者从打击与预防犯罪、受害人个体救济、受害人整体救济三个角度出发, 对刑民一体论与刑民分治论所代表的两种救济模式的适用效果进行比较。
从打击与预防犯罪的角度来看, 对于吸收人施加刑罚惩罚的同时, 强制剥夺对吸收资金的占有和使用, 可产生对其预期的干扰与破坏, 有助于打击和预防犯罪。但若不追缴吸收资金, 惩罚限于刑罚以及对行为人所获非法利益的剥夺, 可能会导致鼓励吸收资金自用。对于出借人而言, 强制剥夺出借人对利息的请求权, 有助于消除高息引诱, 减少犯罪发生几率或抑制其发生的规模。
从受害人个体救济的角度来看, 通过刑事追缴与责令退赔, 个别受害人可能会获得本金的返还, 返还的额度与难度取决于吸收人的经济状况与追缴力度。但无论如何, 受害人利息请求权被剥夺了。通过刑事追缴与责令退赔, 受害人并没有获得最低恢复水平的保障。如果不追缴或责令退赔, 受害人可以通过请求吸收人、担保人个别履行的方式来实现基于合同产生的债权, 包括本金返还请求权和利息给付请求权。权利实现的程度也取决于吸收人的经济状况, 而且受害人也没有最低恢复水平的保障。对于有担保的债权人而言, 如果适用追缴与责令退赔, 债权人向保证人的索赔能否成功, 极不确定。一方面, 保证人可以援引主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时的三分之一责任抗辩;另一方面, 债权人可以援引《民间借贷司法解释2015》第8条的规定, 认为合同有效。若不适用追缴与责令退赔, 债权实现的可能性更大, 且更为确定。
从受害人整体救济的角度来看, 在公平价值的维度上, 作为一种概括性程序, 追缴、退赔能够从整体上顾及受害人之间的救济公平 (1) 15。根据《非法集资意见》的规定, 涉案财物不足全部返还的, 按照集资参与人的集资额比例返还。如果仅仅通过民事程序来进行救济, 只有在执行阶段且被执行人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债权的, 可以适用《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的参与分配制度, 否则, 个别诉讼模式仍以最大化胜诉方利益为目的。受害人的信息能力、诉讼意识等, 均影响着获得救济的水平。在效率价值的维度上, 通过同一套程序, 查明涉及大量受害人的案件事实, 追缴吸收资金, 并通过同一套程序实现向大量受害人的财产返还, 司法资源利用的效率比较高。若刑民分治, 一个受害人一个民事诉讼, 即使刑事程序已经查明的事实, 在民事程序中可能会再次经历举证质证的过程, 司法资源浪费的情形似乎难以避免。
综上, 《刑法》第64条所规定的追缴与责令退赔, 事实上具有“代替”民事救济的功能, 而且, 并非毫无道理可言。但是, 到底是什么使得“先刑后民”的良好初衷走向事实上的“以刑代民”、“刑存民废”?在打击犯罪与受害人救济之间, 在受害人整体救济的公平性与受害人个体救济的充分性、确定性之间, 在司法效率与个案正义之间, 我们到底该何去何从?
(二) 价值衡量方法的应用:刑民一体模式的价值幻象
面对价值冲突的困境, 我们必须分析价值冲突的角度与程度, 认真权衡选择一方到底会对另一方造成怎样的减损, 如此方能找到走出困境的合理路径。
首先, “刑民一体”模式在打击犯罪上的有效性, 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情形下, 似乎并非想当然的那样。就程序控制而言, 即使需要对吸收资金或相应账户、或其他财物进行控制以保障侦查取证, 查封、扣押、冻结的侦查措施即足已。将吸收资金认定为违法所得并予以追缴, 显得有点多余。而就惩罚与预防犯罪的目的而言, 追缴、责令退赔的刑事措施的配置, 不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在吸收人涉嫌犯罪之后, 金融市场准入秩序已经遭到了破坏, 此时, 刑法介入的目的应是惩罚与一般预防, 但是, 追缴、责令退赔实际上并不具有惩罚和一般预防的目的。因为, 于吸收人而言, 即使不追缴、不责令退赔, 吸收人必须按照合同的约定返本付息, 否则的话会面临更重的集资诈骗罪指控。如果适用追缴、责令退赔, 吸收人也只是返本, 无须支付利息, 已付利息还可以抵扣本金返还。构成犯罪之后的经济处境, 会比不构成犯罪时更好, 这样的结果, 难谓惩罚, 也难以起到预防的作用。
其次,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涉众性, 确实要求必须从整体上考虑受害人救济的公平性。然而,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受害人, 人数众多且难以确定。侦查机关并不一定能够查清楚所有的受害人。一般而言, 如果达到下限要求, 侦查机关会倾向于尽快结案。因此, 查明的受害人很难完全包括所有的实际受害人。如此, 相似甚至相同情形下的受害人获得不同的救济, 显然难以避免。受害人整体救济的公平性, 只是一个幻影。如果考虑到《刑法》第64条在适用上的不确定, 这种公平追求甚至可能走向它的反面。因为, 《刑法》第64条的适用对民事诉讼产生了“阻挡”效应。“由于已经在刑事判决中判决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任何时候, 只要发现被告人有财产, 司法机关均可依法追缴或者强制执行。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 否则就会造成刑事判决和民事判决的重复、冲突。即使以前的刑事判决中没有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内容, 也应当继续通过刑事诉讼途径予以弥补和解决, 不宜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8]这意味着, 在刑事责任主体与民事责任主体不一致的情形下, 受害人向刑事被告之外的人寻求民事救济的权利被剥夺了。为追求如此虚幻的公平, 还得赔上实实在在的个体权利的牺牲。这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最后, 实现司法资源的最有效利用, 也不是非得牺牲个案正义, 两者并非顾此失彼的关系。为防止事实认定上的矛盾, 在刑事程序与民事程序的衔接问题上, 先刑后民是一个应予尊重的原则, 如此, 民事诉讼的启动一般会在刑事程序终结之后。如果以有罪判决终结, 民事诉讼必须以有罪判决认定的事实为依据, 刑事程序中为查明事实而投入的资源在民事诉讼中仍然可以产生“效益”。刑事程序中的查封、冻结、扣押, 也可以通过程序的衔接顺利转化为民事诉讼中的保全措施, 这种司法资源的投入也不会被浪费。
(三) 消除干扰:吸收资金不应被认定为违法所得
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 对于受害人救济而言, 继续贯彻“刑民一体”, 还是转道“刑民分治”?上述相冲突利益与价值间的比较与权衡, 已经给出了答案。在追缴与责令退赔是否适用于吸收资金的返还的问题上, 笔者并不赞同应由司法者“能动”地寻求解决的方案。某种程度上, 正是司法者在打击犯罪、受害人个体救济、受害人整体救济之间摇摆不定的“裁量”, 加剧了合同效力认定、救济选择上的不确定性, 事实上使得司法不公的印象愈加深刻。
笔者认为, 解决的要点是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 吸收资金不是违法所得, 不应适用追缴与责令退赔。“所得”二字具有“动态”的含义, “得”, 即意味着“财产状态的变化”。因此, 认定违法所得, 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因犯罪的实施或完成而发生, 二是财产利益上的增加。吸收人虽然事实上占有吸收资金, 这种占有状态也确实因构成犯罪的吸收行为所致, 但是, 与这种占有事实同时发生的, 还有吸收人的返还义务。无论吸收人是否被刑事追究, 吸收人在任何时候都承认这种义务的存在, 并且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确保该义务的履行, 这与集资诈骗罪根本不同。对吸收资金的占有, 并不导致吸收人财产利益上的增加或财产负担上的减少。因此, 将“吸收的资金”界定为《刑法》第64条规定的“违法所得”的《非法集资意见》第5条, 应予修改。法院也不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39条的规定, 将吸收人仍然占有吸收资金的状态, 界定为“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情形。如此, 才能消除刑事判决内容上的不确定性给合同效力认定造成的干扰, 同时, 更为重要的是, 才能避免刑民之间在实体评价上陷入无法消解的矛盾。
此外, 《非法集资意见》对于“将非法吸收的资金及其转换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的情形, 在该他人明知, 或者无偿取得, 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 或者是源于非法债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而取得非法吸收的资金及财物的, 也应当依法追缴。这一规定既增加了认定的难度, 也没有实际的意义。若吸收资金不是违法所得, 这一规定也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基础。同时, 这一规定的消失, 也为前文提及的代偿协议、以房抵债为目的的房屋买卖合同、吸收人作为出借人与他人签订的借款合同等的效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契机。在这些情形下, 民事审判机构基于这些协议或合同行为与犯罪行为的关联性, 特别是在所涉款项上的同一性, 都否定了这些协议和合同的效力。但是, 在吸收人以出借人身份向他人借款而签订的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上, 即使吸收人 (即出借人) 已经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刑事立案, 有法院仍坚持认为:无论“该笔债权源自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还是从事正常的公司经营活动, 某公司 (即吸收人, 笔者注) 起诉王某等三被告行使债权追索权, 人民法院对本案某公司主张的债权进行审理、裁判和执行, 不单是保护某公司的利益, 还能够增强某公司的偿债能力, 有利于对非法集资案件受害人利益的平等保护。”16这一判决, 不仅直接违反了“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的资金属于违法所得”的规定, 而且明显与前述法院在代偿协议、以房抵债协议效力认定上的立场互相矛盾。这种矛盾, 也只有通过否定吸收资金的违法所得定性, 才能予以消除。
三、回归行政犯本质:走出强制性规定的解释论迷思
吸收资金不是《刑法》第64条意义上的“违法所得”, 不是追缴、责令退赔的对象, 这意味着在刑事程序中对合同效力进行裁判的可能性也同时被排除了。合同效力的判断, 发生了程序背景和实体依据上的转换。没有了刑事程序的“前见干扰”, 民事审判机构将在民法的体系内认定合同效力, 虽然, 它仍然不能被认为是一个纯粹的民法问题。更重要的是, 即使刑民分治的救济模式更值得采纳, 也不意味着合同效力评价上的刑民分离论是当然成立的。
(一)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政犯本质及其意义
刑法上, 犯罪行为可以被区分为刑事犯与行政犯。笔者赞同依据立法目的上法益机能的不同来进行此种区分。社会生活秩序分为基本的生活秩序与派生的生活秩序。基本性生活秩序是规制市民社会基本生活构造的秩序, 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破坏这一秩序会使国家和社会处于巨大危险之中。因此, 违反基本生活秩序的犯罪称为刑事犯。派生的生活秩序是基于财政、经济等特定的行政上或政策上的考量, 从外围来确保社会生活秩序, 具有流动性的特点。违反派生生活秩序的犯罪称为行政犯[9]。
《刑法》第176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经济行为构成犯罪, 必须首先是经济行政法规的违法性评价, 然后才是一个刑法的评价。”刑法评价是“二次评价”[10]。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进行第一次违法性评价的, 是《商业银行法》第11条第二款17, 核心要件是“未经批准”。因此,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本质是违反了吸收公众存款业务的市场准入限制。根据《商业银行法》所确立的金融管理秩序, 只有经批准的机构, 主要是商业银行, 才能经营吸收公众存款业务;不是商业银行, 却像商业银行一样去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的业务, 这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违法本质, 属于典型的行政违法行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是刑事犯, 而是行政犯。
根本上言, 行政法的规定, 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违法性判断的规范根据。刑法的规定, 可以为限缩适用范围而增加情节性要件, 但不能改变反映行政规制目的的基本要件。刑事责任设置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行政目的的实现, 即实现“法律上作特别规定”本身所追求的价值。针对该行为的刑法评价本身, 并无“额外”的价值追求, 它只是实现行政法评价的手段而已。因此, 在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合同效力问题上, 能够通过《合同法》第52条第 (五) 项这根“管道”导入民法体系之内而成为合同效力裁判根据的, 并非《刑法》第176条, 而是《商业银行法》第11条第二款。合同效力认定面临的评价矛盾可能性, 只是发生在民法评价与行政法评价之间, 而非民法评价与刑法评价之间。
(二) 两阶段考察法:《合同法》第52条第 (五) 项适用的方法论
依上所述, 《刑法》第176条只是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根据, 并不能据此确定法律规制的目的所在及其背后的价值选择。所以, 合同效力问题的焦点并非《刑法》第176条的规定是否属于《合同法》第52条第 (五) 项的强制性规定这一问题, 而是《商业银行法》第11条第二款是否属于《合同法》第52条第 (五) 项的强制性规定的问题。
《合同法》第52条第 (五) 项中的强制性规定, 仅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违反此种规定的合同即无效。判断一具体规定是否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是《合同法》第52条第 (五) 项适用的核心。方法论上来说, 这个判断是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充分衡量相冲突利益的动态过程。在此, “规范目的分析方法永远都是必要的, 而法律用词、强制性特征和当事人的范围都仅仅起一种表面证据作用”[11]。《民法总则》第153条中“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的规定, 强调了强制性规定之规范目的分析的必要性。苏永钦整理出应纳入考量的八个因素, 即管制的领域、重心、性质、工具、法益、取向、强度、成本效益[6]。基于综合判断的属性和规范目的分析的必要性, 借鉴上述考量因素的划分, 笔者认为,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判断包含两个考察阶段。第一阶段考察是依据规范的表面特征进行的初步考察。该考察包括对法律用语、当事人范围 (即是对一方的强制, 还是对双方的强制) 进行的考察, 还包括对上述八个因素中前四个因素的考察, 即管制领域上是准入管制还是行为管制;管制重心上考察管制内容与合同内容的相关程度;管制性质上是程序性管制还是实体性管制;管制工具上考察管制规范的效力位阶及规范形成的民主政治过程。第二阶段的考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管制强度考察, 按照苏永钦的说法, 是“从立法理由、立法的密度等环境因素综合判断立法者管制的政策强度”。笔者认为, 为保障管制规范实施而设置的配套措施、执法机制等也应属于此种“环境因素”。该考察的目的在于判断该管制规范是否具有影响合同效力的“意图”。二是法益平衡考察, 既包括管制规范所保护的利益与合同自由或私法自治利益的比较与权衡[11], 也包括管制的成本与效益的考察, 目的在于判断:为保护或实现管制规范利益, 是否必须否定违反管制的合同的效力。
通过第一阶段的考察, 并不能得出某规定属于或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结论, 而只是在效力性与非效力性之间定一个倾向, 即属于效力性的可能性是比较大, 还是比较小。在第二阶段考察得出了某种压倒性结论的时候, 即使该结论与第一阶段考察得出的倾向性判断相反, 也应按照第二阶段考察的结论来做最后的认定。但是, 若第二阶段考察出现了“势均力敌”的局面, 第一阶段考察所得出的倾向性判断就可能决定着最后的结论;若一方仅仅表现出微弱的优势, 倾向性判断应再次纳入综合的比较与权衡。无论如何,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判断, 确实需要法官进行自由裁量。考量因素的广泛性、利益权衡的周全性, 都影响着裁量结论的合理性与可靠性, 理论研究的目的也就是在这些方面为法官的裁量贡献可供参考的知识与方法。
(三) 《商业银行法》第11条第二款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首先, 《商业银行法》第11条第二款中的“未经批准”, 反映出了该条管制的基本特征, 即该条管制属于准入型管制。银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金融中介, 能够为其客户 (投资者) 带来投资多样化、规模化、专业化的利益。银行业务具有明显的杠杆效应, 银行又是一国信用创造与支付结算的中心。“银行业是世界上受管制最为严格的行业”, 最主要的理由就是“银行失败会产生显著的外部成本”[12]。银行监管的最终目的就是防止银行失败造成大规模的社会恐慌。市场准入管制是银行业管制的重要内容, 主要目的并非控制市场结构, 而是为持续的审慎监管提供条件。若无市场准入的审批程序, 监管部门根本无法对银行经营进行持续监管, 也无法适用存款人保护机制。将“未经批准吸收公众存款”作为违法行为对待, 并规定行政责任、刑事责任, 目的就在于通过构建准入秩序来保证持续监管的效果, 防止不受监管的金融活动引发大规模金融风险。这种准入管制, 不仅本身属于程序性管制, 而且最终目的乃在于为另一监管程序的有效实施提供前提性保障。因此, 《商业银行法》第11条第二款的管制是典型的准入型、程序性管制, 一般不应对合同效力产生否定性影响[13]。
其次, 为实施该准入监管而设置的执法机制表明, 《商业银行法》第11条第二款事实上并没有影响合同效力的意图。在《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违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相关责任的同时, 《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进一步明确了执法的主体与程序, 强调“一经发现, 应当立即调查、核实;经初步认定后, 应当及时提请公安机关依法立案侦查”, “调查认定后, 作出取缔决定, 宣布该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活动为非法, 责令停止一切业务活动, 并予公告”, 还明确了取缔之后“债权债务的清理清退”程序。这些规定到底有无直接影响合同效力的目的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理由有二。其一, 取缔决定、宣布违法、责令停止一切业务活动是一体性的措施, 也就是《商业银行法》第81条所规定的取缔措施的细化。在行政法上, “取缔的目的在于取消或禁止非法活动等”, “违法相对人需承担不作为的法律义务。该不作为义务本来就是法律要求相对人承担的, 相对人并未取得法律上的实体权利, 剥夺或限制权利的情况并不存在, 即未对其法律权利构成处分, 因而取缔并不具有制裁性”[14]。所以, 取缔是一种向后的禁止, 并不产生剥夺已存在的权利或增加新的义务的法律效果。其二, 取缔之后, 虽然有债权债务清理清退的程序, 但是, 这种程序显然不是必须启动的, 本身不具有强制性18。即使政府组织的清理清退程序, 该程序也被认为不改变“与集资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 不增加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是政府“根据有关规定处置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工作中对非法行为所涉及的民事纠纷进行调处的行为, 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19。
最后, 从法益权衡的角度来看, 借款合同有效的认定并不会对管制目的的实现造成实质性阻碍, 反倒是合同无效的认定, 会引发较为严重的交易安全担忧。比例原则, 作为行政法的帝王条款, 着眼于法益的均衡, 既确保行政目的之实现, 又防止对公民权利造成不合理限制。对于监管目的来说, 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配置, 已经对违法行为人提供了足够的威慑与制裁, 认定合同无效并不能增加威慑与制裁的分量。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属于派生性生活秩序, 为保护此种秩序而作出的规定, 负责从外围保护国家的社会生活秩序, 以实现行政目的为必要, 不得随意干涉作为核心部分的基本性生活秩序。公民之间财产关系的变动属于基本性生活秩序, 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 不得随意改变,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在这一点上, 前文关于“刑民一体”模式与“刑民分治”模式在价值上的比较与权衡及其所得出的结论, 也同样适用于行政法评价与民法评价的关系之理解。
四、总结与展望:债权人救济程序的初步构想
只有将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合同效力评价, 建立在确保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之间无矛盾的方法论立场之上, 建立在刑法与民法各自所保护的价值都得到全面权衡、周全关照的基础之上, 才能消除现有理论观点与实践态度上的偏颇, 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限缩“违法所得”的含义之后, 吸收资金不是违法所得, 不能进行追缴或责令退赔, 如此, 才能消除刑事程序对合同效力评价造成的干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是行政犯, 《商业银行法》第11条第二款才是合同违法性分析的重心。《商业银行法》第11条第二款并非《合同法》第52条第 (五) 项中的强制性规定, 即使违反, 也不会导致合同无效。这种论证方案虽然在结论上与刑民分离论一致, 但是, 本文的论证以防止发生体系间的评价矛盾为目的, 以充分的价值考量为依据, 同时, 并未割裂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 不会导致两者的分裂与陌生化, 保证了法律体系整体价值追求上的一致性。
本文仅论述了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情形, 对于与该罪同处破坏市场准入型金融管理秩序的其他三种犯罪, 即擅自设立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以转贷牟利为目的, 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擅自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 本文结论不一定能够直接适用, 但可以为利益衡量与价值比较的展开提供一套思路、一个框架, 以防出现体系间的评价矛盾。
本文所论合同效力问题, 是实体性问题。因涉嫌犯罪, 合同效力认定问题与刑事程序的进展及其结论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对于刑事程序与民事程序之间的关系, 笔者认为, 先刑后民应是基本的原则, 理由也是因为这一原则能够有效避免刑民体系间评价矛盾。据此, 受理民间借贷案件的法院, 在发现案件事实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时, 应中止审理, 等待刑事程序的结束。刑事案件终结后, 若为有罪判决, 且吸收资金未被认定为违法所得, 亦未判决追缴或责令退赔, 法院将在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的基础上, 在刑事程序已经实现对借款人 (吸收人) 财产采取了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基础上, 开启民事案件的审理。合同效力认定问题将在民事诉讼中得到解决, 卷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案件本身并不导致合同无效, 若无其他效力瑕疵, 出借人所依据的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等应认定为有效。若发生针对同一个债务人的多个债权人的请求无法得到全部满足的情形, 债权人或债务人可以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启动破产程序。如果债权人、债务人或负有清算责任的人均未启动破产程序, 法院可以在执行程序中适用参与分配制度, 或者适用执行转破产的相关规定启动破产程序。
不少人担心, 民事案件的审判如果要等待刑事程序终结才能开启或重启, 刑事程序的冗长、拖沓, 会影响民事救济的有效性。对此, 笔者认为, 刑民交叉案件在程序衔接上适用“先刑后民”的一般原则, 本身就是对民事救济的限制, 也当然包括了刑事程序冗长、拖沓可能引发的担忧, 这可能是卷入非法集资案件的债权人不得不承受的一种“风险”。当然, 如果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行政犯本质坚持到底, 更好的解决办法是先启动行政执法程序, 政府及监管部门始终参与案件的调查与处理, 在必要的情形下, 如被告尚未缉捕归案, 或者明显资金不足, 可以由政府负责取缔并实施接管来应对大规模受害人救济的难题。同时, 因为接管程序与受害人利益息息相关, 受害人配合行政执法与政府接管的积极性可能会更高, 如此, 行政取缔与接管程序的构建能够有效打通刑事与民事程序, 在协助刑事调查的同时, 解决以刑事被告为中心的民事法律关系, 同时, 还可以实施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 从而既不扰乱民事法律关系秩序, 又可以保证对犯罪的打击力度。当然, 行政取缔与接管机制应如何设计, 应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1]王林清, 刘高.民刑交叉中合同效力的认定及诉讼程序的构建---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为视角[J].法学家, 2015 (2) .
[2]龚振军, 方红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借贷合同的效力探究[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4 (3) .
[3]沈芳君.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民间借贷及其担保合同效力[J].人民司法, 2010 (22) .
[4]崔永峰, 李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中民间借贷合同效力之认定[J].中国检察官, 2012 (1) .
[5]张静.民间融资活动中刑民交叉案件审理的困惑与出路---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例[M]//贺荣.全国法院第25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公正司法与行政法实施问题研究:上册.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4.
[6]苏永钦.《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适用和误用:再从民法典的角度论转介条款[EB/OL].[2017-06-30].http://www.privatelaw.com.cn/Web_P/N_Show/?PID=7114.
[7]谢鸿飞.论法律行为生效的“适法规范”---公法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及其限度[J].中国社会科学, 2007 (6) .
[8]黄应生.《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的解读[J].人民司法, 2014 (5) .
[9]黄明儒.也论行政犯的性质及其对行政刑法定位的影响[J].现代法学, 2004 (5) .
[10]游伟.刑民关系与我国的刑事法实践[M]//华东刑事司法评论.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11]耿林.强制规范与合同效力---以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为中心[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9.
[12]Richard Scott Carnell, Jonathan R.Macey, Geoffrrey P.Miller.The Law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ifth Edition) [M].Wolters Kluwer Law&Business, 2013.
[13]许中缘.论违反公法规定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再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5项[J].法商研究, 2011 (1) .
[14]郭庆珠.当代中国行政取缔的法律治理[J].现代法学, 2015 (6) .
注释
1 上述数据分别来自:《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法律政策宣传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非法集资新发案大幅攀升》, 《法制日报》2016年4月28日;《2015年全国法院审判执行情况》, 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18362.html, 2016-08-08;周强:《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7年3月12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7年第4期。
2 张某甲系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犯罪嫌疑人, 被依法刑事拘留。张某甲之父张某乙与一出借人胡某签订《还款协议书》。后胡某基于该协议起诉张某乙。法院认为, 本案债务关系根源于胡某出借给张某甲的款项, 张某甲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胡某也以刑事受害人的名义登记了债权。张某乙是代为其子张某甲偿还债务, “其行为属于债的加入, 并未形成新的借款事实”, 本案不符合《民间借贷司法解释2015》第6条规定的“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情形, 因此, 裁定驳回胡某的起诉。参见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娄中立终字第196号民事裁定书。
3 原告起诉被告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 办理手续。原告与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目的是以房屋抵偿借款, 而该借款所涉款项, 就是被告作为刑事被告人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涉及的款项。原告主张借给被告的款项已转变为购房款, 因此, 本案的房屋买卖合同应当有效, 并应继续履行。但法院认为:“双方间的基础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关系, 而民间借贷所涉款项本身正由刑事案件审查处理。据此, 本案应先通过刑事诉讼程序解决。”参见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7) 黑民终23号民事裁定书。
4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7) 最高法民申233号民事裁定书、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6) 皖民终3号民事裁定书、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6) 甘民初2号民事裁定书、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 陕01民终4106号民事裁定书、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 豫01民终5199号民事裁定书。
5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5) 民申字第2 160号民事裁定书。
6 吴国军诉陈晓富、王克祥及德清县中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担保合同纠纷案判决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11期, 第45-48页。
7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7) 最高法民再2号民事裁定书。
8 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 浙01民终725号民事判决书。
9 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6) 浙民申444号民事裁定书、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 皖02民终1082号民事裁定书、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 辽 (1) 民终464号民事裁定书。
10 参见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浙金商终字第1760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 苏06民终265号民事判决书。
11 参见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 鲁02民终636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 浙07民终1522号民事裁定书、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浙金商终字第2226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 浙01民终2072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 浙08民终144号民事判决书。
12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穗中法立民终字第1844号、第1854号民事裁定书。
13 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6) 浙民申56号民事裁定书。
14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7) 京民申833号民事裁定书。
15 这种公平取向的价值追求, 并非笔者的假设或猜测, 事实上已经纳入我国法院进行价值判断时的考量范围。最高人民法院 (2015) 民申字第2 160号民事裁定书明确指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涉众型犯罪, 涉及所有受害人的公平退赔问题”。
16 最高人民法院 (2016) 最高法民终784号民事裁定书。
17 《商业银行法》第11条第二款:“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 任何单位不得在名称中使用‘银行’字样。”
18 《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16条规定:“因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形成的债权债务, 由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机构负责清理清退。”第21条规定:“因清理清退发生纠纷的, 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通过司法程序解决。”这意味着, 清理清退不是一个行政执法程序。
19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5) 行监字第1278号行政裁定书。





